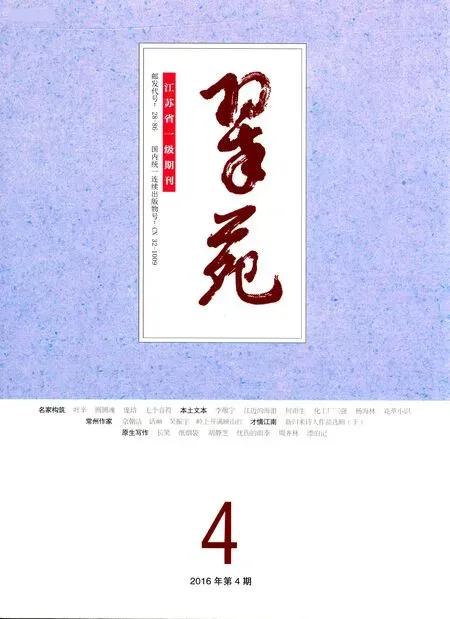在水一方(三章)
■左弦
在水一方(三章)
■左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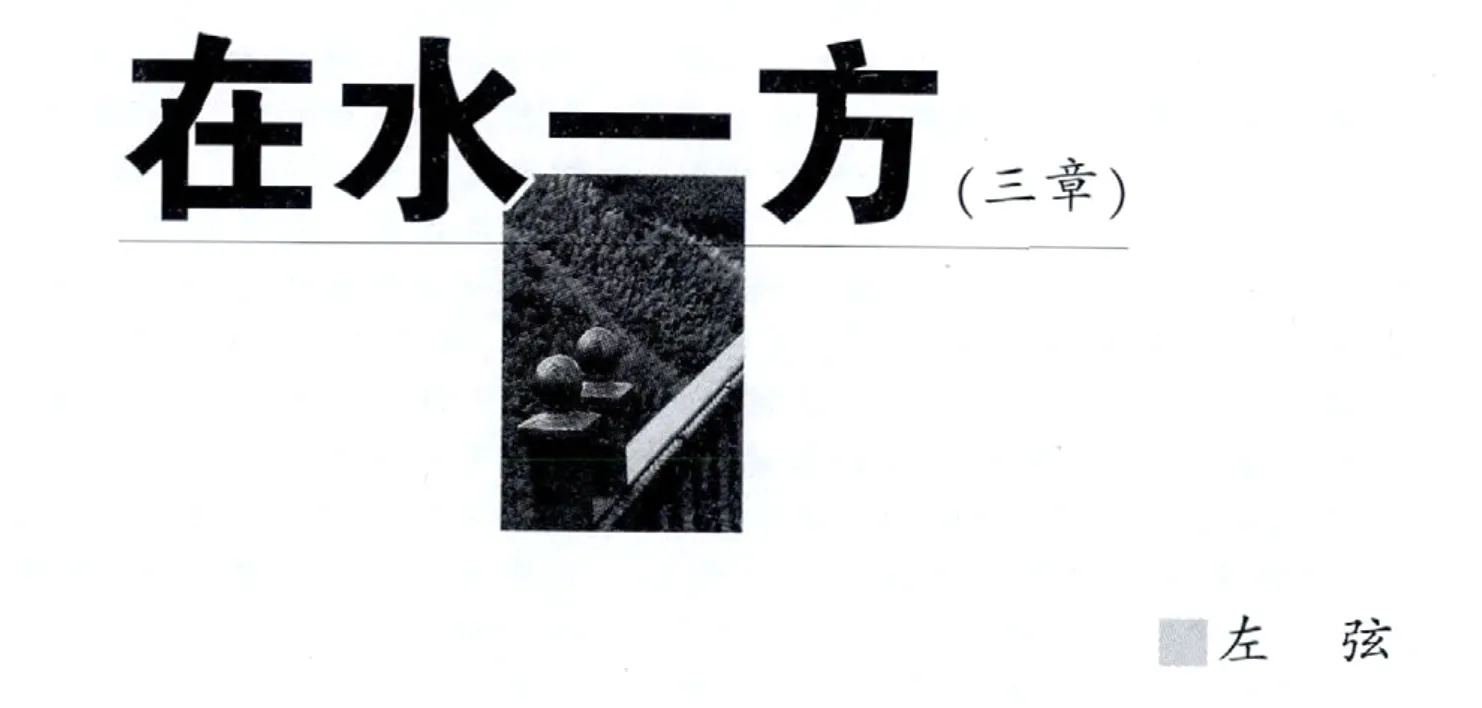
题记:我出生在水乡,我有一种模糊的思念。
年糕
“秋天深了/神的家中鹰在集合/神的故乡鹰在言语/秋天深了/王在写诗/在这个世界上秋天深了/该得到的尚未得到/该丧失的早已丧失”——海子《秋》
10多年前,在高中的课本里,我与海子的《秋》相遇。那时的我不解诗意,而我眼里的秋天还只是硕大的色彩,抬眼可望大片大片金黄,那就是沉甸甸的秋天。
当日子有序走进苏南平原的农历九月,在熟透了的水稻田里,父辈们正弯腰下镰,这样的动作理应包含着艰辛与劳累,然而他们似乎毫无所觉。在他们日渐隆起的脊背上,一种春华秋实的知足,已经牢固地构建起了他们的幸福,以至于当如今他们再无机会下田耕作时,竟然深藏着隐隐的叹息。
当然,少年是不识愁的。在这样的田野里,我们以想象与呼喊表达着嫩青色的年纪对于季节的呼应。不过,我的兴奋在于依稀可嗅的米香背后那种对于味蕾的诱惑,一种以糯米为原料,通过碾磨、筛粉、蒸笼等等细琐的过程转化而成的食物——年糕。
当时的年糕,不像现在这样随处可见,只要你愿意,随时可以吃到,乡村的菜市上是极少见到出售的。年糕的稀少并不见得是制作上的困难,而是从物质匮乏年代刚刚走出来的人们,对于米的珍爱,以及对于习俗根深蒂固的敬畏。当与春节——中国人心中最为重要的节令相互遇合,人们才以年糕缅怀先祖、祈愿来年,更以“年年高”这样中国式的口彩表述着对于生活朴实的憧憬。
在苏州,年糕更显出了几分传奇。相传,吴王阖闾定都苏州之后,不思进取,大将伍子胥预感必有后患,于是在兴建苏州城墙时,以糯米制砖,埋于地下三尺,嘱咐战时饥荒方可取用。后来吴越开战,正值青黄不接,吴人想起伍子胥的嘱咐,争而掘地三尺,果得糯米砖充饥,极大缓解了城内的饥荒。从那以后,苏州百姓每逢过年都会用米粉做成形似砖头的年糕以纪念伍子胥。传说的真实难以考证,却也因为真伪的莫辨而更具魅力。在口口相传之间,姑苏城与伍子胥的情缘倒是真的深厚起来。而因了这个故事,我对为了报仇而利用我的前辈祖先的伍子胥的那份嫌隙才得以稍稍纾解。他的无意而为,让许多血脉的延续成为了可能,而这其中,说不定还有我的那一支。
而对于孩子来说,这样的传说只会让纯澈的眼神稍停几秒,随后他们在意的永远是另一只更加实际的胃。年糕是种“随和”的食物,蒸、炸、炒、煮等各式烹调手段皆宜。而韩国的辣炒年糕则随着汹涌的韩流,成了许多年轻人的心头好。不过相对于这些以酱料来掩盖年糕口感的做法,我更喜欢苏州人在过年时处理年糕的那种古朴:将年糕切薄片,下油锅,煎至金黄,出锅装盆,然后撒一层白糖,就成了一盘老少皆宜的点心。
另外一种汤年糕,更是我的钟爱。将年糕下沸水,煮熟捞起,盛入一只以紫菜虾米汤为汤底的大碗中,撒上几粒葱花,就是一碗色如山水、热气腾腾的汤年糕了。汤年糕要选宁波产的水磨年糕为主料,这样煮出来的年糕才会细腻而有韧劲。这一度是我在上学之前必吃的早餐。天还不亮,年轻的父亲就要早早起床准备。那时候,农村菜市的物品远没有现在丰富,水磨年糕是不常有卖的。有一回,父亲没能买到年糕,汤年糕自然也无从做起。但是,不知为何我心里的委屈和犟性竟在一时发作,并以不上学“威胁”父母去满足我的欲望。父母一时无可奈何,这时爷爷倒神秘地拿来了两条年糕,于是吃饱喝足上学堂。爷爷逝世后,父亲总会跟我唠叨起这件事。原来爷爷为了让我上学,用麦粉临时揉了两条年糕滥竽充数。我于是惊叹,怪不得年糕粗糙了。斯人已往,时隔多年,爷爷的容貌已变得不那么清晰而明确了,然而那份糙味竟还留在舌尖,就像爷爷粗糙的手掌还在精确地呵护着自己的子孙。
现在,我仍然痴爱年糕,也尝过许多口味,然而总觉得年糕虽然还有年糕味,却总也无法留下富足的记忆。最近,《舌尖上的中国》正在热播,那些远比我们久远的食物,像中国人智慧的储蓄罐,开启了数千年的烟火文明。在《转化的灵感》那一集中,我第一次亲眼见到一块年糕的诞生。洗米、浸泡、去水、磨粉、过箩、上笼、捶打、擀条、压模成型,人与人之间用简单的协作和自然秘而不宣的原理,将珍珠状的米变成了洁白如玉、柔糯滑爽的糕。揭开我们的日常,原来还有这样如梦似幻的神奇。不过,影片中说,这样手工制作年糕的工艺正在逐渐失去。当乡村的孩子们涌向城市,故乡俨然在成为一个更加书面意义的词汇,它因丢失了丰富而显得那样孤独而单薄。而那些城里的孩子们,在捡拾财富的同时,生活似乎正在走进逼仄的窄巷。
在这个世界上,秋天正如诗人预言,越来越深了。我们在秋天得到什么,又丧失什么,得到的又是否能弥补失去,我没有答案。这一刻,我关心着那最后一块手工制成的年糕,以及紧紧守住舌尖上正在流逝的味道。
桑树
成群的桑林,至今我见过的只有一次。
10多年前,我是八九岁的孩子,养蚕业还没有像今天这样惨淡,苏州的郊外,都有规模不错的养蚕场。在镇湖西郊的小包围处就有一片,后来则成为了我就读小学的一处德育基地。有蚕的地方就有桑。在那里,我平生第一次见到了一整片桑林。
对于那年的三四月,所有的细节几乎都已经忘却,所有的记忆都只剩下一个尺幅巨大的“绿”字,那一眼绿得发烫的春光烙进了我的童年。桑树比一个孩子要高得多,桑林大得一眼看不到头。春风徐徐地来回林间,千顷万顷的碧波一下就散开了,一浪叠着一浪,是我们从未见过的壮观。我们“哇哇”大叫撒欢,纷纷乱乱的,老师一时都无法叫住,又是慌,又是好笑。这一份片面之缘,总像一枚细小的碎瓦,一头扎进我平静的时光。
桑树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都有。但由于我身在江南的缘故,一叶障目,便自以为桑树是江南独有的植物。当然,桑树其实长得并不江南,树身高大,树叶宽阔,倒是一副北方大咧咧的“筋骨”,而且极能抗寒抗旱,生命力很强,与江南的柔弱又甚是迥异。不过,看惯了烟柳细雨下的江南,再看桑林遍布的江南,倒是又一番滋味,这就好比一个女子的浓妆淡抹,各有千秋。
桑树的历史据说可以追溯到几千年之前,那样的年代只能付诸于人们的想象。我会疑惑,到底是怎样的一场相遇,让桑树与先辈们结下了相依相偎数千年的情谊。但我可以确信,桑树与中国人之间存在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感情,而没有另一种树可以如此贴近中国人的生活。三百首诗(指《诗经》),涉及桑树的就达到二十首以上,仅从这一幅先民生活的风俗画中,就不难窥探出桑树与人们的亲密之一斑。
汉代乐府诗中有一首《陌上桑》,讲述了美丽采桑女子罗敷不畏强权、据理力争,斥责当权者无耻行为的故事。长期以来,这个故事成为了道德中国浓墨重彩的一笔,成为了一杆高耸于地的旌旗,号召着一代又一代中国女性向其靠拢。对于罗敷的高尚品德,我始终保持着敬畏,然而在品德之下遮蔽的日常却更让我觉得可亲。“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罗敷善蚕桑,采桑城南隅;青丝为笼系,桂枝为笼钩……”这是多么美丽的开头:一个美好的清晨,一个美丽的女子,款款而行,直往弄桑。这是一个给予无穷想象的原点,渐渐还原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那一帧恬淡的过往。
在陶渊明的《归园田居》里,这样的日常更为清晰,“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这是一幅乡土中国的标准照,炊烟袅娜,鸡鸣狗叫,在视野足够宽阔的乡野之间,静静伫立一株桑树。桑树是生活的依靠,桑树又丰富生活,“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桑树已经远非一株植物那样简单,它成为了人们生活中茶余饭后的谈资,以另一种更为人们亲近的身份被认同,长存于农业中国的漫长岁月之中。
或许,你读一读《诗·小雅·小弁》这一篇,你更能体会到桑树给予了人们多么复杂的情愫。“惟桑与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属于毛,不离于里。天之生我,我辰安在?”在古人眼中,桑树格外需要敬重,因为桑树的生命里还流传着父母先辈的生息。人物虽往,而精神尚存。一株亭亭而立的桑树于人心,会是一场多么及时的安慰。而不知道从何时起,我们就将有桑梓的地方,叫成了故乡。
当然,现代的苏州已经很少见到桑树了,原来从老人们口中得知的家家弄桑的场景也不过是场徒然的追忆。现代丝织业的溃败,让桑树也迅速淡出了人们的生活,桑树真是成于物质,也败于物质。不过,苏州至今还保留着一丝残缺的记忆,在南园桥的西北,以桑为名的一条巷子,还不时提醒着我们古苏州曾经治桑的辉煌。而身为游子的我,也只有在品尝桑树的果实时,才会愧疚地想起那一个破碎了的故乡。
蚕
有一回,朋友召集聚会,其中有一位小学科学老师,给我们带来了四五条蚕。蚕很细弱,并不白胖,身上有些黑色的斑块,显然还是些幼蚕。它们被安放在用过的茶叶盒子里,盒子底部松软地铺着一层桑叶,蚕就在桑叶上“匍匐”,而桑叶上很快就形成了一道道细琐而笔直的齿痕。
蚕吃桑叶的速度有多快?那要看蚕的心情和胃口,恰逢心情好、胃口好,桑叶就会很快剩下一副“遗骸”,而如果心情与胃口都欠佳,或许桑叶就要被它长久“冷落”了。总体来说,随着蚕的长大,吃桑叶的速度也会成倍增长,这大概跟它成长需要摄取的养分有关。我喜欢看蚕吃桑的样子,当然也很喜欢这个动作所发出的声音。一群蚕一起“用餐”的时候,一片此起彼伏的“沙沙”声,如同细雨穿林。如果是在一个安静的夜里,你恰有份安静的心情,那么这样的天籁或许会是很美的一支安眠曲。
“睡眠”成为一个度量单位,大概只有在计算蚕的成长时才会用到。蚕的一生,是在睡梦中度过的。一生四眠,四眠一生,四眠以后,蚕就破茧化蛾,去实现它这一脉血统的传承,它也就走到了这一生的尽头。不过在我看来,这并不可惜,天下生灵,生来最伟大的任务,就是繁衍与传承。即使这样的繁衍与传承要付出的是性命,也依然灿如烈火。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一个生物,甚至包括一个人,都是生死循环上一枚光荣的补丁。
养蚕是门很古老的手艺,据最新的考古发现,养蚕可以追溯的年代大约在一万年以前。当然,民间自有传说,流传较广的是嫘祖始蚕。嫘祖是黄帝的妻子,作为养蚕缫丝的发明者,人们又称其为先蚕娘娘,也有称蚕花娘娘的。我并不在意养蚕缫丝的肇始,但我却迷信着蚕丝在改变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塑造中国人的性格之中发挥的作用。蚕丝不仅为人们的身体提供了更为妥善的遮蔽,更在文明中扮演着进程重要载体的角色。这一副远古的图腾,虽然因为母系社会的终结而渐渐漫漶模糊,但仍然是华夏文明里最为灿烂的印记之一。
上世纪80年代的苏州还有很多养蚕的地方,我询问过父辈那时候的情况。他们会用一个反问来回答你的疑惑,“那时候谁家不养蚕?”江浙作为养蚕业发祥地之一,历史有载,几乎家家养蚕。曾经的蚕桑,可是一个与稻麦平分整个农业中国的泱泱大业。蚕桑的兴旺,当然离不开蚕桑之利。“天下熙熙,皆为利往”。孟子对话梁惠王就说过:“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五亩之宅并非确数,仅是一个普通家庭的代指。利用不大的地方种桑养蚕,老了就不用怕挨饿受冻,可见桑蚕在一个家庭中的地位,也愈发显出蚕的价值。
蚕的主要经济价值在于丝。蚕茧虽然看起来层层叠叠,实际上只是一根完整的丝线,如果展开可以达到一公里多,这样的构造再次显示出自然造物的瑰丽与神奇。蚕丝可以制成丝绸,丝绸的成衣柔软细腻,穿在身上冬暖夏凉,但一件衣服就要用上数斤蚕丝,对于轻薄的蚕丝来说,“斤”几乎是“不能承受之重”。所以,即使桑蚕业如此兴旺,能穿丝绸成衣的依然是富人。虽不免有“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的喟叹和遗憾,然而桑蚕业依然给予了先人们对于靠近幸福生活的无限可能,如果没有养蚕业,那么生活的艰难或许更加难以想象。正是由于这种珍贵,千百年来的中外贵族都以能穿丝绸成衣为荣。而那一条令人充满绮念与遐想的丝绸之路,则为这样的珍贵作了最具体的注脚。
不过,对曾是孩子的我来说,养蚕其实并不涉及到传承文明这样严肃的话题,也远非是对丝绸之路这样宏大辉煌的崇敬,这样的举动只是在童年之中与小伙伴们找到一种共同的趣味。尽管时隔多年,我还是能记得第一天捧着那些幼蚕时,上课就再没有专心过,隔着一小会儿就要察看它们的情况。晚上则抱在怀里,临睡前还不忘跟它们道个晚安。那种关心的程度有些让现在的自己不能理解。即使我曾经是这样走过,却再无法还原当时的心情。然而,任我如何冥思苦想,依然想不起那条蚕后来遭遇了怎样的命运?是夭折了,抑或成了飞蛾?这样的疑问就成了我平生偶尔触手可及的一道淡淡瘢痕。
姑苏人呼蚕,总爱称“宝宝”。大概是蚕能吃、能睡,才有此雅号。但也可能跟成熟的蚕有关,因为完全成熟的蚕,通体洁白,肥嘟嘟的很像个小宝宝。蚕成熟了,就要上山,山并非真山,只是人们编制的草垛供蚕吐丝织茧的,随后一根丝线将缠绕住他们今后的命运。李商隐有句“春蚕到死丝方尽”,现如今早已成为奉献精神的一曲煽情,然而在这悲美的背后,或许也有蚕一丝丝“壮志难酬”的不甘之情吧。
已经许多年没看到蚕了,家家养蚕也只是一个偶尔听听的老故事了,或许以后也无人再能述说。现在,当我再看见蚕的时候,总觉得它是一种与我生活如此格格不入的生物,也很难想象它们与父辈们生活之间曾经存在的亲密关系。当养蚕退出了人们的依靠,蚕似乎就在一夜之间退出了世界,物质总是在物质面前败退得太过迅速,甚至牵连了无辜而丰富的记忆。在姑苏的街头,在旗袍娉婷的曲线里,谁曾忆起,蚕在古老中国里所有的鲜亮与落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