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岁
2013-12-25 02:23贾平凹
读者 2013年13期
贾平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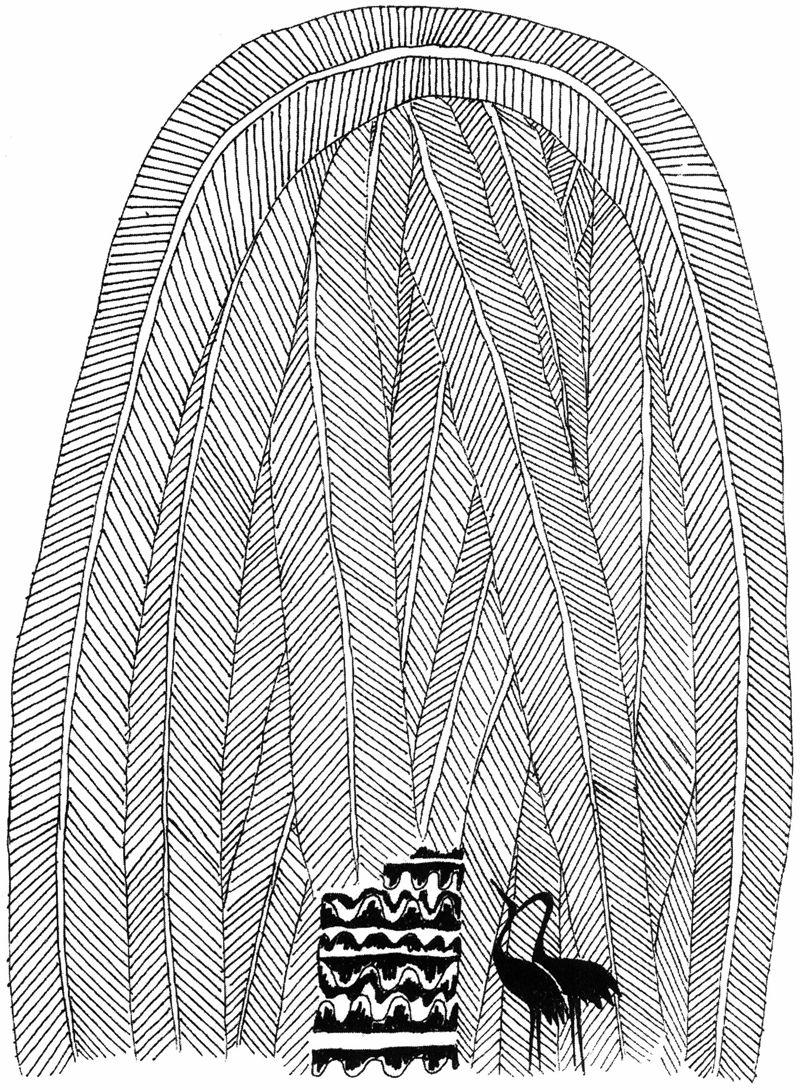
进入六十岁的时候,我就不愿意别人对我说今年该给你过个大寿了。很丢人的,怎么就到六十岁了呢?生日那天,家人和朋友们已经在饭店订了宴席,我就是不去,一个人躲在书房里喘息。其实逃避时间正是衰老的表现,我都觉得可笑了。可是,在母亲的遗像前叩头,感念着母亲给我的生命,说我并不是害怕衰老,只是不耐烦宴席上长久的吃喝和顺嘴而出的祝词,况且我现在还茁壮,六十年里并没有做成一两件事情,还是留着到八十、九十再庆祝吧。
整个夏天,我都在为《带灯》忙活。我是多么喜欢夏天啊,几十年来,我的每一部长篇作品几乎都是在冬天里酝酿,在夏天里完满。别人在脑子昏昏、脾气变坏、热得恨不得把皮剥下来凉快时,我乐见草木旺盛、蚊虫飞舞,意气纵横地在写作中欢悦。这一点,我很骄傲,自诩这不是冬虫夏草吗,冬天里眠得像一条虫,夏天里却是绿草,要开出一朵花了。
这是一个人到了既喜欢《离骚》,又必须读《山海经》的年纪了,我想要日月平顺,每晚关心着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和天气预报,咀嚼着天气就是天意的道理,看人间的万千变化。
王静安说:“且自簪花,坐赏镜中人。”
(林海泉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带灯》一书)
猜你喜欢
东坡赤壁诗词(2020年3期)2020-07-04
人物画报(2020年17期)2020-03-13
发明与创新·中学生(2018年12期)2018-12-29
环球时报(2018-11-03)2018-11-03
养生保健指南(2017年7期)2017-12-07
祝你幸福·午后版(2017年4期)2017-05-02
小学生作文·小学低年级适用(2016年4期)2017-01-16
意林(2014年21期)2014-05-14
知识窗(2001年2期)2001-03-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