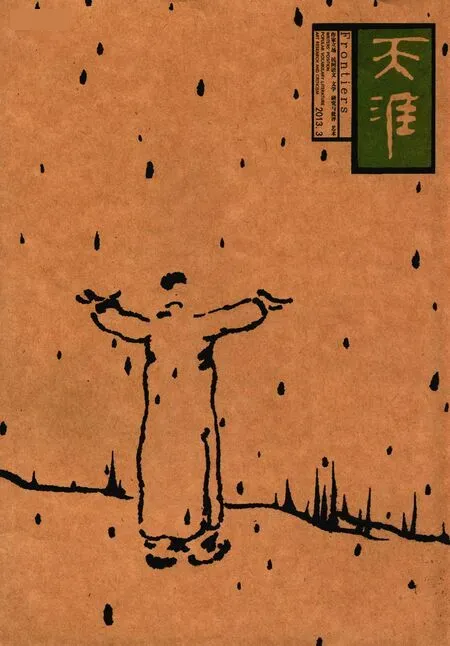美国不是美丽的榜样
近日,《观察者网》发表美国塔夫茨大学教授兼中文部主任钟雪萍的文章,批评国人对美国的一厢情愿的浪漫想象。
钟雪萍说,1980年代,在国内某大学读英美文学研究生班,一位来自美国某州立大学英语系的教授,作为“外国专家”,给我们开“美国文学文化史”课。谈到美国文化特征和主要倾向时,教授说,“反智”,并举出各种例子解释。当时的我,无论如何都理解不了:你们不是代表最先进的文明吗?我们现在的宣传就是这么说的。先进的文明不就是富裕加人民有知识有文化,有文明的行为,有极强的求知欲?怎么会是反智的?不明白。
到了美国,最初几年继续读英美文学,必修功课最多的就是所谓读原著,看作品,上下千年的主要作品,先是英国的,后是美国的。尽管对完全没有基督教文化背景和资本主义社会经验的人来说,理解上困难重重,但读不好就没奖学金,就拿不到学位,只能“迎着困难上”。逐渐倒也看出些眉目:工业化前文学大多与基督教有关,更多的是怀疑者内心的挣扎,或者是对教会虚伪的揭露,对被压抑人性欲望的抒发等;工业革命后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带来很多新问题,个体从孤独开始,内心的挣扎似乎远远超出我们这些来自所谓“集权”国度人们所经验的。
从美国文学中能看出其社会各类特殊历史和现实问题。最为突出的是种族问题,尽管其中很大意义上其实是阶级和政治经济问题。在漫长的种族歧视历史中,三百多年的黑奴史与美国的资本主义发展直接相关,后遗症继续在多个层面上延续。单说华人,最早是作为苦力劳工,在十九世纪中期来到美国的,成为修建横贯美国东西铁路的主要劳动力。这跟鸦片战争打开中国门户直接相关。这些劳工当时所经历的以及铁路修成之后所遭遇的歧视和压迫,在美国只有马克·吐温和极少数的作家予以揭露和抨击,而其政治主流则利用底层的种族歧视,拉选票,玩政治,竞相排华,直至美国国会1882年通过“排华案”。这一法案直到1963年才被去除。从1882到1963的八十多年间,除留学生以外,华人不得正常进入美国。最早出现在旧金山的所谓唐人街,完全是因为华人受到歧视,不被接受,无法在任何其他地方立足而出现的ghetto(少数族裔聚居区)。与此同时,认同主流的压力有形无形随处存在,即使积极认同也不排除仍被另眼相看。
钟雪萍说,美国的历史从霸占别人的领土开始,而这段历史因权力的不平衡至今得不到主流文化和认同主流文化人群的正视。确实,除了偶尔在美国公众电视台(PBS)上看到一些纪录片,讲述部分历史和现状,北美洲印第安人的历史遭遇和现状完全处于主流媒体视线之外。而一旦视线聚焦曝光,很多很多有关这个“美丽的榜样”的宣传就会难以自圆其说。
最近,跟一位同事聊天,一起抱怨学生水平差。同事说,不过,总有百分之五非常优秀,而这个国家,也就是由这个比例的精英们所掌控。这个观察让我想起上述那位教授的话,从反面证明他的说法:大多数人反智,正好方便了少数精英的统治。这不正应了儒家的上智下愚吗?
钟雪萍最后说,对所谓的“榜样”应该有全面和历史的了解,省得连“榜样”自己都偷笑你傻。自己几千年的历史,留下的有好的也有不好的,而且无论好坏,加起来就很多,很沉;别人几百年的历史,通过掠夺强占才成就“地大物博”;自己国家十三亿多人口,基本都是“土生土长”;别人三亿人口,是资本主义现代扩张历史中出现的移民国家,在摧毁原住民的生存方式之后,直接发展资本主义,引进劳动力,引进人才,等等。就算人家是西施,看上去很美,你是东施,别人都说你丑,你也不能效颦。越学越丑,这道理古人都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