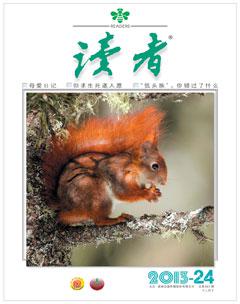但求生死遂人愿
阿西瓦·马苏德/文 杨戈/译

70岁的肯尼斯·普拉格医生是一位医学伦理学家。一天,他接到另一位医生史蒂芬·威廉姆斯打来的电话,后者56岁,曾在普拉格手下受训,现为一所医院的主治医师。但是,当普拉格医生弄明白这通来电的原委后,开始有些心神不宁。
多数情况下,只有患者家属不愿放弃治疗时,才需要医学伦理学家的介入,但这次恰恰相反。威廉姆斯正在治疗一位36岁的病人,这位病人虽然眼下不省人事,依靠多种生命维持设备存活,但仍有望康复。可病人家属认为,终止治疗才是最佳选择。
躺在ICU(重症监护室)病床上的男子名叫约瑟夫·布朗,身材高大,体格健壮。此时他意识尽失,他的父亲、妹妹和女友都认为应该撤走维持其生命的各种医疗设备。布朗需要截肢——事实上,必须多处截肢。他的工薪家庭成员单方面认为,他不会愿意这样活着。他们声称,作为一名砖瓦匠,布朗得靠双手工作,如果没了双手,他的生活将毫无价值。
普拉格对这家人的决定很是不解。自1992年伦理委员会成立以来,普拉格每年要处理150~200起医学伦理业务。布朗的情况是他遇到的极罕见的复杂案例之一。
“如果不能确定病人的意愿,挽救生命似乎更为合理。与其无缘无故地死,不如不明不白地活,前者比后者更不公平。”普拉格说。
作为布朗的主治医师,威廉姆斯通常能处理大多数棘手病例。但是,由于此案异乎寻常,威廉姆斯需要听听其他人的意见,以确保做出正确判断。如今医学技术进步巨大,医生很难断定在哪个时间点上治疗是无效的。
如果患者、家属和主治医生在治疗上发生分歧,医生就会咨询医学伦理学家,后者将尽力使三方达成一致,并提出最有利于患者的建议。
白人男子布朗是单身,和家人住在一起。2005年11月,他的脚趾被感染。起初,他并不在意,觉得在家用些抗生素或药膏处理一下就可以了。但他脚趾周围的皮肤逐渐硬化、变红,最后不得不去医院。即便那时,布朗仍认为只需要做个外科手术,去掉脚趾里受感染的部分就没事儿了。不幸的是,情况并非如此。
当布朗到医院就诊时,细菌已侵入血液并扩散到他全身,发展成为坏死性筋膜炎——一种“噬肉性”疾病,确诊患者的死亡率高达73%。
这种病的起因很简单,只是被纸割伤或丘疹即可引发感染。细菌通过伤口进入人体,沿着皮下筋膜(肌肉和脂肪之间的隔层)扩散。
布朗很快出现了败血症和多个器官衰竭的症状,不得不注射镇静剂,在气管上插管,戴上呼吸机。
在见到布朗的家人之前,威廉姆斯曾以为他们不了解患者的临床状况。“我想让他们明白,布朗的情况还是可以救治的,有修复术、康复中心,即便在截肢之后也能拥有高质量的生活”。
威廉姆斯在一间会议室与布朗的家人见面。布朗的父亲约翰将近70岁,面容粗糙,却很健壮,一看就是历经数十年努力工作才能维持收支平衡的工薪族。他一直坚持说,布朗宁愿死也不会愿意截肢——一旦截肢,体力劳动者将毫无用处。
威廉姆斯说:“我跟他们说,通常这种情况下,不会移除生命维持设备。如果患者年纪不大,就要尽一切可能挽救他,除非已经确定没有希望。”
但病人家属一直摇头表示不赞同。“这是一个工薪家庭,只能维持基本生计。我猜他们没有受过大学教育。他们都是很好的人,但是,必须用简单词语向他们解释。”威廉姆斯说,“我告诉他们,布朗目前的一切不良状况都可以好转,因为早期迹象表明他正在恢复。”
但是家属似乎不为所动,坚持认为:布朗没有四肢还能做什么?他的未来会怎样?
“他们很平静,但非常固执。”威廉姆斯说,他仍旧很难相信家属想让布朗离去。布朗的家人既不生气,也没有太多情绪。他们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就是停掉呼吸机,并且确信这也是布朗自己的想法。他们相信,布朗宁愿死也不愿带着残疾活着。
有时候,家属会告诉威廉姆斯:他不是上帝,不能决定谁能活多久。威廉姆斯笑了,捋着花白的胡子:“我告诉他们,上帝的欲望清晰明了。每时每刻我们都在通过呼吸机、静脉注射、起搏器与上帝抗争。上帝想把你们至爱的人拉入天堂,而我却拼命把他留在人间,这种拔河比赛我经历过很多次。”
会面之后,威廉姆斯知道自己需要其他人的观点来拖延时间,他决定找医学生命伦理委员会商量。
生命伦理学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主要研究生物医学中的道德问题。医学技术的进步使人类越发有能力干预人的生老病死,这将引起积极和消极的双重后果。一方面,人们能更有效地诊断、治疗和预防疾病;另一方面,在各国的医疗和研究工作中,违反生命伦理的事件总是存在,技术的进步也带来了对人的尊严和价值的挑战。
20世纪70年代,纽约第一个伦理委员会成立时,普拉格还是一位胸腔内科医生,由于与重症监护室的病人打交道的机会越来越多,他开始思索医生们治疗绝症患者究竟是在延长他们的生命,还是在延长其死亡过程。
威廉姆斯把布朗的案例扔给了普拉格。普拉格认为,治疗丧失意识的患者时,尽管通常的做法是遵循家属意见,但他觉得,听任布朗死去是不妥的。只要布朗的大脑没有严重受损,他就可以活下来。“他(布朗)绝对想不到会有这么一天。我不清楚他的亲属怎么如此确定他的意愿。”普拉格说。
正如威廉姆斯期望的那样,随着时间的拖延,布朗的病情开始好转。由于药物发挥作用,他的白细胞数逐渐增加,而后趋于正常。毒素含量开始下降,肾功能得到改善。尽管骨科医生仍建议将布朗的四肢都截掉,但即使这样,他应该还能活三四十年,放弃治疗实在让人惋惜。
经过数日讨论后,布朗的家属还是坚持撤掉布朗的生命维持仪器,他们担心延迟太久的话,布朗将带着残疾度过余生。
医院终于撤走了布朗的生命维持设备,所有的蜂鸣警报器、呼吸机和闪烁的显示器均已停用。床边的空间全部留给家属,以便家属在布朗可能留在这个世界的最后时刻里陪伴左右。
医生关掉了呼吸机,拔出了插在气管中的管子。但奇迹发生了,布朗并没有呼吸困难,他开始自主呼吸,平静而自如地呼吸。
15天后,布朗开始恢复知觉。他的妹妹试图和他说话,并告诉他医生建议对他的手和腿进行截肢。
令她吃惊的是,布朗的第一句话就是:“只要能活着,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一个月后,布朗做了四肢截肢手术,然后出了院。
几周后,在医院的候诊室内,布朗坐在轮椅上,阅读放在轮椅折叠桌上的杂志。在等待转移到康复中心期间,他的残肢均被包扎起来。威廉姆斯主动和他打招呼,布朗伸出残肢同他握手,但并不清楚威廉姆斯是谁。当威廉姆斯向布朗解释了发生在他身上的一切之后,布朗尽管对截肢感到相当沮丧,但表示他很高兴自己还活着。
“许多人都避讳谈及残疾问题。当真正面临这种境遇时,更多人还是想活下来。他们可能会说,我或许有残疾,但我热爱生活。”普拉格说道。
(黎 戈摘自《海外文摘》2013年第10期,李晓林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