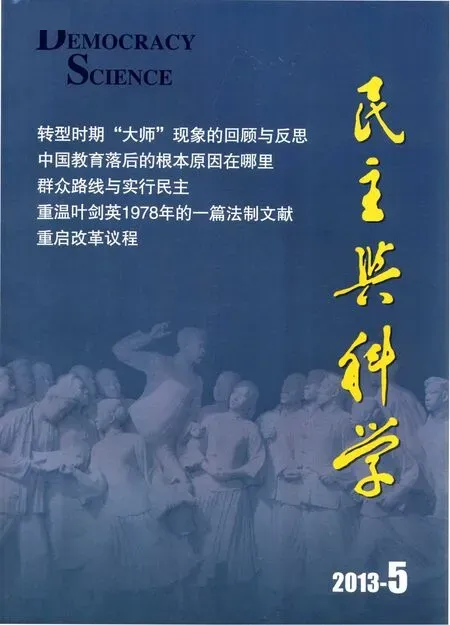从王书金到聂树斌——“疑罪从无”的误用
■张千帆
近日,河北省高院维持了王书金案的死刑判决,并支持检方提出的“石家庄西郊强奸、故意杀人案不是王书金所为”的结论。众所周知,王书金案之所以引人注目,并不在于这个案件本身,而是在于他主动承认了自己就是聂树斌案的真凶。也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戏剧性的一幕:被告不断供认自己就是某案的真凶,公诉方却坚决否定是他干了这事!公诉和被告仿佛角色互换,在被告是否是一桩强奸杀人案的凶手这个重大问题上相互“谦让”起来;被告一再表白不让别人替自己“背黑锅”,检方却坚持“疑罪从无”,一副要将被告权利捍卫到底的样子。然而,后者的出发点似乎不在于保护被告,而在于一旦承认王书金是聂树斌案的真凶,也就等于承认聂树斌的死刑判决是一起发生在河北的陈年冤案。
河北高院不认定王书金为聂案真凶的理由是其提供的杀人证据不尽符合被害人的勘验笔录和尸检报告,主要是具体作案时间差了几小时、被害人身高差了20公分,尤其是王未能供述被害人的颈部缠绕了一件花衬衣“这一关键、隐蔽性细节”。据此,河北高院支持了检方提出的王书金并非石家庄西郊案真凶的结论。如此听起来,河北高院和检察院在这一起案件中成了坚持“疑罪从无”原则的典范。
然而,在石家庄西郊案适用“疑罪从无”显然是一种时空错位,河北高院认定该案“不是王书金所为”的结论也带有很大的误导性。“疑罪从无”原则并不能帮助我们推断被告是否作案,而只是要求国家在证据有疑点的情况下不能给被告定罪,因而是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对被告自由的保护。譬如美国法院适用“疑罪从无”,判定辛普森“无罪”,这只是说检方起诉辛普森杀人的证据中有疑点,未能达到“超越合理怀疑”的举证负担,因而不能判他有罪,但这并不是说法院就此宣布杀人案不是他干的。事实上,很多人都怀疑这桩案就是他干的,可能连法官本人也不例外,只是证据未达到让国家动用暴力把他铐起来的地步。
现在河北检方根本没有起诉王书金犯了石家庄西郊案,“疑罪从无”从何谈起?如果证据有疑点,只能说国家不能因为这个案件判他有罪,而绝不能断定这起案件“不是王书金所为”。换言之,以现有的证据,河北高院既无权宣判石家庄西郊案是王书金干的,也无权以“疑罪从无”的名义宣判此案不是他干的。如此适用“疑罪从无”,显然是对这一原则的误用,目的是把他从聂树斌案中彻底抹掉。王书金的自供确实和勘查笔录存在一定的出入,但他完全可能是石家庄西郊案的真凶。如果该案真凶不是他,他有什么理由主动冒名顶替呢?检方给出的理由是以此获取轻判,但是这种理由恐怕是很难成立的。撇开石家庄西郊案不说,他已经犯了强奸三名妇女、杀死其中两人并杀害一人未遂的死罪;冒名顶替之后,他的罪变成了强奸四名妇女并杀死其中三人。这种主动交代即便算是“立功”,对他来说也是得不偿失,只能加重罪责。
至于被害人颈部的花衬衣,也许对于公诉人来说是“关键细节”,但在普通人看来未必是什么重要证据,未曾招供也不难理解。毕竟,王书金是在案发多年之后招供的,记忆模糊、细节出入纯属正常,不能用“疑罪从无”认定他和该案无涉。更何况他还供述出现场的一串钥匙等符合勘查笔录的关键证据,而这个细节在聂树斌的口供里却没有。如果不是作案人,很难解释他会知道如此微小的现场细节。因此,现有证据确实不足以为王书金是否是石家庄西郊案的真凶定罪,但是证据中的疑点亦同样不能否定该案真凶很可能是他,而非聂树斌。
真正应该适用“疑罪从无”的对象是聂树斌,而王书金的自供不论有什么疑点,都构成聂树斌的重大“疑罪”。作为聂树斌案的关键证人,他对重新审查聂树斌死刑判决的合法性具有重要价值;在这个时候判他死刑,给人的印象恐怕不是“疑罪从无”。众所周知,聂树斌案的判决已遭社会质疑达十多年之久,而最高法院也曾责令河北高院再审,但是后者一直未能拿出一个令社会满意的答复。王书金的自供让社会看到再审聂树斌案的希望,而河北高院对其死刑的维持不禁让人担心,为聂树斌讨回公正的希望会否再次泯灭?
当然,如果河北高院像对待王书金那样对待聂树斌,严格适用“疑罪从无”,那么聂案的公正判决不难实现。然而,这一原则用在了一起不该用的案件,却未必表明它也会用在该用的案件上。鉴于河北法院系统以往对聂树斌案的态度,社会有理由怀疑它能否公正处理聂案或与其相关的案件,譬如王书金案中的自供部分。事实上,河北司法和聂树斌案已经产生了一种“利害关系”,判决聂树斌无罪即等于给河北司法“抹黑”。我对河北司法系统没有偏见,但是在这种利害关系影响下,很难指望任何司法系统能够公正审判。在这个意义上,河北司法已经失去了处理和聂树斌案相关案件的资格,而由河北高院对王书金的自供证据定性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如果要再审聂树斌案,最适合的主体当然是最高法院。如此也能妥善衔接聂树斌案的再审与王书金的死刑复核,等到王书金在聂树斌案再审中做完证人之后,再复核其死刑判决。否则,如果匆忙核准并执行王书金的死刑,聂树斌案的再审又遥遥无期并失去关键证人,中国司法的公信力无疑将又一次受到重大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