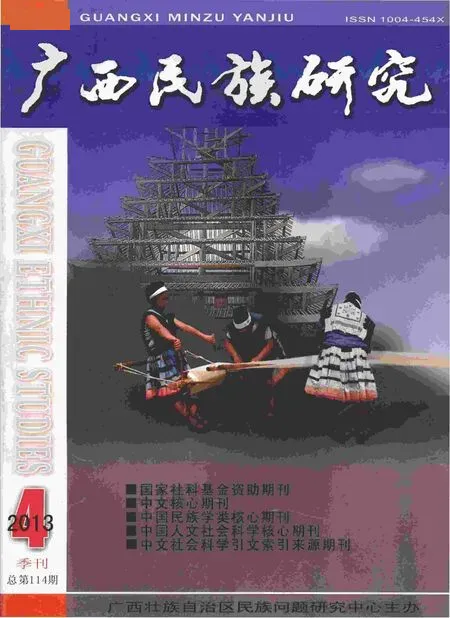族群身份、资本治理与现代国家的领导权*
——以东南亚地区为视域
傅景亮
族群身份、资本治理与现代国家的领导权*
——以东南亚地区为视域
傅景亮
东南亚地区族群众多,族群间关系复杂,在现代国家的构建过程中,由哪个族群拥有现代国家的领导权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由于外来的现代性的扩展造成了东南亚地区的族群普遍面临生存、认同和整合危机,族群的发展问题尤为紧迫。在这种情况下,现代资本方式、价值和制度的发展促使族群身份向民族身份转换,为现代国家的建构提供了民族动力。主体族群恰恰是在族群整合过程中、现代资本治理中居于优势地位的族群,其对国家领导权的要求也成为题中应有之义。
东南亚;族群身份;资本治理;现代国家;领导权
根据《麦克米兰人类学词典》的解释,所谓族群是指一群人或是自成一部分,或是从其他群体分离而成,他们与其它共存的、或交往的群体具有不同的特征,这些区别主要表现在语言、种族和文化方面,族群实际上就是不同群体互动和认同的过程。族群的意义和价值绝非限于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范畴,在现代国家的框架中,族群的发展、族群间关系、族群的政治经济能量直接关系到现代国家的建设和领导权。
东南亚地区的族群现象颇为纷繁复杂,其族群种类、规模、来源呈现为多样化的态势,族群间关系直接关乎到东南亚现代国家的成长。近代以来,东南亚地区的族群面临着外部现代性的挑战,因此其身份危机严重到危及其生存的空间。现代资本技术、理念和制度的介入则为族群身份向民族身份的转换提供了条件。但是,由哪个族群来领导现代国家摆脱殖民独立,进行工业化建设,不仅仅是各个族群之间的博弈关系,亦是由族群在现代性挑战中和资本治理结构中的地位所决定的。
一、现代性的扩展导致族群身份危机
族群生存危机发生于西方殖民扩张、世界体系扩展和国家建设的过程中,东南亚地区普遍面临着族群延续、文化传习、生活方式、居住环境等方面存在的危机。在东南亚传统社会状态中,虽然地方族群间冲突从未间断,外来移民和经商联系不断增长,但族群结构却呈现为固化状态,其原因在于各种各样的威胁是在传统的规范框架中进行的,既未能动摇族群统治的权威结构,也不能改变权威赖以建立的经济基础。当西方进入到近代社会,在诸种动机作用下,西方船舰、商人、传教士、探险家通过各种方式进入到东南亚,一种迥异于传统规范的西方价值、制度和技术慢慢起到了一种销蚀的作用,直接威胁到东南亚的族群生存状态。
第一,西方殖民方式导致族群意义的转换。西方殖民者的入侵是东南亚地区传统社会解体的起点,也是东南亚地区族群生存危机的开端。西方殖民者通过不同的方式对东南亚地区进行统治,不同的入侵者、不同的统治方式对东南亚各个国家和地区而言具有不同的意义。J·S·弗尼瓦尔比较英属缅甸和荷属东印度的殖民统治时指出:“在殖民统治的具体实施方面,他们又是完全不同的。英国人在缅甸从一开始就依赖西方的统治原则,即法律和经济自由原则;而在荷属东印度,荷兰人则尽量保留当地的习俗和权力的热带特征,并使之适用于现代社会。”[1]79
这显然是两种不同的殖民方式:一种为直接统治,意味着将西方的法律、制度、价值移植到东南亚地区,通过西式的“统治方法”改造传统社会治理结构;一种为间接统治,意味着在保留东南亚地区传统的权威结构基础上与当地的统治阶层建立合作关系。其实,两种统治方法并非可以截然分开,在一定意义上殖民统治者二者兼用。如西班牙在统治菲律宾的过程中,其就着力于与菲律宾传统的统治阶层建立合作关系,拉拢不同地区和族群的精英阶层,“殖民政府完全依赖于当地合作阶层的封建依附关系,由此而使传统的上层人士通常得到正式的认可,并且日常管理工作就是由这些人来执行的。”[1]70在西班牙的间接统治过程中,其所具有的西方制度、价值和技术开始慢慢渗透到菲律宾社会的某些层面,特别是基督教思想和势力的影响。当西班牙的统治让位于美国的殖民统治,后者似乎更具有雄心壮志,在继承与菲律宾传统阶层进行合作的间接统治的条件下,美国开始有意识地将自身的立法传统、民主体制、经济政策、意识形态置于菲律宾的框架中,尝试改变后者传统的制度结构。
不管是直接统治还是间接统治,西方殖民的基本逻辑就在于,将西方的“民族”概念框架套用到东南亚地区的“族群”意识之中,在这个意义上,“族群”意义发生了重要性转换:首先,族群利益开始重新界定。由于外来殖民的压力,传统的族群利益 (如对土地的占有权、对地区公共事务的管理权等)开始遭到破坏,族群利益必须重新构建,这一过程是由上层人士与殖民统治者之间的妥协和合作来完成的,缺乏应有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其次,族群意识在不断被唤醒。本地族群、外来族群、西方殖民者等概念就是族群身份识别的过程。一方面,本地族群与外来族群有着截然分明的差别;另一方面,通过比较识别,本地族群慢慢确定其本身所具有的价值,包括族群文化、生活习惯、应得利益等。再次,族群权威结构的改变。传统社会族群各据一方、互不侵扰的格局在殖民统治者“分而治之”的统治下被打破了,殖民统治者按照西方意义上的“国家”疆域重新划分版图,势必导致族群权威格局的混乱,从而造成不同地区、不同族群为争夺“国家”领导权而相互征战。
第二,世界体系扩展导致族群整合的复杂。随着西方力量深入到非西方地区的腹地,世界体系在不断扩展,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联系不断增强,人类社会已经渐次呈现为一个“全球格局”,这既是一个客观的结果,又是一个主观的结果。对于东南亚地区而言,世界体系的扩展打破了传统族群封闭状态,族群整合成为一个长期的主题。一方面,族群整合是由西方工业革命的冲击造成的。“工业革命不仅是美洲和澳大利亚被欧化的主要原因,也是欧洲庞大的殖民地结构在亚洲和非洲得以建立的主要原因……殖民地可以作为数量日渐增多的制成品的市场……”[2]311-312工业革命以科学和技术革新为标志,促进了知识领域的扩展,不仅激发着现代化的早期先行者,对于非西方社会同样具有吸引力,特别是对于族群中的精英阶层,精英和大众之间的冲突成为族群整合的重要内容。工业革命扩大了物质基础的范畴。工业革命亟需能源 (石油、煤炭)和原料的供给,而非西方地区显然成为西方社会进行剥削的主要对象,但同时也为非西方地区物质基础的扩展提供了条件,能源供应和原料的供给在改变着东南亚传统地区的产业结构,对族群传统的生活方式不啻为重大的打击。工业革命意味着交通系统的发展,以火车、轮船为代表的交通工具,以铁路、公路为代表的交通网络,以电话、电报为代表的通讯手段,将整个世界连为一体,国家、地区间联系成本骤然下降,同时意味着人们之间的交往距离骤然缩小,交往方式使得族群间关系、族群内的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另一方面,人口迁移带来族群整合的困境。东南亚地区自古就存在人口迁移现象,既有陆路迁移,如华人、印度人到泰国、马来亚、缅甸等地;亦有海路迁移,如华人从广东沿海迁徙到“南洋”地区。由西方发轫的殖民扩张和世界体系的扩展,人口迁移在规模、来源、目的地、数量等方面急剧扩大,当然也包括国家内部地区间人口迁移的情况。人口迁移必然面临族群差异的现实,即本地族群与外来族群的关系问题。外来族群在语言、文化、肤色、习惯等方面与本地族群存在着明显差异,更重要的是外来族群往往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成为社会经济中重要的力量,本地族群在经济结构中的边缘化必然导致族群之间矛盾的加剧。
第三,传统社区破产导致族群范畴的扩大。东南亚传统社会无论是处于中央集权体制之下,还是处于封建割据状态,都是由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所决定的,传统社区成为地方精英和大众整合的重要空间结构。传统社区的整合功能对于族群的意义极为重要:对于不同族群而言,大都呈现为同一族群聚居状态,即同一族群的人们往往集中生活在同一地域之内,形成族群社会交往网络,至于族群之外的社会则较少关注甚至持有敌意。在聚居社会经济结构中,族群对于权威的认同更倾向于地方管理机构。东南亚传统社会呈现为庇护-侍从结构形态,族群内部形成了一定的等级结构,人们往往通过社区的认同实现自我价值和族群利益。地域、族群和认同天然地结合在一起,此种生存状态千古未变,直至在现代社会和国家的强烈冲击下才渐趋瓦解。一方面,族群天然的地域结构被打破,人们似乎在一夜之间突然发现,外来力量已经渗入到传统社区之中,他们带来了截然有别的价值、技术和制度,他们在不断开发并摧毁传统社区所独享的资源;另一方面,族群认同结构也在悄悄地发生变化,对于外来的影响,传统社区的人们先天性地进行抗拒,但是对于现代化的抗拒显然是无力的,变迁势在必然,传统社区的权威结构不断被侵蚀,即使仍然苟延残喘,也已经深刻影响人们的权威认同。
传统社区的破产意义深远。一则,传统社区的封闭状态不复存在,外部冲击性带来的重要影响之一在于社会流动性不断增强。人们越来越具有“放眼看世界”的开放视野,先前对于外部世界的认知过于荒谬,只有重新改变自我知识结构和价值体系,才能真正应对外来的社会力量。东南亚上层精英开始了远洋之旅的学习,他们去英国、法国、葡萄牙等国家,真正地去接触西方的先进知识、技术、理念和制度,从而为其国家之独立和建设提供新型的人才。传统社区人们之间的分界——精英与大众的界限一目了然,社会流动性增强在改变着人们的身份属性。对于中下层的人们而言,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在不断增强,对于上层的人们来说,传统利益的守护越来越困难。此外,传统社区固化的劳动分工已不能适应现代化社会的发展趋势,特别是随着市场进入、工业化和土地改革的进行,职业分工越来越复杂化和细致化,职业改变了人们的习俗结构。
二则,传统社区的互惠网络在发生变化。随着现代化带来的教育水平的提升、城镇化的进程、工业化的发展、社会流动性和政治参与的提高,传统社区的互惠网络已经不能满足人们之间的交往关系。社会网络更加复杂化,传统社区的单向关系向复合型关系发展,基于血缘和地域的社会关系网络渐次淡化,而基于职业的社会关系网络则成为人们交往的主要依据。传统社区之中精英和大众的分化是一种简单的“二分法”,即身份的简单化,而现在的社区身份结构之中,阶级阶层的意味越来越浓,这是一种现代社会分化的结果,也是一种现代的身份意识。传统社区权威结构是在一定的地域之内,而今必须超越地方的局限性,超越地方的认同,超越地方的权威,因为要构建一个更大规模的权威和认同结构。
三则,传统社区的族群意义在改变。从权力层面看,传统社区拥有自己的族群权威,在自己的地域内处置族群的事务,具有一种“自治”结构。权力结构在现代化的影响下在发生变化。一方面,外来权力结构在不断挑战传统的权力结构,传统社区的族群权威越来越难以保护本族群的权益,或者放弃传统的权威结构,或者与外来权力结构进行合作,不管采取何种措施,传统社区的族群权力结构在发生变迁;另一方面,超越地域结构的更高权力结构 (以民族国家的权力结构为代表)的出现。地方社区以族群权力结构为主,然而现代民族国家显然高于该权力结构,如何实现传统社区权力认同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认同,俨然成为传统社区族群意义转变的重要内容。从身份层面看,当人们审视传统社区的族群意义时,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是:“族群是社区的族群,还是国家的族群?”这里就包含着一个身份自我认定的过程,其关键之处在于族群在传统的社区中是主导力量,而在民族国家构建的过程中扮演何种角色,后者是一个更加复杂的过程。我们可以简单地予以界定:族群已经不仅仅是社区的族群,而是一个民族国家的族群。从利益层面看,传统社区族群利益体现在两个层面即族群利益和地方利益,二者又是相互作用、密不可分的。族群利益主要体现为族群生存利益和族群文化利益,前者关系到“种族”延续,后者关系到“族群”身份。地方利益主要是指社区的资源,包括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物质层面的利益危机最为重要。族群和地方社区的利益也在发生转换,即向一个新型的共同体——民族国家的利益转换。
二、资本内在逻辑导致民族身份的展现
现代资本的产生和发展是现代化的应有之意,其不仅推动了现代国家的构建,而且成为“族群”向“民族”身份转换的重要动力。现代资本之所以具有如此强大的能量,源于其内在的逻辑要求。
首先,现代资本的发展要求统一大市场,进而推动民族现代化。现代资本的发展必然要冲破传统小农经济设置的藩篱,原因在于现代资本追求的是一种自由的经济、平等的经济和人性的经济。所谓自由的经济意味着资本在其发展的过程中自由配置、畅行无阻,要求废除封建割据的状态。所谓平等的经济意味着资本主体是平等的,不存在任何高于资本的权威存在,而传统社会的权威往往高高在上,或者敌视资本力量,或者利用资本力量,已经不符合现代资本的发展要求。所谓人性的经济意味着“人”是资本的主体,人可以通过资本实现自我价值,当然物极必反,当资本成为人的追求和目的之时,人也开始“异化”为资本的工具。现代资本的本质属性要求建立统一的大市场,这又反过来对族群向民族转换提供了可能性,正如徐迅所言:“社会的经济联系复杂化是现代民族形成的决定性条件。”[3]16随着西方资本的进入,东南亚地区的民族资本在不断成长,虽然其成长的速度、模式、品质被扭曲,但是确实对于其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意义,因为,民族资本的成长为民族整合奠定了基础。
第二,现代资本要求自由劳动力。资本与劳动力是一对相互依存的存在:资本首先是一种所有权,强调财产自由权,资本所有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处置其资本。与资本所有权相对应的则是没有资本的劳动者,他们只能通过出卖劳动力赚取工资维持其生存和发展,正是在资本所有权的意义上形成了资本与劳动力的物化关系。资本对于现代社会而言,既是占据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又是占据主导地位的价值物。资本的此种社会经济地位的优势是相对于传统的农业和土地关系而言的,因此需要构建新型的资本关系,即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的关系,此种关系不断扩大化,导致社会结构的复合化。资本体现了一种现代制度结构,资本是市场的主导者,是市场交易的主体和市场规则的制定者。资本在经济链条中的制度作用还体现在资本要规范其主体与劳动者之间的关系。资本的“经济价值”必然反映在权力配置上,政治现代化的一个必然性就意味着政治体系必然反映经济分配的状态,也就必然反映资本与劳动力在权威制度结构中的状态。资本还是一种意识体现,传统社会的等级结构、神权结构、分封结构、土地结构所体现的是人的不平等:人往往是神权的附属者,人缺乏流动性,必须依附于一定的土地。现代资本倡导自由、平等、民主的理念,必然动摇传统的意识形态。正是在这些意义上,现代资本要求自由的劳动力,资本与劳动构成了现代社会的“双剑”。
当东南亚传统社会慢慢解体,以社区为中心的族群社会与现代资本所倡导的分工结构砰然相撞,族群内部结构性分化慢慢开始,这对于族群身份向民族身份的转换同样意义重大。族群内部结构分化体现为:族群内部阶级阶层分化,族群内精英越来越具有“国家”倾向;族群内部的社会流动性增强,特别是社区所赖以“自治”的土地关系开始分崩离析;资本对于自由劳动力的需要导致一种“自由、平等”的劳动者出现,虽然他们尚且是资本的服从者,但是却越来越具有“公民”身份,公民身份是族群向民族转换的内在需要和动力。
第三,现代资本要求现代化权威。现代资本超越地方权威结构,摒弃传统土地权威结构,代之以现代化权威结构。现代资本是在一定疆域内,并非无限发展的,现代资本必然为该疆域内的人们和权威服务,疆域也是现代民族国家基本的地理界线。现代资本的理念要求“人民”的主体地位,每个人都是作为公民存在,而不是传统社会的“臣民”和“村民”角色,人民、公民的角色又必然是与“民族”的身份联系在一起,因而现代资本要求现代民族权威的树立。现代资本体现了“国家主权”,只有为国家服务才是现代资本的内在发展要求,国家意义上的民族主义构成了现代资本发展的动力,反过来,现代资本又加强了国家意义上的民族主义。现代资本要求崭新的权威认同,即以民族主义为认同,而“民族主义将个体认同的本源定位于‘人民’之中,‘人民’被视为主权的持有者、效忠的主要对象和集体团结的基础。”[4]1从民族国家构建的4个基本要素,即疆域、人民、主权和认同,可以看出,现代资本所要求的现代化权威就是基于民族国家的权威,从而实现族群向民族身份的彻底转换。
三、主体族群与现代国家的领导权
族群差异是自然的,因历史记忆、文化符号、生活方式、宗教信仰之不同而千差万别。长期以来生活在同一地域的不同族群,虽间或有冲突,却基本上能维持各自的权力领域。在现代化冲击下,族群差异自然性却开始得以强化,原因在于族群差异在现代国家构建的过程中在领导地位、资本积累、价值取向、族群关系等方面出现了新的变化,直接影响到不同族群地位的差异性,导致族群身份危机的发生。东南亚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由于族群差异性繁复,族群地位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变动性使得族群身份危机表现得尤为明显。
不管从何种视角去审视东南亚地区,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菲律宾等由于族群状况相对复杂,族群关系一直存在折冲。在现代国家构建过程中,主体族群如何确定其领导权则成为关键之钥,因为这些国家出现了典型的“族群民族主义”和“领土民族主义”的结合。[1]235
首先,从领导地位看,主体族群扮演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基本领导力量。所谓主体族群往往是指在人口规模、历史传统、居住区域和权力结构中处于优势地位的族群。如泰国的泰族人占泰国全部人口的80%以上,泰族人在历史上一直是泰国的主体族群,泰族人居住在泰国的核心地区,而泰国传统的君主制度也是以泰族人的利益为至上的权力结构。泰族人之所以构成泰国现代化的领导者是由其主体族群的身份和地位所决定的。一方面,从历史传统看,泰族人始终是泰国的主导者,泰族人不仅占据权力的中心,掌握泰国最主要的资源,并且依靠佛教在价值导向上统驭泰国;另一方面也许更为重要,即泰族人在泰国现代化过程中始终以其代表者的形象出现。在西方强势面前,泰王室率先垂范力图改革,与西方殖民者进行合作,开放港口区域,主动应变,特别是朱拉隆功改革使得泰国免于殖民统治的厄运。1932年革命后的领导者皆为泰族人,他们都竭力革故求新推动泰国的现代化,甚至一度采取“泰化”政策。菲律宾的情况因其岛屿众多山川纵横而增添了诸多变项,而各地方言差异、地区本位主义、族群信仰有别,直到19世纪“共同的‘民族’特性开始发展,少数人开始把菲律宾作为一个整体……”[1]211菲律宾有90多个民族,其中马来族为主体民族,包括比萨扬人、他加禄人、伊洛克人、比科尔人等,其他少数民族包括棉兰老岛的马奴亚人、巴拉望岛的巴塔克人等。菲律宾的主体民族居住在地理条件相对优越的平原地带,即菲律宾北部与中部的河谷地带和沿海平原,在平原民族中,他加禄人成为佼佼者,也成为菲律宾在现代化过程中居于领导地位的一个族群。其他族群特别是山地族群和南方穆斯林族群则构成了被领导者。
其次,从资本积累看,主体族群构成了现代资本积累的主导者。主体族群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居于特殊的优势地位。一是主体族群社会经济条件优于其他族群,在传统社会主体族群就占据着该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态势相对优越的农业地区。由于东南亚地区资本发展的逻辑,农业所提供的原料和外汇是本国或地区资本积累的基础,因而农业地区成为资本积累的主战场。毫不夸张地说,谁能够控制农业地区,谁就能获得国内资本的控制权。印度尼西亚的爪哇族自古就控制着农业区,因而其在向现代资本转换过程中始终居于主导性的地位和优势。二是主体族群是国家或地区市场经济中的主体。市场构成了不同族群相互交往的主要空间,[5]73-74市场交往有助于形成共同的“民族意识”,更有助于在经济资源上占据优势的族群主导市场。此外,在西方殖民统治的影响下,主体族群的统治者往往与西方殖民者进行妥协与合作,因而对西方市场制度规则较为熟悉,这也是主体族群成为市场主导者的重要原因。三是主体族群构成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主体。主体族群无论在传统社会还是在现代社会相对于少数族群而言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方面都具有优势,如菲律宾的平原地带的民族,“平原民族社会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领先于较早期的社会经济形式的各种成分而居支配地位。这些民族居住的地区是大城市,亦即是哪些工业生产、政治和文化的中心。”[6]258
再次,从价值取向看,主体族群始终掌握着现代国家构建过程中的话语权。一则通过宗教信仰的方式整合族群关系。宗教信仰往往成为主体族群和少数族群文化符号的差异,主体族群将宗教信仰上升到现代国家整合的意义层面,如泰国一直宣扬“佛教、王权和民族”三位一体,而菲律宾则接受了基督教的信仰体系,印度尼西亚则是以伊斯兰教为主。二则通过彰显本国传统文化的方式宣扬民族性。东西方历史文化有别的观念成为现代化精英笃信的理念。虽然菲律宾在西班牙入侵之后就开始逐渐模糊东西方文化方面的差异,但是在其争取民族独立运动的过程中,不乏对马来族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人物进行广泛宣传。随着现代化深入和全球化的展开,东南亚地区日益对传统文化进行发掘和宣传。泰国的披汶政权追求统一国家和统一文化,旨在进一步提高民族国家的认同感和凝聚力。[7]86-87三则通过吸纳西方话语权的方式体现现代制度的优越性。东南亚在现代化进程中慢慢凸显出其“后发优势”。这些国家和地区不仅主动调整发展战略,引进西方先进的技术和理念,更着重于对西方制度的引介和吸收,将西方的制度形态与本国或本地区的实际协调在一起,从而奠定其权力、市场的制度基础。当然,制度移植总是要适应于国家的发展情势,制度改造往往使得东南亚地区的制度形态表现为“西方的制度,东方的价值”。四则民族主义的话语权。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具有根深蒂固的心理基础,此种心理基础存在于最广大的国民中,问题就在于由哪个民族和阶层担纲起民族主义的领导者。马克斯·韦伯给出了一个明确的答案:“经济政治领导阶层的特殊职能恰恰就是要成为民族政治意识的担纲者,事实上这是这些阶层存在的唯一政治理由。”[8]99经济政治领导阶层出自于主体族群,主体族群需承担起民族主义话语权的控制与运用。
第四,从族群关系看,主体族群政策变量是族群关系中的关键要素。有学者将东南亚地区的族群关系概括为“政治对立型”、“经济利益冲突型”、“文化碰撞型”。[9]4-9对于不同的族群,由于在现代化过程中所处的位置不同,必然会带来冲突和对抗,问题就在于居于国家权力领导位置的族群如何审视和对待其他少数族群,这里就有一个态度和政策的问题,而且必须从动态的视角进行分析。新加坡主要民族有华族、马来族、印度族和欧亚人,分别占新加坡人口的74.1%、13.4%、9.2%和1%。新加坡从其建国伊始就奉行多元种族政策,正如李光耀所言:“我们要保留多元种族,因为它是我国的财产。政府不会为大多数种族利益而牺牲少数种族利益。”①参见《联合早报》,1988年3月11日。在多元主义种族的制度设计中,新加坡的民族关系呈现为“公民型”关系。泰国面临南部穆斯林的挑战,一方面对分裂主义分子坚决予以镇压,另一方面则是通过经济改革给予南部穆斯林以实惠,但是泰国的族群政策倾向于领土的完整,因而仍然属于“领土型”关系。菲律宾不仅面临基督教与穆斯林的冲突,还面临着众多岛屿族群的经济要求,因为在菲律宾现代化的过程中,族群获得的利益好处存在严重的歧视,菲律宾的族群政策在一定意义上则是“种族型”关系。
总之,东南亚地区在近代以来面临着外部挑战的情况下,其传统的族群结构发生了彻底的改变,族群意义向民族意义转换,由此为民族国家的构建提供了前提。在与西方现代文明碰撞和吸收的过程中,东南亚地区的现代资本开始发轫,由此为民族意义注入了经济的根基,特别是资本所带来的市场统一为整体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奠定了基础。但是,东南亚地区族群众多的格局表明,尚需一个居于领导地位的民族站出来并领导国家之发展,而领导地位的民族则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诸多层面具有优势,这些优势赋予了领导地位的民族必须担当重责,但是,其态度、政策和价值又决定了东南亚地区现代国家的进一步发展。
[1]尼古拉斯·塔林﹒剑桥东南亚史:第二卷[M]﹒贺圣达,等,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
[2]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M]﹒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
[3]徐迅﹒民族主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4]里亚·格林菲尔德﹒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M]﹒王春华,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0.
[5]吴元黎﹒华人在东南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
[6]古小松﹒东南亚民族[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2006.
[7]周方冶﹒王权-威权-金权:泰国政治现代化进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8]马克斯·韦伯﹒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M]﹒甘阳,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
[9]韦红﹒东南亚五国民族问题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
ETHNIC IDENTITY,CAPITAL GOVERNANCE AND THE LEADERSHIP OF MODERN STATE——In the Perspective of Southeast Asia
Fu Jingliang
There are numerous ethnic groups in Southeast Asia.The relations among the ethnic groups are complicated.Which ethnic group commands the leadership of the state is a key issue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 state building.The expansion of the external modernity has created crisis to the existence and identities as well as social integration of ethnic groups in this area.The development of ethnic groups has become an urgent task.Under such a social context,the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value system and formation of institutions transform the ethnic identity to the national identity,providing the modern state with the national drive in its construction.The dominant ethnic groups are accidentally in the advantageous position in the process of ethnic social integration and modern capital governance.The demand for the leadership of the state is the scheme of this article.
Southeast Asia;ethnic identity;capital governance;modern state;leadership
【作 者】傅景亮,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讲师,北京大学博士,中央编译局博士后。北京,100081
D063
A
1004-454X(2013)04-0016-007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国跨境民族经济交往的政府治理研究”(12CZZ059)。
〔责任编辑:黄仲盈〕
- 广西民族研究的其它文章
- 《广西民族研究》2013年总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