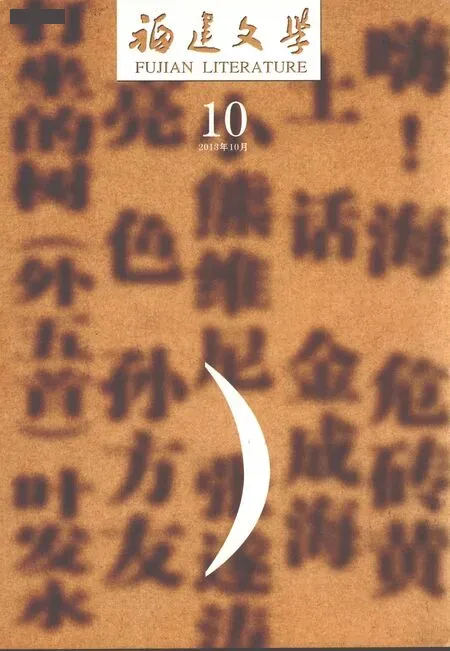关于爸爸的流水账
□林语尘

我有个这样的爹。
三十二岁当上爸爸。在产房外跟女儿说的第一句话是:“糟糕,怎么把我的塌鼻子给长上了!”
抱着婴儿期的我到处溜达,不停跟我说话,告诉我周围都是些什么植物。别人笑话说婴儿怎么听得懂,他毫不理会。有一天抱着我跑去河边散步,走着走着发现我睡着了,只好找一片芦苇丛蹲着避风,一边挨着蚊子咬,一边等我自然醒。
后来我知道日语里有个词语叫做“おやばか”(溺爱孩子的笨蛋父母)。不就是那时的他。
两岁前我的消化系统很弱,俗称“胃浅”,吃什么都易吐。他到处找偏方,买来鸡胗,自己挑出鸡内金晒干磨粉。逮田鼠、钓黄嘎、抓四脚蛇,细细剔干净骨头,给我熬粥。
至于缺钙、咳嗽,种种问题,都让他慢慢用各种食疗偏方治好。我能有今天的身高和体质,他功不可没。
他把古诗当儿歌教我背,笑话我分不清“bo”和“do”,还用一卷磁带录下了我背“鹅鹅鹅……红掌多清多”的证据。
我喜欢小动物,他就给我画手帕,一条是小鹿,一条是白兔,它们至今在我抽屉深处躺着。他也默许我乱涂乱画,用水彩笔把书房的墙壁搞得乱七八糟。
这些人生起点上的故事,都是后来的伏笔吧。
六岁以后,开始带我去钓鱼,专门做了个我能甩得动的小鱼竿。从浅水处钓上来很多小小的白条和泥鳅,拎回家炸得酥脆,给我当零食。偶尔野炊,拿河边的石头垒个灶,用搪瓷缸子煮螺肉和白菜。
后来我们搬到离河稍远的地方,不再经常钓鱼,改为每年三月到楼后的田野摘荠菜。他教我辨认家荠和野荠,择出鲜嫩的清炒,长老了的,就煮成碧绿的素汤。
他的朋友送给我一对文鸟,养在阳台,结果引来一群野生的白腰文鸟。在我软磨硬泡下,他做了个鲁迅先生的捕鸟设备——用一根连着线的筷子支起塑料篓子,底下撒了稻谷,我们俩捏着线头躲在屋里,像两个侦刺敌情的地下党,或者等敌人踩雷的土八路。前后共抓到二十多只,都养在大铁丝笼子里,还繁衍了一代小鸟。
笼子里鸟的密度太高,终于开始生病。他说日中则昃,月满则亏,教我把它们都放掉。——仿佛是开了个头,后来我捡回过从巢里掉出来的雏燕和白头翁,养过通人性的八哥,结局总是放走。在所有这些养鸟的故事里,他都是一边臭着脸抱怨麻烦,一边每天帮我捉虫喂鸟。燕子总在屋里乱飞,折腾得他跟着跑来跑去收拾,白头翁小时候最爱扯他脚趾头上的汗毛。那只八哥学会了叫他的名字,他也礼尚往来给它取名叫林肯。我不知道这些鸟之中,哪一只才是他最喜欢的。
年轻时候他还有很多隐士般的浪漫。每年春天,下班特地拐小路,折回来一两枝桃花,插在案头白瓷笔筒里。有时我赖在他们床上睡午觉,醒来会发现他跟妈妈在阳台上静静地下围棋。
九岁时,我还从柜子里翻出他早年写的古体诗词,翻出他和妈妈的各种小纪念物,比如结婚后一起回老家时,在海滩上捡的圆石子。比如一个铝制的椭圆形针头盒,里面放着妈妈帮他拔下的白发,和一把红豆。
十岁夏天,他买了台VCD机回家,每晚我拖着抓萤火虫的网子在外疯玩时,能听到他在家放老歌,《北国之春》接着《好汉歌》,《弯弯的月亮》之后是《少年壮志不言愁》。兴致来了还举着麦克跟唱——虽然五音不全跑调万里。
我们家一直保持着严母慈父的分工,淘气捣蛋被妈妈训了,总会憋着眼泪,等他来安慰一句就哇哇大哭。他真的极少对我发火,而一旦因为原则问题生起气来,总是非常吓人。但是,初中时我经历了一段失败的“早恋”,却是唯一一次,他非常生气,却没有训我。
中考后被他带回老家玩,看到了他出生的乡村,泥泞的小径,家家户户的莲雾和番石榴树,蔚蓝无垠的大海。我跟着他钓鱼、抓螃蟹,在广袤的滨海平原上看星空,感觉离他那百宝箱一样神秘的童年,稍稍近了一点。而了解一个人的童年,大概只算是深入了解这个人的开始。
再后来,我报了住宿制的高中。他很少来学校,但也曾在我错过周末校车时亲自跑来,跟我一起挤公交回家。高考时我还住在宿舍,他和妈妈也没有像多数家长一样来考场蹲点,只在考试当天很早的时候,来学校外面远远看了一眼。
报志愿的时候,同事跟他说了一套“生女儿就不能让她考外地学校”的理论。他听了回家当笑话讲。在我为选历史系还是新闻系犹豫时,他说我的性格已经足够闭门造车,别再皓首穷经跟社会越离越远。
大学离家太远,每逢假期回去,都是他下厨做饭,花样千变万化。就算早餐是普通的切片牛奶吐司,他也不嫌麻烦要用油煎一下让它变得美味。
我收集了很多种子,他就趁我不在偷偷把其中一些古怪的拿去种在花盆里。后来长出了两棵很不错的鳄梨、一棵黄皮,他就跟我炫耀:“你看我们家水土多好,还是回来吧!”
渐渐地,同事那套理论又经常被他在电话里提起,虽然还是讲笑话的语气,妈妈却在背后嘲笑他:“你爸老了。”
毕业了决定工作,刚开始还不会做饭。他跟妈妈趁暑假来住了一周,每天做家庭煮夫,教我如何料理食物。
回家的假期变得更短,于是他找各种机会来北京出差,专门到我的住处来视察,看我最近的画稿。每次见面,总说我瘦了。
前不久一起吃晚饭,喝了点酒,坐着聊天。他为了给我灌输“谈恋爱想太多也没用,未来的变数很大”这个道理,还向我揭秘了他的初恋史。后来我转述给妈妈,听她在电话那头笑得前仰后合。
在我写以上这些流水账的过程中,新的细节不断不断地从记忆里涌现出来。我觉得如果把跟他有关的故事统统写出来,至少需要一本书的厚度。那也就是我恋父情结的厚度。
他喜欢的东西,有那么多也变成了我喜欢的。植物,钓鱼,文字,北国之春。但是终究不能完全一样,不可能翻版,不可能重复他的人生,甚至也无法变成他人生的延续。
那句话怎么说——“儿子是时间给男人的一个不变的考验,考验他所看重的一切终究会被儿子视为愚蠢无稽,而且考验他在世上最爱的这个人,一定会对他有所误解。”
女儿或许稍微好些。但毕竟也会让他有些少年壮志无以继承的遗憾。我们还是有分歧,有代沟,会吵架,他有时也颇觉遗憾地感叹女孩子终究心比较小,女孩子到底不关心时势……以及女儿终究是羽翼长成就会飞走。
多年父女,到底是成了什么样的存在呢?但不管如何,那句很泛滥的话真是对的:世界上再不可能有哪个男人,像他这样待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