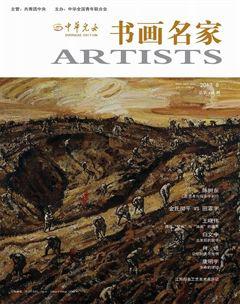金氏彻平 VS 田霏宇
主持语
田霏宇,UCCA馆长。金氏彻平,日本艺术家。一场名为“卓之物”的展览把二人联系在了一起。作为艺术家的金氏彻平擅长的创作方式就是在大量的收集日常物品的基础上,通过重构,再次赋予这些事物新的涵义和可能。作为策展人的田霏宇打破了传统对于艺术的认识,用后现代主义的眼光把金氏彻平的展览舞台移步到了中国,这是一次貌似偶然的碰撞,却为中国艺术界注入了一股新鲜气息。二人对于艺术观、创作方法、文化影响等都有各自独特的见解,有趣的对话就这样在他们之间展开了!
金氏彻平 艺术家
田霏宇 尤伦斯艺术中心馆长
田霏宇:我想先从你的展览的标题开始,最后选择叫“卓之物”,是不是可以从这里谈一下,这个展览中不同的作品和标题之间的关系。
金氏彻平:我确实经常使用一些日常的物品进行创作,除此之外我在创作的时候,除了这些大家看得到的东西,我还经常用一些你们肉眼看不见的东西,把这些东西堆放在一起形成一个巨大的作品,这是我对创作作品的一个基本理解。
我创建一件作品之前,就要收集材料。我在全球各个地方,各个国家都进行过创作,每到一个地方创作之前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收集材料。我之所以愿意到所在地方收集当地的材料,这里面有很有趣的事情,我通过收集材料,会了解这个国家当前所处的一个境况,以及这个国家所拥有的独特氛围,从我收集的这些材料当中,会去思考和我之间的关系性,从而自然的进行我的创作。这次我能够有机会在中国居住一个月进行创作,虽然是一个月,但是相对于这个展览的规模而言,其实还是很短的一个时间。但是中国的活力,中国这种快速的节奏,这种速度感给了我很大的灵感,使得我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这么大规模的一个展品。刚才田霏宇馆长也围绕我们这个展会介绍了一些背景,作为我本人来讲,中国和日本人的关系怎样,跟我是没有关系,我只是作为个人来到这里,在北京度过一个浓密相处时间,对于我来说是非常难得的。
田霏宇:作为民间的艺术机构,我们提倡这样一对一的交流,其实这跟国家的大背景是没有直接的关系。这个展览也不是日本基金会,也不是由官方机构来推行的。其实我最早知道他的作品是在2007年,他参加过《美丽新世界》。这应该是十年来最大的一次日本年轻艺术家在北京的一次展出。后来因为也经常看双年展的一些展会,每次都会遇到他的作品,每次印象都会更深刻。为了规划第一批展览,我去了一次京都,他在京都的美术学院做了很多年的老师。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学生在准备他们的毕业作品,他在那儿一边指导他们创作,一边跟我们谈论这次展览怎么做。我们决定找到了一个合适的时候,让他过来待一段时间,在这里把材料找到把作品做出来,然后展出。他最被人知道的一件作品,除此之外他还在这儿做了其他方面的创作,包括影像,也包括白地图系列,也包括一些新的拼贴。因为他最早是雕塑家,但是现在也开始做很多二维的东西。我想这是不是可以对整个展览的概念说几句。
金氏彻平:是的,关于这个问题可能会和这次展会“卓之物”这个标题会有所重叠。它是在一个虚空环境里的想象,可以说是对假象空间进行想象,“重力”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我也会使用很多漫画里的概念,一些相关的要素收集在一起。然后打破它们原有存在的方式,超越上下连续的关系,把它们连在一起,这是我的一个基本考虑,它和白色释放是一模一样的,这是我的一个基本考虑,它们是各自有各自的用途,但最终是作为一个巨大的整合体出现在所有人面前。它是一个不具备任何意义的巨大雕刻,以这样的形式得以呈现的。
田霏宇:日本有那么多的艺术家,为什么我们选择做他的个展。现在日本当代艺术、前卫艺术也在被反复重新探索,被具体运用。他们留下一个美术史的主张:就是对物本身的一个探索,对物品的一种特殊属性和特殊的兴趣。接下来可能就是对于本地问题,并且对亚洲及其他地区产生影响,启发了很多人。出现了两个主要的潮流,一个是50年代末,一个是90年代到2000年初。他的作品也不是很刻意,但是这两个潮流的一些痕迹,都反映在他的作品中,等于把这两个因素相结合,做出一个新的艺术世界。这个如果要去写文章的话,肯定要有很多阐述,但是在今天,他做出一个特别有趣、有效的回答,对于我们现在不仅仅是日本,甚至整个世界当代艺术所面临的问题都是很有意义的。“卓之物”这个展览,如果是对物和结构的探索和解读,比如针对什么印象,如果放大一点是对中国的还是日本的,还是小到某一个城市或者您对家乡的反映,还是您到北京的一个阅历?从一开始创作到完成有什么样的变化,是一开始就有灵感直到完成创作吗,这期间您最大的一个变化是什么?
金氏彻平:针对什么现象是很困难的,因为它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所以才采用作品这个形式,它不是某一个日本的现象,中国的一个现象或者我家乡的一个任何现象,它是“存在的东西”,你是纯粹存在的,你是用肉眼看不到的,但是它是任何地方都会充斥着的东西,如果用语言来表达,它就是这样一种状态。如果专业来说,它也是美术当中的一个现象,也是我们生活中的一种现象。总之,它是没有办法用语言来表达的一种东西,因此它可能是包含许多意义的东西,正是因为有这样一种无形的东西,我通过形状把它表现出来。但是我赋予每一种形状去解释它,去承载它的份量有多种,这就是我想要去做的事情。还有我要说我在中国待了一个月有什么变化?那就是我作品的大小,它的尺寸远远超过我来的时候的想象,另外我要创作的作品数量也超出我的想象,至少多出了一倍,之所以发生这样的变化,也是来自于北京这个城市本身所给我带来的影响。
田霏宇:你在刚才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你更希望用有形的东西去表达无形的观念。我们看到你的作品中所用到的材料,都是可以在任何商场买到的日用品,有一个潜在的消费观念会在您的作品当中,而且在其他日本艺术家的作品当中也可以看到这种很干净,很消费化的东西出现。我想问一下,这种很明显的作品消费行为,对您的影响在哪一块?它是不是成为了日本当代艺术潜在的一个主流现象?
金氏彻平:确实!这个世界你怎么样去表达它?我想其中的一种方法之一,就是去购买一些东西。也就是你说的这种消费形式来购买我所需要的这些材料。也许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确实如你所说,消费创作,有一个潜在消费意识在里面。你所问的问题,是创作当中出现的问题,比如你做一件使用了铁雕刻的作品,或者你用木头去雕刻,同样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也就是你先要去购买铁、购买木头才能去创作。虽然我使用常见的物件去创作,在全世界都可以看到,而不是在日本才可以有的,在过去很常一段时间我都在用这种方法。这样做的好处是,不管在什么地方,集到的材料能够很真实的反映,那段时间、那个空间、那个地方所有的一些真实状态。
田霏宇:我想问问你在日本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工作方法吗?
金氏彻平:不管去哪里完成作品的做法都是一样的。但我的作品是从收集材料开始的,在不同的城市,我收集来的材料不同作品就不一样。这次在中国的作品也是用同样的方法,材料都是在中国买的。
田霏宇:在中国买东西开心吧?
金氏彻平:特别开心,因为中国的东西很便宜,种类又很多,有很多新的发现。
田霏宇:有什么新的发现?
金氏彻平:在中国特别有意思的是可以找到世界各地的东西,除此之外,中国还有一些自己特别的东西,别的地方找不到。
田霏宇:你组合这些不同的东西有没有一个规则和原则?
金氏彻平:在选择这些作品的一个简单规则就是,比如说在这边的大型堆积物,所选的材料都是容易堆积的。太重的不适合堆在上面,还有的形状适合做柱子,一些适合做樑,我就用这种感觉把这些堆在一起,不管它是什么材质,什么物件,只要在物理上适合堆积我就会一直往上堆。但是这些日常生活用品在堆积过程中会产生新的功用,比如这个瓶子在被我用作柱子的时候就会产生新的功用。在这过程中这些物品我们熟悉的日常功用会产生变化,比如这个被用作柱子的瓶子有一瞬间看起来特别巨大,产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一瞬间我的作品就成型了,它就是一件作品了!我在乎的是原来这个物品在变成一个平常不熟悉的形象或观念的时候,你还可以看出它是什么东西,你还可以看出它是一个矿泉水瓶,但是在作品里又产生了很奇妙的变化,在两边都可能,“不安定的临界变化”就是它们成为我作品的时候。
田霏宇:刚才有一句我没听懂,特别大是什么意思?是看起来特别大的一个东西吗?
金氏彻平:在堆积的过程中不仅仅只有一个瓶子,它周围还有其他的堆积物。在过程中这个瓶子可能会看起来像是一个大物件的模型,比如说宫殿,柱子,可能是这种东西或者别的,那个时候它就是我的作品了。
田霏宇:你选择很日常的东西做作品,但在选择材料的态度上是否也有自己独到的考虑。
金氏彻平:其实我选材料没有特别的讲究,尽量选择多的种类,尽量有多的可能性,让他们能发挥尽量多的功能,把它们放在一起。我作品里除了日常用品还有很多建材,主要用的时候看看怎么好用。在做作品的时候,虽然我都是取自生活中普通物件,但是把它们放到一个不可名状的空间,一个非日常的空间或者说一个零的空间去展示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作品在家里或在展厅展示最终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当然有时候受具体场地限制,只能在展厅创作,但是最好将创作的空间和展示的空间分开。
田霏宇:你做作品经常是这样堆起来的。
金氏彻平:对我来说,尽管是同样的动作不停地重复,但每一次也在不同的地方。空间的样子、大小不一样,使用的材料不一样,所以做出来的作品就会不一样。还有一点,我每次根据现场的具体情况堆着试试看,最后呈现出一个让自己特别惊讶的东西,有一种“自己”和“自己作品”突然相遇的感觉。
田霏宇:你的作品对观众控制是比较强的,你怎么对待这个问题?
金氏彻平:我确实没有考虑完成作品时要和观众有直接的交流,我还是希望通过作品和观众交流。
田霏宇:我觉得不同的事物都有不同的阶级性在里面。我想问一下,你在中国这段创作期间,“阶层”和“阶级”是否也是你创作的一个切入视角?
金氏彻平:关于您所问的是否存在阶级的概念在里面,确实我所使用的材料包含各式各样的东西在里面,这些作品各不相同,有的是很贵的东西,有的很便宜,甚至有一些很垃圾的东西都包含在里面,从阶级的角度分析可以有这样的一些区别,显而易见。比如我的一个作品《白色释放》,它就是把很多的东西堆放在一起,都是白色的,最后用一些白色的树脂浇铸在上面,只是为了这个作品更统一而存在,就是说这些作品的存在,能够使这些作品堆的更高一些,当它达到某种意义而又没有任何意义的时候,才具有了一种“存在”的意义。因此我又赋予了所有这些东西一种不一样的意义,从这个角度来讲,所有的东西都是平等的,我对所使用到的材料都是平等的对待。还有《白地图》这件作品,当中也是白白高高的树脂粉喷在上面,放在桌子上面。通过给它喷射这样的粉末之后,所有的东西都平等的相连了,可以说达到了这样一个目的。之所以我开始想创作《白地图》,是和我所居住的城市有关系。有一天下雪了,我突然得到了这个灵感。我所居住的城市每年要下一次雪,有一天下雪后我发现所有的东西都相连在一起,而且都变得不一样,它的形状、它的规模都是白白连在一起。在我眼前的景象当时仿佛一台很高的车,旁边有一个小狗拉了一堆屎,这些所有东西都连在一起成为了一个形状,而且这些东西非常漂亮。它们本身是没有意义的形状,但是经过白色覆盖后就出现很有意义的形状在大家面前。包括在走廊里看到那幅作品,墙上有很多线条连在一起,这线是让小孩子涂颜色留下来的线,有的是绘制地图当中留下来的线,它们都是不一样的线,我把本身不具备任何作用、没有任何意义的线,仅仅只当做线来看待,并把它仅仅作为线连在一起,以达到本身没有意义的作品意义,就成就了一个作品。
田霏宇:谈到这里,我觉得还是亲自去欣赏一下你的作品比较有说服力,和你的谈话开启了当代艺术的另一个话题和思考。非常感谢!
金氏彻平:我也很高兴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在中国办展览,也希望可以多进行这样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