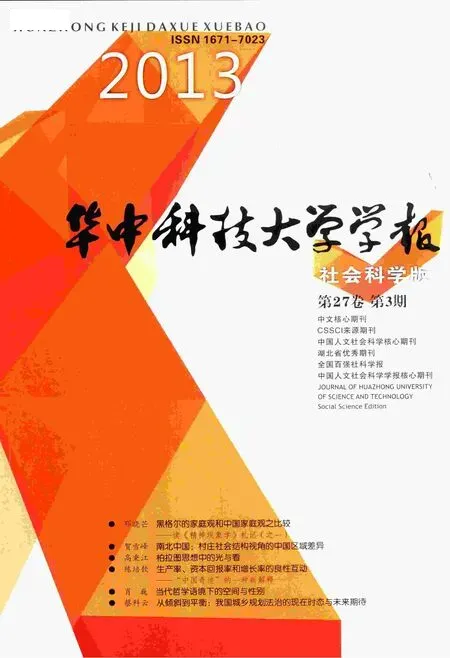意愿与行为的悖离:农村社区小型水利设施农户合作意愿及合作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
王格玲,陆迁,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陕西 杨凌712100
一、引言
农村基础设施是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先行资本”,对改造传统农业、消除农村贫困、提高农民的社会福利水平具有重大作用。但我国农村基础设施长期处于供给不足、结构失衡、效率低下的状况,已成为制约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巨大障碍。从一些实地调研来看,农村基础设施的确能够通过农户合作来自发供给,但也有许多村依托村民合作供给基础设施困难重重。
农村社区小型水利设施合作供给是众多单个农户行为选择的结果。小型水利设施参与行为不仅是主体对各种因素判断、权衡成本-效用后的决定,而且受社会环境约束,具体的参与行为是合作意愿与社会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政治、经济、文化都会对合作意愿及支付行为产生影响[1]。在具体社会环境中,各综合性因素对合作意愿与参与行为所起的作用是有差异的,但在这一过程中,哪些因素将影响农户的合作意愿?哪些因素将影响农户的支付行为?农户具有明确的合作意愿为何最终并没有形成具体的支付行为?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合作意愿与支付行为的悖离?这是实现农村社区小型水利设施合作供给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但是,目前关于合作意愿与支付行为的研究缺乏统一的和更深入的理论分析框架[2],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尚未形成一致性结论[3],对合作供给过程中农户的合作意愿与支付行为之间的关系依然缺乏细致的实证研究。因此,本文根据对陕西省关中地区393 户农户的问卷调查,对农村社区小型水利设施合作意愿、支付行为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重点探讨导致合作意愿与支付行为偏离的原因,寻求集体行动实现的有效途径,为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提供决策参考依据。
二、文献回顾
传统经济学认为公共物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存在市场失灵,政府应该提供众多类型的公共产品。随着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缺陷日益暴露,许多经济学家把研究重点转移到非政府供给领域,在公共产品市场化供给和多元化供给上取得了许多创新性的成果。英国学者Kranuze(2000)认为公共物品供给存在低效率、短缺和质量低下等诸多公共生产所存在的弊端,强调通过私有化解决公共物品供给问题。随着新公共服务理论研究的兴起,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讨论公共产品多元化的供给模式(Zhang,2005),学者对公私伙伴关系(PPP 模式)给予了特别的关注,研究了PPP 模式中政府和私营部门利益均衡、融资以及政府补贴等问题(Abdel,2007;Brandao,2008)。萨缪尔森、林达尔等众多学者对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条件进行了分析。萨缪尔森认为个人消费边际替代率的总和等于公共产品边际转换率是一般均衡状态下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条件,但鉴于其模型高度抽象,适应条件过于苛刻,难以与实际经济相联系。
国内对农村基础设施供给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我国农村基础设施供给制度障碍分析,二是对农村基础设施供给的创新设计。黄祖辉等对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研究做了全面综述,指出了此领域有待进一步深化研究的方向[4]。从制度层面来讲,我国农村基础设施供给面临着偏好表达机制扭曲、问责机制不健全、乡镇财权事权不对称和建设经济机制不合理等内在制度机理困境,其本质是制度变迁所导致的农民“沙化现象”,农民合作意愿缺失。郑凤田等指出在农村基础设施制度变迁过程,面临“双重两难”困境,既存在着计划与市场的双重失灵,也存在着“政府主导”与“农民主体”之间的矛盾[5]。毛寿龙等认为,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搭便车行为的影响、社会资本的制约,导致农民自主治理能力的欠缺和合作的困境[6]。为了走出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集体行动困境,学者对不同的行为主体进行分析并给出解决方案,组织成员结构应该存在差异性、组织成员间存在合理的利益共享、成本分摊机制和组织受益存在超可加性是走出农村公共物品供给集体行动困境的主要条件[7]。从农民行动逻辑的角度,农户行为主要受私利的驱使[8];而就制度环境而言,通过实施“有偿”供给、重构乡村社会资本、政府财政介入、构建小集团供给模式等是走出村庄公共物品供给困境的可能选择[9]。此外,坚持农民的主体地位,重视声誉等非经济诱因的作用,“由农户自愿供给农村社区内的公共物品会是一个有效的结果”[10]106-109。国内对集体行动关系的研究尚处于引介阶段。集体行动能否实现主要取决于偏好异质性,即个体偏好对集体行动均衡的影响,由于人们自身存在各种层次的异质性以及不同群体中存在个体间的交互作用,集体行动结果可能存在多重均衡或者均衡不稳定[2]。学者主要是采用国外的典型博弈模型,讨论“异质性U型曲线”,考察个体偏好差异以及个体决策时知识结构的偏差对公共物品自发供给的影响,但结论的可靠性仍需进一步验证[3]。
总体来看,国内外相关研究主要理论与实践,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研究主要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方式、治理方式、机制与投资效率展开进行定性分析,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其理论和方法对我们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但现有研究主要以理论分析为主,实证研究不足。强调得更多的是激励制度的构建以及分析农民的合作意愿,鲜见从集体行动视角分析合作意愿与合作行为悖离的文献。因此,本文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运用Heckman-Probit 模型,基于农户合作意愿与合作行为悖离的现实,研究农村小型水利设施合作供给集体行动的实现问题,对合作意愿和合作行为二者之间的差异及影响因素作探索性研究,以寻求农村小型水利设施合作供给的有效政策途径及解决方案。
三、研究方法、数据来源与变量选择
(一)研究方法
农户对小型水利设施的合作供给决策有两个过程,首先是农户对小型水利设施合作供给的感知,即合作的意愿;其次,才是农户对是否合作做出适应性应对决策,即合作行为。本质上,合作行为是农户对合作意愿的一种选择行为,因此,可采用Heckman-Probit 两步模型分析。第一阶段,识别影响农户合作感知概率的因素;第二阶段,对于具有合作意愿的农户,考察其具体参与行为的概率及影响因素。
(1)第一阶段,关于农户小型水利设施合作意愿的影响因素,模型如下:
式中,因变量P为农户的合作意愿。为了得到农户对是否合作的态度,问卷中设计的问题为“如果有人提出建设小型水利设施,您是否愿意参与”,如果回答是,其因变量取值为“1”,否则为“0”。G(* )是累积分布函数,x1,x2,x3,x4,…,xn等是m个影响农户合作意愿的因素,βx为自变量合作意愿xm的系数。
(2)第二阶段,关于农户小型水利设施支付行为的影响因素,模型如下:

式中,因变量为潜在变量。为了得到农户支付行为的相关信息,问卷在假设农户具有合作意愿的基础上,设计了如下问题:“如果您愿意参与小型水利设施建设,是否已支付小型水利设施建设费用?”如果回答是,则其值为“1”,否则为“0”,x1,x2,x3,x4,…,xk等是k个农户支付行为的影响因素,αk为支付行为影响因素的系数,ε 是随机误差项。
(二)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
所用数据来源于课题组2012年2月和2012年6月的实地问卷调查及村委会主任等相关人员的访谈。调查区域涉及陕西省关中地区实施小型水利设施工程的8 个县。调查对象是16-75 周岁、没有交流困难并积极配合调查的农民。调研采取多阶段随机走访的方式进行,采用分层抽样调查方法,每个县按照经济发展水平随机选取3 个乡镇,每个乡镇随机选取3 个自然村,再在每个抽样的自然村中随机选取10-12 个农户进行调查及访谈。调查内容包括农户基本特征、农业生产情况、政府投入、农户认知、社区环境以及农户参与小型农田水利建设意愿情况(包括农户是否具有小型水利设施合作供给意愿?若愿意参与,是否有具体的参与行为,参与行为受哪些因素的影响)。此次调查共获得有效问卷393 份,样本有效率为90.2%。

表1 调查农户基本特征
1.村庄基本特征。村庄以拥有小型水利设施或实施小型水利设施建设的村庄为主。
2.农户基本特征(见表1)。调查对象具有以下特征:以女性为主,占50.8%;以中青年人为主,年龄分布呈现正态分布趋势;以初中文化程度为主,占42.5%,小学占38.4%,高中及以上的仅占11.5%;多以3—5 人的中小型家庭为主,占76.8%;有6%是村干部,10.5%是党员;89.2 %的农户从事农业生产。
(三)变量选取
本研究选取了以下5 大类共12 个自变量,即农户基本特征(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农业生产情况(种植面积、从事农业生产的年限)、制度因素(政府粮食补贴)、农户认知(小型水利设施对农业生产重要性、是否清楚小型水利的资金使用情况、对现有灌溉设施服务的满意度、收入变化)、社区环境(小型水利维修情况、是否经常发生用水纠纷),因变量选择了农户小型水利设施合作供给意愿以及合作行为,其变量定义、统计性描述及其预期作用方向见表2。在农户选择是否具有小型水利设施合作供给参与意愿的情况下,由于参与意愿主要受农户的个人特征、农户的家庭特征和政府对小型农田水利建设投入情况的影响,因此,在第一阶段农户小型水利设施合作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模型中,选取变量不考虑变量x8和x10;而在第二阶段农户小型水利设施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模型中,小型水利设施资金使用情况与收入变化是影响农户支付意愿的主要考虑因素,因此第二阶段考虑所有变量。
1.农户基本特征方面。选取农户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三个变量来反映其基本特征。与女性相比,男性对水利的知识了解更多,其合作供给意愿更强。农民年龄越轻,接受新生事物的能力越强,而农户的年龄越大,安于现状的心理越强,合作供给意愿越弱。农户受教育程度越高,越能充分意识到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的重要性,收入也可能越高,从而参与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合作供给的意愿可能越强。由于在具体的投入行为中,农民文化程度越高,越有可能进行兼业或从事其他非农经营活动,因而其参与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合作供给意愿的可能性就越低,因此,受教育程度的影响方向不确定。

表2 变量说明和统计性描述
2.农业生产情况。选取种植面积与从事农业生产年限来反映农业生产情况。农户种植面积越大,对小型水利设施合作供给的需求越旺盛,其合作供给意愿也越强。从事农业生产的年限越长,对农业知识了解越深入,其合作供给意愿也越强烈。
3.政府投入。选取政府粮食补贴来反映政府投入情况。农户之所以对小型水利设施具有需求,是由于农业生产可获得收益,从而引致农户对水利投入要素的需求,小型水利设施这种派生性需求的特点,意味着政府对粮食补贴的资金越多,农户从经营农业中获得更高收益,农户种植积极性就会越高,农户对小型水利需求越大,从而提高农户小型水利合作供给的参与意愿与参与行为。
4.农户认知。选取水利设施对农业生产的重要性、小型水利设施资金使用情况、对现有灌溉设施的满意度、收入变化四个变量来反映农户参与小型水利设施合作供给的心理认知状况。农户认为小型水利设施对农业生产越重要,其合作供给意愿就越强。小型水利设施建设与运行的资金使用越公开和透明,农户的合作供给意愿越强,从而进行参与合作供给行动。预期对现有灌溉设施满意度越高,参与小型水利设施合作供给的可能性越大;预期使用水利设施灌溉后,如果使农业收入有明显增加,则农户的合作供给意愿越强。
5.社区环境。选取小型水利设施维修情况以及是否经常发生用水纠纷来反映农户参与小型水利设施合作供给的社区环境。小型水利设施属于准公共产品中的俱乐部产品,排他性比较强,存在着“选择性进入”方式,因此水利设施供给的社区环境是影响农户合作供给的重要因素。
四、模型估计结果与分析
根据所获得的调查数据,采用SPSS16.0 统计软件对农户参与小型农田水利建设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回归结果见表3。由表3 可知,模型的总体效果显著,模型整体拟合效果良好,回归分析所得结果可以作为分析和判断各影响因素作用方向和作用大小的依据,解释变量的作用方向也基本符合预期。

表3 农户对农村小型水利设施合作供给意愿的分析结果
(一)农户基本特征对其参与小型水利设施合作供给的影响
1.农户受教育程度对农户小型水利设施合作供给参与意愿与参与行为都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农户受教育程度在第一阶段决策模型中通过了5%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其系数为负,表明农民文化程度越高,其参与小型农田水利建设的意愿越弱。其主要原因是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户,越有可能获得其他正规的非农就业机会和渠道,从而得到更高的收入。因此,参与小型水利设施合作供给的意愿缺乏(Baland and Platteau 1996)[11]。在第二阶段决策模型中,农民文化程度这一变量通过了5%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表明文化程度的提高降低了农户的参与行为,这一结果与Johnson et al.[12]的研究结论相一致。农户受教育程度虽然弱化了农户自愿合作供给动因,是导致集体行动失败的主要因素,但是,对农户合作供给的参与意愿与支付行为具有同向作用,因此教育程度因素并不是导致农户参与意愿与参与行为悖离的原因。
2.农户年龄在第一阶段模型中影响不显著,虽然不具有统计学上的意义,但从经济学含义来讲,农户具有正的参与意愿。在第二阶段决策模型中,农户年龄变量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影响方向与预测影响方向一致,呈负相关。模型系数为-0.1033,表明农户年龄每增加一岁,其具体支付行为将会下降10.33%。由此可以看出,年龄是导致农户参与意愿与参与行为悖离的原因之一。纵向比较发现,随着农户年龄的增大,实际参与数大于意愿参与数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反映出年龄较大的农户更倾向于采用传统的方式或根据自己的经验从事农业生产,新生事物的接受能力较差,对小型水利设施合作供给支付行为的可能性降低。这一结论得到Hugo Storm[13]的证实。
(二)农业生产情况对农户参与小型水利设施合作供给的影响
1.种植面积对农户小型水利设施合作供给参与意愿没有显著影响,但对小型水利设施合作行为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在第二阶段决策模型中,灌溉面积通过了5%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其系数为负,表明随着种植面积的增加,农户参与小型农田水利建设的行为逐渐减弱,因此,种植面积是导致农户合作意愿与合作行为悖离的主要因素。主要原因是拥有较多耕地的农户虽然有参与小型水利设施合作供给的意愿,但从成本收益角度考虑,更倾向于采用自有灌溉设施而非与人合作的方式来降低成本,从而实现“规模经济”。因此,其他灌溉方式的存在给农户以“选择退出”的可能,从而降低农户参与集体行动的可能性[14]。Wang 的研究也证实了上述研究结果。研究发现,拥有私有水井与耕地面积显著正相关[15]54-84。
2.从事农业生产年限在第一阶段模型中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而在第二阶段决策模型中,变量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影响方向与预测方向一致,呈正相关。显然,从事农业生产年限是影响农户合作意愿与合作行为悖离的主要因素之一。原因是农业生产年限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户的种植经验,从事农业生产年限越长的农户愈希望通过自己的种植经验来进行农作物播种、灌溉等农业生产行为,但农户作为“学习人”,通过观察其他参与小型水利设施合作供给农户,证实小型水利设施合作供给更有利于农产品产量的提高以及成本的降低,从而采用“用钱投票”的方式证明了合作灌溉的有效性。
(三)政府投入情况对农户参与小型水利设施合作供给的影响
政府投入变量通过第二阶段模型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政府投入每增加1%,农户小型水利设施合作行为可能性将会增加0.37%。而政府投入对农户的合作意愿影响不显著。因此,政府投入情况是农户合作意愿与合作行为悖离的主要因素之一。研究结果表明,政府政策支持对农户小型水利设施合作意愿的激励作用并不明显,但从具体的参与行为来讲,农户期望立竿见影的效益,只有看得见摸得着的利益才能驱使他们参与进来,而过长的预期对于他们的参与意愿是缺乏吸引力的,因此,对于政府投入,农户从行为上给予积极响应。
(四)农户认知程度对其参与小型水利设施合作供给的影响
1.小型水利对农业生产的重要性影响方向与预测方向一致,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呈正相关,表明农户认为小型水利越重要,其合作供给的意愿越强。统计调查显示,认为农村社区小型水利设施非常重要和比较重要的比例为90.2%,比较不重要和非常不重要的比例仅占2.2%。但是参加小型水利合作的农户比例为58%,主要原因是小型水利合作供给的实施需要投入相应的资金、人力与物力,它的重要性虽然被大家一致认可,其合作意愿虽然较高,但合作行为却因为种种限制无法实现,参与比例有所下降。
2.小型水利设施资金使用状况的影响方向与预测方向一致,呈正相关,其系数为0.0804,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表明小型水利设施资金使用情况是农户参与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资金使用情况的公开与透明不仅解答了农户对资金使用效率的疑问,更增加了农户参与的积极性与主体意识,使小型水利设施的使用情况更符合农民的意愿,促使小型水利设施的合作供给更有效率,资金使用情况更加合理、公正。
3.收入变化在第二阶段决策模型中影响显著,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其影响方向与预测方向一致,呈正相关,其系数为0.1222,表明收入增加是农户参与行为的主要推动力,收入改善能有效推动农户的参与行为。
以上三个因素的分析结果表明,农户对事物的认知程度直接或间接影响其选择偏好和意愿,农户小型水利设施的参与意愿必定受其在小型水利设施合作方面心理认知状况的影响。具体的参与行为却受到除农户认知外的硬约束,如资金的使用、收入的变化等,从而导致合作意愿与合作行为的悖离。
(五)社区环境因素对农户参与小型水利设施合作供给的影响
在第一阶段模型中,用水纠纷是影响农户小型水利设施合作意愿的关键因素,系数为0.3722,在1%的水平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其影响方向与预测方向一致,呈正相关。在第二阶段决策模型中,用水纠纷对农户小型水利设施合作供给参与行为影响不显著。因此,用水纠纷是导致合作意愿与合作行为差异的主要因素之一。实际调查发现,用水纠纷是农田灌溉中经常发生的冲突,水权的不确定导致农户在自发灌溉中的利益冲突比比皆是。因此,农户更倾向于通过合作供给的方式处理纠纷与冲突,显示了小型水利设施合作供给制度安排的优越性,具体的制度实施过程也表明,小型水利设施合作供给是解决用水纠纷的有效方案,根据农户访谈结果,灌溉的排序与灌溉量的多少每个村都有特定的规则,如根据缴纳水费的时间早晚排序,按土地面积缴纳水费等,较好地解决了用水纠纷问题。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以陕西省关中地区393 户农户为调查样本,建立Heckman-Probit 模型实证分析农户小型水利设施合作意愿与合作行为悖离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农户的参与行为与参与意愿有较强的相关关系,但较高的合作意愿并不必然导致最终的参与行为。农户的合作意愿主要受农户个人特征、农户认知情况以及社区环境的影响;而小型水利设施合作供给中具体的参与行为能否实现,更多地取决于心理认知状况、政策因素、农业生产情况等。农户参与具体小型水利合作行为不仅受客观环境的制约,而且受到相互间依存和信任关系等心理认知的影响,导致农户小型水利设施合作意愿与合作行为的悖离。为促使小型水利设施合作供给集体行动的实现,应着力从以下几点入手。
1.完善小型水利设施合作供给机制。按照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强化对农田水利的政策扶持,加大对水利建设的投入力度。在农村小型水利设施供给上,以统一规划、尊重民意为前提,以财政补助为引导,以农民、农民用水合作组织、村组和基层水管单位为载体,加强政府的引导作用,使农民由被动建设转变为农民自主建设,实证研究也表明,农户认知程度的提高可以增加小型水利设施的合作供给意愿,提升合作供给效率,促进农田水利建设步入“农民自愿投入、政府给予补助、明晰产权归属、落实管护责任、实现良性发展”的轨道。
2.加强资金和项目科学管理。由于农村公共物品提供过程中的暗箱操作、水权不明确和利益夹杂等因素,导致农户对参与农村小型水利建设存有疑虑,合作供给的意愿虽然较高,但由于在具体操作中存在资金使用不透明、水权不确定等问题,最终导致集体行动失败。这一问题正好解释了合作意愿与合作行为悖离的原因。调查显示,参与机制越完善,资金管理透明度越高,管理机制越公开、民主,农户越能在农村公共物品提供过程中表达意愿和需求,农村公共物品合作供给的可能性就越大。因此,在农村小型水利设施合作供给中,应以公开透明的资金管理制度为基础,加强对项目的科学管理,明确水权,使参与农户充分了解小型水利设施项目资金的使用情况,产权界定合理,项目的运转执行得到有效监督,形成良性运转机制。
3.重视农户合作意愿对合作供给的影响。公用物品供给要遵循的第一准则是自下而上确定需求,满足千百万农户的生产生活需要,在此基础上,通过政策的自上而下统一执行,实现农户的合作意愿。完善农村公共物品的合作供给,需要考虑农户异质性因素导致的不同类型农户对小型水利设施的需求情况各不相同,农村公共物品的合作供给应满足不同收入水平农户及不同类型农户的意愿,增强其对合作供给重要性的认知,明确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优先次序,通过加强政策宣传,使更多农民理解政策的背景和意图,提高农户满意度,从而增强其合作意愿,减少合作意愿和合作行为的悖离。
[1]Das Gupta,Monica,H.Grandvoinnet,M.Romani.2004.“Sate-Community Synergies in Community-Driven Development.”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40 (3).
[2]彭长生、孟令杰:《异质性偏好与集体行动的均衡:一个理论分析框架》,载《南开经济研究》2007年第6期。
[3]宋妍、朱宪辰:《异质性U 型曲线假说成立吗?一种替代性说法》,载《管理工程学报》2009年第3 期。
[4]黄祖辉、游旭平:《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的研究综述》,载自网络[EB/OL].http://happy257.bo kee.com /4395677.html,2006-02-07。
[5]郑风田、董筱丹、温铁军:《农村基础设施投资体系改革的“双重两难”》,载《贵州社会科学》2010年第7期。
[6]毛寿龙、杨志云:《无政府状态、合作的困境与农村灌溉制度分析——荆门市沙洋县高阳镇村组农业用水供给模式的个案研究》,载《理论探讨》2010年第2期。
[7]张明林、吉宏:《集体行动与农业合作组织的合作条件》,载《企业经济》2005年第8 期。
[8]贺雪峰、罗兴佐:《论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中的均衡》,载《经济学家》2006年第1 期。
[9]陈潭、刘建义:《集体行动、利益博弈与村庄公共物品供给》,载《公共管理学报》2010年第3 期。
[10]符加林、崔浩、黄晓红:《农村社区公共物品的农户自愿供给——基于声誉理论的分析》,载《经济经纬》2007年第4 期。
[11]Baland,Jean-Marie,and Jean-Philippe Platteau.Halting Degrad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Is There a Role for Rural Communities,New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
[12]Johnson,N.,Evangelinos,I.K.,Iosifides,T.,Halvadakis,P.C.,Sophoulis,C.M..“Social factors influencing perceptions and willingness to pay for a marketbased policyaiming on solid waste management”,Resources,Conservation and Recycling,2010,54 (9).
[13]Frederic Gaspart,Jean-Philippe Platteau.“Heterogeneity and collective action for effort regulation”,Lessons from the Senegalese small-scale fisheries,2002.
[14]DiPasquale,D.and Glaeser,E..“Incentives and social capital:are homeowners better citizens”,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1999,vol.45 (2):354 –84.
[15]Wang,J.,Xu,Z.,Huang,J.,Rozelle,S..“Water management reform and the poor:Impacts on income,output and water use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China,International Water Management Institute,Colombo,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