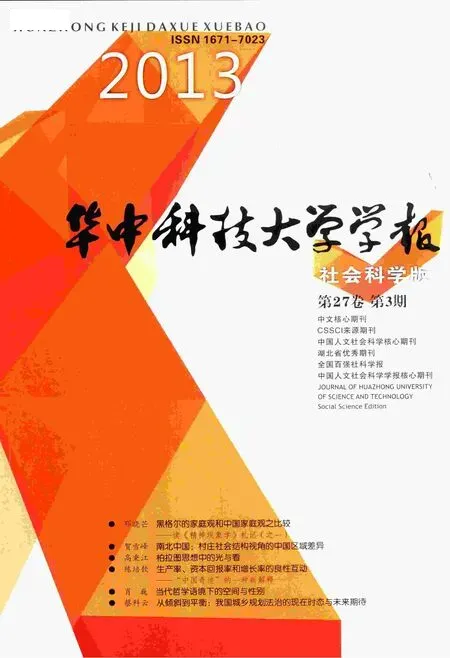农村人情的区域差异
宋丽娜,河南农业大学文法学院讲师,450046
一
农村人情的区域差异因为村庄社会结构的不同而呈现出来,村庄社会结构则由农民的“自己人认同”及村庄社会关系模式形塑。
在不同类型的村庄,农民形成“自己人认同”(即“我们感”)的机制和过程是不同的。如何形成“自己人”概念?社会心理学家杨宜音给出的答案是“类别化”和“关系化”。所谓类别化,就是通过角色义务规定,也即身份性的特征而形成的社会关系;所谓关系化即指建构的过程,彼此之间的相处是关键。杨宜音的答案分别对应于农村社会的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血缘关系的架构来自于传统文化的民间教化,是农村社会的基本社会关系。血缘关系的形成及其在熟人社会的运作具有先赋性特征,血缘标定农民的身份,血缘关系组织熟人社会的结构。地缘关系的形成多与移民社会的性质有关,农民之间的血缘联系较弱,彼此之间的地缘关系成为主导。地缘关系具有后致性特征。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基础,农村的社会关系模式可划分为三种:血缘关系主导、地缘关系主导、血缘和地缘关系的混合。三种社会关系模式构成了贺雪峰意义上的三种村庄社会结构状态:团结型村庄、分裂型村庄、分散型村庄。
团结型村庄多是宗族性村落,聚族而居,血缘联系紧密,组织结构也较为明显,农民的行为遵照“人情原则”。宗族是一个层层向外延伸的体系,从亲房到大房,从自然村到本地域的祖先,祠堂是其象征。尽管宗族可以不断向外扩展,不过,由于共居一处的地域总有个范围,因而就凸显出自然村的重要性。在团结型村庄,自然村通常是血缘和地缘关系重合,是一个行动上的宗族组织,也是一个团结的集体。团结型村庄的特性体现在三个层面:第一,道德、伦理、礼仪、规矩都导向“团结”;第二,村庄中的象征体系(祠堂、族产、“礼生”)也导向“团结”;第三,农民的行为逻辑也导向“团结”,农民彼此之间温情脉脉,在共同祖先的庇护下生活,很少有“撕破脸皮”和“结仇”的情况。
分裂型村庄农民的内外边界在小亲族的范围,小亲族是农民的“自己人认同圈”,村庄由若干个小亲族组成,形成分裂的态势。同一个小亲族的人家,农民有着天然的认同关系,“荣辱与共”,彼此之间讲究人情和面子,是守望互助和相互慰藉的集团。对小亲族之外的熟人则不同。熟人之间可能因为“处得好”而成为朋友,但是朋友的亲密关系只是个人感情和个人偏好,在牵涉到小亲族利益的时候,则会坚定不移地站在自己小亲族的立场上说话。小亲族之间的分裂与竞争成为主导村庄生活的核心要素。村庄政治、经济、文化各层面都体现出“分裂”的特性。
分散型村庄多是历史较短的移民社会,农民在血缘关系上构不成组织系统,这样的村庄是原子化的。地缘关系是农民在日常生活中首先要维持和处理的社会关系,因为农民日常生活中的诸多功能性需要都要地缘关系的参与。农民以地缘关系为基础建构松散的自己人认同圈(正是熟人社会的范围),因为血缘关系不是主导,农民之间并不亲密与团结,他们只能在日常生活中维持低度的“和谐社会”,成为原子化的个人。在文化层面,分散型村庄边界较开放,农民易于接受外界事物,在特定条件下受外界文化冲击较强;在行动层面,农民“个性”凸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做人方式;在村庄整体层面,讲求关系并且相互给面子的农民在努力维持一个低度均衡的社会。
三种村庄社会结构构成了理解农村人情区域差异的基础。
二
团结型村庄中,人情是依附性的;分裂型村庄中,人情充当着“黏合剂”的作用;分散型村庄中,人情则是个人表达性的。
人情在团结型村庄中的作用是依附性的,人情依附于血缘关系的结构,是血缘关系及其背后道德伦理的表达。人情仪式表达道德性的内涵,是礼仪的体现;人情往来的规则也要遵守道德性,人情本身就要受道德性的规约,人情在熟人社会中的扩展也要依据血缘关系的框架进行。人情在农民的日常生活中只是道德的“润滑剂”,人情本身并没有主体性,必须要依附于道德才有社会意义。
在团结型村庄,农民讲究“人情”的时候并没有个体的主体性,他们不能随便更改礼金,也不能够随意建构社会关系;农民讲究人情的时候要“从众”,而在人情方式上发生的任何变化都要经过大家共同的商议。农民是人情规矩自觉的遵从者和维持者,道德内涵是人情社会表达的核心,而公共性则是维系人情内涵的社会机制。人情看起来是个体的特征,个人支付礼金,个人进行各自的人情往来,个人做个人的“为人处世”,然而,人情作为社会行动,其各个方面都要遵从一定的规矩和礼仪,人情对于农民来说是公共性的。在团结型村庄,只有尊重规矩和礼仪,才是一个人能够在熟人社会中获得合法性和权威的基础。规矩和礼仪既是熟人社会对于普通农民的日常教化机制之一,也是农民赖以在熟人社会中获得结构性位置的资源。
人情在团结型村庄的意涵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人情所表达的内涵要充分表达道德伦理因素,其在日常生活中的体现就是规矩和礼仪;其次,人情在日常生活中的功能为以道德伦理为代表的核心价值服务,人情是社会关系的“润滑剂”,人情是组织社会生活的架构,人情作为一种社会机制在熟人社会中起着重要的教化作用;最后,作为一种社会行动,人情的主体性并不是由其实施者——个人——来建构的,而是由熟人社会来建构的。人情的主体性表现为熟人社会整体的主体性,这意味着人情要表达的是熟人社会整体的结构性特征,依附于熟人社会的性质而存在,具有公共性。
分裂型村庄中,内外有别的关系是人情要处理的核心命题。在分裂型村庄,熟人社会圈大于农民的自己人认同圈,在农民的日常生活中,他们都要处理不同类型的社会关系:对内的自己人和对外的外人。这种血缘关系结构决定着,处理社会关系在农民的日常生活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这就是农民通常所讲的要懂得“人情世故”。所谓人情世故,简要地说就是要懂得怎样与不同的人相处,怎样借助于社会关系上的优势转化为自身“势力”上的优势。
分裂型村庄的人情仪式在于通过礼仪和规矩来处理各种类型的社会关系,建构人情和社会关系的平衡。分裂型村庄的人情起着沟通人际界限的重要作用,而人情在熟人社会中的延展更加充分,表现在农民对于人情世故和为人处世的重视。
分裂型村庄的农民要面对两种类型的关系,一个是小亲族内部的关系,讲究人情、亲密、“让人沾光”等;另一个是小亲族之外的其他小亲族和其他社会关系,讲究相互之间的平衡、面子。对内的公共性与对外的私人性共存于农民的人格结构中,人情正是这种结构的反应。分裂型村庄的仪式性人情是一个分工合作的体系,也是一个讲求关系平衡的系统,更是农民人格结构的反映。
分散型村庄多是历史较短的移民社会,农民相互之间的血缘关系并不紧密,是以地缘为基础建构起来的熟人社会。因为既有的血缘关系系统不发达,长期生活在一起的农民为了满足各种功能性需要,地缘关系就变得较为重要。在地缘关系建构的过程中,人情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人情是农民建构社会关系的主要手段,有了人情,彼此之间的社会关系就建立起来,把外人转化为了自己人,具有人情关系的农民就会按照自己人的行为逻辑办事。人情在农民的日常生活中有重要的功能,农民对于人情异常看重,他们总是愿意结交更多的社会关系,注重彼此之间“处”关系,不愿意得罪人等。
分散型村庄中的人情是一种个人表意,也即人情少有结构性规范的制约,是个人依据自身经济状况、社会地位、性格偏好、理性算计、情感等因素而确定的,有钱人能够建立更加广泛的社会关系,穷人则尽量缩减人情交往的范围。人情是一种私人性的建构,人情成为个人情势的表达。个体农民在人情建构的过程中具有主体性,然而,在熟人社会的情境中,个体的主体性却无法依附于更大的主体性。这造成一个显在的社会后果,即个体主体性的张扬正是整体主体性的式微。熟人社会在个体主体性凸显的情况下,变得不稳定,变得“异化”。
三
农村人情的区域差异是不同村庄社会结构的一种表达,其中人情的社会性质也借此呈现出来。
以紧密血缘关系认同为主导的宗族性村庄较为团结,人情现象总是要按照规矩进行,进行复杂的仪式和程序,其中的人也总是要恪守“礼仪”,这是因为人情本身就是一种公共性的社会建构。人情的公共性贯穿于团结型村庄的方方面面。农民遵照“人情原则”相处,彼此之间温情脉脉,在共同祖先的庇护下生活,很少有矛盾冲突,农民习惯于“从众”,不能“跟别人不一样”,农民个体的主体性表现为村庄整体的主体性,个人的情绪和偏好不外显,彼此收敛。人情依附于血缘关系和自己人认同体系,是一种集体表意,起着类似于润滑剂的作用,并且承担着社会关系类别化的重要功能。此种类型广泛存在于华南地区,如福建、江西等省。
血缘和地缘关系混合的村庄是分裂的,小亲族是农民的“自己人认同圈”,以小亲族为基础的内外关系是导致村庄具有分裂特征的结构性因素,其中的人情就起着沟通内外界限的重要作用。分裂型村庄的人情要处理的核心问题是村庄社会关系的均衡,自己人与外人的关系是关键。人情的社会性质呈现了双重特征:对内的公共性和对外的私人性。在小亲族内部,人情是一种公共性的建构,贯彻着集体意志;而小亲族之外,人情则是一种私人性的建构,按照私人性的规则运作。这种区分使得农民“做人”的功夫凸显,人情成为农民的社会表意。此种类型多在华北平原,如河南、山东、陕西等省。
在广大以地缘关系为主导的熟人社会中,社会结构较为分散,人情是一种私人性的表达,私人规则主导人情的各个方面,在这种性质之下,人情异化现象就容易发生。因为人情规则是私人性的,个人就可以根据自身的性格爱好、经济情势等来决定自己的人情行为,其中人情礼帐的盈亏和平衡算计、个人情感的表达等自然是农民要精心考虑的事情;理性的农民希望自己不在既有的人情网络中“吃亏”,又希望能够表达自己在人情网络中的位置,人情就成为个人表达的载体。可是,人情中的个人表达消解了集体意志,个人特质的凸显使得集体的意志和集体的秩序成为虚设,人情现象呈现出各种异化现象:人情名目不断增加,人情仪式扭曲变形,人情礼金攀升,人情负担加重等。在笔者的社会调查范围内,在两湖平原周边地区、贵州遵义地区、浙江宁波地区、东北地区等都发现了不同程度的人情异化现象,而这些农村又都是以地缘关系为主导的熟人社会。

表1 村庄社会结构与人情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