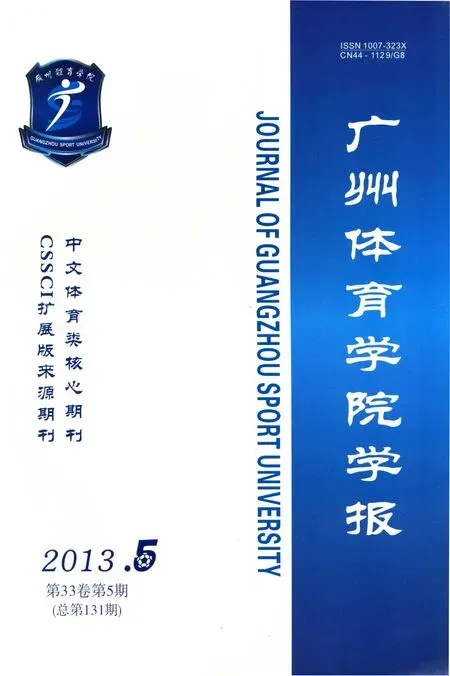体育文化生态系统的类型及其特征*
龚建林,许 斌
(广东工业大学体育部,广东广州 510006)
体育文化生态系统是指体育文化与体育环境相互联系而构成的有机统一体,体育文化生态系统是一个开放、自组织的系统,它具有自身的结构、功能和一定的自适应、自我调节能力,并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体育文化生态系统的要素主要包括体育项目、象征符号、乡土情结、历史传承、文化认同、社会组织、体育环境,这些要素之间存在生态关系,这些关系的总和就是体育文化生态系统。[1]体育文化生态系统占据一定的地域空间。多种多样的体育文化是在不同的地域环境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具有鲜明的地域性特点,是地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依附于一定的民族、群体或地域,如中原武术中的少林武功、陈氏太极拳,岭南武术中的广东南拳、蔡李佛拳、咏春拳,珠江三角洲龙舟、梅州足球、台山排球、石龙举重以及回族武术等都具有不尽相同的地域文化内涵和特点。在体育文化生态系统形成中,最核心、最深层的要素是文化认同。文化认同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族群文化认同,如岭南文化、伊斯兰文化;另一种是乡土意义上的地域、地方文化认同。在同一体育文化生态系统中,这两种文化认同可以独立存在,也可以结合而存。以文化认同为依据,根据族群文化和地方文化认同的离合情况,我们将体育文化生态系统划分为以族群作为主要联系纽带的体育文化生态系统、以地域作为主要联系纽带的体育文化生态系统以及以族群和地域两者结合作为联系纽带的体育文化生态系统三种类型。当前对于体育文化生态系统的分类及其特征研究阙如,本文拟对三种类型的体育文化生态系统及其特征进行深入的探讨,加深对体育文化生态系统理论的认识和运用。
1 族群和族群认同的内涵
在深入探讨体育文化生态系统类型之前,先对族群和族群认同进行分析。
1.1 族群
族群一词最早是1930年代开始使用,被用来描述两个群体文化接触的结果,或者是从小规模群体在向更大社会中所产生的涵化现象。族群(Ethnic group)是个含义极广的术语。有关族群的概念是多种多样的。当前许多人类学、社会学家比较认可的定义如下:族群,是指在一个较大的文化和社会体系中具有自身文化特质的一种群体;其中最显著的特质就是这一群体的宗教的、语言的特征,以及其成员或祖先所具有的体质的、民族的、地理的起源。[2]目前在我国学术界,常常使用“族群”替代过去习惯所用的“民族”。
中华民族分布在辽阔的国土上,各个地区有不同的生态环境,不仅可以看到不同民族适应不同的生态环境所造成的文化差异,例如游猎于大小兴安岭密林中的鄂伦春族所创造的森林猎人文化,与云南南部傣族的亚热带稻作农耕文化迥然不同。就是在汉族的不同地区,也同样显示出了地域性的差异,形成了区域性文化。罗香林首创“民系”一词指一个民族中的各个支派,认为一个庞大的民族,会因环境和时代的变迁,逐渐分化,各个局部成为若干不同系派、各个微有分别的民系。[3]
与民族相比较而言,族群涵义范围更广阔,指不同层次不同性质的人群。从学术意义上说,研究民族或族群的特征及其认同的依据则是共通的。[4]本论文中的族群,既包括我国的少数民族,也包括汉族中的不同民系,如广东汉人的广府民系、潮汕民系和客家民系。
1.2 族群认同
认同一词有许多不同的用法,原本属于哲学范畴,后来在心理学中的应用日益频繁,但作为一种操作性概念主要是一种能动的与个人主义的价值理念密切相连的归属性。族群认同不仅是族群成员对族群文化的接纳,而且还是他们主观心理归属的反映。有的学者认为族群认同是“社会成员对自己族群归属的认知和感情依附。”[5]纳日碧力戈认为,族群认同产生于传统和表达,它涉及神话、宗教、信仰、仪式、民间历史、民间文学和艺术。正是这些文化表达和族群认同的符号形式,为族群关系赋予了意义。[6]共同的历史渊源是族群认同的基础要素,语言、宗教、地域、习俗等相似的文化特征也是族群认同的要素。
2 以族群为纽带的体育文化生态系统
在该类型中,体育文化生态系统的主体(人)有着共同的族群背景(少数民族或者汉族不同民系),他们具有共同的族群文化,而且对本族群的文化包括体育文化具有广泛的认同。该体育文化生态系统的主要特征表现在:多数有一定的偶像作为精神符号;具有深厚的地域文化作为支撑的土壤,如岭南文化、民族意识等。由于体育文化可以扩散传播,所以通常可以表现为较大范围的体育文化生态系统。例如咏春拳、蔡李佛拳、洪拳等不仅在其发源地佛山蓬勃开展,也在整个岭南文化区域,包括香港、澳门等地方广为传播。又如龙舟文化,也在湖湘文化和广府文化区域广泛开展。这种类型体育文化主要是传统体育项目,我们还可以将其应用到分析少数民族传统体育。
佛山武术形成的文化生态系统属于这种类型。佛山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也是武术之乡,南派武术的重要基地。佛山武术源远流长,历史上门派林立、武风甚盛,南拳北腿,各擅胜场,历代武术名家不胜枚举,也是黄飞鸿、李小龙的故乡。历史上佛山有众多的武术组织,如鸿胜馆、佛山精武体育会、天地会、众义国术体育会以及一些武林精英设馆授徒,使佛山成为蔡李佛拳、咏春拳、洪拳、少林南拳、太极拳、螳螂拳、白眉拳以致黄河派、长江派等南北门派荟萃的武术基地。佛山武术界出现了众多的武术流派和无数名家,如蔡李佛拳的张炎、陈盛、李苏、梁桂华、吴勤、刘忠、汤锡、孔德光、陈雄志、崔章、李广海、陈艺林、胡云绰、谭三、雷灿、钱维方等;咏春拳的梁赞、陈华顺、陈汝棉、叶问、吴仲素、阮奇山、招就、张保、姚才、彭南、叶准、芩能以及国际武术明星李小龙等,洪拳的黄飞鸿、林世荣、林祖等,少林拳的梁细苏等;梅花桩的李铭清等;龙形拳的林耀佳、曾根等;白眉拳的刘少良、仇太生等;太极拳的曾坤、区荣钜、黄颖心、郑玲、潘炎流等武术名人,这些人物对于佛山武术的发展、弘扬,对于人们从事这些项目的活动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武术在佛山成为民间的一种传统,并且代代相传,积淀起深厚的佛山武术文化,成为南派武术的代表。清末民初,佛山已经成为南派武术的中心,在20世纪20年代,佛山武术达到了空前的繁荣。一直到解放前,虽然社会环境动荡、比较乱,但是政府一般不干预,只是武术开展的条件差些而已。解放后,众多的政治运动,使佛山武术的发展一度受到很大的冲击,特别是1953年的“打击一贯道等反动会道门”和文化大革命时期对武术的压制,对武术的发展打击得很厉害,文革时甚至要从根上铲除武术。文革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佛山武术逐步复苏。在当前,传统文化受经济发展特别是经济全球化的冲击很大,不少传统文化已经或正在失去生存的空间。佛山武术虽然身处珠江三角洲核心区域,但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仍顽强地生存和保留下来,原因就在于武术文化生态系统的结构和要素完整,而且具有深厚的岭南文化作为支撑,使得当地人对武术文化一直有较高的认同,并且通过影视等使黄飞鸿、李小龙名扬海内外,蔡李佛拳、咏春拳、洪拳等武术在佛山发扬光大并在包括中国香港、澳门等地区的岭南文化区域广为传播。这种类型体育文化主要是传统体育项目,我们可以将其应用到分析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以族群为纽带的体育文化生态系统除了佛山武术文化之外,贵州台江苗族独木龙舟文化也是如此,而且这种族群性表现得非常突出。
3 以地域作为主要联系纽带的体育文化生态系统
地理空间是人们生存和生活的基本条件,也是维系共同生活方式的一种联系纽带。某一人群共同体中的人们并不一定生于同一个地域,但却成长或生活在这个地域。共同的生活环境和经历等导致人们对所生活的地方逐渐产生一种认同感,即地域认同。
在地域认同基础上形成的体育文化生态系统主要有这样一些特征:一定有偶像作为精神符号以凝聚该地域的民众;通常与特定的地理环境或区域相关联,如东莞的篮球文化生态、梅州的足球文化生态和台山的排球文化生态,都只是存在于相应的地理区域;体育文化生态系统中的人们具有浓厚的乡土情结,并对某项体育活动的价值表现出高度一致的认同;此种生态系统的扩散性较差,通常仅存在于局部地域。这是本类型与以族群作为主要联系纽带的体育文化生态系统最大的区别所在。
东莞举重和篮球所形成的文化生态系统均属于这种类型。东莞石龙是举重之乡,石龙举重之乡的形成,主要是在陈镜开作为新中国第一个打破世界纪录的运动员及其连续打破世界纪录的背景下促成的。陈镜开的成绩在新中国成立不久的特定的年代里,引起了家乡人极大的反响和自豪感,使人们的举重热情高涨。在石龙镇,20世纪50~70年代,每个村都有举重队和练习场,很多学校和工厂都设有举重队。在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石龙举重人才辈出,除陈镜开之外,还涌现出了陈满林、叶浩波、曾国强、赖润明等众多世界级举重运动员,多次打破世界纪录,曾国强成为中国第一个奥运举重金牌获得者。石龙举重具有陈镜开、陈满林、陈伟强、曾国强等著名运动员作为偶像,成为一种凝集石龙人积极参加举重活动的象征符号,使举重在石龙得到广泛开展,但是主要局限在石龙这块地域空间内,一旦石龙本地人不再愿意从事举重练习,举重失去了乡土情结,它作为一种文化生态现象在石龙就衰落了,这种体育文化生态系统也逐渐崩溃。随着经济的发展,富裕之后的家长不愿将小孩送到体校训练,特别是练习举重,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已很难再招到本镇的学生。只好到外地招生乃至于买运动员,对于石龙人而言,乡土情结就不存在了,离开地方认同,这种举重文化就不能生存了,自然就衰落了。所以当社会条件、经济状况、经济形态、社会组织形式发生变更,作为体育文化生态系统的石龙举重已经缺失了地域认同和乡土情结等要件,正是因为要素不完整,使石龙举重急剧衰落,这也从反面证实体育文化生态系统割裂或缺失某些要素,难以持续发展。要长盛不衰,可持续地发展下去,必须具备体育文化生态系统的必要条件(包括必要的要素及其之间的联系)。可以说,石龙举重,是在特定时期的偶然性原因形成的,当社会环境回归本位,必然失去其赖以存在的条件和基础,从而归于消失。
篮球在东莞一直就有比较好的基础,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收入的提升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篮球已经作为一种城市生活方式融入到居民的日常生活中。而且东莞职业篮球队涌现出易建联、朱芳雨、杜锋、王仕鹏、陈江华等著名球员,成为东莞人的偶像和象征符号,将很多群众凝集在篮球周围。即便对于这些著名的球员,东莞群众也有着明显的乡土情结,在若干个小样本的调查中发现,他们最喜欢的球员还是易建联(来自同样是移民城市的深圳)和陈江华(东莞本地人)。东莞村村都有球队,各街道(社区)、镇也均有自己的球队,有自己的联赛;很多工厂企业也有球队,也有企业篮球联赛。每逢双休日、节假日,各镇、村坚持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因时制宜的原则,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开展篮球活动和比赛。当前东莞市农村篮球活动已经形成风气、形成制度,乡镇篮球活动得到较好的普及和推广。在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篮球活动深入开展,竞赛形成制度化,许多机关、事业单位都有自己的业余篮球队,人员、装备齐整,经常组织训练比赛。在街道(社区)、学校篮球活动方兴未艾。并且每年均举办东莞市篮球联赛,市篮球联赛分为甲级、乙级和丙级联赛,实行升降级制,篮球联赛是东莞人业余篮球最高级别的赛事。在甲级联赛中,无论竞技水平还是场外的准备工作,都显示出了极强的“职业水准”,具有“职业”味道。每年的东莞市篮球联赛,比赛时出现商铺关门、万人空巷、体育馆内座无虚席,政府重视,市民踊跃,当地媒体全程报道的盛况。[7]而且在东莞,举办篮球赛事,很容易获得企业的赞助,社会力量为东莞篮球运动的开展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4 以族群和地域结合作为联系纽带的体育文化生态系统
在部分体育文化生态系统中,族群和地域同时作为联系纽带,将人、体育文化与生态环境紧密地结合起来,成为有机的整体。在这种类型中,往往是同一族群或多个族群集中居住在某一地域,长期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体育文化。该体育文化生态系统的主要特征表现在:一般有偶像作为象征符号;具有深厚的区域文化作为支撑的土壤,如岭南文化;具有一定的可扩散和传播性,主要是周边地区;仅是分布在较大的局部区域。
桂北侗乡抢花炮文化所形成的文化生态系统属于这种类型。抢花炮是用火药把炮圈打到高空,待其下落时众人进行抢夺的一种民间体育活动。[8]抢花炮完整的仪式过程包括还炮、游炮、抢炮、接炮、养炮等程序,各地的抢花炮仪式不完全相同,一些地方的仪式有所简化。抢花炮在侗族聚居区很流行,从事这项活动的人们为它设计了一套仪式化的程序,赋予它丰富的文化内涵,往往以“抢花炮”为中心,结合其他的文体活动,形成花炮节。在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抢花炮是由在此经商的汉族商人引入的,经过侗族人的自觉和自然的改造,使抢花炮很好地整合到侗乡的本土文化之中,完成了对抢花炮的文化重构,抢花炮在广西三江侗乡已有几百年历史。三江侗族自治县是侗、苗、瑶、壮、汉等多个民族居住的地区,位于广西北部,全县人口34.71万,以少数民族为主,少数民族人口为28.78万,侗族占全县人口的56.76%。[9]在侗乡,民间组织几乎把各项集体活动仪式化,并且与信仰文化相结合,通过这些仪式性活动形成集体记忆、凝集族群、强化权威,抢花炮也不例外。侗乡人把花炮与自己的信仰结合,形成了各地祭祀不同神灵的抢花炮。在侗族地区的历史上,抢花炮承载的是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同时也是为求子、求财、求平安。抢花炮活动被构建成表达信仰和凝聚集体的仪式性活动,花炮把人们联系起来,在欢愉中释放压抑的情绪。该活动由于符合人们的需要而得到最广泛的支持,正是在群众热爱的基础上,民间组织能够克服种种困难,使该活动生生不息,传承至今。抢花炮作为一种民间文化符号,既是族群记忆表述的载体,也是族群文化传承的载体。在桂北侗乡,抢花炮和人群姓氏、信仰崇拜、生活习俗等一起使人们获得并延续其认同感。抢花炮作为一种跨村赛的多民族参与的民间体育活动,既强化了族群认同,也加强了侗、苗、瑶、壮、汉等民族族际之间的理解与沟通。抢花炮作为一项大型的民间集体活动能够有序地进行并且稳定地传承,与当地民间组织的存在以及民间组织的权威与号召力有直接关系。
此外,梅州足球也是以客家族群和特定的地域(梅江区、梅县、兴宁、五华)作为主要联系纽带而形成的体育文化形态,也具有本类型体育文化生态系统的特征。梅州的近邻河源虽然同属客家族群聚居地,自然地理环境也与梅州相似,但由于球王李惠堂不是河源人,所以只是在梅州而不是在河源形成了有特色的足球文化生态系统。在梅州,族群认同与地域同时对体育文化生态系统的形成均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5 小结
通过上述研究可以看出,在不同类型的体育文化生态系统中,虽然具有一些不同的特征,发展形态不一,发展轨迹各异,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在发展过程中均具有比较强的生命力和广泛的文化认同。在体育文化生态系统的众多要素中,体育项目、象征符号、文化认同、社会组织、生态环境,均是基本要素,不可或缺。当体育文化生态系统结构和要素完整,要素之间联系紧密,运行机制顺畅时,体育文化生态系统处于良好的平衡状态;当体育文化生态系统的结构或要素不完整,要素之间的联系打断,运行机制不顺畅时,体育文化生态系统存在的条件或联系被割裂,那么体育文化生态系统就受到破坏甚至于崩溃,该项目的发展就会弱化甚至于消失,传统的项目优势将不复存在。
[1]龚建林.论体育文化生态系统的结构与特性[J].体育学刊,2011,18(4):40 -44
[2]周大鸣.族群与族群关系[OL].[2002-10-31].“学说连线”网站 http://www.xslx.com/htm/zlsh/shrw/2002-10-31-10922.htm
[3]吴泽霖.人类学词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1:195-196
[4]黄淑娉.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182
[5]周大鸣.族群与族群关系[OL].[2002-10-31].“学说连线”网站 http://www.xslx.com/htm/zlsh/shrw/2002-10-31-10922.htm
[6]纳日碧力戈.现代背景下的族群建构[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65
[7]廖开放.东莞市篮球竞赛表演消费市场调查研究[J].湖北体育科技,2008(1):69 -70
[8]李志清.乡土中国的仪式性少数民族体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58-59
[9]李志清.乡土中国的仪式性少数民族体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