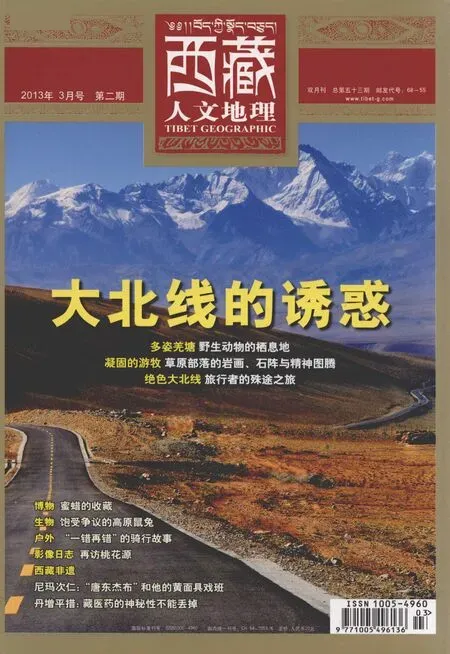朋友 o r敌人饱受争议的高原鼠兔
撰文/杨乐(西藏高原生物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黑唇属兔,三江源(摄影/董磊)
2012年7月,我陪同朋友一块乘坐旅游中巴前往纳木错,行至当雄西侧的草原时,同行的游客们在一片彼此关联,大小相若的洞口区域,看到一种没有尾巴、耳朵圆圆的小动物来回出没,时不时警惕地四下观望,待到驻车探视时它们又胆怯地钻回洞里,察觉你没有进一步的动作时又探头打量你一番。
“瞧这高原上还有老鼠呢!”游客甲惊奇地说。“这不是老鼠,是兔子!”游客乙急忙纠正。“哪能啊,这明明是老鼠!”游客甲坚持。“兔子!”游客乙也不松口。导游出来圆场:“这个叫鼠兔。”有游客问了,“是害兽还是益兽啊?”导游应道:“这玩意破坏草场,是害兽,这边正准备灭杀呢!”大家仿佛得到了正确答案一般,不多言语了。不一会,朋友冲我嘀咕:“我看这小家伙还挺可爱的,真是害兽吗?”于是我在纠结中沉默了——高原鼠兔,到底该算作是朋友还是敌人?
“高原土著”从夏入冬的生活
高原鼠兔(Ochotona curzoniae)隶属于兔形目鼠兔科,藏语名字叫“阿布拉”,通常活跃在青藏高原海拔3000~5000米的地区。据古生物资料记载,现存的各种鼠兔是由古鼠兔亚科(Subfamily Sinolagomyinae)演化而来,在青藏高原的北缘发现它们的化石距今约3700万年,故而高原鼠兔是不折不扣的青藏高原土著动物。

图为猎隼捕食高原鼠兔的情景,猎隼是鼠兔众多的天敌之一。(摄影/彭建生)
高原鼠兔是食物链中植物向动物转化的第一物种,它们是植食性动物,主要啃吃植物的嫩茎、叶、花、种子及根芽,尤其喜欢垂穗披碱草、早熟禾和棘豆类的植物鲜嫩多汁的茎叶部分。这一方面,也使高原鼠兔被迫成为动物扑食关系中最低端的存在;另一方面决定了高原鼠兔在一年四季的变换中,将面临高寒草原上,食物资源多寡的剧烈变化带来的巨大冲击。
由于身处动物捕食关系中最底端,高原鼠兔不得不疲于应对草原上所有的猎食动物,从毛色古怪的艾虎,到笨重憨厚的棕熊,从狡猾多变的狐狸,到善于奔跑的狼,从静守洞口的大鵟,到盘旋天际的兀鹫,从俯冲迅疾的猎隼,到举止高雅的黑颈鹤,它们几乎都以高原鼠兔为食。与天敌的斗智斗勇让高原鼠兔养成了谨慎胆小的习性,它们总是小心翼翼地从洞里探出头来,四下环顾,观察周围环境中是否有天敌的存在,以确保自己和家人的安全。
每年4~5月间,当羌塘草原上的海子开始化冻的时候,捱过严酷一冬的高原鼠兔开始了新一年生活,积极进食、储备能量、清理粪球、拓展洞道。当然,还有最重要的——追逐异性和生产后代。鼠兔的生活很有规律,每天太阳初升的时候,鼠兔们就三五成群地从洞里钻出来,用温暖的阳光驱走一夜的寒冷。它们还极其惬意地用自己敦实的屁股和后腿作支撑,而前足置于身前,让自己的身体直立伸展,让阳光可以晒到平时紧贴地表的腹部。因为这个动作和磕长头时的起始动作非常相似,当地人看到鼠兔在朝阳光朝拜,认为它们也有佛性。当然,轻松晒太阳的时间不会太长,当猛禽们开始出现在鼠兔的视野时,鼠兔就不得不结束了它们的早课,转而开始进行“躲猫猫”的游戏,游戏的目的就是获得尽可能多的地表活动时间,为了这个目标,它们不得不频繁辗转于地表与洞道之间,经验丰富的成年鼠兔能让自己在地表活动的时间达到总时间的90%。取食是鼠兔一天之中最为重要的活动,它们每天能吃掉相当于自己一半体重的植物,为此它们需要投入至少六成以上的地表活动时间来进行取食,这个时间也会随着草原的枯荣而有所变化,在草枯期取食所花的时间会比草盛期更长。

川西鼠兔川西鼠兔是高原鼠兔的远亲,学名为格氏鼠兔(Ochotona gloveri),是我国的特有物种,主要分布在青藏高原东部的四川、青海和云南等省。(摄影/雷波)

马尼干戈雪地里的高原鼠兔。(摄影/彭建生)
鼠兔以家群为单位建立领域,当有入侵者进入领域,雄性鼠兔就会跳出来捍卫领域,当然这也会“因人而异”。与入侵者相互接触后,若发现对方为异性个体,主人就会表现出亲密的行为,若为同性个体,主人将持续攻击,直到将对手赶出自己的领域为止。组建家庭后,鼠兔家群开始孕育后代,雌性高原鼠兔在从4月至8月的整个繁殖期一般可繁殖3次,每次产仔3~7只。所以当每年7、8月份鼠兔的繁殖停止时,高原鼠兔种群中成年鼠兔与幼年鼠兔的比例将发生剧烈的变化,新生的亚成体鼠兔一般会占到70%以上的比例,然而由于它们的稚嫩,它们也是草原的夏天最容易夭折的群体。我曾经在那曲古露附近的草甸,观察到两只亚成体鼠兔,耽于顽皮打闹,忽视了环境中的风险,在追逐中离开了父母的庇佑,瞬间即被一旁看似慵懒,实则虎视眈眈的大鵟掠走。在生机盎然的夏天,不光是高原鼠兔的种群数量有所增加,它的天敌们同样增加了捕食的频率和强度,它们也在养育自己的后代。
每到7~9月份,经验丰富的成年鼠兔会为冬天储备草食,以应对冬季食物条件的不可预测性。它们会把生长旺盛的植物咬断,在具有宽大叶片的植物上晾干,以防止腐烂,然后把干草堆成一个一个的小草垛,每垛重约3~4千克。有时,为了防止所堆草垛太多引来邻居的觊觎,鼠兔还会把一部分食物悄悄藏在自己的家里。鼠兔的家看似洞口众多杂乱无章,其实却是融取食、侦查、仓储、防御于一体的高档复合住宅。高原鼠兔会在食物丰富,距离水源地不远的地方建起自己的住房,这样可以减少取食时往返奔波的时间。它们喜欢疏松的土质,这样可以让住宅有更大的可塑性;喜欢栖息在干旱草原、河岸滩涂、山麓缓坡等植被低矮的开阔生境,而回避灌丛及植被郁闭度高的生境,以扩大它们的观察视线,减少被天敌捕食的风险。
经营修缮多年的高原鼠兔的住房由核心区域的栖居洞(主洞)和拓展区域的躲藏洞(副洞)组成。栖居洞是鼠兔居住繁殖的基地,构造相对复杂,一般有6~10个出入口,洞道蜿蜒10米,卧室里还垫有柔软的草茎,这是高原鼠兔生活起居的主要场所。躲藏洞主要分布在栖居洞周边,是高原鼠兔用于扩大自己的活动区域,方便的紧急关头躲避天敌的捕食的临时洞道,洞口小,出入口少,洞道也相对短,同时,躲藏洞也兼具厕所的功能,经常能在洞口发现成堆的粪球。

芒康的高原鼠兔。(摄影/彭建生)
说到鼠兔的住宅,就不得不提到经常有人提起的“鸟鼠同穴”。鼠就是指的鼠兔,而鸟呢?有人说是褐背拟地鸦(后因分类地位改变,更名为地山雀),有人说是雪雀,我通过观察和了解,发现地山雀不会使用鼠兔的洞穴,它们每到繁殖季节就自行挖洞,所以它并非“鸟鼠同穴”中的“鸟”;而雪雀,作为高寒草甸生境的一个优势物种,和鼠兔抢洞的事情倒是屡见不鲜,但是它们也不会和鼠兔同居在一个屋檐下,它们会非常不友好地把高原鼠兔赶跑,然后强占鼠兔们辛辛苦苦挖掘出来的洞道,再依照自己的喜好重新装修。我暗自猜测,“鸟鼠同穴”的始作俑者估计是看到这样一幕:一番打斗后,鼠兔抱头“鼠”窜,而某只强壮的白腰雪雀则是从洞口探出头来,洋洋得意的样子。而后,始作俑者遂有了“鸟鼠同穴”之谈。
抛开雪雀们的侵扰不谈,对于高原鼠兔来说,10月以后的冬天依旧是残酷的冬天,草原已经枯黄,也许还有冰雪覆盖。由于高原鼠兔并不冬眠,尽管它们已经尽力地为冬季而准备,但整个家群所需的食物依然过于庞大,大自然将无情地淘汰掉除了第一胎以外,发育不完全的亚成体鼠兔,及垂垂老矣的成年鼠兔。剩下的高原鼠兔唯有紧紧依偎在一起,等候着春天的到来。
益害之争
甲方高原鼠兔并没有一个好名声,事实上,它们被视为青藏高原最主要的有害生物。因为其食物生态位与家畜高度重叠,繁衍生息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就会和牲畜争夺草场,从而给农牧业的生产带来巨大的破坏和冲击。1998年底对西藏、四川、青海和甘肃4省进行的鼠害调查表明,鼠害波及面积达1.533×107公顷,占青藏高原草地可利用面积的13%,每年损失牧草约1.32×1010千克,相当于748万只绵羊的年采食量。而被归为鼠害的主要物种,首当其冲就是高原鼠兔。

胆小而警觉的高原鼠兔在洞口张望。(摄影/雷波)
另一个高原鼠兔是害兽的证据,来自它们的挖掘及觅食。一部分生态学家认为它们的行为会影响草原正常的生态演替过程。由于地形结构的改变,将导致水土流失加剧,鼠兔幼体的扩散使鼠洞迅速增加,草皮以下的新、老洞交错成网,在外力作用下,不断塌陷,使原生植被被切割成“孤岛”,与裸地一起形成斑块状结构并逐渐沙化,最终使原生植被退化消亡形成“黑土滩”,从而对草场造成严重的破坏。
此外,高原鼠兔惊人的繁殖速度也是让农牧民紧张不安的重要因素。有在退化的草地环境中,因为牧草生长得比较矮小,鼠兔可以轻易地发现天敌动物,其种群数量不仅容易激增,而且还会辐射状地扩张到周围的草原中,长期保持较高的种群密度,又进一步加剧草地退化的速度。
乙方然而,并非所有人都同意高原鼠兔是害兽的论断。尤其近年来,草原鼠害防治研究的重点由片面强调提高草原生产力,转向为生态保护前提下的可持续发展以后,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生态系统的平衡并不是生产量上的简单的数字换算能代表的,高原鼠兔是生态系统退化的指示动物而不是致使其退化的原因。
而一些新的研究也提供了积极的结果:高原鼠兔挖掘活动可促进下层和表层土壤的混合,鼠兔的洞道系统能增加土壤通透性,同时提高土壤水分涵养水平,进而减少水土流失程度,加快物质循环的速率。
有的学者更是直言不讳,所谓鼠兔破坏草场,只不过为了掩盖人口增加和过度放牧给草原带来的过大压力罢了。把高原鼠兔作为草原退化的罪魁祸首,完全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他们指出:①鼠兔在高原上存在了上千万年,假若鼠兔的存在会导致草原的退化,那为什么这么长的历史时间中,青藏高原的草原生境没有消亡,而直到近年才出现退化的趋势;②从生态系统能量和物质流动循环的角度来说,在草原生态系统中,鼠兔作为草食者所能获得的能量和物质,会严格受到它的上一级植物所能提供的能量和物质的限制,不可能发生超过草原承载能力的种群爆发;③从鼠兔对生活环境的选择上来看,如果草原正常发育,较高的植被会让它们的生存空间大减,众多猎食动物的捕食下,它们只能在草原与荒漠的交界地带,在盐碱性湖泊周围植被稀疏的区域内苟延残喘。

鼠兔在高山草原上已经存在了上千万年。(摄影/雷波)
我很难得出一个鼠兔是害是益的结论,因为甲乙双方都不缺乏缜密的思维和设计全面的试验作为论据,只是想到了范长风教授在谈到高原鼠兔时举的土拨鼠的例子:上个世界初的美国,草原上的土拨鼠被农场主和联邦政府一致认定每年吃掉大量的牧草,对草原破坏力极大。1902年美国农业部将其定义为有罪的“害虫”,1915年美国第一个灭鼠法案在科罗拉多州获得通过,1920年在450万英亩的草原上实施毒杀行动,即“根除项目”,该项目持续50年,消灭了90%以上的土拨鼠,然而当地的草原生态系统也随之崩塌。此后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开始反思这次大毒杀行动,意识到土拨鼠与草原应该是一种互惠互利的关系,它们是“天然的肥料制造者”,其生物活动增加了牧草的蛋白质和适口性,而且为草原的食肉动物提供了食物来源。生物学家重新定义了土拨鼠的生态作用,将其作为草原生态系统的关键物种。虽然2000年土拨鼠被美国列为濒危物种而加以保护,但已无法挽回近一个世纪生物多样性的巨大损失。
灭与控的抉择
抛开高原鼠兔是害兽还是益兽的争论不谈,目前高原鼠兔较高的种群数量的确给青藏高原及其周边的牧区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谈高原鼠兔的保护显然还为时过早,公众的目光依然聚焦在采取何种手段减小和控制高原鼠兔的危害,缓解目前草原为此承受的压力上面。由于甲乙双方对鼠兔地位大相径庭的判断,对于控制鼠兔的危害规模和范围,又衍生出来两种不同的处理方法。一是药物灭杀,另一个则是生物控制。
半个世纪来人们最广泛采取的防治措施,即药物灭杀。药物灭杀的优点是周期短、见效快,可以有效打断鼠兔种群的激增过程。然而灭杀药物带有毒性,会给环境带来一定的冲击,虽然近年来一直从弱化毒性、减少二次中毒方面进行了改进,但结果还是不尽如人意,殃及许多高原鼠兔外的其他物种。更容易被人们忽视的问题是,即便药物灭杀达到精确的灭杀鼠兔的效果,也会导致食物链中更高一级的肉食性动物也因为食物断链而消失。这种单一的只追求杀灭鼠兔的模式降低了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内的生物多样性。而长期使用药物灭杀,导致鼠兔以上的食物链中断,还会导致潜在的风险——就是高原鼠兔上升到了这条食物链的顶端,一旦鼠兔产生抗药性,或是减小投放剂量,鼠害的复发将成为必然结果,甚至可以预见,卷土重来的鼠兔数量将比以前更大,危害也更加严重。
坚持生物控制的人也不在少数,由于青藏高寒草地生态系统是较为脆弱的,一旦遭到破坏,自然恢复的周期相当长,而高原鼠兔以其独特的生态位,在这个生态系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生物控制显然更为生态环保。他们认为高原鼠兔不能实行灭绝性试验,而应该把它的数量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考虑到鼠兔种群受多种因素制约,例如天敌、食物资源、竞争及灾害性天气。通过天敌动物的物种多样性及种群数量恢复、植被结构的改造等方式,使群落稳定性增加,以此来强化竞争机制、制约数量。这种做法降低了人为活动的影响,有利于草原生态平衡的建立,同时还可以避免药物灭杀带来的环境污染。然而生物控制并非万全之法,当鼠兔的种群数量超过可控的数量阈值时,这种生态系统自身的调节机制将会失灵。
我恰好在羌塘草原做了这种方法的对比试验,结果表明,单纯使用药物灭杀并不可取,有些投药区域的高原鼠兔在近年来屡屡复发,鼠兔种群数量不减反升。如果仅依靠生物控制,那么在鼠兔种群数量急速上升的过程中,产生的效果不明显,而且相对滞后。如果将二者综合使用,以生物控制为长效措施,将药物灭杀作为补充性的应急措施,或许会有更好的效果。
结束语
科技在进步,人们的观念也在不断发生改变,或许对于高原鼠兔是害是益的争论仍将继续,是灭是控的抉择仍要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上演,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个看起来又像鼠又像兔的小家伙,是承载高寒草甸生态平衡的重要物种,是青藏高原物流能流体系中的关键一环,它,不可或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