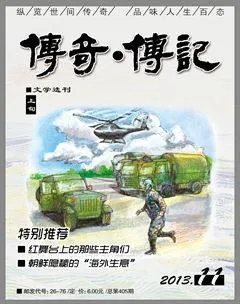中国远征军在印度集训
1942年,中国远征军第一次远征以兵败野人山为结局落下了帷幕,日军席卷了整个东南亚,不但彻底断绝了中国与外界的陆路交通线,还出兵滇西威胁我国的大后方。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太平洋战场上,日军在美军的攻击下节节败退,1943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局势越来越明朗。此时,为履行中缅印战区的作战义务,国民政府决定扩充中国驻印军的编制,而当务之急就是要解决部队中官兵文化素质较低的现状,由此,国民政府放开了学生从军的限制,提出了“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动员国内的知识青年加入中国驻印军,奔赴印度受训。第二次远征军作战就此拉开了序幕……
邓某,男,民国15年生(1926),这个山东布匹商人的儿子,自打11岁起就被迫背井离乡,1938年下半年跟随家人辗转来到战时的陪都重庆,开始了新的生活。随后,他考取了内迁的南开中学,开始了求学生涯……
1943年,17岁的小邓面临着一个两难的选择——是继续考大学,还是参军抗战?小邓的两难,主要是因为和家人出现了分歧。家里人都希望家中的这个独子能老老实实地完成学业,而小邓则具有那个时代年轻人普遍的热血情怀,希望有一天能穿上军装,保家卫国……
远征军老兵邓某通过自述,带我们回顾了那段岁月。
十万青年十万军
家里人自然是希望我考大学的,但我并不情愿,一是家里的经济环境不太好,从山东老家搬家到重庆后,虽然父亲一直还在维持着自己的小生意,但战争年代的萧条以及人离乡贱的事实都让家里的经济情况每况愈下,供我读完中学都非常勉强。更何况当时的校园也正经读不了什么书,常常上课铃刚一响,鬼子的飞机就准点来了,乱哄哄地疏散躲避,等空袭结束回到学校,大半天就过去了,还常常有老师因为迫不得已要安置家人,寻找跑散的同学,搞得连剩下半天的课都上不好,那个时候的学校都是如此。对于继续上学我还是希望的,但要想安安静静地求学,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彻底打败日本人!
当时在学校里,被人谈论得最多的就是何时反攻的话题。自从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直接参战后,那个时候的陪都几乎所有人都觉得反攻在即。但时间一天天过去,政府始终没有提到反攻的事情,反而前线不断有不好的消息传回来。
1943年下半年的时候,我的一个好友李壮丁带来了一个消息,说政府有意放开学生参军的口子,鼓励学生参军。
李壮丁带来的消息让我们很是吃惊,学生从军不是没有先例,但情况比较特殊,参军的大多是学校没有随同南迁的零散学生或者类似于东三省流亡学生。而且政府一向都不提倡学生参军,即便是鄂西会战的时候。眼看着日本鬼子就要杀进四川的危急情况下,政府也同样没有放开这个口子。我们知道李壮丁家里有个不得了的亲戚,但对他的这个消息还是半信半疑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的消息越来越多,李壮丁的消息看样子是真的了。
1943年年底,学生从军已经成了重庆各大学校的一股暗流,很多原来对我们横眉冷对的街头征兵官开始对大胆报名参军的学生和颜悦色起来。
1944年年初,有确切的消息传来,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决定开展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广泛动员在校学生参军。带回来这个消息的国文老师马上就被兴奋的同学包围了。很快,学校就统一开辟了学生参军的报名点。那个时候我们才知道,之所以从拒绝学生到现在鼓励学生参军,主要是因为美国人的因素。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和美国成为战略同盟,为保卫滇缅交通大动脉,成立了中缅印战区,由蒋介石担任司令官,美国将军史迪威担任参谋长,以中央军精锐为基础,组织了第一次远征军。但10万大军因为战略决策上的失误,兵败野人山,精锐之师或葬身异域,或被迫撤退到印度,仅有少部分回到国内。中缅交通也随之中断,中国已被日本形成了半包围的战略态势。但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略态势的好转,美国迫不及待地开始武装中国驻印军,但让那些大字不识一个的壮丁兵学英文,了解活塞发动机的工作原理,这显然是强人所难,所以美国人一再要求蒋介石输送知识青年到印度参加远征军。
政府放开了学生参军的口子,我第一时间就报了名,但也是偷偷摸摸的,我知道家里一定不会同意。李壮丁也和我一起报了名,同样也是瞒着家里人。我们报了名后就回家偷偷简单收拾了一下,并且预先写好了书信。到了集合的那一天,离家的时候才感到有点不舍,但还是一步三回头地走了。
我们先是在学校集合,点了名后,大部分报了名的同学都来了,还有一些家里死活不同意的没有到场,之后我们就上了卡车,被运到了郊外的兵营中,拿到了没有军衔的军服和一些生活物资。穿上军服,虽然没有军衔,但依然觉得自己容光焕发。随后我们进行了一个月的新兵训练。当时还有这样的一个事情,由于很多同学都和我一样是瞒着家里来参军的,到家里发现人失踪以后纷纷发动人手来找,有的学生家长能量比较大,找到了这个兵营。但守营的士兵不管是谁都不让进,所以营门口每天都有很多唤儿唤女的家长徘徊着。我不知道我的父母来了没有,我不忍心去想,更不忍心去看……
新兵整训结束后,我们放了几天的假,被允许回家看看,但严格规定了归队时间,而且得同学们相互作保,若有人不按时归队,作保的人就得受到牵连。我没忍住思念,还是回到了家里。父母见木已成舟,只有默认了这一事实,只是带着眼泪不断地叮嘱我注意身体和安全。假期快结束时,我才在父母和邻居们依依不舍的送别下回到军营。因为我们被告知,过几天将通过空运的方式前往印度远征军营地。
坐飞机对于我们这些学生兵来说还真是新鲜事,日本鬼子的轰炸机倒是经常见,但坐飞机,而且是飞到国门之外,这种新鲜感是无与伦比的,当时几乎所有的战友都在讨论坐飞机的事情。但后来残酷的事实击碎了我们之前所有的幻想,那几小时的旅程是我一生中最难熬的时刻。
到印度去
在刚上飞机的时候,飞机远没有我想象中那么神秘,不算大的机舱并不舒服。在上飞机之前我们还要经过体检,全部脱得光溜溜的,只剩下一条内裤,由美军的军医挨个替我们检查,检查了很多项目,检查完毕的,由每个医生在每个人手臂上用章盖个戳,当时的感觉就像当年准备被卖到美国的“猪仔”一样,浑身不自在。本来以为检查完就可以穿上衣服,但上面传下来了一道莫名其妙的命令,所有人都不允许穿上衣服,部队配发的枪支弹药、背包水壶等东西也一律不准带,大家都得光着身子上飞机。
当时是初春时节,但四川盆地一向气温不算低,再加上都是些年轻的棒小伙子,所以即便是光着身子上的飞机也不觉得有什么,而且大家都光着,也就没有了怨言。不知道发愁的同学们还在比谁的肌肉多,甚至还取笑某位胖同学身上的肥肉。
但飞机起飞以后,我们就再也笑不出来了。飞机里人很多,大家几乎都贴在了一起,没有多少活动的空间,起飞的时候颠簸得很厉害,飞了一阵才平稳,然后一群本来都很紧张的半大孩子又开始了嬉笑打闹。但没过多久,大家就发现了异样:随着飞机越飞越高,气温也越来越低,有眼尖的发现机舱的窗户上已经结了霜。当时大家就开始打哆嗦了,后来实在冷得受不了就相互抱在一起取暖。在最冷的时候,机舱的喇叭传来通知,是美国飞行员用英语发出的通知,大意是说飞机准备飞越喜马拉雅山,空气中有强气流,请所有成员注意做好准备。
没过多久,飞机就开始颠簸起来,而且更糟糕的是气温更低了,很多人就抱在一起在那乱骂,有的人甚至哭了起来,要求停机返航。但驾驶舱的飞行员根本听不见,机舱里的人都被冻坏了,有的人甚至开始出现幻觉,在喊着热,当时我也几乎失去了知觉。也不知道过了多久,飞机降落了,等飞机停稳以后,机舱门被打开,除了大鼻子的飞行员之外,还有很多美国的军医和教官。舱门一被打开,我分明听见了一声惊呼“Oh My God”,然后就失去了知觉。当我再度醒来的时候,是躺在一片陌生的草地上,周围到处都是同机的伙伴,依旧没有衣服,但盖着一床薄毯子,印度的太阳暖洋洋的,晒得人很舒服。之后,很多在飞机上被冻昏过去的同伴都纷纷醒了过来。这时候才有一个美国教官过来整理队伍,全部的人都经过了医生的体检,然后每人先发了一身军服穿上,美式新军装,但遗憾的是依然没有军衔。
那个美国教官很好奇,就问我们为什么是光着身子从飞机上下来的,难道我们之前被强盗洗劫了吗?有同学回答说是长官的命令。那个美国教官皱了皱眉,耸了耸肩膀,说道:“真是奇怪的命令。”
后来我们才知道为什么我们会受这一路的罪了,原因在于当时需要转运的学生兵太多,而飞机有限,所以官僚们拍了拍脑袋就想出了这么个馊主意,让所有人把衣服脱光,这样每架飞机能多塞几个人上去,而且留下来的衣服还可以给后来的士兵穿。这个办法简直是一举两得,惠而不费,反正我们这些人到了印度以后美国人也要负担我们所有的装备补给。但他们却没有想到在零下几十度的气温下,光着身子是一种什么感觉,或者说这些官僚大老爷根本不在乎。因为出现了冻死冻伤的情况,美国方面拍电报向重庆提出了抗议,从那以后,这一现象没再出现。
到达印度后,因为在飞机上被冻狠了,我们休息了好几天才缓过神来,然后就到了选择兵种的时候。出乎意料的是,不是让我们来选部队,而是部队来选我们。当时的专业科目很多,最受人瞩目的自然是坦克兵,最倒霉的自然是工兵,比较无所谓的则是汽车兵或者通信兵了,而偏偏汽车兵和工兵的需求量最大。我那个时候虽然年纪不大,但个头不小,坦克兵训练营的教官经过我面前,我连忙抬头挺胸作威武状,结果那个美军少尉看了我两眼以后就摇摇头走开了,反而是站我前面的李壮丁被选上了。李壮丁虽然比我年龄大很多,却是非常典型的四川人的身材,比我矮一个头,又瘦又小,他居然被最被人看好的坦克兵营选走了,几乎让所有人跌破了眼镜。后来我才明白,越是像坦克或者战斗机的驾驶员就越需要身材瘦小而灵活的人,因为坦克里活动空间有限,要是弄几个大胖子进去,大家在里面都不能动了。
在一众同伴或羡慕或嫉妒的眼光中,李壮丁欢天喜地地被领走了。接下来,又有多个兵科的教官来选人,到工兵营的教官来的时候,我赶紧佝偻着身子,生怕被选中,但世界上偏偏怕什么来什么,这个教官是一个中国教官,走到我面前时,我几乎把头都缩进脖子里了,结果他喝了一声“立正”,我在前面军训的时候养成了下意识的反应,立即站直了。这个教官捶了捶我的胸口,称赞我长得结实。其实我当时很想告诉他我身体很差,但终究没有说出口,我不幸中标,在同伴们幸灾乐祸的眼神下进了工兵营报到。
美国式集训,操练新来的学生娃
1944年,随着国内知识青年的踊跃从军,兰姆伽这个印度东北部比哈尔邦的一座偏僻小镇突然间热闹了起来。最初到达兰姆伽的是在远征军第一次作战失败的新三十八师及后来败退至此的第五军残部约一万人,随着空运的开展,到后期平均每天有四百多名学生兵从国内空运至此。在这里,学生兵们按照美军的训练方式训练,并全部配备了最新的美式装备,为反攻缅甸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工兵营应该说是科目最多的特种营了,虽然我主要的学习方向是舟桥专业,但是例如爆破、排雷、排爆、测绘、工事建筑、伪装等科目也需要学习,经常听课都要听一天。给我们上课的都是美国教官,因为我英语听和说的能力较强,相比营里其他从战斗部队转过来的老兵来说,学习起来进展很快。那些老兵当初都是战斗部队的士兵,有的还负过伤得过军功章,说到打仗他们是一套一套的,但说到听用英语讲授的工兵课他们就傻眼了,很多人斗大的中国字不识一个,就更别说英文了。偏偏工兵又是各部队需求量最大的兵种,所以人员缺口极大,不得不从战斗部队里选拔合适的人。但这里的合适也只是个相对的概念,当时国民党军队伍里的文化水平低,能把自己的名字完整写下来的都是了不得的文化人了,让他们听英语工兵课程明显是强人所难,所以当时驻印军才迫切需要知识青年从军。
由于我们是最早一批来到印度的学生兵,所以在工兵营里就我们三个学生兵勉强能跟上进度,我们的王教官见老兵们在美国教官的课程上如听天书,觉得不是个办法,就请求我帮他们补习,一开始我是在课堂上进行同步翻译,后来我就逐渐培养他们听说英语的能力。其实能被部队保送来工兵营的大多数人比较聪明,只是少年时期少了受教育的机会,而我也因此成了工兵营里的新兵班长。后来在评定军衔的时候,我因此直接成了中士,而其他人除了一个老兵在部队上就是中士军衔外,其他都评为下士。
在驻印军序列中,士官的待遇相当优厚,因为采用的是美国的军衔与相应的补给制度,士官比普通士兵多了很多福利。其实福利什么的我倒不在乎,我是觉得有一些身经百战的老兵能恭恭敬敬地叫我一声班长,那得意劲确实不摆了(四川方言,就是不说了,大家都心知肚明的意思)。
我们在驻印军的训练中,除了要学习相关的特种兵(这里的特种兵是指汽车兵、通信兵、工兵等辅助兵种)知识外,还得进行相应的军事训练,毕竟我们以后也要被分配到作战部队中去。因此,老兵们总是喜欢在这个时候收拾我们,许多学生兵因为一来就成了班长,很多老兵就不服气,所以在训练场上就使坏要整我们。但这种整也不是说刻意的害人,而是采取一种高标准、严要求的训练标准,拼刺动作不达标,跑操场20圈;站军姿不达标,跑操场20圈。好在我身体还好,还经得起这样的磨炼。
在印度的时候还有个很不好的现象,就是士兵们拉帮结伙的现象比较严重。有一次,在食堂打饭的时候,负责放饭的班长是东北人,每个东北籍的新兵每人多打一勺菜,第二天,轮到四川班长执勤,就给每个四川籍的新兵多打一勺菜。结果那个东北的班长不愿意了,那个四川班长就反唇相讥:“你打得,老子就打不得喽?”然后两个老兵班长就扭打起来,东北籍和四川籍的新兵们也去助拳。周围其他省籍的新兵就在边上起哄,一时间包子与馒头齐飞,汤锅与碗筷共舞,打成了一锅粥,一些开始还在边上看笑话的人屡屡被误伤,也撸起袖子加入战团。结果当天在那个食堂吃饭的,统统被关禁闭一天。
在印度的生活其实现在回想起来有笑有泪,但总体来说还是开心的时候比较多。到1944年年底的时候,随着到印度受训的学生兵越来越多,我们第一批受训的学生兵大多已经毕业,接下来就准备开赴缅甸前线对日作战了。
〔本刊责任编辑 柳婷婷〕
〔原载《中外书摘》201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