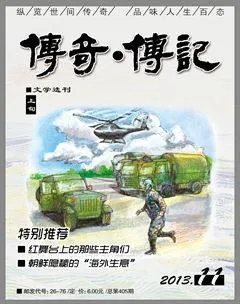飞来的好运
吴渊是一家装潢公司的老工人,这家公司负责装修的“燕鲍一品”酒楼下水道出了问题,老板派他和几个工友过来维修。干完活已经是晚上九点多,吴渊拎着在后厨讨的一些剩菜,不想正跟一个醉醺醺的胖子撞到了一起,手里的剩菜撒了一地。胖子一个趔趄,回手一个大耳光重重地扇在吴渊的脸上,他猝不及防摔了一个大跟头。
胖子暴跳如雷,嚷嚷着要讨说法。楼层经理一溜小跑过来连连赔着不是,还呵斥吴渊,让他赶紧掏钱赔偿。这时吴渊的工友听到吵嚷也赶到了,围上前跟胖子述说着吴渊家里的窘状,求他网开一面少要点损失费。
听到吴渊的名字,胖子愣了一下,再次揪住他的衣领,直勾勾盯着他。
胖子似乎酒醒了,呆呆地说:“你……叫吴渊?78届三中毕业的?”吴渊一愣,心里升起了一丝希望,赶紧使劲点头。胖子的手松开了,使劲揉眼睛晃脑袋,口齿也不伶俐起来:“小……小从文?天啊,我……我是李大元啊!是我呀班长!”
吴渊慢慢挺直了腰。“小从文”,几十年没听见有人喊他的绰号了。从眼前这张近在咫尺的肥脸上,他找到了三十年前那张娃娃脸的模子,没错,这个盛气凌人的胖子正是高中同学李大元。三十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饱受生活磨难的吴渊看上去已经是个老年人了,难怪李大元一时半会认不出。
忐忑不安的经理和工友意识到危机解除,都长长松了口气。
要说这酒可真是好东西,恰到好处地盖住了胖子李大元的脸,他擦着汗非要拉吴渊去包间喝酒。原来巧得很,今天正是他们老三班的同学在聚会。吴渊再不愿见同学,也由不得自己了。
打开房门那一刻,吴渊脑海里浮现出一个人——大观园里的刘姥姥。那一瞬间他产生了强烈的悔意,如果可以选择,他宁愿赔那件价值不菲的T恤,也不愿穿着脏兮兮的工作服,红肿着半边脸,万分狼狈地跟老同学们见面。
同学聚会一向是成功者乐此不疲的游戏,主旨无非是男生们夸官斗富,女生们比美比老公,所以这豪华大包房里到场的三班同学,非富即贵。其中以李大元最为显赫,已经是省里的厅级官员了。
大家对突然闯入的老班长热情有加,一杯又一杯红的白的灌下肚,所有人都心潮起伏,回忆起当年集体逃学去偷农户的黄瓜,半夜翻墙出去看露天电影,李大元考试不及格被班主任蔡老师暴打……提到班主任,有人居然背诵出他写的诗歌,不过这诗人总是惨遭家暴,动不动包着半边脸来上课……酒越喝越多,情越唠越稠,吴渊的脸还在隐隐作疼,心里一阵酸,一阵苦。
眼前一张张承载了过度热情和酒精的脸恍惚起来,吴渊的脑子开始发晕,嘴也没了把门的,含含混混唠叨着:我?我是班上唯一住在大山里的学生……穷啊,打小没爹,老娘还是一条腿,三十多岁才混上媳妇……媳妇?人是挺好,就是她家族有遗传病,好好的人到了二十多岁胳膊腿儿就不听使唤,不到三十就都没了,要不人家也不能嫁给我……后来,后来她给我生了一对双胞胎儿子,她先发病就死了……孩子们?开始还好,脑子是真聪明,我寻思是老天可怜,孩子们遗传了我,能躲过去这一劫,就带他们来县城租房打工上学,哪想到……现在俩孩子都在床上瘫着,吃饭都得我老娘一口口地喂……
多了,真是喝多了,多到舌头根本不听大脑的控制。似乎后来他还号啕大哭,哭诉当年的学习一点不比在座各位差,可就是造化弄人高考落了榜,这些年,苦哇……写稿?对,当年在校文学社,我还是社长,蔡老师一直指点我写作,夸我是“小沈从文”,可这些年,苦得我啊,诗情画意风花雪月早拌着黄连和泪吞了……
吴渊醒来时天已经大亮,老娘和两个身子软如面条的儿子六只眼睛惶恐地望着他。他慢慢坐起来,只觉得头疼得要裂开一样。然后他的眼睛就瞪圆了,嘴巴也大张着合不拢——身边的炕上,有好多崭新的百元大钞!
儿子们含混不清地抢着告诉他,昨晚是一辆小汽车把他送回来的,他已经醉得人事不知。车走以后大家才发现,吴渊的衣袋里,怀里,塞满了钞票。
吴渊哆嗦着捧起钞票,大略清点一下,居然有两万多块!他赶紧给李大元打电话,问起这笔钱的来历,李大元打着哈哈说是老同学的一点心意,也别细追问了。吴渊不停地用袖子抹着眼泪,这时他才确信,昨晚误打误撞闯进这个聚会,也许不是坏事。他很想跟李大元多说几句感恩的话,可对方的口吻虽然和蔼,却多了种说不出的疏远隔膜,吴渊也就知趣地结束了通话。
吴渊在家歇了一天,转过天一大早来到单位上班,平时总拉着长脸像欠了他几世钱的经理居然笑容可掬地找他了:“吴叔,你是咱这儿的老工人了,公司发展到今天的规模,你老功不可没!公司管理层经过研究讨论,决定提你当带班班长!薪水涨到四千,全脱产呦!”
面对工友们羡慕得发红的眼睛,吴渊一头雾水。就是这个长脸经理,昨天不是还嚷嚷要辞退他吗?吴渊硬着头皮拨通李大元的电话,询问是不是他从中帮了忙。李大元的声音冷漠而不耐烦,说自己绝对没安排,马上要去跟省长汇报工作,不多聊。
听筒里传来电话挂断的声音,吴渊犹豫了一下果断地删除了这个号码,他知道,自己和李大元之间的鸿沟,远比当年鲁迅和闰土的要深得多。
几天以后,好几家省内大报记者涌到吴家采访。很快,各大报大篇幅发文呼吁有关医院伸出援手帮帮这可怜的一家人。吴渊带着儿子们辗转了几家医院,病情却丝毫不见起色,一家福利机构伸出了援手,愿意免费接纳孩子们。
好运接踵飞来。这一天吴渊正在工地忙碌,一个骑着摩托车的邮差高喊他的名字,说有他的汇款单,手里还举着一本杂志!吴渊连连说他找错了人,可邮递员一口咬定是他的没错。
吴渊疑惑地打开杂志,见发表的文章是一篇两万多字的报告文学,署名正是吴渊。他立刻跟杂志社联系,声明这文章绝不是自己撰写。可那家大杂志社的编辑斩钉截铁地说,投稿的就是这个名字通联,绝不会错。
吴渊对着飞来的两千多块稿费单发了几天呆,那篇文章当然读得烂熟。这一天和煦的阳光照射进出租屋的窗子,照射在他花白的头发上,他心里豁朗一声仿佛有一扇窗被推开了!他对着那篇报告文学大声叫着:这东西有什么啊?我也写得出!
这飞来的好运激活了吴渊沉睡多年的文学细胞,文采如同地下的岩浆,呼啸着喷涌而出,大半生的苦难也翻转为巨大的财富,他忘我地投入到文字创作中。每个月都有汇款单从各地雪片一样飞来,小说、故事、剧本,应有尽有,只不过一年多以后,他收获的绝大多数都是自己的劳动果实了。“民工写手”、“农民作家”,一个个头衔纷至沓来让他应接不暇。
两年以后,吴渊原创的一个地方小戏获了省里的奖,县文化局戏剧创编室主动向他抛出了橄榄枝——在没有花费一块钱好处费的情况下,吴渊被作为特殊人才,由县长特批,特招进县文化局任职专业创编员,公务员编制。
带着老娘搬进单位安排的适用房没多久,儿子们先后离开了人世。丧事过后,他从悲痛中抬起了头,撰写了一篇长长的散文,他要表达的情愫是感恩。工作落实以后,他曾经去省城找过几次李大元,希望找出托起他的那只幕后巨手,可惜每一次李大元都有事,这个心愿也就始终没有达成。
恩人无从找起,吴渊准备去拜访文学之路的启蒙恩师蔡老师,给自己的散文结一个精彩的尾巴。几十年过去了,自己终于熬到了可以堂堂正正拜见恩师的一天。
蔡老师跟儿子住在邻近的城市,听说身体不太好。吴渊拨通了同学给他的号码,听到那个苍老却依稀熟悉的声音,他激动得心跳都加速了,报上名以后迫不及待地提出见面,电话那边的老人却似乎被吓住了,好半天才抖抖索索说了句:“你找错人了!”电话就挂断了。
吴渊对着电话发愣,再次拨过去对方已经关机!难道老师得了老年痴呆?他悔恨着联系得太迟,打算周末过去看望老师。不料他临行前再次拨打那个电话却被告知,蔡老师突发脑溢血死了!而且他发病的日子就是自己打电话那一天!
蔡老师的墓址在一湾自然湖泊的附近,是他最有出息的学生李大元亲自选的,据说是一处风水佳绝、福佑儿孙的宝地。李大元读书时没少挨蔡老师的板子,难得他对老师的回报之心。
那个周末,吴渊在蔡老师的墓前献了一束花,对着照片上那张老态龙钟的脸深深鞠了三个躬。
几个月以后,参加同学聚会的吴渊得知,李大元被双规。这年头的官员出事没什么稀奇,只是他落马的原因比较特别。李大元为蔡老师挑中的墓地果然好风水,被所有方以高价一墓多卖。李大元仗势强行下葬,被人实名举报了,这一查就查出个大贪官!
李大元的落马让吴渊着实惴惴了一些日子。他一直怀疑幕后的贵人就是李大元,只怕自己这饭碗要端不住。好在一直风平浪静,如果这事儿真的跟李大元无关,就是吴渊的成就起了决定性作用。
李大元被法警带进法庭的时候眼神落在了坐在边缘的吴渊身上,他一愣,随即就漠然地转过了头。
审判员的第一句话就让吴渊大吃一惊:被告李大元,曾用名吴渊……怎么李大元还曾用过跟自己相同的名?吴渊盯着李大元那张到老不改的娃娃脸,眼前似乎有一层云翳即将被拨开,他急切地想抓住什么,却还是看不清楚。
经过了冗长烦闷的庭审程序,审判长宣布,判处李大元有期徒刑20年。
同学们惋惜地看着李大元。当他走到大家面前时,忽然转过身子,扑通一声跪在吴渊的面前。
所有人大吃一惊,吴渊赶紧弯腰去扶他,那一刹那脑子里豁然一亮,一件往事跳了出来。那些年曾有同学开玩笑说李大元是蔡老师的私生子,他们的娃娃脸一模一样,而蔡老师也的确因为各种传闻导致家庭失和。当然这都是小道消息,蔡老师管教李大元格外严厉倒是真的。这个念头一闪即过,一句足以吓住吴渊的话脱口而出,声音大得让他自己都吃惊:“李大元!当年,你比我学习差得远!我考上了对不对?是蔡老师跟你合谋,让你顶替我上了大学?对不对?”
李大元低垂着头费力地站起身,良久才吐出两个字:“报应!”
盯着那个夹在法警当中的臃肿背影,吴渊的脸抽搐成了一团,他捂着脸慢慢瘫坐在地上:可怜的人,你早该想到的,如果不是这大贪官出于愧疚起了恻隐之心,枪手发文、请记者、特招公务员……命运哪会如此怜悯你?
福佑儿孙的风水宝地成为葬送李大元锦绣前程的坟墓,他已经一败涂地,要查清当年的事并不难。可当事人已经死的死,倒的倒,查清了又怎么样呢?吴渊一遍遍回味着这悲惨的大半生,终于发出一声短促的苦笑,鼠标一点,删除了那篇只差结尾的散文。
〔本刊责任编辑 吴 俊〕
〔原载《百花·悬念故事》总第34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