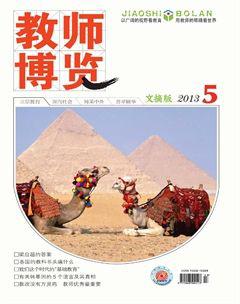偏执狂瓦格纳的音乐之路
苏禾
2012年12月4日起,国家大剧院连续上演5场德国作曲家瓦格纳的歌剧《罗恩格林》,这是该剧自诞生162年来首次登上中国舞台。该剧导演、意大利人强卡洛·德·莫纳科曾担任过瓦格纳孙子维兰德的助理。神话般的舞台、宏伟壮丽的音乐、原汁原味的演唱,使该剧成为2012年国家大剧院歌剧的收官之作,也为国家大剧院五周年庆典拉开序幕。国家大剧院在2012年4月还曾上演瓦格纳的另一部歌剧《漂泊的荷兰人》,这是国内首家在一年内上演两部瓦格纳作品的艺术机构,这种厚爱也是为了向瓦格纳诞辰200周年、逝世130周年致敬。
19世纪的德国群星闪耀,声名显赫的音乐巨星就有贝多芬、韦伯、门德尔松、舒曼、勃拉姆斯、瓦格纳等人,而瓦格纳算是其中争议最大的音乐家。他一生跌宕起伏,思想偏执,是个可怕的人物:谎言家、骗子、夺人妻者、败家子、背叛者;反犹太主义、反天主教、敌视法国、有妄想症。世人一方面鄙夷他的为人,另一方面又为他的音乐着迷。
理查德·瓦格纳长相并不讨喜,短小的身板顶着一个硕大的脑袋,有些病态,事实上他本就神经脆弱,有着夸大妄想的毛病。他确信自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戏剧家、最伟大的思想家、最伟大的作曲家之一。他侃侃而谈,喋喋不休,像是莎士比亚、贝多芬和柏拉图三者附体,而话题中心就是他自己,并且他一味坚信自己总是对的。无疑瓦格纳有些神经质,样貌不佳,却有天赋,运气不太好也不太坏。
漂泊的德意志人
1813年5月,瓦格纳出生于德国莱比锡,6个月大时父亲就病逝了,母亲改嫁给了父亲的好友,一个集演员、画家和诗人才华于一身的戏剧演员盏耶尔。继父给了瓦格纳良好的教育,为他打开了戏剧和音乐的大门。幼年时,他对韦伯的歌剧《自由射手》非常着迷,苦练钢琴技巧,后来继父就将韦伯介绍给他。这位作曲家、指挥家、钢琴演奏家将“一种对音乐的热情”灌输给了瓦格纳。17岁时,瓦格纳进入莱比锡大学主修哲学,却对音乐产生浓厚兴趣,20岁就成为了维尔茨堡剧院的合唱指挥,不久在柯尼堡和里加歌剧院担任指挥,从而有机会近距离接触舞台与歌剧。可惜26岁时瓦格纳已经负债累累,不得不带着戏剧演员的妻子米娜以及一条纽芬兰狗,坐船去往当时欧洲的文化中心巴黎。在巴黎的3年,是其一生中最贫困的时期,人才济济的巴黎没有瓦格纳施展才艺的舞台。尽管生活窘困,他仍潜心创作,同时广交社会文化名流,与作曲家李斯特、柏辽兹和诗人海涅等人交往密切。1842年,瓦格纳在巴黎创作完成的歌剧《黎恩济》终于在德累斯顿歌剧院上演,一举成名,于是他得以回到德国。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爆发,瓦格纳积极投身于德国的革命潮流中,1849年的“五月暴动”失败后,瓦格纳遭到通缉。于是他又开始了逃亡生涯,在李斯特的帮助下他逃往瑞士苏黎世。这一次逃亡长达12年。
在瑞士,无固定收入来源但生性挥霍的瓦格纳不到5年就背上1万法郎巨债。其间他接受伦敦爱乐协会邀请指挥音乐会,但收入菲薄。在这期间,他曾染上疟疾和丹毒,身体遭到严重摧残。幸运的是,瓦格纳遇到了大富豪奥图·威森东克夫妇,他们被瓦格纳的音乐所吸引,成为他在瑞士期间最亲密的朋友和赞助商。有了威森东克夫妇的支持,瓦格纳举办了“苏黎世音乐节”,可以去其他国家考察和学习,生活品质也有很大提升。可瓦格纳爱上了威森东克的夫人玛蒂尔德,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就是为玛蒂尔德而作,这段暖昧感情被瓦格纳的妻子发现,也引发威森东克的家庭风波,1858年瓦格纳不得不离开瑞士,逃到意大利威尼斯。
1860年瓦格纳得到政治特赦回到德国,但生活依然拮据。他在莱比锡、维也纳等城市指挥音乐会赚取的微薄收入,无疑是杯水车薪,狼狈不堪的生活令他几乎陷入绝境。穷途末路之际,他遇到了贵人,1864年5月,瓦格纳前往慕尼黑觐见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二世,一见面路德维希二世就给他一个热情的拥抱。这位国王是个疯狂的瓦格纳崇拜者,瓦格纳也因此得到前所未有的款待。国王帮他还清债务,提供豪宅,为他的音乐创作扫清一切障碍。国王的热情引起其他人的嫉妒,担心瓦格纳会影响国王的政治立场,于是瓦格纳被迫离开德国前往瑞士,不过仍得到国王一如既往地慷慨解囊,创作的歌剧《纽伦堡的名歌手》在慕尼黑得到首演,由他的好友、著名音乐家冯·彪罗担任指挥。就在这段时间,瓦格纳与彪罗的妻子、李斯特的私生女柯西玛坠入爱河,1869年他们的儿子齐格弗里德出生,瓦格纳为此创作了歌剧《齐格弗里德》,第二年等到柯西玛离婚,两人正式结婚。1872年,路德维希二世出资在拜罗伊特筹建新的歌剧院,瓦格纳全家也迁到了拜罗伊特。拜罗伊特歌剧院有个剧场专门用来演出瓦格纳的戏剧,这种特殊待遇在全世界上所有剧院中是极为罕见的。
歌剧改革家
瓦格纳是一个有野心的音乐家,年轻时博览群书,13岁时就已翻译过荷马史诗的前12卷。他希望将音乐、文学、哲学、历史等学科集于一身,超越音乐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人物。他在14岁时创作了人生第一部剧本,一出模仿莎士比亚作品的五幕悲剧《劳伊巴德》,只是剧情较为血腥,剧中42个人物全部死去。他的第一部成名之作是《黎恩济》,但是随后在德累斯顿歌剧院上演的另两部歌剧《漂泊的荷兰人》和《汤·豪瑟》却没有取得如前者的赞誉。
在创作《漂泊的荷兰人》《汤·豪瑟》和《罗恩格林》三部歌剧时,瓦格纳就已经有意识地要改变当下的歌剧创作。流亡瑞士期间,他写下了《艺术与革命》《未来艺术品》《歌剧与戏剧》等著作,以此阐明自己的艺术观点和歌剧改革思想。他提出,在未来的歌剧中,音乐、歌词与舞蹈等必须综合成有机整体,交响乐式的发展是戏剧表现的主要手段。其后期的8部歌剧都是基于这种改革理念而创作出来的。1868年,歌剧《纽伦堡的名歌手》在慕尼黑首演,它以生动的音乐语言取代了深奥沉重的戏剧表现,除了传统的咏叹调、二重唱,还有和谐的五重唱,管弦乐的表现力也更为丰富绵密,规模更加宏伟,展示了瓦格纳与众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尼龙伯根的指环》是瓦格纳最为重要的作品,创作历时20年,是一部四联歌剧,其对欧洲的社会生活和人们的思想本质都有精辟揭示。由于歌剧的演出时间长达12小时,没有一家剧院能够上演这部庞大的歌剧,为此他不得不到处筹资新建剧院,于是就有了后来的拜罗伊特歌剧院。1876年8月新剧院正式落成,《尼伯龙根的指环》的三部剧在这里完整上演,德国皇帝威廉一世、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二世都出席了公演,李斯特、圣桑、柴可夫斯基等音乐家也前来捧场。
瓦格纳一生共创作了16部歌剧,其中14部成为世界经典歌剧。他的歌剧没有咏叹调和宣叙调的区别,所有声乐唱腔完全根据剧本的需要,因此歌唱居于次要位置,独唱演员只是诠释者,而非创作者。这也使得瓦格纳歌剧对演员要求更高,一方面是曲谱记忆难度加大,另一方面是演唱的声音要穿透强大的管弦乐队,对嗓音要求更高。因此在瓦格纳歌剧上演时,唱破音的概率比较高,甚至把嗓子唱毁了的也大有人在,有人戏言瓦格纳是“毁人不倦”。此外,由于整部歌剧上演时间长,对演员的体力也是个考验。他很早就意识到,只有自己创作的剧本才能符合自己的要求,他在作品构思和处理、乐器的运用、舞台布景及灯光处理上都有独到见解。瓦格纳对后来的歌剧创作影响深远,布鲁克纳、马勒、理查·斯特劳斯、圣桑、普契尼等作曲家,都或多或少受到他的影响。
著名的“瓦格纳症”患者
在谈到瓦格纳的音乐成就时,不能绕过他的哲学思想。19世纪30年代,他是“青年德意志派”;到了40年代,他追随费尔巴哈和蒲鲁东,是一个社会主义者;50年代初开始接受叔本华的悲观哲学,晚年又转向神秘主义。这种复杂庞大的世界观和思想观,对他的创作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而他不仅在世界音乐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甚至影响了一些世界名人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乃至改变人类历史。
在医学上有种病叫“瓦格纳症”,即“音响震颤麻痹”,指受到瓦格纳的作品及言论刺激后,中枢神经组织发生病变,表现为崇拜瓦格纳,情绪波动不稳,爱憎极端偏激。在“瓦格纳症”的患者名单上,有许多耳熟能详的名字:哲学家尼采、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二世、种族主义理论家张伯伦、指挥家冯·彪罗、音乐家布鲁克纳、纳粹头目希特勒等等。
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二世12岁时读到瓦格纳的论著《未来艺术品》,就开始患病了。他沉迷于瓦格纳歌剧,热衷修建歌剧中描述的城堡宫殿,因为忙于看瓦格纳歌剧排练而取消了与未婚妻的婚姻,以致终身未娶。他不仅让瓦格纳回国,还为其慷慨解囊,总共为他支付了25万马克。后来由于修建各种城堡耗尽国库,路德维希二世1886年被迫退位,给他的家族留下1400万马克的巨额债务。他的经典语录是:“我不爱女人,不爱父母,不爱兄弟,不爱亲戚,没有任何人让我牵挂,只有您(瓦格纳)!”
德国哲学狂人尼采,中学时在同学家中用钢琴弹奏了《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自此视瓦格纳为完美的偶像,1868年登门拜访,成为瓦格纳的门徒,但后来又与他决裂。在瓦格纳的“异常强烈的刺激”下,尼采完成了《偶像的黄昏》《人性,太人性的》《瓦格纳事件》《尼采反对瓦格纳》《看,这个人》等哲学论著。尼采形容“瓦格纳是一种病菌”,“瓦格纳之发生作用,犹如连续饮用酒精饮料,使人麻醉,使人胃液增生”。
纳粹德国头子希特勒17岁时观看了《黎恩济》的演出,从此对瓦格纳终身崇拜。在维也纳求学期间经常买站票去听瓦格纳的歌剧,光是《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就听过34遍。在许多集会上,瓦格纳的《众神的黄昏》片段频繁响起,他让从前线回来或将要奔赴前线的官兵,前往拜罗伊特歌剧院欣赏瓦格纳的歌剧,作为最高奖赏。他继承了瓦格纳的反犹观点,二战期间瓦格纳的音乐经常被用作集中营中处决犹太人时的背景音乐,因此以色列至今仍拒绝上演瓦格纳的作品。
1883年2月13日,理查德·瓦格纳因心脏病复发在威尼斯逝世,几天后他的遗体运往拜罗伊特,这个“漂泊的德意志人”终于结束漂泊安眠于此。威尔第得知瓦格纳逝世后,在信中写道:“悲!悲!悲!瓦格纳死了!!!大人物已消失,在文化史上留下伟大痕迹的那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罗曼·罗兰说:“我们需要瓦格纳的音乐,因为它给我们带来的不是死亡,而是生命!”
(解 敏荐自《看世界》2013年第3期)
责编:袁海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