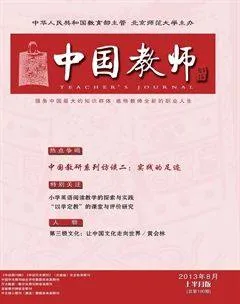校园暴力旁观者的调查研究
美国国家犯罪受害者调查(National Crime Victimization Survey)1993年到1999年对12岁及以上孩子的家庭调查显示:在学校发生的袭击和抢劫案中,80%的案件有一个或多个第三方在场[1]。康奈尔(O’Connell)等1999年的研究发现,在初中,85%的校园欺负和暴力事件有至少一个旁观的同辈在场,一半以上的事件中有两个以上的旁观同辈在场[2]。可见,旁观者在场是校园暴力的一个重要特征。但是在我国,作为校园暴力第三方的旁观者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研究。本课题组通过对5个省份25所中学的2 500名学生的问卷调查,了解到我国中学生在校园暴力中旁观的现状影响因素等,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干预校园暴力的新途径。
一、旁观者及其分类
在校园暴力的语境中,旁观者是指目睹了打架及其他身体、言语攻击行为的人。国内学者蔡唱认为,“旁观者”主要是指紧急事件发生时现场临时聚集起的众多围观者,他们与实践事件本身并无联系,但从社会的伦理角度看,他们具有某种不可推卸的道德义务、责任,因而具有某种精神联系[3]。吴妮则从事件所涉及的人群类型对旁观者进行了界定,她把旁观者简单地定义为“那些既不是欺负者又不是受欺负者的人群”。她还将旁观者分为3个类型,即强化者、防卫者和局外人[4]。
以上这几个概念都强调了旁观者观察争执与冲突的“当下性”,而忽略了在暴力事件发生前就已经掌握相关信息的这一群体。这个易被忽略的群体被称为“潜在旁观者”,笔者认为这一群体也属于旁观者的行列。因此,本研究中的“校园暴力旁观者”,既包括事先已经掌握即将发生暴力信息的潜在旁观者,也包括校园暴力事件发生时围观的群体。
结合以上对校园暴力旁观者概念的分析,笔者将校园暴力旁观者的特征归纳为以下四方面:一是时间上的潜在性与当下性;二是旁观者聚集的临时性和无组织性;三是旁观者之间关系的无关性与无作为的一致性;四是潜在功能性。旁观者不仅仅是一个消极的看客,通过他们的作为和不作为,可以很大程度上影响校园暴力是否发生和怎样发生。在此基础上根据旁观者的行为类型可将其分为四类:协同欺负者(协助施暴者捉弄、折磨受害者)、煽风点火者(通过一定的煽动性语言、姿势或行为鼓动施暴者)、置身事外者(保持中立,不介入将要发生或正在发生的校园暴力事件)和保护者(安慰、帮助受害者,并努力制止暴力行为)。但这里要注意的是,协同欺负者与校园暴力参与者的区别在于,协同欺负者事先并不知情,只是偶遇到校园暴力事件发生,便落井下石,协助施暴者。
二、校园暴力旁观者的现状
本课题组按照目的性抽样和随机抽样相结合的原则,于2012年9—10月对山东、河南、江西、广西、内蒙古5个省份的初、高中,按照重点、普通和职业中学三种分类抽取5所中学,并从每所学校完全随机抽取100名学生。本课题组对被调查者采用入校调查的方式,共发放问卷共2 500份,有效回收2 434份,回收率为97%。全部问卷中,男生1 127人,女生1 297人,10人性别缺失。
1.旁观者的现状
本课题组的调查发现:81.4%的学生曾经做过校园暴力的旁观者,而且34.7%的学生多次旁观过校园暴力。可以说,校园暴力因其发生地、暴力双方至少有一方是学生等特点,使得旁观者在场的可能性非常大。具体来说,在1 980名旁观者中,有33%的学生在小学时旁观过校园暴力事件,67%的学生在初中时旁观过校园暴力事件,33%的学生在高中时旁观过校园暴力事件。而旁观的校园暴力事件类型包括:77.1%的学生旁观过“打群架”,60.6%的学生旁观过“两人打架”,50%的学生旁观过“欺负弱小”,12.8%的学生选择了“勒索钱财”,10.2%的学生选择“持刀威胁”,还有3.1%的学生看到过其他类型的校园暴力。
笔者对比2005年北京市7所中学的调查结果,发现旁观多寡除了跟该类型暴力发生频率相关之外,与暴力类型的观赏性、旁观人数多少、旁观者的行为反应预期等都会有关系。所以当问及被调查者“遇见哪种类型的校园暴力更可能停下来观看”时,选择比例由多到少依次是:打群架59%、两人打架43.2%、欺负弱小24.8%、持刀威胁13.3%、勒索钱财5%。
在旁观的地点上,调查结果显示:最多的是上下学路上,占55.2%;其次是校门口,占45.5%,紧接着是教室,占42.5%,操场上,占41.6%,然后厕所,占33%,宿舍,占23.3%。可以说,缺乏监管的地点容易成为校园暴力的发生地,同样容易成为旁观者聚集的地方。另外,在调查中发现,49.6%的学生曾在网上观看过校园暴力视频。可见,网络会成为校园暴力“二次传播”的途径。
在对校园暴力的反应的测量中,我们通过前后两道题的对比来测试,一个是“第一次看见校园暴力的时候,你怎么做的”,另一个是“现在看见校园暴力,你会怎么做”。其中第一次看见校园暴力,最多的是“在旁边观看”,占19.8%;其次是“不记得了”,占17.2%;然后是“赶紧溜走”,占16.8%;“吓呆了,不知所措”,占9.2%;“上去制止施暴者”和“在旁边呐喊加油”的分别只有1.8%和1.6%。而在“当下看见校园暴力的做法”中,31.6%的学生表示会“告诉老师或报警”,29.3%的学生选择“赶紧走开”,17.1%的学生选择“静静观看”,2.2%的学生拿手机来拍,14.1%以上的学生选择“情况都有可能”,表示“上去制止施暴者”和“在旁边呐喊加油”的仍然最少,分别占2.5%和0.6%。对比这两项选择,可以发现,学生在旁观校园暴力这一事件上的态度基本没有变化:原来持袖手旁观态度的现在仍然主要持旁观态度,原来溜走的,现在仍然溜走。可以说,对校园暴力旁观的态度变化不大。
2.不同社会距离下对校园暴力旁观者的评价
已有研究中经常出现将旁观者等同于道德冷漠者、法律意识淡漠者或者社会责任扩散及从众者等消极评价,如万俊人教授认为“道德冷漠”是一些社会事件旁观者的主要原因,朱力也认为,盲目从众、屈从压力也是一个心理原因[5]。那么,中学生会如何评价旁观者呢?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学生对旁观者的普遍观点和评价比较中立,他们不赞同用“道德败坏”“法律意识淡漠”“心理阴暗”等话语评价旁观者,或者至少持不否定的态度(见表1)。因此学校在教育和引导旁观者在校园暴力事件中积极干预的时候,不可以盲目地批判旁观者行为,而是要因势利导,努力抓住旁观者的积极资源,化旁观者为积极干预者,从而有效制止暴力。
但当问及如果自身作为校园暴力的受害者,会如何看待旁观者的时候,学生的观点发生了变化,大多数持反对态度(20.8%的被调查者觉得“很讨厌,他们和那些欺负我的同学一样可恶”;35.8%觉得“不能理解,认为他们很冷漠”);但也有30.4%的被调查者觉得可以理解,认为同学们都喜欢看热闹;3.7%的学生很赞同,他们遭到校园暴力时自己就很喜欢看;其他占9.4%。可见,社会距离与对旁观者的态度影响较大。
而对于网络中的校园暴力旁观者,以“熊姐打人视频”为例,本课题组调查如何看待旁观者在熊姐打人事件中的角色作用。调查发现:50.4%的学生表示“不能理解,觉得他们冷漠且缺乏同情心”;19.8%的学生表示“不喜欢但觉得无可厚非”;13.5%的学生觉得“他们很坏,是帮凶”;9.9%的学生认为大家“都喜欢看新鲜事和热闹事,如果自己在现场也会观看”;6.5%的学生选择其他。而对于观看网络校园暴力,被调查者中,35.7%的人认为“这样不对,会使校园暴力推广”;32.6%的人认为“这样是对的,会帮助受害少女,使肇事人受到网友和舆论的谴责”;16.4%的人表示“不知道对不对,但觉得他们很无聊”;10.4%的人认为“无所谓对错,他们爱怎样我们无权指责”;4.9%的人选择了其他。
3.对旁观者影响的评价
校园暴力事件本身就形成了一个生态圈,旁观者的在场必然会对施暴者、受害者、其他旁观者及其他未在场的人产生影响。因此,本课题组对“你认为旁观者在场,会对几方面造成影响”进行了调查。
首先,对于施暴者来说,29.6%的被调查者认为,他们会觉得“爽极了,变本加厉折磨受害者,表现自己的威风”;27.8%的人无所谓,有没有旁观者对他们没有影响;24.2%的人不好说;18.5%的人表示会觉得有压力,不敢或不好意思继续,从而减轻对受害者的暴力或欺负。其次,对于受害者来说,49.3%的被调查者会认为他们“觉得会更羞辱”;25%的人觉得“有希望获得帮助”;6.3%的人觉得“无所谓,没影响”;19.3%的人不好说。可以说,旁观者在场,会增加施暴者的“气场”,加剧了对受害者的伤害。从这一点上看,将旁观者视为“问题”也不为过。
另外,对于其他旁观者来说,若已有旁观者在场,15%的被调查者表示会一起观看;1.5%的人拿出手机来拍;0.7%的人为打架者助威。而对于潜在的旁观者来说,当听到别人描述学校发生的校园暴力时,会有17%的被调查者“遗憾当时没有在场”。所以说对校园暴力事件来说,旁观者在场会造成一种环境压力,这种环境压力对施暴者、受害者和其他旁观者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而且更多的是一种负面的影响。
三、旁观者的影响因素
1.旁观者效应
对旁观者不作为的现象,社会学中常常用“旁观者效应”来解释,指在紧急情况下由于有他人在场而没有对受害者提供帮助的情况。救助行为出现的可能与在场旁观人数成反比,即旁观人数越多,救助行为出现的可能性就越小。用社会心理学的话语解释就是利他行为会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即个体对于紧急事态的反应,在单个人时与同其他人在一起时是不同的,由于他人的在场,个体会抑制利他行为——社会心理学将其称之为“责任扩散效应”[6]。
在本课题组的调查中,也表现出了“旁观者效应”,即当观看校园暴力时,81.5%的被调查者表示身边还有其他旁观者:其中,54.1%的学生表示“当时身边有很多人”,27.4%的学生表示“身边有几个人”。当问及“在什么情况下,你更可能旁观”时,69.3%的学生选择了“有很多人观看时”,14.1%的学生选择了“有几个人旁观”,1.9%的学生表示即使无人也会去围观。可见旁观者的问题不在于旁观者的“病态”人格,而在于旁观者对其他观察者的反应,是由于在紧急状态下有其他目击者在场,旁观者才无动于衷。如果学校希望学生报告正在发生的或可能发生的暴力,他们必须采取行动克服这种群体抑制效应。
2.同心圆结构
已有研究发现,旁观者与施暴者、受害者之间的关系距离会影响旁观者的干预行为。这一点类似费孝通先生所提到的“同心圆结构”理论,即以自我为中心,按照与自我关系的亲疏远近形成一个个大小不等的同心圆,与圆心距离的远近会成为人们处理人际关系、采取行动的重要依据[7]。鲁特科夫斯基(Rutkowski)等所做的实验研究表明,与陌生的群体相比,有社会关系联系的群体有时能克服“群体抑制”效应,更有可能对紧急情况采取行动[8]。
在本课题组的调查中,我们也发现了这种关系距离对旁观者作为的影响。如果认识施暴者或受害者,积极干预行为会多得多,超过一半的学生会采取“出面制止”“告诉老师或报警”等积极干预的方式。而如果不认识暴力双方,那么最多的选择是“赶紧离开”,占39.1%,其次是“告诉老师或报警”,占27.8%,然后是“静静旁观”,占22.5%。可见,大多数被调查者都倾向于在一边旁观“陌生人”之间的校园暴力,而对于自己认识、熟悉的施暴者或受害者,个体更多地倾向于干预(见表2)。因此,从有效制止校园暴力的角度来看,学校是可以通过增加学生交往和认识度,打造“熟人社会”的方式来有效促进旁观者行为方式的转变。
3.结果期待
结果期待是指个体对自己完成某一行为的后果所做的推测与判断,旁观者对自己干预结果的预期也会影响旁观者的行为。澳大利亚学者肯等的调查分析结果表明,旁观者干预校园暴力与5个变量相关:对于受害者的同情态度、来自他人的预期和社会规范压力、有过帮助受害者的干预经历、高的自我效能感和有过被欺负的经历。随后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有过帮助受害者的干预经历、同情支持受害者的态度和朋友的社会期待是影响旁观者选择积极干预的原因[9]。可见,曾经成功的干预经历会提高学生的结果期待,从而促使他更积极地干预校园暴力。在本次调查中,被调查者对于“旁观者不报告老师或警察的原因”的描述中认为“害怕被报复”的占43.5%,可见对结果的负面预期是导致旁观者消极反应的主要原因。
四、变旁观者为积极的干预者
校园暴力是一个过程,其中蕴含着一个复杂的互动状态,因而绝不仅仅是施暴者和受害者之间的事,它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所处的微观社会环境的影响,包括作为旁观者的第三方的反应与行为。研究发现,无论是青少年还是成人,旁观者在场都能提供激发或阻止暴力的关键的社会约束力[10]。因此针对前文所得出影响因素提出有针对性的措施,这些措施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让更少的人旁观校园暴力,二是让旁观校园暴力行为的人更多地成为出于善意目的的积极干预者。
首先,增加同学之间的相互了解,营造带有“熟人社会”性质的学校社区。学校可以通过“结对子”“同伴互助”等方式增加不同年级、班级之间的人际交往以达成学生之间的相互认识、了解,通过减少学校社区模式的差序层级,增强学生之间的私人感情——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沾亲带故或非亲即故”。如此一来,即使校园暴力行为现场有较多旁观者,也会有一些人能感受到比别人更加强烈的责任,而不是大家“平等地”互相推诿或等待别人去帮助,即减少差序层级可以有效地减少校园暴力行为发生时的责任扩散和陌生人效应。
其次,建立明确、健全的预防及处置机制。有学者指出:旁观者成为施暴者的呐喊助威者还是受害者的保护者,是积极干预还是消极干预,取决于社会和环境中对规则、责任标准和社会期望的规定和清晰程度[11]。因此,学校应当建立明确、健全的预防及处理校园暴力机制,对施暴者予以惩处。明确清晰的规范化机制可以为旁观者提供积极的结果预期,这样才能有效地将旁观者纳入到干预系统中来。
注: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11年度课题“校园暴力的旁观者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1YJC880091)。
参考文献:
[1][10][11]Stueve, A., Dash, K. et al. Rethinking the Bystander Role in School Violence Prevention[J]. Health Promotion Practice, 2006(7).
[2]O’Connell, P., Pepler, D., & Craig, W. Peer Involvement in Bullying: Insights and Challenges for Intervention[J]. Journal of Adolescence, 1999(22).
[3]蔡唱.论旁观者的不作为侵权行为——以民事救助义务的确立为视角[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2).
[4]吴妮.旁观者群体对欺负行为影响的研究综述[J].中国校外教育(理论),2009(1).
[5]朱力.旁观者的冷漠[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1997(2).
[6]巴伦,伯恩.杨中芳等译.社会心理学(第十版)[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501.
[7]费孝通.乡土中国[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27.
[8]Rutkowski, G. K., Gruder, C. L., & Romer, D. Group Cohesiveness, Social Norms, and Bystander Intervention[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83(44).
[9]Rigby, K.& Johnson, B. Student Bystanders in Australian Schools[J]. Pastoral Care in Education, 200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