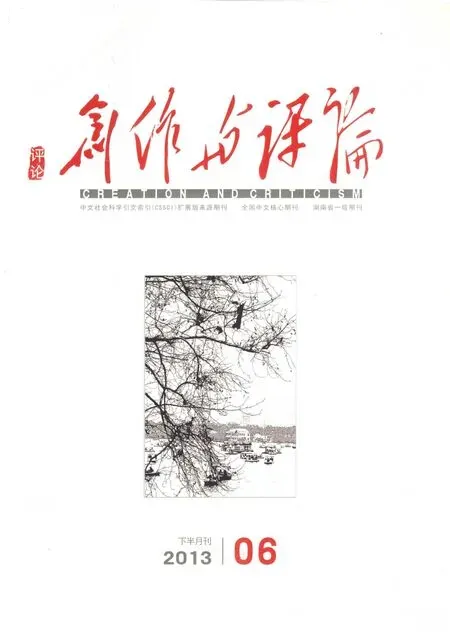诗意:在虚无世界的故事尽头——王威廉小说论
○ 房 伟
新世纪以来,小说的叙事冲动似乎在终结,又似乎在重复发生。无论小说形式探索,还是人性深度的掘进,似乎都到了“无以为继”的地步,诸多禁忌,包括政治的自觉规避,新时期纯文学规范,都成为创新的巨大枷锁。而现实种种的光怪陆离与触目惊心,只能以黑话和隐喻的形式,曲折地出现在文学中。于是,故事便成了最后的救命稻草。但人们并不信任故事,人们只在故事中得到廉价快感。人们希望读细腻感人的故事,伤感凄婉的故事,通俗曲折的故事,暧昧煽情的故事,浪漫甜蜜的故事,悲壮激情的故事,甚至纯文学范围内家长里短的故事,永远也说不完的婚外情的故事……故事像瘦肉精或增白剂,作者们千方百计地搜集故事,以涂抹苍白的小说面孔。然而,我们的故事没想象力,没有真诚,或者说真诚不多,早已被封闭的生活耗尽。我们没有直入人心的故事,震撼灵魂的故事,也没有匪夷所思的故事,故事之外的故事。于是,虚无就成了故事最后的与最强大的敌人,也成了我们生活中最大的真实。
从某种意义上讲,青年作家王威廉,就是一个“反故事”的作家,尽管他的故事同样可以讲得非常精彩。他是一个黑暗与光明交织的天使,虚无与悲情共存的信徒。在他笔下温暖潮湿,又不乏黑暗晦涩的文字王国里,我们可看到他从好孩子变成充满矛盾的怀疑主义者的心路历程。他的小说中存在两种笔调,一种是纯粹抒情性的,一种是黑暗哲学性的。他时常表现出这两种笔调的杂糅。黑暗的哲学,为现实提供虚无真相,而纯粹的抒情,则能为黑暗提供精神的终极疗治。他的很多作品都透露出了大学中文系出身的文学基础,我们能从之看到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对文学趣味的训练。那是从鲁迅到海子等一系列文学家所铺垫的。抒情性的笔调,表现在他对一系列抒情女性形象的塑造。这些女性都具有高贵品质与浪漫情调,又是作者超越虚无与黑暗的生存现实的希望所在。《信男》中美丽的文艺学硕士琪琪,只有她才能理解主人公写信的初衷。《暗中发光的身体》中的孟晓雪,不惜以自杀挽救男友绝望的心境。《辞职》中的女白领鹳,引导主人公真正有勇气面对生存倦怠。《倒立生活》中的神女,在诗歌和绘画的蛊惑下,和主人公一起体验了倒立生活的乐趣。《秀琴》中善良的秀琴,为了丈夫之死而心怀愧疚,心甘情愿地以丈夫宝魁的名义活了20年。而《梦中的央金》与《铁皮小屋》则写得干净、神秘、浪漫,基本符合上世纪90年代抒情文学的规范。当然,如果穷究这些小说的底色,我们却会发现一些完全不同的东西。《梦中的央金》写了健康蓬勃的藏族姑娘央金为我带来的心灵净化,有些乌托邦色彩,然而,背景却是主人公对大都市生活的极度厌倦。《铁皮小屋》写了孔用教授于功成名就之时的自杀身亡,探讨的却是当铁皮小屋的阅读激情变成乏味的生活后,人心面对黑暗虚无的抗争。梦幻般的抒情,甚至因绝望而变得感伤。《看着我》中,因现实的压抑,主人公开始写诗,然而,这种内心唯一的隐秘抵抗也被领导破译,领导也写诗,且强迫主人公读他的诗,而最后导致主人公精神崩溃的是,当他历经精神折磨后,写了一个献媚的“读诗报告”,却受到了领导的无情嘲讽。最后,主人公以刺向领导的尖刀,回应了诗意的抵抗与自尊。《老虎!老虎》也写出了绝望的青春抒情之死。老虎、巴特尔和“我”是多年的好友,曾经共同在广州打拼,然而,生活的重压让老虎几次自杀未遂,就在我们以为老虎已走出死亡阴影的时候。老虎来广州和朋友们欢聚,并在灯火辉煌的桥头一跃而下,“像一只暗夜中的蝙蝠”,以完美的死亡祭奠了残酷青春。小说最后写道:“那个蝙蝠样的身影像梦魇里的毒蛇撕咬着我,我攥紧拳头,掌心全是汗。巴特尔越跑越快,我大口喘着气,用尽全力追赶着。我感到自己的身体也随之变得越来越轻,越来越稀薄,仿佛周围这些坚硬的灰色正在进入自己、驱散自己,让自己渐渐变成一个谁都无法认识的陌生人。”刻骨铭心的生存悲剧感,渗透于青春生命的逝去之中,令我们格外感到沉重。
于是,在王威廉的文字森林中,除了和煦的阳光,我们更多看到了“森森的鬼气”。这些鬼气有如黑暗狞厉的雾瘴,弥漫于森林之上,提醒我们世界的真实底色,警告我们自以为是的肤浅乐观。那些鬼气便是虚无的力量。虚无让他的小说有了本质性的力量,虚无让他厚重、深刻,犀利,勇敢,摆脱日常叙事的陈辞滥调。虚无也让王威廉找到了一种小说语言。这是一种伪装成现实主义的哲学化语言。王威廉试图探究世界和人之间那些诡异的关系,而揭示的正是世界失去意义后,在繁华的消费景观与壮丽的政治图景的底板上,人性支离破碎的惨烈与无处救赎的悲伤。现实出现在他的笔下,也不再是简单的批判或认同,而是呈现出一种本体性结构维度。这种本体性结构维度,使得世界不再是逻各斯的意义结合体,而呈现出意义丧失后,或者说意义空洞化之后,世界在不同存在维度上的混乱状态。很久以来,我们的文学一直没正视虚无的存在。新时期文学以来,无论是与政治结合的新改革小说,伤痕小说,还是努力突破政治规范,回归文学本体的寻根小说和先锋小说,虚无一直作为“负能量”而存在,无论是新时期高歌猛进现代化叙事,还是先锋小说的语言迷宫,虚无或被作为思想病,或是语言实验的副产品,很少有作家能如鲁迅一般,正视世界的虚无底色,拥有反抗绝望的深刻与智慧。而《废都》、《一腔废话》等作品之中,虚无更变身为废话的狂欢,欲望的教谕与浮躁的表演。虚无是点缀,是由头,是写作策略,是否定者,但虚无决不能成为世界本质。然而,新世纪中国文化语境面临的一大问题就是,当我们为新时期文学的丰盛幻觉而喝彩,意义却在不知不觉中被终结了。无论是物质致富的创业神话,还是汉语的实验与抒情的美化,我们日益中产化的文学创作界和评论界,都不能解释两极差异所导致的社会混乱状态,特别是相对物质丰裕与人们内心意义感的丧失。无论是为房子和工作在生存中挣扎的都市青年,还是在欲望中迷失的中产阶层,意义的丧失导致的虚无感,犹如巨大的旋转舞台中物质的冷酷仙境,虚无的迷津弥漫在世界的尽头,令我们不知所措。当然,王威廉的创作状态与文学思想构成又是“复调式”的。面向虚无,并没有让王威廉沉溺于黑暗之海,反而让他拥有了实践自由的勇气。他对于神秘浪漫的诗意追求,为黑暗之体装上了金色的自由之翼,让他轻盈、飞翔、想象、骄傲。由此,王威廉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认知世界的复合式装置,在这种认知中,我们看到了世界的虚无,也看到了爱与自由的终极意义,这些小说让我们在欲望和丰饶面前保持清醒,在说教和劝诱面前保持警惕,在压迫和欺辱面前保持尊严,在压抑和绝望面前保持诗意。
王威廉小说的小说世界,常呈现出很强的哲学装置性。《辞职》这篇小说乍看颇有些新生代小说的意味,那种对生活的边缘游走态度,让我们读来很熟悉,然而,该小说并不是就辞职一事探讨边缘化生活,而是从这个矛盾出发,探讨常规与变异之间的哲学关系,及出走与回归之间的虚无地带。当男主人公的辞职信被鹳真地送到了领导手里,他被单位辞退了。辞职后的主人公并没有以此为契机走入更广阔的世界,而是在鹳的肉体中走向了新的沉沦。正如小说的辞职信上写道:“工作中我找不到人存在的踏实感,平时感到的都是些毫无意义的忙碌以及浪费生命的虚无感。”虚无才是他辞职真正的原因,也正是虚无导致他走向新的沉沦。由此,辞职就不是一个励志的通俗主题,也不是一个边缘化反抗的主题,而是一种在虚无中无限堕落的行程描述。它黑暗无比,却真实地令人悸动。《暗中发光的身体》为我们讲述的也不是一个有关叔嫂乱伦的故事,而是哥哥死后,虚无对人精神的伤害,嫂子为了摆脱这种伤害,不惜去当站街妓女,以自毁的方式求得心灵平安,而肉身的媾合带来的不再是乱伦的快感,而是黑暗虚无导致的短暂“幸福假象”。《没有指纹的人》,则以指纹代指现代人的自我确认,这篇小说带有浓重的“福柯意味”,它揭示了我们被控制的生存本相。当外在的标准化自我确认,成为一切日常生活的法则,没有指纹的人,也就成了一个现代社会所无法规训的人,没有规训,也就没有了安全感,没有了幸福感,也就没有了存在感。最后,失去了指纹的主人公,只有踏上了逃亡之旅。
王威廉的这些小说,我比较喜欢中篇小说《内脸》,该小说完全有资格成为中国新世纪文坛中篇小说代表作之一。小说中的第二人称非常诡异,它让小说叙事者和阅读者之间的审美距离变得复杂,充满着不断调换位置的“看与被看”的权力紧张关系。它有很强带入性,让阅读者进入人物的心理时空,制造更强烈的逼真感,从而使“内脸”这样一个哲学命题成为复杂人性的考量。小说主要讲述了一个小职员和公司女领导,及一个失去表情的女病人虞芩之间的情感纠葛。然而,小说的重点并不在男女欲望本身,而是探究人们面对世界的自我悖论和分裂。小说还探讨了性爱中的权力关系与性别意识,施虐与受虐的关系。更难能可贵的是,这篇小说叙事非常有耐心,能不断地从感性经验入手,达到哲学的反省,而小说中大量隐喻,都成为熨帖逼真的细节,以真实的细节服务于荒诞的整体。每个人都有一张灵魂的内脸,而肉体表面的脸,却又是如此不真实,甚至可根据环境变化以求得权力关系最大化,变成无数脸的面具。面具隐藏着内心,脸会变成面具,而内脸则成为灵魂的抽象象征。然而,正是在对内脸的否定中,面具脸具有了某种权力性,这种权力性来自权力压迫者本身的支配性幻觉。它以完美的假象完成了对内脸的否定与真实的遮蔽。因此,它便具有了完美理性的假象,它的大义凛然,正气浩然如同它的和蔼稳重,亲切精明,都成为一种支配性力量。女领导正是凭借面具脸获得事业成功。这种心灵与肉体的分裂,灵魂与肉身的对峙,使女领导的面具游戏具有了某种虐恋味道。而主人公和女领导之间的性爱游戏,则可以视为复杂的权力关系的映衬。现实生活中主人公被女领导欺压,而性关系中主人公依然被动,每次性交后的疱疹,就是一次灵魂受侮辱的印记。然而,这种扭曲的男女关系中,主人公不是结束被动状态,而是在被动中为自己制造“主动幻觉”,进而陷入女领导的性爱游戏不能自拔。比如,主人公几次要和女领导决裂,却因为女领导坦然承受他的辱骂,让他在性征服的幻觉中再次与之结合在一起。福柯的权力论中,权力在微观层次上从来都是双向的,面具脸对内脸的否定,必定会遭到内脸的反抗,而虞岑就是内脸反抗性的表现,不过这种反抗也是以一种悖反的情况出现的。虞芩面部表情的丧失,可以看做人性分裂的反讽。虞芩善良、敏感,温柔多情,然而,她却无法表达真实情感。或者说,她的无表情,却恰被认为是最丰富的表情,最现代的表情。它能在物质和欲望面前否定一切情感因素。因此,虞芩的内脸与外在表情的不一致,情况与女领导正好颠倒,却同样陷入意义混乱的癫狂。脸本是内心的真实反映,却成为了我们虚伪应对世界的武器。因此,虞岑完美的脸,才成为我们欺骗自己和他人的幻觉之物,成为死亡的终极象征。完美的脸比完美的心更重要,人们重视的不是真实,也不是善良,而是“完美”这一符号意义本身所到来的衍生性象征幻觉。由此,鲍德里亚有关仿像的理论,在此也得到了诠释。有了完美,就有了最大的现代性自我确认,有了在仿像世界继续生存的勇气,并因此收获他人的认可。小说中的主人公,则在明白了这一道理后,通过整容得到了一张“完美的脸”,并取得了一系列事业成功。小说结尾意味深长地写道:“而你的灵魂正在变得僵冷。你看着女领导的脸在你眼中变得越来越逼真,你感到时间在越走越慢,终于,时间停下了脚步,一切都静止了。女领导的脸静静看着你,仿佛静止的雕塑。在你的脑海中,她的脸与虞芩的水晶脸雕塑正在一点点的移动并靠近,最终,它们合二为一,你看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新人。”按照鲍德里亚的说法,仿像生产阶段,生产成为对仿照之物的模仿,再与真实无关。而在这篇小说最后,女领导的脸和虞岑的脸合二为一,成为一个新人,这个所谓的新人,不过是另一个面具脸的仿像而已,再与内脸无关,也与真实和灵魂无关。王威廉以迷宫式的哲学探索与疯狂大胆的文学想象,为我们当代社会的虚无迷失做了冷静的笔录。如果说,小说《内脸》有非常强的福柯与鲍德里亚的影响,而小说《第二人》则延续了《内脸》的话题,进而将拉康的镜像论引入了故事。小说中的大山因毁容而具有了震慑人心的力量,然而,拥有了一切物质条件之后的大山,却无法摆脱丑脸对自己心灵的折磨,而他的解脱之道则在于将主人公也变成丑脸,进而找到内心平衡。拉康的镜像理论认为,婴儿最初在镜子中才能确认自我,镜子为婴儿提供了一个主体映像,进而让婴儿对此产生了心理自我认同,即只有通过他者,才能确认自我。很明显,大山的选择如此疯狂,出乎人的意料,又深刻地揭示了人性的特征。这篇小说的情节性明显增强了悬念和故事性,人物也更为丰富饱满,然而,却似乎缺少了《内脸》带来的哲学冲击力。
另外,在王威廉的“法”字三部曲中,我感兴趣的还有中篇小说《非法入住》,这篇粗硬暴烈、狂放恣肆的重口味小说,似乎在王威廉的创作谱系之外,却透露出作家独特的文学想象力。小说表面上好像讨论的是有关都市个人空间问题,然而,在“侵犯”与“被侵犯”的故事拉锯中,小说显然溢出了规范,表现出了对恶劣生存环境中人性堕落底线的哲学思考。逼仄的生存空间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复杂、恶化,庸俗、丑陋,这样的主题其实在方方的《风景》中早有讲述,然而,王威廉的笔下并没有多少启蒙色彩,反而出现了反启蒙的反思。当主人公入租一个大杂院,他受到了鹅男、鹅男的弟弟,鹅男的女人,鹅男的孩子,还有鹅男的父母一刻不停地骚扰。小说为我们描述了一个抽象的非理性的“暴烈侵入”,鹅男一家人因生存困难导致精神扭曲,对所有弱者有天然的敌视,鹅男对主人公个人空间的侵入,完全理直气壮,恬不知耻。这既是如今高房价导致的中国人新空间危机的现实隐喻,也是对人性恶的集中操练。更耐人寻味的是主人公的反应。主人公试图反抗鹅男一家人,但他所有的努力都被化解,他被侵犯,被殴打,所有的隐私都被曝光和嘲弄。他陷入了心理的绝境。这个时候,鹅男妻子的出现,让主人公的身份发生了转移,由被侵犯者变成了侵犯者。他在和鹅男妻子的通奸中,不仅释放了肉欲,且获得了侵犯的快感。需要注意的是,他和鹅男一家的斗争,都以不触动现实法律为基础,或者说,狡猾地在现实法律的边缘地带游走。因此,暴力的侵犯与反侵犯的游戏,最后变成了丑陋肮脏,龌龊无比的“口水战”,甚至丧失了暴力本身的原始强力。这是这篇小说中最浓烈的一笔,也是最传神的一笔,王威廉毫不犹豫地写出了我们这些盛世草民们绝望的生存现实。他击中了这个煌煌盛世中最脆弱的真相。这是一个彻底黑暗虚无的世界,因为黑暗已侵入骨缝,所以肆无忌惮的恶和狡猾的躲避,就成了最实用的生存策略,而虚无则早已侵入灵魂,所以任何人性的温暖、爱和拯救,都成为无用的奢侈品和滑稽的玩笑。我们所能做的,只有不断堕落,不断从一个自已为低的人性低点,堕落向更可怕的人性黑暗的深处,谁也无法挣扎,只能沉醉于互相伤害的快感中:“你们都不说话,连大气也不敢出,仿佛一不留神恶心的秽物便会钻进你们黑暗的体腔。你们谁也没有勇气看看对方,因为你们没有勇气面对龌龊的自己。”小说结尾,当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孩出现在了合租大院,主人公重复了鹅男一家的作法,以再次的非法入住,完成了对一个新人的侵入——从这一点而言,鹅男一家成功了,他们成功地将一个普通人改造成了“黑暗的囚徒”。
很多年前,当村上春树出现的时候,文学史家柄谷行人就大胆地预言日本现代文学终结了。这种终结,其实是文学现代性所形成的一系列故事审美规范被终结了。我们千变万化的生活,早已脱离了那些宏大美好的规范。当然,我们讨论王威廉的小说,并不是说他的文字就非常完美。这个不断进步的作家,还有一些问题需要克服。比如说,当虚无沉入无边的黑暗,如何保持诗意的尊严和自信?当抒情性为虚无提供意义的超越,是否也会沦为一厢情愿的伦理抚摸?小说《暗夜中的身体》,孟晓雪自杀的情节,显然没有在虚无与抒情间找到恰当平衡。小说《秀琴》对秀琴朴素善良的品质的颂扬,还缺乏文字节制。哲学思维要如何更好融入文字肌理,形成辨识度更高的,更具特色魅力的小说语言,也是一个问题。王威廉的一些小说,故事痕迹还太重,而他试图用日常化小说语言包裹哲学内涵的作法,还不够圆熟。他的小说语言还不够简省凝练,缺乏瞬间爆破力和破坏感,有时也匮乏语言的适当节奏。小说最终为我们呈现的不是故事的心机设计,而是故事的本质状态,不是故事的情节,而是故事的存在,不是有限的故事世界,而是无限的心灵想象的诗意世界。当然,作为一名青年作家,王威廉已经表现出了非凡的创作潜力和挑战难度的勇气,我相信,在将来的创作中,他必定能克服这些问题,走向更广阔的艺术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