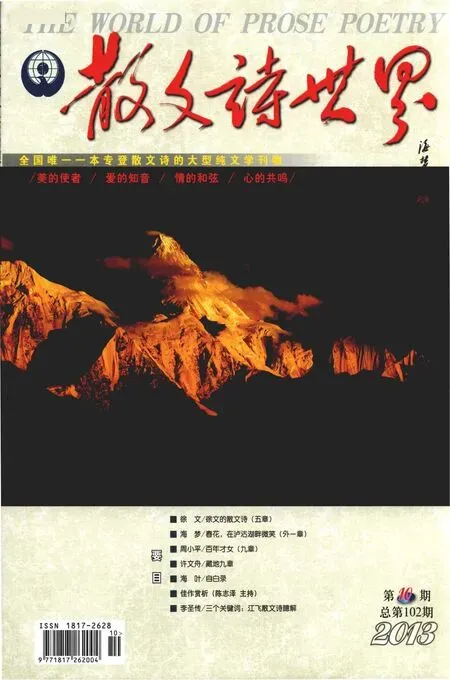藏地九章
云南 许文舟
一、桃花盐
盐以液态的方式,长眠。盐井,让一些人,与盐有相似的命运。
麻绳,啮咬着肌体,比芒康的山谷还深。负重的行走,每一枚脚印,都比盐苦咸。一粒盐经过阳光反复浣洗,才能长出让诗人联想的翅膀。
桃花盐,根本无烂漫可言哪,悬空的盐柱,是高原苦涩的母乳。
上路的马帮,其实是一次豪赌,离开澜沧江的盐,仍然有江水的迭宕起伏。无数战役,盐就是引线,卤水如镜,直播过血淋淋的杀戮。
盐回到大地,入土仍不能安。格萨尔王用食指蘸了蘸这片红土,就又把一场与羌巴的战事挑起。盐井,如同掠夺去的女人,安排了很受尊重的席位。
晒盐场上,那些沉默不语的女人,她们轻轻地抚摸水里的盐分,我的心也五味杂陈。
二、米堆冰川
1000多米宽的大河,被神引领,奔流到停顿,没有原因。
一定是刀削斧劈,让一条路止步,水说停就停,是什么收敛本该飞扬的激情?
它停下来,完全彻底,死亡没有声音,只有痛苦的表情,沉默没有表情,只有痛苦的声音。其实是生命微醺的姿容,六千米海拔的水,其实是神的花蕾。
渴望流动,恢复河流的属性,那些飞奔的石头,就是河流的脚印。摔打、磨砺、扭曲,沙粒是小小的伤,用白云包扎,我听到冰川深腹的呻吟。
每年都有一场或两场雪崩,那是冰川睡醒的发怒。带着翅膀的水停止飞,它裸得全面,我看见一滴柔软,一滴安静。
俗世的人,不要随意打扰啊!一条酣然入梦的大河,只允许春风轻轻抚慰。
三、收土豆的卓玛
淡蓝色的花朵,都被神收起,它们回到天宫,还是地狱?
现在,卓玛备下足够的时间,她要与沉默了一个季节的土豆,细细交流。土豆不挑肥捡瘦,再寡的土地,先要让微笑盈盈的花朵,表明态度。
土豆是幸福的,它们傻傻地出土,然后让卓玛一一放进围腰。远处已升起淡淡的晚霞,卓玛抖抖围腰,那些细碎的花跟着舞蹈。
那是神护佑着的古屋,薪火不熄,正等着土豆,镀上生活的温度。
有一些土豆,要走很远的山路,在城里的某个地方,羞怯地等待挑选。
卓玛唱着比土豆还补素的情歌,前一段被风掐去,后一段随水流走。我始终听不懂,收获时节的卓玛,为什么忧郁。
四、背卤水的妇女
她们是加纳村的妇女,她们让藏得很深的卤水,经过自己的背,重见天光。
她们的脚印是盐的脚印,她们从潮湿的坑洞,背着沉重的卤水,晒干的盐,有她们干涸的汗水。
苦与咸,是她们身上的两块胎记,一架木梯,二十三级台阶,开头是她们的青春,结尾有她们的暮年。
离她们最近的江水,每年都会冲毁她们的盐井。盐或粗或细,都是她们可以触摸的黄金。
已经两千年了,这口叫擦卡洛的盐井,始终含着最诱人的泪滴。几个世纪,都是这盐浸渍着路,人走远方,马失前蹄。
风马旗突然停下来,为落入江中的盐致敬。背盐的妇女,时常双膝及地,被风吹跑的一粒盐,始终没有逃脱她们比盐还粗的手心。
买一点盐吧,叔叔,我要去拉萨朝佛。
我掏出零钱,买下两小袋,之后的旅程,总不是滋味。
五、磕长头的朝拜者
这是必须的吗?
匍匐于地,就能聆听,大地的真言。他们表情肃穆,衣衫破旧,以掌击路,我真的不忍多一秒注目。
但我又不想离开他们的行程,哪怕翻越白马雪山,有被满天风雪围堵的危局。有想陪他们走走的想法,秉烛,推开夜,想陪他们从傍晚走到三更,从子夜迎接最干净的黎明。
他们之中有小孩和老人,扑入朝圣的路,日子就用肉身翻动。
让白发低到云看不见的位置,让心贴近尘土,诸神面前,低下,是一种谦卑。他们从盐井出发,滇藏线上苦咸密布。
护手板噼啪作响,诵经声响起……
我突然感到孤独。
六、哲蚌寺
朱印的大藏经,已经蒙尘,晒一晒,阳光就镀上佛的真身。
1.29米高的文殊铜境,照见妖魔鬼怪,可照得了文殊坐像生动的内心?
顺治皇帝所赐,想想应该有更深的一层用途。据说,悬镜一个时更,烛灭了两次,雷响了三声。
莲灯正被风安抚,任何一朵笑靥满面的烛光,都没有风生动。
风应该记得一场战役,箭穿过暗夜,扎进锈烛的壁炉。
那些夜光杯,那些经卷轻轻合上的光阴,或明或暗,或疾或缓,被历史册封。
风在打扫晒佛台,僧人目光有炬,一千支烛光,也燃不起空气里飘浮的冷。
七、拉萨的月光
非常适合挑一些干净的梦,绣在上面。它很薄,还只能用拉萨河边的芦花,伊人的睫毛。
还适合种小步小步的沉思,一眼一眼的怀想;适合抱一壶普洱,推开门,便与它撞上。
是一条没有源头的河流吗?有没有岸,让我略略停顿?我知道平面的月色潜藏的暗礁。沉没,实际是投向另一种怀抱。
我是绕不过一块月色的,在拉萨的夜晚,我只想知道星空谁洒了那么多钻石,我才不管它会有多蓝。
那么多人的脚在踩,一大张月光,始终纤尘不染。
八、古格城堡
浸泡在阳光里的石头,仍然叫冷。
人的温度,喘息、发毛与很骚的酒,就在这堆石头里,苟且偷安。做爱的紫檀木床,呻吟的雕花,弱过上弦的月光。
有吉日与神,用来兑酒的孤独,比鹰还高的歌声。有邮差与衙门,爱与恨,疼痛与欢愉,贩卖蒙汗药的美人。
有葡萄美酒,艳遇的烛光,不怀好意的猎手,虎视眈眈的黄沙……
没有谁准确地考证,夜色如何熄掉灯火,暴风如何扯去旌旗,时间如何淹没钟声。最后是谁关的城门,值更的小卒,听到了什么?
城墙挂满了比云还软的线条,华贵的紫,富丽的黄,临摹着白殿红殿,坚贞的爱情,等级森严的表情。
长号眠于沙砾,谁还在郊外厮杀?二十六位登机的国王,比一粒沙走得急促。
九、桃花沟
波密的桃花,只有到了五月,才被春风解除卦条。河谷红了,流动的光焰,拍打着山冈的肩膀,风沉默,微醉的牧羊人身边,背着光阴过河。
一千朵,有一千朵的姿容。
那是血,溅在静静的山谷。一千多年前,一群被清兵追赶的女子,在这里锻石为茅,抵挡屠刀,箭飞如雨。
及膝长裙的高夫人,剪下三千烦恼丝,虽然没点豆成兵的本事,一山的滚石都听她指挥。马死在史书里,证明那场力量悬殊的战争。
水声淙淙,吞噬着历史的诸多情节,一位颤巍巍的老汉,向一沟桃花长跪不起。有人证明,说那是李自成,他来得太迟,错过了英雄救美的机遇。
那场战争发生地,正预谋一场浩大的春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