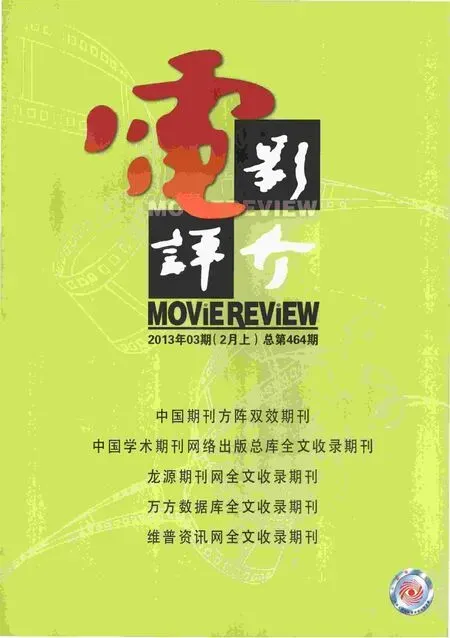论《一九四二》的艺术特色
1942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正如影片开篇所说,这一年,世界各地发生的事情有斯大林格勒战役、甘地绝食、宋美龄访美和罗斯福感冒。也是在这一年,中国内陆的抗日战争进入白热化阶段,而河南省在旱灾、蝗灾的影响下,发生了“吃的问题”,全省民众被迫迁移——逃荒。
影片上映以后,不乏论者和观众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陈述电影《一九四二》与史实诸多不符之处,展开了一场关于电影与历史之间真实性的大讨论。论调主要有“缴国军械的是地方武装,而非普通百姓,国军被缴械,与日军没关系”等,并且通过当事人回访和资料查询的手段条分缕析地指明自己的论点依据。笔者认为,再精准的历史还原只能是在一定程度上无限的接近历史真相,不可能完完全全、准确无误的贴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同时,电影虽然具有“照相本性”,即克拉考尔提出的“物质现实复原论”,但是国内早有论者提出真实不能再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说,电影具有的是“物质现实的复现”功能,而非还原。于是针对电影和历史真实性之间的冲突和矛盾,我们的态度应该是在兼顾史实、尊重历史的前提下,从电影的可看性和趣味性上对史或事进行二度阐释。否则,在某种程度上,电影和纪录片并无二异,那么电影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和空间。明乎此,关于“1942”的真实性讨论应该告一段落,也正是在这样的态度下,本文将试探讨影片的艺术特色。
一、于细节处展现人性
刘震云在谈《一九四二》时说过这样的话,“中华民族(在对待人性、心灵史时)有另一种表达的方式:一个人倒地了,后面一个灾民从这儿过,把前头人的裤子一扒,拿着刀子就上来割肉,一割肉一疼,倒地的人又活过来了,说‘我还成’,那人马上说:‘你不成了。’嘣,割下来。”这段画面感极强的描述生动地概括了中国人的人性状态,或者可以说是一种国民性,尤其在大饥荒的条件下,饥饿让民众无家可归,亲眼目睹了饿殍遍野从而使他们变得穷凶极恶起来。影片《一九四二》在表现国民性时没有大张旗鼓的宣教和指谪,而是于细节处见人性点滴。
瞎鹿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他既胆怯又无畏,既朴实又狡猾,这实际上正是那段时期中国农民的典型性形象,他代表着逃荒路上的大多数人。在影片伊始,他是地主少爷手下言听计从的一员,却在少爷濒死之际吐出了他早有的不满情绪,同时在械斗的混乱场面中趁火打劫了自己东家的粮食。足见这个人的隐忍和营钻。
最具戏剧性的应当是瞎鹿之死。他与东家和栓柱刚合伙强抢了一顿美餐,却无福消受,在与别人的争执中竟“咚”的一声,栽倒在烹煮的热锅中,结果尸无觅处。耐人寻味的是瞎鹿被打倒在锅里时周围人的反应,他们没有丝毫的惊异之色,面对一个活人、一个同胞被自己打死,他们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咦,怎么把他打到锅里去了呢?”这简单的一问如同是一种责备,怪那个失手杀人的家伙为什么把瞎鹿打到锅中坏了他那驴肉汤的美味。这种漠视和冷淡是令人胆寒的,但这在中国并不少见。鲁迅先生曾说:“四千年来时时有吃人的地方”,而“我”也是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国人早就丧失了对生命的悲悯情怀,面对每天不是被饿死抑或是被炸死的生活,他们已经习以为常,只要自己还能活下去,旁的一切都算得了什么呢?这种对生命冰冷刺骨的旁观并不比惨绝人寰的杀戮逊色。
二、情感抑扬难抒的硬伤
一般而言,言说苦难史的电影,在铺陈了民众的苦难,传递了苦难的信息之后,应当制造些许效果,让当下的人们于情感上得以升华,获得某些现实的意义。
电影《一九四二》的叙事策略在于“没有态度”,不引导观众的思维,只提出命题,答案靠观众自己去寻找。片中的许多场面表达骇人听闻,比如日本人狂轰滥炸老百姓,而民众手无寸铁又无处藏身只能尸首异处最终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比如外国记者镜头中的狗,它们睁着猩红的双眼撕扯着暴毙的尸体以寻一线生机……这些段落无疑是真实的写照同时也给予观众极强的心理冲击,但是电影似乎是急于表达和叙述痛苦和绝望,让电影成为被堆砌的平台。正如尹鸿所说,“只有苦难的表达是不够的,电影过于沉浸在苦难中不能自拔,几乎没有一丝亮色和一点透气口,其影片透露的那种绝望的气息,多少会让观众有些审美上的畏难情绪。”
最重要的是,电影设置了太多的促使观众震撼的兴奋点,但是每一个刺激都缺乏坡度和持续力,这应该是由于导演在处理灾难戏的过程中,希望以冷静客观角度去叙述这场悲剧,但是到段落结尾处又免不了来一段煽情,这种方式让观众处在一种尴尬的境地:本来会觉得很压抑,但是转瞬间导演又把你的情感提起来了,正当观众沉醉在这种悲痛中时,情感又被克制,于是不得不硬生生地结束。这样给观影造成一种抑郁情绪,那就是眼泪老是在眼眶处打转却不得爆发。这种情绪克制得不彻底,同时爆发的也不足量,让人们除了尴尬还是尴尬。
三、关于信仰的理性探讨
中国人在五四时期经历了一场关于信仰的危机、求索、冲突和选择期,这也是因为中国积贫积弱,人们屡经战乱和混乱的百般颠沛,确立了要“活”的人生信条。正如陈丹青所说的:“中国人有自己的信仰,那就是活下去最要紧,这是很伟大的信仰。什么东西有用咱们就用,没用就打到它。”最粗浅的信仰却是最伟大的,当中国人以“活下去”为目标时,一个民族的悲哀感便油然而生。
影片中,小安子对主深信不疑,战乱中他扯起了宣扬“主”的大旗。操一口河南土话的小安子奔走于哀鸿之间,试图启蒙民众:一切苦难的缘由都是因为“不信主”,于是失去了主的庇佑。且不说外国的“主”能不能管得着中国的事,单就小安子的成就来看,回报他的仅仅是一张张疲惫的脸和死不瞑目的心。可以看出,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时期,物质生活都得不到保障的中国人连精神世界都是虚空的,只求一丝残喘,其余一概不予问诸,这无疑是中国人集体的悲哀。随着影片的推进,小安子亲身经历了日军的狂轰滥炸,亲眼目睹了生命在一瞬间肉沫横飞、血流不止,也正是在这一刻,他坚固的信仰也被摧毁,他内心产生巨大的疑问,既然有主,既然主会庇佑他的子民,那么面对这样的一幕,主在何方?可见西方的所谓神明在中国的环境下也是无能为力的,而对于中国人来说,是要信仰而不得,有信仰也无从信起。
明乎此再来看蒋介石。他作为中国当时被国际承认的领袖,同样在耶稣基督面前寻求一丝慰藉、一点救赎,甚至留下了眼泪,但这一切祷告都无济于事,灾民依旧颠沛流离,官员依旧腐败贪赃,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讽刺。
另外,笔者看到,近年来中国大片常邀请国外的演员加盟客串甚至主演影片,代表性作品有张艺谋导演的《金陵十三钗》、伍仕贤导演的《形影不离》和冯小刚导演的《一九四二》等,这些影片中的外国人在某种程度上扮演着救赎中国人的角色。《金陵十三衩》中,贝尔饰演的教父在完成了对自己的洗礼后引领学生离开虎口,《形影不离》中史派西饰演的角色是片中男主角的精神导师,而《一九四二》中的记者白修德被塑造成一个勇敢的见证者和影响者的形象。所以,在排除了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之后,我们是否应该考虑中国电影应当如何定位和安置外国人角色,让人们觉得既不脱离事实,也不会有盲目媚外之感。
冯小刚导演历时近二十年酝酿和等待,完成了一部关于诉说中国曾经苦难伤痛的电影,这种悲悯的情怀和严肃的态度是值得赞誉的。电影《一九四二》以见微知著的方式揭露国民性,给予大众情感的激荡意义深远,但是习惯了以喜剧手法驾驭影片的导演在影片情感控制力上还有不足,当然导演秉着严肃的态度对中国人的信仰进行了探讨,具有历史和现实的警示意义和关怀。从这个角度看,作为商业电影的这部《一九四二》有多少票房已经不是多么重要,重要的是,这个电影痛陈了一段历史,揭开了民族的疮疤,在书写中国苦难史的丰碑中留下了值得思考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