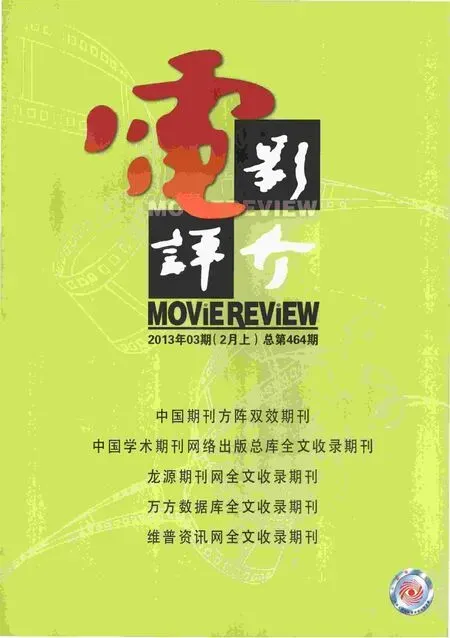从神经喜剧中的性别战争谈《太太万岁》
张爱玲是二十世纪伟大的小说家、散文家、编剧及翻译家。近年来,每一次对于张爱玲小说的改编,都成为当年影坛的一次大事件。对于张爱玲小说改编电影的研究也很纷繁多样。仅2007年《色·戒》上映后,在《电影艺术》一刊中,关于《色·戒》的评论文章就有一百多篇之巨。但是,张爱玲作为编剧创作的一系列影片,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受到了学术研究界的冷遇。
在张爱玲的“电影生涯”中,《太太万岁》是其中票房最为辉煌,观众最为喜爱的一部电影。《太太万岁》上映于1947年,由上海文华公司拍摄,张爱玲编剧,桑弧导演,上官云珠、石挥、蒋天流、韩非等主演。影片通过发生在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中的悲欢离合,较好地塑造了富有鲜明特色的人物。影片彰显了桑弧对于讽刺喜剧艺术的可贵探索和流畅成熟的导演能力。
《太太万岁》的人物群像中,以家庭主妇陈思珍为主线,围绕着她的有性格乖张、待人小气的婆婆,不成器的丈夫,天真活泼的小姑子和充满活力而略显轻佻的弟弟,状似古板而实则轻浮的父亲,还有娇媚迷人的交际花咪咪。在这么一群人中,陈思珍是主线,串起了其他所有人,使这些人的生活紧密联系起来,形成立体的人物图谱,并发生了一系列跌宕起伏、险象丛生的故事。在这些人物中,并没有“高大全”式的人,相反,每个人都有大大小小的缺点,都有滑稽之处,都多多少少受到了些许嘲谑。这种轻喜剧的表现手法非常好莱坞化,使得人物形象不那么呆板,人物性格得以丰满,人物意涵得以丰厚。
在张爱玲编剧电影研究中,台湾的郑树森教授最早认为张爱玲编剧的电影具有好莱坞神经喜剧电影的特征。郑树森教授甚至说:“中国电影中与神经喜剧有最密切关系的,是张爱玲担任电影编剧的一些影片。她所编剧的《太太万岁》有不少神经喜剧的元素,也是当时中国电影界独一无二(unique)的神经喜剧……影史上神经喜剧这个电影类型的开拓,可说是张爱玲独一无二的贡献。”[1]
所谓神经喜剧,目前国内做出这一类型电影的基本定义的也是郑树森教授。他写到:“所谓‘神经喜剧’(screwball comedy)中‘神经’的原英文词‘screwball’……似乎与变化球有关,当时美国影评人绝大部分是男性,喜欢看棒球比赛,利用体育术语来形容电影特点也不足为奇,约在20世纪30年代便有电影评论者用‘screwy’来形容这类喜剧……神经喜剧中的喜剧成分,介乎高乘喜剧(又称高雅喜剧,high comedy)与低乘喜剧(又称低俗喜剧,low comedy)之间……高乘喜剧多通过对白来刻画人物,而低乘喜剧则强调身体语言(physical action),包括打骂、吵架、说话荒腔走板、闹酒,以各种动作为主,对白则无甚意义,多是骂战、吹牛皮、鄙俗笑话等……神经喜剧一方面又高乘喜剧的成分,如注意对白与人物之间的互动,对人生社会有所观照,批判大多委婉含蓄;另一方面,个别场面也吸收了低乘喜剧的元素,如穿插惹笑的肢体语言、吵架、打架等。神经喜剧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中间落墨……神经喜剧整体效果大多风趣轻松,并不沉重,题材大多取材自上流社会,与社会的黑暗面留有距离,人物大多优雅机智,机锋处处……”[2]
神经喜剧中的性别战争一般指代来自不同阶层的男女主人公,在相遇后由于各自不同的阶级属性和不同的世界观、价值观产生的种种分歧,并针对这些分歧发生了一系列暗藏机锋、机智有趣的争吵。神经喜剧中的性别战争一般是以密集的对白作为标识,而男女主人公的争辩中往往带有性挑逗意味,来自不同阶层的男女主人公也往往会发生爱情。
《太太万岁》中并没有像通常神经喜剧中那么明显对立的两个阶层,《太太万岁》中,所有的戏剧冲突都是限于中产阶级内部的,并没有向下延伸,也并不是两个阶级矛盾的碰撞。归根结底,这只是两性战争的延伸。因为没有那么明显的阶级对立层面,男女主人公在价值观、世界观、立场上并没有那么明显的分界,由此较一般神经喜剧弱化了冲突层级。并没有一般意义上神经喜剧机锋处处、唇枪舌剑的战争,却将性别战争延伸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
作为太太的陈思珍,并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神经喜剧的女主角。神经喜剧中的女主角,一般是独当一面的职业女性,出身较为富庶的殷实家庭,遇事有自己的见解,不受传统的男女地位观念掣肘,甚至在性格上偏向于强势。在某些问题上与男主角有了冲突时,能够毫不相让,甚至与之产生相当强烈的交锋。神经喜剧作为一种以性别战争为主体的喜剧,一种无性的性喜剧,正是在对女主角这种独特的性格设定上才能够成立的。
而《太太万岁》中的陈思珍,她没有自己的职业,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她的气息是我们最熟悉的,如同楼下人家炊烟的气味,淡淡的,午梦一般的,微微有一点窒息……家里上有老,下有小,然而她还得是一个安于寂寞的人。没有可交谈的人,而她也不见得有什么好朋友。她的顾忌太多了,对人难得有一句真心话。”[3]从张爱玲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虽然每天陈思珍身边都有许多人需要周旋,许多事需要处理,但她基本上是过着一种近于孤绝的生活。而她生活的唯一重心,就是要让周围所有人满意,令周围所有事向着相对圆满的方向发展。为此,她不惜不断撒谎,自己贴钱,甚至发现丈夫有外遇后继续强颜欢笑,处处隐忍。陈思珍说的谎,无疑构成了本片的绝大多数笑料。但她说的谎几乎不被所有人欣赏和理解,她对这些只有无奈承受,甚至在丈夫、父亲、婆婆发现她说的谎时,纷纷指责她时,她唯一用的武器,也只是最传统最女人的武器——哭。陈思珍的性格谈不上强势,她本人更是深受传统的男女地位观念掣肘。
在陈思珍与丈夫、与婆婆、与自己父亲、与丈夫情人的种种角力中,充满了通常神经喜剧中常见的戏剧化反讽。即陈思珍设计的所有谎言,对于观众来说都是知悉实情的,观众处于全知视角,自然会对这些误会、巧合、冲突造成的喜剧效果报以会心一笑。演员对这些却全然不知,造成了认知上的距离,使观众获得了认知上的优越感,因此制造了最常见的喜剧效果动因。
与同期的好莱坞神经喜剧中的女主角的不同在于(如1941年美国导演普莱斯顿·斯特奇斯(Preston Sturges)的另一部电影《淑女伊芙》(The Lady Eve)),好莱坞神经喜剧的女主角通常是基于阶层冲突的基础上为了维护尊严而奋战,却在其间陷入了爱情中。《太太万岁》中太太所为之努力经营的,显然不是爱情所能够表征的。“尽责的太太呢,如同这出戏里的陈思珍,在一个半大不小的家庭里周旋着,处处委屈自己,顾全大局,虽然也煞费苦心……然而实在是更不近人情的。没有环境的压力,凭什么她要这样克己呢?这种心理似乎很费解。如果她有任何伟大之点,我想这伟大倒在于她的行为都是自动的,我们不能把她算作一个制度下的牺牲者。”[4]
由此可见,编剧张爱玲将陈思珍作为模范主妇的一番努力并不看做是女性或者男性的胜利,当然也不是时代的悲剧。陈思珍具有相当正统的中国传统女性美德,克己勤俭,识大体懂事理、温柔而善解人意、坚强又顾全大局。在整个家庭事务中,貌似圆滑周旋,实则掌握大局。但她并不是女权主义,甚至不是女性主义的代言人。她并不是代表女性力量的崛起,最终她丈夫的失败也并不代表夫权(父权)的颓落。《太太万岁》的结局,陈思珍与丈夫达到和解,交际花咪咪继续寻找金主讨生活,与其说是大团圆结局的需要,毋宁说是浮世悲欢的写实画卷,在一幕幕悲喜剧中,纵然充满了“咬噬性的烦恼”[5],生活依然要演下去。从这点上看,张爱玲无疑是让电影忠实地还原了生活真实。陈思珍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为了维持生活的安稳,无非是为了跟轻浮又不成器的丈夫,能够继续维持一夫一妻的生活。
在全片中,不仅有着误会、巧合、闹剧、夸张、反讽等寻常的喜剧元素,更是有着一些欧美神经喜剧的典型元素。这跟张爱玲是个好莱坞电影影迷不无关系。她本人深受三四十年代风靡好莱坞的神经喜剧影响,而神经喜剧中以两性战争为主导的情节安排,更是张爱玲小说中时常涉及的。但《太太万岁》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神经喜剧,相较于好莱坞神经喜剧类型电影,《太太万岁》更像是建立在现实主义意义上的社会风俗喜剧。少了理想主义色彩,多了更为写实的主妇生活映射。神经喜剧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时,当时的人们喜欢这种富有娱乐性的影片,以满足暂时性的逃避现实的心理需求。但与许多好莱坞电影相同的是,《太太万岁》中一样有着标志着冲突双方的男性和女性方面达到了和解,实现了传统大团圆结局的设定。而好莱坞神经喜剧中最后往往以求婚结束,来自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阶级的男女主人公紧紧拥抱,预示着接下来会结婚并组建和美的家庭。更象征着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得以弥合,化解,像男女主人公一样完成了两个阶级的同一与和谐。这当然是与现实相悖的一种理想主义乌托邦想象。《太太万岁》中陈思珍与婆婆、丈夫、自己的父亲、丈夫的情人咪咪之间的一系列矛盾更像是传统女性与整个封建男权社会的矛盾缩影。“她盼望的‘温柔乡’……那是一个男性主导的地盘,女性争得头崩额裂,也只能委身当‘乡’里的‘温柔’。”[6]
婆婆与丈夫的情人咪咪虽然是女性,但在这场性别战争中无疑也是丈夫那方的兵卒。婆婆代表丈夫传统的男权主义压制,甚至陈思珍自己的父亲,也很容易地被女色诱惑,很快地跟她丈夫站在了同一战线上(由此而知,在电影中张爱玲也彻底否认了传统的父权),而情人代表了从封建社会起,男性亘古不变的朝三暮四属性。咪咪似乎被处理成了一个略有符号化色彩的反面形象。不论是她娇媚的外貌、娴熟抽烟的手势,还是她老练驾驭男性谋取利益的能力,都贴了相当外化的“坏女人”标签。表面上看,咪咪比起陈思珍,更像是典型的神经喜剧电影中的女主角。她成熟、漂亮、高度地世故化,并能优雅地达到谋取自身利益的目的;当利益受到侵蚀时,更是能够最快速度地全身而退。但最后咪咪尽管不乐意,却不得不退还陈思珍丈夫送给她的胸针时,她的姘头甩给她的那一耳光,无疑是响亮地宣布这个社会仍是由男性(夫权/父权)主导的真相。即便是咪咪这样相当有能力,有现代性气息的女性,骨子里仍然是为一个男性所控。在两性战争的意识形态战场上,无疑是以男性获得了全盘胜利,女性的完败而结束的。
到了结尾,虽然陈思珍和丈夫获得了和解,“太太”生活中所有的矛盾与问题无一化解,婆婆仍然挑剔苛责,父亲仍然貌似道学气实则伪君子;丈夫仍然无能怯懦并轻浮不实在;仆人仍旧百般差错而脾气急躁,而这个大家庭中仍然有无数的问题需要万能的太太继续出面,化解一切主持一切,“粉白脂红地笑着,替丈夫吹嘘,替娘家撑场面,替不及格的小孩子遮盖……”[7]。陈思珍曾经策划过一次对这种中产阶级生活的“叛逃”,即与丈夫离婚。但最终轻易地被丈夫赠予的一只胸针改变了主意,心甘情愿地继续回到以往生活中去。陈思珍计划过的离婚,也未必意味着她在这场意识形态战场上能够获胜。而陈思珍最终的和解,也是观众意料之中的。
《太太万岁》显然缺少革命精神,它讲述的仍然是一群封建士绅们,或者是普通中产阶级的生活。当时的上海,属于抗战刚刚结束的乱世时期,大部分电影公司仍然在拍摄一些具有鲜明左翼倾向的进步电影。例如昆仑公司的《一江春水向东流》、《乌鸦与麻雀》、《万家灯火》、《八千里路云和月》等等,这些电影往往以时代为背景,反映抗战时期人民颠沛流离的生活,并有着一定的政治色彩。但《太太万岁》中几乎没有时代背景,没有左倾色彩,也与当时国内国共两党争战不断、战后物价紊乱,有人大发国难财忙于“劫收”的现状几乎脱节。《太太万岁》的没有时代性,某种意义上却成就了它的现代性。放在今天,这些故事仍然在生活中屡见不鲜,《太太万岁》中太太曾经笑的哭的伤心的宽慰的,至今仍然每天都在发生,仍然具有普世价值。《太太万岁》无疑是借鉴好莱坞电影并将之中国化的成功样本。在当时的社会变革时期,新女性思潮主导的社会中,仍然表现出男性本位的思想,也是需要勇气的。《太太万岁》的故事中,乍一看似乎表现了男性主权(父权/夫权)的颓落,其实还是写了女性的悲剧。这是有悖于当时的“五四精神”的,并且完全没有大起大落的英雄情结,只是娓娓道来一群最普通的小市民的生活风情画。而对于太太来说,无疑她费心周旋的家庭即是她世界的全部。某种意义上说,这部电影与张爱玲苍凉压抑的小说是一脉相承的。但张爱玲深知电影与文学的区别,相比文学,电影的受众要广泛得多,而受众对电影的娱乐性要求也是比文学高得多的。张爱玲在电影剧本中,时时加插入误会、巧合、闹剧、反讽等喜剧元素,并运用了好莱坞神经喜剧中舞台化的冲突模式,在当时的电影中是相当前卫的做法。关于《太太万岁》这部电影的深入研究,对如今的社会风俗喜剧和家庭伦理片,都具有一定的意义。而《太太万岁》中意识形态战场上性别战争中女性的完败,也进一步说明这一部描绘“浮世的悲欢”的电影,骨子里其实是“浮世的悲哀”。
注释
[1]郑树森,《电影类型与类型电影》,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6月第1版,第137页
[2]郑树森,《电影类型与类型电影》,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6月第1版,第141-142页
[3]张爱玲,《太太万岁》题记,载于1947年12月3日上海《大公报·戏剧与电影》
[4]张爱玲,《太太万岁》题记,载于1947年12月3日上海《大公报·戏剧与电影》
[5]张爱玲,《天才梦》,选自《张看》,经济日报出版社,2002年9月第一版,第3页
[6]黄爱玲主编,迈克撰写《天堂里的异乡人》,选自《国泰故事》,香港电影资料馆,2009年第一版,第146页
[7]张爱玲,《太太万岁》题记,载于1947年12月3日上海《大公报·戏剧与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