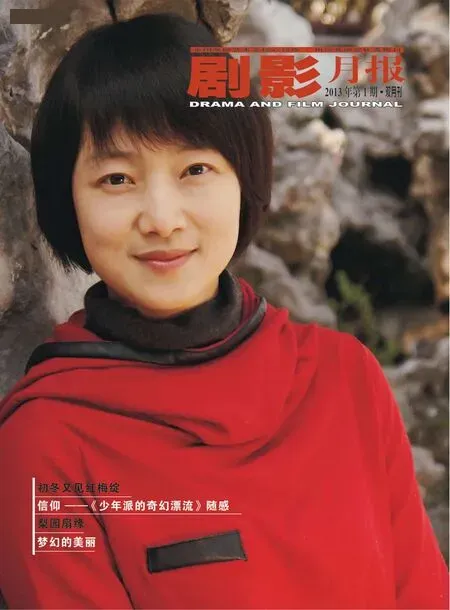如何在舞蹈创作中把握好动作形象塑造
■姜国萍
如何在舞蹈创作中把握好动作形象塑造
■姜国萍
舞蹈是人们表达情感的一种身体语言,而舞蹈创作是舞蹈编导对社会生活和日常感悟的一种感情的升华。在舞蹈创作过程中,对动作结构进行了解和研究是更好地激发创作思想,合理进行舞蹈创作的前提。因此,在当前舞蹈编导领域,人们更关注舞蹈创作过程中对于动作结构的研究。
一.舞蹈创作中动作形象塑造方法
(一)由形到意
舞蹈动作的创作中,对动作的感知及对意境的把握是一个逐渐的由表及里、由量变到质变、由被动到主动的过程,动作创作的优劣,直接反映出对舞蹈意境的挖掘程度。初级的动作想象,开始只能引发舞蹈的最初意境,如基础训练、手臂的结合、手的动态练习,只是身体内在起伏和节奏感的体验。单一的动作,从动作的动态、动律中,从直观的细小的看似外在的方面,抓住动作的特点,进一步加以分析、体会,便是动作意境的最初感知。也就是说,当“形”已具备了其艺术性质之后,要使舞蹈表现出“神韵”,这就要求舞蹈者将自己丰富深刻的内心情感和对动作的独到的理解与感悟,灌注于形体动作中。这样创造出的舞蹈意境必然情深意远。如当作起伏流畅的“华尔兹”舞步时,就如同一叶小舟在大海中随波荡漾;简单的一个硬腕动作,宛若迎风的海燕在展翅飞翔。如此对动作的形逐渐地感知、理解、想象,才使外在的形与内在的神韵相融合。
(二)身心合一
舞蹈是一种形象艺术。舞蹈的形象直接决定了舞蹈的特殊性,在舞蹈中常有模仿大自然的作品,如《雀之灵》、《荷花赋》、《小溪江河大海》。它们不仅仅停留在模仿阶段上,而更重要的是从直观的模仿中抓住规律,引发更高级的动作想象,并结合自己的内心体验,以情带形进行再创造,从而达到身心合一,情境相融。
(三)感性到理性的升华
舞蹈创作的任务在于用形体动作、韵律创造一个“意会”的世界。它所提供的视觉形象与意境最具直观可感性,有着生发、启迪、引导观众思考的作用。有时一个动作、一个姿势都可能胜过千言万语。罗丹说:“人体由于它的力或者它的美可以唤起种种不同的意象。”舞蹈正是通过动态意象表现那些语言所不能表达或不能完美表达的东西。人们从舞蹈中体悟到的情、意、境,是不能用语言恰切传释的。所以如此,就因舞蹈是一种典型的“意会”形式,是不能翻译的特殊语言。在这一点上,舞蹈语言与人的情感模式具有同构性质。用舞蹈来展现人类的情感生活可以获得最为理想的效果。这也正是《毛诗序》所说的“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的原因。
二.在舞蹈创作中如何更好的进行动作形象塑造
(一)提升个人修养
艺术是来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表现形式。创作和设计者必须从实际出发又归于实际。作为艺术的一种形式,舞蹈编导必须遵循这一原则。较高的个人修养包括敏锐的洞察力、开阔的艺术视野和深入生活的精神。生活是所有艺术形式的基础,舞蹈作品必须从生活中汲取营养和创意。舞蹈编导只有积极地深入生活,了解生活,感悟生活才能累积素材,从生活中提炼出更符合大众审美的舞蹈素材,而较高的个人修养又是对这些素材进行整理、归纳和改变的前提。
艺术不单单是如实反映生活,还应当适当地高于生活,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富有表现力。舞蹈编导还需要在生活的基础上对各种素材进行高度的浓缩与升华,使其成为鲜活、动人的舞蹈内容,给人以美的享受与熏陶。
南通艺术剧院创作的,并有我参加演出的获得大奖的舞蹈《踩文蛤》,通过海边渔家女子在海水退潮时到海边踩文蛤的场景,表现了她们快乐生活的一面,舞蹈在一群头戴纱帽,系着围裙的姑娘欢快的嬉戏、双脚飞快的踩踏中开始,随着队形的变化,音乐节奏的变化,姑娘们不断地变换步伐,扭动腰肢,用力地踩出埋在沙泥中的文蛤。这个舞蹈的音乐具有鲜明的江苏民间音乐风格,编导通过观察渔民赶海时的动作,通过提炼,创作出了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优美的舞姿搬上舞台。一个好的舞蹈作品除了专业的技巧外,重要的就是生活中的元素在节目中的体现,这样大家都看得懂,都会拍手叫好。舞蹈本身就来自人民群众在劳动和生活中根据自娱、祈福、达情所需而创作并直接表演的一种艺术形式。
(二)夯实专业基础
理解舞蹈动作结构,不但要有较高的个人素养,较深厚的舞蹈基础也是必不可少的。较深厚的舞蹈基础包括舞蹈技巧基础、舞蹈创作基础。首先,舞蹈表演基础是核心。一个较好的舞蹈创作者首先应该是一个较好的舞蹈表演者。他必须熟悉表演者在舞台上的心态和情景,才能创作出好的符合舞台实际的作品。而且,具有一定的舞蹈表演基础,才会帮助舞蹈创作者更好地熟悉各个舞蹈动作之间如何衔接最为合理,是舞蹈结构研究的前提。
其次,舞蹈创作基础是关键。不是任何舞者都能够进行创作,这是因为不同的舞蹈演员同时也受个人素养的限制。舞蹈创作需要舞蹈创作者具备全局意识、创新意识和模仿能力,只有具备这些能力,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编导,也才能更好地理解舞蹈动作结构,为舞蹈创作营造更良好的氛围。
群舞《中国妈妈》讲述的是一个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母亲抚养日本遗孤的故事。在这个舞蹈里,无论是在动作上,表情上,还是情感表现上,都完美地用脸部表情以及肢体语言,细腻地塑造了这个故事里的每一个人物,每一个细节。成功地反映描绘出了一个母亲最伟大、最本真淳朴的胸怀,和对每一个弱小生命的珍视。在整个舞蹈里,没有华丽的服装衬托,炫目的舞美灯光。最朴实的东北妇女日常生活的服饰(朴素的棉袄),梳着典型农村妇女发髻的中国妈妈形象给人一种重归历史的自然、亲近与苍凉。默默地辛勤劳动的体态,因劳作而略弯的腰,描述了生活的单一与凄苦。全舞围绕着主题“母爱”发展开来。在情感上运用不夸张造作而又具有真实感的表情,动作完整地表现出了这一系列的心理活动的复杂变化。憎恨、接纳、养育、送行四个环节紧紧相连。憎恨时的家恨悲痛,接纳时的拒绝挣扎,养育时的真情奉送,送行时的恋恋不舍。脸上诚恳而又丰富的表情,细腻而极具表现力的动作完美地演绎了这段过程,把“母爱”的主题演绎得淋漓尽致。一段跨国的母爱,一位善良的中国妈妈抚养令人发指的日本鬼子的遗孤,彰显出了女性的伟大胸怀。爱能超越国界、超越阶级,母性的包容强烈地震撼每个人心灵。没有高超的舞蹈技巧,没有刻意的展示。用简单的劳动的动作,构成了舞蹈的动作主题。不断地强化和发展的主题动作,动与静、立与跪、下蹲与抱起,层层渲染,层层强化,给观众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强大的震撼力,直抵每个人的内心深处,拨动每个人的心弦,撼动着每个人的心灵。清新的音乐带着东北特色的民间小调,简单的儿歌民谣,贯穿了整个舞蹈主题的故事结构。憎恨、接纳、养育、送行。随着故事的发展,音乐也随着变得跌宕起伏。在激昂、舒缓、快速、深沉的音乐变化中,让人不但在视觉中得以震撼,也在听觉中完全溶入整个故事里。音乐与舞蹈的结构丝丝相扣,使舞蹈各部分的衔接更加自然,给人一种“浑然一体”的亲切。这个舞蹈既表现了舞蹈创作者具备较高的个人素养也展现了深厚的舞蹈基础,如果不是了解舞蹈演员的基本要求,那些细致的神态动作也就无法创作出来,这部作品是动作结构研究中的经典作品。
[1]江靖弋.动作解构之于中国舞编导的功能[J].北京舞蹈学院学报,2005,(01)
[2]于平选编.舞蹈编导教学参考资料[M].北京舞蹈学院内部资料,2011,(68).
[3]蔡霞.浅谈舞蹈的创作[J].内江科技,2009,(01)
[4]徐艳.太极拳与中国古典舞的关联[J].四川戏剧,2008,(04)
[5]冮毅.舞蹈编导课程中的动作动机探索[J].艺术评论,2008,(08)
[6]王虹.舞蹈动机与编舞[J].广东艺术,2007,(03)
[7]孙娟.舞蹈作品教学初探[J].河南教育(基教版),2007,(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