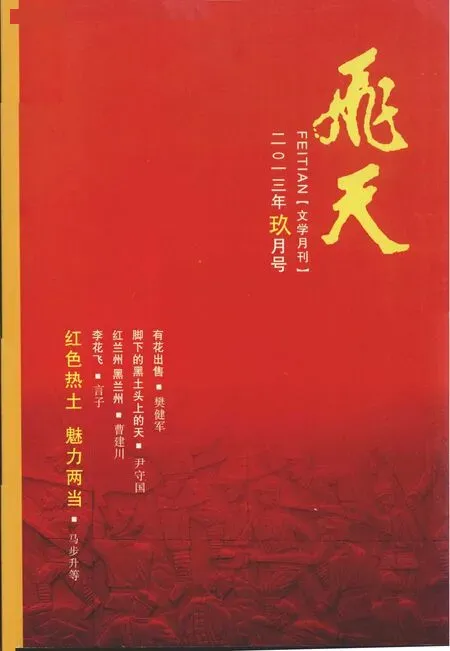黎明前的红月亮
丁志贤
一
远远地望见了南城门,不知怎的,毛丫子觉得脚步越来越沉了,既盼着三两步赶回家中,却又有些发愁回到那个家。
毛丫子是昨天下午跑出城去的。听到红军马上就要进城的消息后,妈就对她说,远远地跑,往山里跑,跑得越远越好!毛丫子便伙在人群里没命地往城外跑,一直跑到了离城很远的山窝窝里。天寒地冻的,一伙子人(大都是些年轻的姑娘媳妇和一些怕被抓丁的青年)挤在山隅里呆了一个晚上,有人愁得哭哩,说红军要是不走了,难道永远不回家了不成?毛丫子也在犯愁,但在犯愁的同时倒也有一丝轻松,不回去了,也就不用愁着嫁给文宝做媳妇了。
今天一早就有人带来了城里的消息,说红军已经进城了,但红军并不祸害老百姓,还劝说大家都回城去哩。人们将信将疑,但也就有人起身回城了。毛丫子犹豫着不知该怎么办,后来见回城的人越来越多,想了想便也提起包袱往回走,往山丹城里走,也就是往文宝媳妇那条路上走去。
城门上已有了红军安排的岗哨,满街满巷也都是红军,拉电线的,打锣吹号唱歌跳舞宣传抗日的。让毛丫子觉得好笑的是这红军穿啥的都有,有穿灰色军衣的,也有穿老百姓衣服的,看起来破破烂烂的就像群“叫花子兵”。来到东街上,毛丫子看到有一个戴眼镜的红军,把几张大大的白纸铺在桌上,用毛笔蘸了黑墨写字,毛丫子就停住了脚步看,只觉得那人字写得真好看。那红军就放下手中的笔,笑着问她认得字吗?毛丫子摇摇头,那红军就往鼻梁上推推眼镜,给她指着一字一字念了出来:推翻中国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又指着另外一幅标语念道:红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听这红军一口浓浓的外乡口音,毛丫子便问他是哪里人?他又往鼻梁上推推眼镜,笑着说,四川的。
毛丫子就寻思,看来红军并不可怕嘛,不像事先马家军宣传的,红军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灭回灭教等,把妈吓的,这些日子白天晚上都紧闭着大门。
那个四川兵抬头打量着她,看到毛丫子涂得脏黑的脸蛋,便问,妹娃子,你是昨天下午跑出城去的吧?我们红军是老百姓的队伍,从不欺压老百姓。你现在回来啊就对头了。
听他这么一说,毛丫子就不好意思地笑了。
二
夜里,毛丫子在炕上翻来覆去地忍着越来越重的尿意,实在忍不住了便鼓起勇气拉开屋门,对门口屋檐下睡着的红军说,你们能起身让我出去一下吗?
城区家户家的都住满了红军,此刻毛丫子家的院子里躺满了红军,北屋里(文宝在甘州城里学皮匠,冬月里才能回来,北屋一直就空着)炕上地下也睡满了红军,就连毛丫子和妈睡的那间屋子,门口屋檐下也满躺了红军。这些红军疲乏得几乎躺下就睡着了,此刻毛丫子连喊了几声,靠近门口的一个红军才闭着眼睛说,妹娃儿,你就直接从我们身上跨着过吧。毛丫子心想,这些人也太不讲究了,让一个女人家的从身上跨过去咋成呢!还想再喊,那人已经睡着了。毛丫子觉得这人说一口四川话有点耳熟,仔细一看,竟然是那个在街上写标语的戴眼镜的四川兵。没法子,毛丫子只好从他们的身体缝隙处一个一个横跨过去,脚碰着他们的身子也没有反应。
已是初冬,夜里非常寒冷,院子里的红军身上还有老百姓送的被子,屋檐下躺着的那些则大多只是和衣睡着。毛丫子看到门口的那个四川兵身上的衣服非常单薄,就想,当红军也真是遭罪哩!自己家里穷,也再没有多余的被褥了,回到屋里便和妈商量,把炕席上铺的那条毡子扯下来给门口的几个盖上,妈叹口气,点头同意了。
第二天一早,毛丫子醒来,看到院子里架着两口大锅,几个红军正在烧水做饭,那条毡子被叠得整整齐齐放在门口。
三
红军挖了东关刘麻子家的浮财,又开了马二家的两个大粮窖,在城东放粮散财赈济百姓哩。妈打发毛丫子也去看看,毛丫子就去了,去了就分到了一小口袋粮食。提着粮食口袋回家的路上,毛丫子看到了那个天天睡在自家屋檐下的四川兵(毛丫子已经知道他姓姚,妈就把他叫姚共产),他正和另外几个红军在墙上用白灰和木炭写标语。对面走过来十多个女红军,毛丫子知道,她们是红军前进剧团的,每天到街上来向过往群众宣传红军的抗日政策。今天她们站在街边向群众教唱起歌子来,毛丫子先是一眼不眨地盯着她们看,后来就不由自主地走了过去。
这都是些和她差不多大的姑娘子,留着齐耳短发,嘴里说着她听不太懂的话,唱着她不会唱的歌,看起来是那么高兴那么快活,毛丫子觉出了自己心底里的羡慕。“鼓声咚咚,红旗飘飘,战士们好英勇!”这歌子听起来好有劲,毛丫子刚开始还有点害羞,只是在嗓子眼里小声哼哼,后来不由得也跟着大声唱了起来。
歌子教唱完后,人群逐渐散了开去。毛丫子叹口气,也准备要走,却听见一个女红军指着街对面说,那不是姚才子吗?不知道给咱们的新歌写好了没有?另一个就笑着打趣她说,你为什么一提起这个军中才子就两眼放光啊?两个人就大笑着追打起来。
毛丫子的眼光追着她们,看着她们走过去和姚共产一起说话,看到姚共产拿出了几张纸交给她们(想来就是给她们写的新歌了),看着她们叽叽喳喳地走远了。毛丫子又远远地打量起了姚共产,瘦高个,无论是站着还是走着腰板都挺得笔直,一副眼镜却又使他显得文绉绉的,看起来又像个军人又像个念书人。毛丫子就叹口气,想,这群人就是和她身边的男人和女人不一样啊。这时,姚共产在街对面向她招招手,毛丫子便不好意思地吐了下舌头,走了过去。
姚共产说,女娃儿,我看你很羡慕这些女红军啊!你要是想当红军,也可以来啊!
我也能当红军?
能啊!
毛丫子的眼神亮了起来,但又立刻黯淡下去,半天低声说,翻过年去我就要给文宝做媳妇了!我现在的妈不是我的亲妈,她养我是要给她的儿子文宝做媳妇的。
姚共产说,所以你更要起来反抗啊,我们队伍中有个妇女独立团,里面好多同志和你一样,以前也是给人家做童养媳,后来都参加了革命。我们革命就是为了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新社会,在这个新社会里,男女平等,你们女娃儿同样可以上学读书,婚姻自主,做社会和国家的主人。
毛丫子支棱起耳朵细听着,想了想却又摇着头说,男女平等,婚姻自主?我不相信会有那样的社会。那姚共产你就是为了这个新社会参加红军的吗?
姚共产点点头说,是的,这个新社会是我的信仰,我信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我对新世界的向往和追求。
虽然不是完全能听懂,但毛丫子还是感受到了姚共产说这番话时的那种激情。
四
毛丫子对妈说,我想把文宝哥那件旧棉袄给姚共产穿去,这风天雪地的,红军身上的衣裳太单薄!
妈瞟她一眼说,你男人的衣服你倒给别的男人穿去!
毛丫子说,文宝哥现在身上有穿的呢,那件棉袄又旧又破,里面的棉絮都碾成碎疙瘩了,等以后我再给文宝哥做新的。
过了一会儿,毛丫子又对妈说,县苏维埃政府动员群众参军哩,我们街上已经有十几个人报名参加红军了,每天都在学校训练哩,要跟随红军西征,里边还有两个女的哩。
妈就剜她一眼,说,别人当不当女红军不关我的事,我把你养这么多年,是让你给文宝当媳妇子的,我可不是养女红军的!
毛丫子就低头做自己的事情,不敢再说什么了。她每天清早出去,和街上的一些年轻妇女聚在一起给红军做毡鞋,补衣服。毛丫子还把文宝的那件破棉衣补缀了一下给姚共产了,她本来是想把那破棉衣拆洗后翻新一下再给的,但想到天越来越冷了,姚共产身上的衣服太单薄,不如让他早点上身御寒。送衣服的时候毛丫子有些不好意思,说这衣服太破了,但姚共产接过来就穿在身上了,他谢了毛丫子,还坚持给毛丫子打了条据,说等以后革命成功了,凭条据付款。
一有闲时间,毛丫子就偷偷地跑去学校看新红军训练,看他们排成队伍,有的端着步枪,有的举着系红布条的大刀在凛冽的寒风中操练着。
这天毛丫子在队伍里面看到了一个认识的人,就是住在西街上的彩彩,她的眼睛就不由得盯在了彩彩身上,觉得这时的彩彩咋也不像是过去那个彩彩了,咋看都像是个女红军了。彩彩在队伍里招手叫她,她便忸怩磨蹭着,心里既想去又觉得有些不好意思的,彩彩一伸手便把她拉进了队伍。
那个红军教官就走了过来,问她是不是想参加红军?毛丫子腼腆地说,就是过来先看看。那教官把手中的一杆步枪交在毛丫子手中,说看看没啥意思,还是跟着一起练练吧。接过步枪的刹那,毛丫子就觉得自己的人生不一样了,究竟咋不一样,她自己也说不清楚。她九岁起就知道自己要做文宝的媳妇,她是文宝家的童养媳,这使她每次见到文宝都觉得别扭,甚至有些怕他,她也说不清是为啥。可是她再不愿意也得走这一条路,成为文宝媳妇是她唯一的归宿,她似乎只有这么一个活法,可是眼下她好像不知不觉走到另一条路上来了。
五
红军几乎天天打仗,不是大仗就是小仗。伤员越来越多,总部医院住不下了,一些住家户里也安排了伤员。毛丫子家里也有两个伤员,毛丫子每天为他们用盐水擦洗伤口,伤刚好些他们就又上战场了。毛丫子已经好多天没有看见姚共产了,她最后一次见姚共产是在街上,姚共产对她说红军虽然作战疲劳,缺乏冬衣弹药,但士气高涨,还动员毛丫子也来参军。
这一天训练完回家后,毛丫子将几块银元交到妈手中,妈问是哪来的钱?毛丫子说是红军给的安家费。还说,所有在山丹新参加的红军都被编入了新兵团,都给发了安家费。
妈睁大眼睛望着毛丫子,半天才问了一句,你还真的要去当红军啊?
毛丫子点点头。
妈一下就吊下了脸子,说,毛丫子,我养了你六年啊!
毛丫子就扑通一声跪在妈的面前,说,妈,我现在没法报答你,等革命成功了我一定会回来孝敬你,给你养老送终!妈盯住毛丫子的眼睛,问,你该就是看上那个戴眼镜子的姚共产了吧?
毛丫子低头想了想,又摇摇头,说,就是红军里面没有个姚共产,我也要去当红军!
妈说,毛丫子,你丫头还傻着哩,你以为那是“革命”呢?你还不知道那是“要命”哩!
毛丫子说,我要是怕死就不去当红军!
妈低下头想了想,不再说话,把钱收了起来。
第二天清早起来,毛丫子发现门窗被妈从外面锁上了,任她怎样拍门呼喊,妈就是不开门。就和她铁了心要当女红军一样,妈也铁了心要关她一辈子。直到天黑了妈才送进来一碗饭,对毛丫子说,你是文宝的媳妇,我不能做主放你走!文宝这一两天就回来了,放不放你走,文宝回来说了算!
毛丫子心里急得起了火,整夜里坐在炕上睡不着觉,现在红军已经开始撤离山丹,她能听到街上传来的人声马声。想到那群人离自己越来越远了,想到他们描绘的那个世界离自己越来越远了,想到再也见不到姚共产了,毛丫子心里又急又痛。
文宝是第二天下午回来的。夜里,妈把文宝搡进了毛丫子的屋子,说毛丫子是你的人,留不留得住她就看你了!文宝把从甘州城里给毛丫子带来的两块花布放在毛丫子的枕边,但毛丫子脸冲里睡着,看也不看。文宝不由得来了气,说,你在我家过了这么多年,共产党才来了几天,你就死了心要跟他们走,你个没良心的!
毛丫子闭着眼不做声。
文宝又说,你是我媳妇,想走也由不得你!说完就躺在了毛丫子的身边,抱着毛丫子没头没脸的亲起来。毛丫子没有一丝的挣扎反抗,这让文宝有点诧异,他记得去年他从甘州回家后,有一天把正在扫院子的毛丫子抵在院子的西墙根下,抱住了想亲亲她,毛丫子挣扎不开,便一口咬在他的嘴唇上。
文宝三两下解开了毛丫子贴身穿的花布小袄,当少女果肉般的身子展露在他面前的时候,文宝浑身颤栗起来,他把那个身子紧紧地搂在自己的怀里。这时他看见毛丫子紧闭的双眼中有两颗大大的泪珠滚落下来,这两颗泪珠瞬间就把他冻成了个冰坨子。他听见毛丫子说,你想干啥就干啥吧,从此我再也不把自己当成个活人!
文宝就呆在了那里。
我再也不把自己当成活人,毛丫子这话他信。妈让他今夜要把毛丫子留住,他现在明白了,他就是留住了毛丫子的身子也留不住毛丫子的心了。文宝懊恼地坐起身,看着身边躺着的女人,这个和他在一个家里生活了六年多的女人,此刻让他觉得是那样熟悉又那样陌生。一时间,两个人都不再说话,一个在炕上坐着,一个躺着。恍惚间文宝觉得此刻毛丫子死了,他跟着也死了,然而黑漆漆的夜并没有死,文宝能听到隐隐的人声脚步声、马蹄声。
文宝站起身来,叹了口气,说,想走就走吧!估计到明早晨红军就撤光了,你要走就跟上快走吧!
炕上的毛丫子立时睁开了眼睛,坐起身来望着文宝,两只眼睛黑漆漆亮闪闪的。
文宝烦恼地挥挥手,说想走就走吧,我不拦挡你!
毛丫子迅速地扣上小袄,起身穿上棉衣,两手在脑后胸前快速地编好了长长的辫子,抬腿就要出门,文宝指着柜上放着的一碗饭说,吃了再去吧,两天水米没粘牙了!
毛丫子说,我不饿!
文宝知道,毛丫子不是不饿,毛丫子是怕耽搁了时间他会反悔,就是他自己,也不能保证再过一会就不会反悔哩!
冲到门口的毛丫子回过身来,望着他喊了声,文宝哥!
毛丫子这丫头平时嘴硬得很,以前他要她叫声哥,她从来不喊,平日里和他说话总是没个称呼白搭话。此时一声“文宝哥”倒把文宝的眼睛叫湿了。他挥手要她快走,然后眼睁睁看着毛丫子像一条欢快的游鱼游进了黑漆漆的夜色里。
六
毛丫子走后,文宝就觉得他的心空下了,对以后的日子也没心劲了。再有半年他就把皮匠学出来了,妈也早说了过完年叫他和毛丫子圆房哩,他原本计划着在城里开家皮货店,挣钱养活妈养活媳妇,过个太平安稳日子。
话又说回来,现在兵荒马乱的哪有个太平日子过呢。红军离开后,马家军和保安团又回来了,苏维埃县政府“八大委员”、各街市政府成员和其他一些与红军有瓜葛的人,前前后后被抓了有二百多人。因为自己家里出了“共产丫头”,文宝也被抓去关了几天,挨了几次打,好在妈把红军付账留下的十几块白洋和大烟拿出来买通了马家军官,才算保住了性命。回家后也不得安宁,三天两头就有马家军上门搜查,看有没有窝藏共匪。文宝烦躁得不行,和妈商量了一下,两人就收拾了行李铺盖雇个驴车回双洼子老家去了。
来到双洼子,打开久锁的院门,一股荒凉破败之气扑面而来,夹杂在这股破败之气当中的,还有另一个人的气息,文宝和文宝妈都感受到了这个人的气息,一时间,两人都没有开口说话。那人就是文宝爹,其实不是亲爹,在文宝记忆中,那人背有些微驼,双洼子村民们都叫他杨罗杆。想当年杨罗杆在双洼子也有近百亩土地,可是让杨罗杆发愁的是自己光有土地却没个后人,先后娶了两房女人都不生养,杨罗杆自怨命舛,每夜把女人打得惨叫哩。四十岁上又娶了邻村的寡妇,也就是文宝的妈。文宝的妈是带着文宝嫁过去的,杨罗杆之所以娶文宝的妈就是为了确保找个不但能生娃而且还能生男娃的女人,可文宝妈进门两年也没有生养。有一夜杨罗杆喝了酒,一双醉眼看着正在逗弄文宝的女人,怒从心起,举拳就打,打完了女人又要打文宝。文宝妈就跳起来扬着嗓子喊,怕是你有毛病吧,你自己没本事,就知道天天打女人!杨罗杆听到这话,一下子就泄了气,跌坐在地上半天起不来。其实这个念头他自己心里未尝没有过,只是一直不愿也不敢相信。被女人喊破以后,杨罗杆在女人面前再也直不起腰来,自此性情大变,不再勤勉经营土地了,后来干脆遣散了长工,变卖了土地,成天坐在房顶上,抽着烟锅子,望着远方出神。最终在一天黄昏,一头从房顶上栽了下来,啥也没留下,既没有留下一句话,也没有留下几个钱。死后的杨罗杆就成了村里人久久猜测和议论的一个谜,他变卖田地,村人都能理解,谁愿意把土地家业留给旁姓人呢,只是他卖了地的钱呢?
男人死了,文宝妈也不想在这院子里住了,就锁了院门,带着文宝进了城,在城里给有钱人家打零工讨生活……
妈在默默地打扫着屋子,文宝转到堂屋,看到地上有水淌过泡过的痕迹,知道是屋顶的瓦漏了,就攀着梯子上了房去拾掇屋顶。在屋顶揭起几层瓦,忽然发现了一个油纸包,文宝的心立时就乱跳起来。油纸包沉甸甸的,文宝起初以为是金银,在手里仔细捏着又感觉不像,他颤抖着手一层一层打开油纸,才发现里面竟然是一把黑油油的枪,还有子弹。文宝张着嘴半天合不拢,心里既失望又觉得奇怪,坐在房顶上苦苦思谋着,这样的东西咋会出现在房顶上呢?他不禁回忆起小时候经常看到杨罗杆坐在房顶上出神的样子,意识到这油纸包就是杨罗杆变卖了田地后买来的东西。然而文宝实在想不通,杨罗杆为啥会对一把既不能吃又不能喝的枪产生兴趣,莫非是觉得土地和女人都不如一把枪可靠?或是他仇恨着身边的女人甚至身边的一切想毁灭了它们?这一切已经伴随着杨罗杆的逝去成为永远的一个谜。
直到妈在院子里喊他吃饭,文宝才从房上下来。他不会摆弄枪,对枪也没兴趣,又用油纸包好小心地放在了瓦下。他没有对妈说起枪的事,但这把枪让他有点兴奋又有点害怕,他这一夜都没睡安生,翻来覆去脑子里尽是那把枪,好不容易睡着了也尽做和那把枪有关的梦。
安置好了家,就该过年了。文宝今年根本没心思过年,正月十五还没过就收拾了几样东西动身去甘州了。一路上耳朵里不时听到红军的消息,偶尔也能看见有红军作战后遗下的军帽、背包、饭碗和鞋子等物。每当听到和红军有关的消息,文宝就觉得离毛丫子近了一些,觉得毛丫子还没有彻底从他自己的生活中消失。快到甘州城时,他听到一个买卖人说,前一阵在山丹参加红军的大部分人都又跑回家来了。文宝听了就想,毛丫子说不定也会回来的,当红军那是要把脑袋提留在手里呢!心里就急,想现在妈搬回老家了,毛丫子回去找不着家该咋办呢?
进了甘州城,文宝又听到两个人悄悄议论说,红军在临泽倪家营子吃了败仗,刚才马家军又押走了几个共产丫头,听说里面还有个山丹丫头哩!
文宝一听,心就咚咚跳了起来。忙上前去追着问,是个啥样子的山丹丫头,叫个啥?人家望他一眼,说不知道叫啥,看着就十五六的样子。
文宝感觉这个山丹丫头肯定就是毛丫子。他立刻奔到皮匠师傅那里,说明了情况,求皮匠师傅出面托人四处打听。经打听,确实刚才又有几个女红军被押到了大衙门,但人家说里面没有个毛丫子,只有一个山丹丫头叫胡自英。文宝听了满心的失望,忽然又想起毛丫子在娘家似乎姓胡,他便四处求人,最终把身上带的几个钱都花光了,又借了师傅的钱,才把那个山丹丫头保释出来。
没想到那丫头果真就是毛丫子,但眼前这个毛丫子似乎又不是原来他熟悉的那个毛丫子了。瘦伶伶的身子,身上穿着肮脏、肥大的男人衣服,头发剪得短短的,脸上不仅有伤,还用黑灰抹得脏乎乎的,可能是伤了脚,瘸拉着走不顺当。但让文宝感到陌生的还不止是这些,而是毛丫子的眼神。以前毛丫子哭的时候眼睛里就是个哭,笑的时候眼睛里就是个笑。此刻毛丫子见到他既没有哭也没有笑,但毛丫子的眼睛里有了别的东西,有了他看不懂的东西。这东西让他觉得,毛丫子长大了,毛丫子不是原来的毛丫子了,毛丫子现在变成“胡自英”,毛丫子和他越来越远了。
毛丫子望着他只说了一句,我们一起被抓的还有五个人哩!
文宝知道毛丫子的意思,他摇摇头说,我身上没钱了,就是有钱也没有办法。我师傅到处托人,说你是我的婆姨,人家才让我把你保释出来的。
毛丫子便不再说话。
文宝就问,毛丫子,你咋就成了胡自英?我刚开始还以为不是你呢!
毛丫子说,是在部队上起的新名字。
文宝忽然就有些伤感。“毛丫子”这个名字还是他起的。六年前,文宝第一次见毛丫子的时候,毛丫子才九岁多点,带着两个弟弟跟在她亲妈的后面讨饭到了自家门口,一头乱扎扎的黑头发,浓密的眼睫毛粘着泪珠儿,还有冬日晨光照亮的脸上细细的绒毛,都让文宝联想起小狗小猫之类毛茸茸的小东西。妈留下了毛丫子,对文宝说这个九岁的丫头子是你将来的媳妇,十五岁的文宝就瓮声瓮气地说,我不要媳妇,我才不要这个小毛丫子当媳妇!
此后大家就都叫她毛丫子了。
七
毛丫子先是不开口,后来整个夜晚都处于不停地回忆和讲述中。毛丫子讲的都是红军的事。刚开始文宝不愿听,一听毛丫子说红军两个字他就头疼就心疼,但后来在毛丫子的讲述中他不知不觉就听了进去,为毛丫子捏着一把汗,为那样的一支军队悬起了心。
毛丫子说,她追上部队后,就被分在了红军总供给部。部队供给不足,是数着一粒粒粮食在打仗,她就利用自己本地人的优势到老百姓中间给部队筹粮。到倪家营子后,她和其他一些卫生部门、后勤部门的零散女红军都集中编入了妇女团,白天守围子、抬伤兵、送饭,每天夜里或快天亮的时候,到河边上砸冰、背冰,守在那边的马匪听到动静就开枪,毛丫子说我们好多姐妹就死在冰河上,我自己也差点死在那里。
毛丫子说,马家军围攻倪家营子的几十天,几乎没有一天不不打仗,有时白天晚上都在打仗,累得站着都能睡着,有的战士打着仗也能睡着。
毛丫子说,人家马匪有炮哩,我们没炮,武器和子弹都缺乏,后来女同志把武器都交到男同志手里了,再后来男的有武器也没有子弹了。再后来也不分男同志和女同志、轻伤员和重伤员、战斗人员和勤杂人员了,大家把武器砸折、分散埋了,人人手里都握着大刀、长矛、木棍或石头,单等马匪上来拼杀。前面的同志倒下去,后面的同志就堵上来。
毛丫子说,我们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最后敌人用汽油、柴火烧开了庄门,我们几个人就和其他的战友打散了,后来跑着跑着就被抓了。
在以前,毛丫子还从没有和文宝说过这么多话,文宝注意到,毛丫子说话的时候,眼睛既像是望着他,又像是望着他身后更远的什么,让文宝觉得毛丫子又像是和他说话,又像是在和别人说话。
毛丫子,有句话我一直想问你,你为啥要当红军?文宝打断她,问。
毛丫子愣住了,为啥要当红军呢?是为了反马抗日?是为了逃避和文宝的婚姻?是为了姚共产描述的那个未来的社会?或仅仅是为了姚共产?似乎都是又都不是。好半天,她才说,我就是想过和以前不一样的日子。
文宝又问,后悔了吗?
没后悔!
可是我那晚把你放走就后悔了。红军被打散了,你现在跟我回去吧,回家去过个安生日子。
毛丫子说我已经回不到过去了,我再也忘不掉那些惨死的和被俘的战友,再说在马匪手底下哪有安生日子过?我一定要找部队去。
两人就半天不说话。文宝后来就叹口气,苦笑着说,我记得你从小挨妈打就不告饶,现在想起来,你可真是个当红军的料。
毛丫子也咧嘴笑了,也就想起了小时候的事,想起了在爹病死后无力偿还债务被迫远走他乡的亲妈,想起了九岁时的那个雪后的早晨,想起了文宝妈递在妈手心里的两块大洋,想起了自己脸蛋上冻结的两行泪痕,自那以后她就再也没见过妈和两个弟弟。毛丫子的眼里就有了一层薄薄的泪,想起了自己从小就嘴硬,刚开始死也不叫文宝妈是妈,文宝妈就打她,有时活没干好,文宝妈也打她,她性子倔,心想,妈又不是亲妈,告啥饶呢!所以从来都是支着身子在那儿让妈打,文宝妈就越打越气,越气越打。
八
文宝说,红军已经被打散了,你到哪儿找部队去?是找死呢!
文宝说,马匪时不时地搜山、清乡哩,他们抓到红军就活埋,有的就用刀砍、火烧,还有的就割破喉咙或是挑断筋肋,更有好多女红军还让糟蹋哩。
文宝说,我知道你不怕死,但你为啥非要急着去送死呢?要找部队也应该先把身子养好,等过了这一阵,把情况打听清楚了再去找。
在文宝的反复劝说下,毛丫子终于答应先跟文宝回双洼子养伤。文宝松了一口气,想不管咋样先回去再说。
他们是在离双洼子不远的地方遇见姚共产的。文宝停下了雇来的驴车子,跑到远处荒滩上撒尿,往回走的时候看到几处坟包,其中一个坟包上伏着一个人,而且浑身上下血糊拉拉的,把文宝吓了一跳,仔细一看这个人头上身上都有刀伤。更让他吃惊的是这人身上穿的棉衣,从几块熟悉的补丁上文宝认出那是自己穿过多年的棉袄,只不过那棉袄现在更加破旧,布满了脏污和血迹。猛然看到自己的棉衣穿在别人身上而且浑身是血倒在一个坟包上,文宝虽在白天也觉得有点头皮发麻,不过他很快就想到了这人一定是个红军,而且十有八九就是妈给他提说过几次的那个姚共产。文宝大着胆子上前摸摸,身子还软着,手搭在嘴边,嘴里还有一丝气息。文宝站在坟包前犹豫了很久,最后跺了一下脚,见死不救丧良心哩,就把姚共产扛在了背上。
毛丫子等半天不见文宝回来,就从驴车上下来远远地望着,看到文宝背回了一个人,等到了近前认出他背上的人竟然是姚共产,忍不住惊呼了一声,忙上前把姚共产扶下来,帮着文宝把他弄到驴车上。
文宝就想,现在是带着两个红军回家哩!说啥也不敢白天走了,就把驴车赶到一处土崖下,等天黑再走。
姚共产醒过来说,他是在三道柳沟突围时被俘的,在甘州城里关押了两天,又和另外几百名俘虏被马匪押往西宁。一路上,他们受尽了马匪打骂,稍有反抗便被砍死。姚共产因为腿上有伤,走不快,一个马匪便上来在他脖子上、头上连砍了两刀,他当时就昏了过去,第二天早上苏醒后,看到地上到处是凝固的血迹,四周还有其他战友的遗体。附近来掩埋尸体的老乡见他还活着,就悄悄把他抬到一个小庙里,天黑后,给他送来了一罐米汤。姚共产不愿牵连老乡,喝完米汤就挣扎着走了,走了半天却又昏倒在这里。
听着姚共产的讲述,毛丫子的眼里就蒙上了一层泪水。文宝则细细地打量着眼前这个共产,瘦高个子,深凹的眼睛,眼镜早折了一条腿,用鞋带子绑在脑后,眼镜片上还粘着血迹。咋看这人也不像个红军,倒像个念书人。姚共产说一口四川话,文宝就想不通他为啥要从四川跑到这儿,要受这份罪?
文宝就问,你大老远地跑来吃这些苦,还差点搭上性命,究竟图了个啥?
姚共产说,为了我的信仰,为了正义的共产主义理想。
文宝思谋了一阵,还是不明白,就又问,那你现今是啥打算?
去延安,党中央在延安。我还要继续战斗,为死去的同志报仇!
马家军狠着哩,见人就杀,你不怕死?我们山丹也有一些人参加了红军,后来大多都跑回家来过安生日子了。文宝后一句话是说给毛丫子听的。
姚共产说,这些新红军参加革命时间短,接受的革命道理少,容易思想动摇,不像我们这些参加过长征的红军意志坚定。真正的革命者是不怕死的,如果怕死,中国革命就不能成功。
毛丫子就说,我没有参加过长征,可我的意志也坚定着哩!
嘿嘿,文宝不再说话,心想,这两人都是天生当红军的料。
天黑下来了,星不多,一钩新月把晴朗的夜空衬得明净而深沉。
九
妈的眼睛睁得老大,把文宝拉到一边,说现在谁还敢收留红军?你可好,一次就带回来两个!不过当妈看到姚共产和毛丫子身上和脸上的伤,又叹息道,孽障啊,孽障啊!
文宝和妈商量了一阵,最后就把姚共产藏在了地窖里,每天用盐水给他擦洗伤口。姚共产不愿牵连文宝一家,住了两天就提出要走。文宝看他伤重,不放心他现在走,又怕毛丫子会跟他一起走,就劝他再呆些日子把伤养好。
十多天后的一个中午,文宝他们正在吃饭,就听见有人使劲地捣打着院门,妈吓慌了,文宝急中生智,把姚共产连人带碗都藏进了炕洞。上门的是四个马匪,说文宝家里藏了红军,然后就四处乱搜,连地窖也下去了一趟。文宝一口咬定,家里是有一个共产,就是自己的媳妇子,在甘州城里保释出来的,现在是良民,早就和共产没关系了。
马匪没有搜到共产,就把文宝踢了两脚,又用枪托捣打了几下。临走的时候,一个马匪特地回过身对文宝妈说,凡藏共产的人不交出者不但要罚款,抓住了还要和共产一起枪毙。你家要是真的藏了共产,就把你的儿子一起毙掉。
文宝看到妈的脸上就失了色,整整一个下午,妈都没有开口说过一句话。
姚共产从炕洞里出来后就要走,文宝说马匪这两天使劲抓人哩,你今天出门就是个死,不如躲过几天再说。
十
吃晚饭的时候开始落雪,四月的地已经热了,雪片子落到地上留不住,眨眼就化成了水。毛丫子心想,怕是今年春里的最后一场雪了吧!
妈晚饭也没吃,炕也没煨,早早就躺下了。临睡的时候,毛丫子想把自己压在棉被上的毡子给姚共产送到窖里,下雪了,冷着哩。抱毡子的时候,她看见妈睁开了眼望着她,才知道妈一直没睡着。也难怪,妈今天被马匪吓着了,马匪狠着哩,杀人不眨眼。再过两天姚共产的伤好些,就得赶紧走了,也免得让妈让文宝担惊受怕。
朦朦胧胧刚睡着,就听到屋门呼嗒响了一声,毛丫子心想风太大了,把门都刮得响哩,听着再无声息,便又沉沉睡去了。却又开始做梦,梦到自己也去参加长征了,正过草地呢,脚踩在草地上一脚一个水窝窝,好几次陷下去又被姚共产拉起来。有敌人骑着马追来,却是马匪,看面目竟是今个下午来院里的几个,姚共产这时却不知道哪里去了,只见几个马匪朝着她举起了枪,啪啪啪啪连打许多枪,奇怪的是马匪的枪也不怎么灵光,自己咋也没被打死,也不是很痛,心里急着想跑却脚软得抬不起来。这时就听见有人毛丫子毛丫子使劲地喊她,仔细一听却是文宝的声音,毛丫子睁开了眼,才知道自己原来是在做梦,文宝的喊声却是真的,忙披衣下炕,发现门开着。文宝站在门口急急地说,妈刚去告马匪了!
毛丫子立时就觉得每一根毛发都清醒了。让文宝快去窖里把姚共产背上来,自己去灶房往包袱里收拾了几块干粮,等文宝把姚共产背出了地窖,看着穿戴齐整提着包袱的毛丫子,就问,你也要跟着走吗?
毛丫子点头说,我也要找部队去。文宝软软地靠在院墙上,张着嘴说不出一句话。毛丫子轻声说,他的腿有伤,我和他一起走也是个帮衬。
文宝眼睁睁看着毛丫子和姚共产走出院门,呆愣了片刻,就攀着梯子上了房,从那片瓦下掏出了那个油纸包,三两下剥开几层油纸,把那把枪拿在了手里。他摸索着手里的枪,沉甸甸的,子弹滑润润的,看到这枪他就想起了杨罗杆,他总想不明白杨罗杆为啥要卖了地买来这把不能吃不能喝的玩意儿,如今看来也许一切都是天意,一切都是为了今天。他三两步跑出门,朝着远处那两个渐渐走远的黑影子追去。
十一
几个马匪来的时候,文宝正在炕上装睡。他听到妈把马匪引到窖边,他听到有马匪下到窖里又上来。他听到马匪在院子里搜腾了一阵,有两个来到了他睡觉的屋子。他紧紧地闭着眼,心里紧张得咚咚直跳。一个马匪用枪托在他身上打了一下,他唉呀一声坐了起来。一个胡子长满了半个脸的马匪把马灯举到他眼前问他,共产党到哪里去了?他说不知道,我一直睡觉呢。脑门上就被半脸胡子砸了一枪托,另一个瘦子上来举刀要砍,妈立刻嚎叫着护到身前,说他是我的文宝儿,不是共产党!半脸胡子说,算了,糟杀他干啥,紧着快追吧!
马匪走后,文宝就在炕上呆坐了一夜,一夜里他精神恍惚,神不守舍,耳朵尽响着枪声。天刚麻麻亮,文宝就出了门。凌晨的乡村寂然无人,雪在夜里已经停了,落在地上的雪先是化成了水又在寒夜里冻成了一层薄冰。文宝抬头又望了望天,天边挂着一轮血红血红的月亮,衬得这个黎明更加凄冷。文宝把腰里的草绳紧了紧,向东走去。
他走过梁城子,见到一匹马倒在地上,抽搐着,马腿上有枪伤。他围着马看了一圈,发现马的背上身上都有血迹,看来是有马匪受了伤。一定是毛丫子打的,这马匪一定没有料到毛丫子手里还有枪哩。他想起昨夜里毛丫子接过他递给的枪,毛毛眼里装满了惊奇,连声问文宝哥你咋会有这个东西?他就说,你不要管了,拿上快走!
毛丫子临走又喊了他一声,文宝哥!
这一声文宝哥,又把他的眼睛喊湿了。
又向东走了几十步,就发现了姚共产。姚共产脸上没有了眼镜子,但没有眼镜子他也认出了姚共产,姚共产躺在地上,身上有几处深深的刀伤,肉往外翻着。文宝只觉得喉头发紧,连连咽了几口唾沫。大喊了一声,毛丫子!
最终看到毛丫子躺在一处坡上,一双毛毛眼半睁半闭着,身上血肉模糊。文宝明白,他的毛丫子死了,那双毛毛眼再也不会睁开,毛丫子再不会喊他文宝哥了。
文宝只觉得一口气憋在腔子上不来,好半天才冲着天冲着地冲着这血色的黎明暴喊了一声,老子也要去当红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