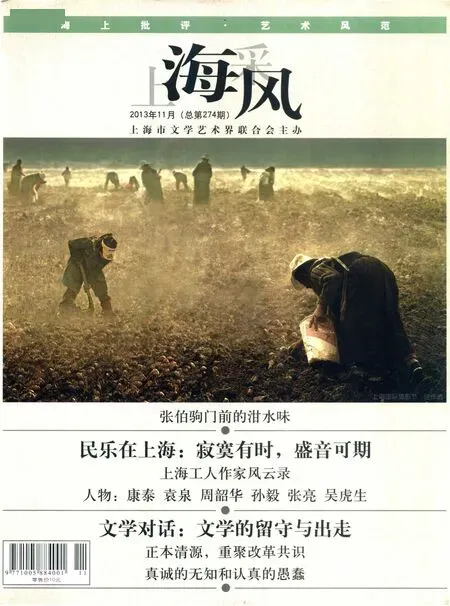写作的罪与罚
文/张 闳
如果小学生写作文也是一种写作的话,那么,任何人的写作生涯都可以从小学三四年级开始。这一时期的写作状态,预示了未来的写作面貌。对于我来说,也就是大约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真切地感受到的确是写作的严酷性。这是一种直接诉诸身体的严酷性。
一天晚上,我同二哥从邻村看完露天电影回来,父亲突然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他脸色阴沉、威严,我知道我们当中又有人要大祸临头了。父亲对我说:“你过来!”哥哥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因为这一次被叫去的不是他,而是我。我忐忑不安地走进父亲的房间,瞥见在父亲的书桌上摊放着我的书包和作业本。事情显然跟读书和功课有关,但我在这些方面很少会出纰漏。没容我多想,父亲开始说话了。“这就是你写的作文吗?”父亲拿起我的作文本,在我面前挥动着,问道。我没有吱声。他突然挥手朝我头上敲来,说:“就知道堆砌一些华丽的辞藻,净写些空洞无物的东西。”就这样,我莫名其妙地挨了一顿揍。
身体上的疼痛倒在其次,让我委屈而又费解的是,我居然为那些辞藻挨了一顿打。在不久之前,这些辞藻,这些成语和形容词,还是我经常得表扬的根源。这些表扬不仅来自语文老师,即便是我父亲本人,他也曾多次公开夸奖我知道的成语多,语汇丰富,等等。在他心情好的时候,他还会向家里的来客炫耀自己的小儿子的修辞能力。而现在,这一切都成为罪过。从荣耀到罪愆,距离并不太远。究竟是什么原因促成了父亲的这一观念变化,始终是个谜。我尚未来得及向他询问此事,他老人家就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这是我第一次因为写作而受到惩罚。但这种惩罚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因文获罪,也就是说,并非因为其内容。我所受的惩罚的原因纯粹属于修辞范畴,勉强可以说成是“文风”问题。第二天,外出开会的母亲回来了,她得知此事,也颇感诧异。她责备我父亲说,你能要求一个小孩子写出什么样的文章呢?!但父亲坚持认为,修辞问题会影响到一个人的人品,如果现在不加以整肃,将来孩子会变成一个虚夸的人,云云。可见,修辞是危险的,虽然不过是一种外表华丽的辞藻,但它可能由外及里地侵犯到一个人的德性,就好像体表沾染了毒素,经由皮肤吸收,而致使身体内部病变。语词并不必然诉诸言说的意义呈现,相反,它有可能带来意义的空洞,而这种意义空洞有可能成为言说者在品质上不诚实和轻浮虚夸的表征,进而遭到暴力训诫。
这是一个严酷的教训。写作与身体惩罚联系在一起,它对我日后的写作无疑产生了某种影响。虽然我至今依然对修辞术有某种程度上的迷恋,但很显然,我无法将修辞视为写作的根本,它只能是第二位的,如果修辞不能带来语义上的清晰和深刻的表达的话,那就只能放弃它。这一点,与中世纪哲学家奥卡姆的“剃刀原理”相类似。“剃刀原理”简单化地说,也就是所谓“简约原则”——删繁就简,少卖弄辞藻。据称,美国作家杰弗瑞·沃尔夫对他的学生传授的写作要义是“别耍廉价的花招”,而雷蒙德·卡弗则说:“我还要更进一步:‘别耍花招’,句号。”在卡弗看来,任何花招都是廉价的和多余的。
奇妙的是,父亲以一种传统中国的方式,传授了卡弗式的写作戒律。当然,他不曾知道这些个美国作家。他老人家心目中最好的作家是中国的鲁迅。其实,在写作原则上鲁迅跟卡弗相去不远。除了鲁迅的影响之外,我想,医生身份也是他推崇“简约原则”的根源所在。言辞就像药物,任何药物都有毒副作用,滥用会带来不良后果。如果能够以一种方式(或药物)解决的病症,就尽量不用两种。后来,我的临床诊断学老师也教导过类似的原则。在我接下来的读书和写作生涯里,这一原则的影响是根本性的。
其实,要找到以繁复和华丽修辞为写作风格的例子,也不是难事。父亲对辞藻的警觉有一定的道理,但有些过分,患上了那个时代特有的“道德过敏症”。喜欢美艳的辞藻和优雅的文体,如同喜欢华丽的衣裳和精美的食物,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然而问题在于,在今天的语境下,父亲的训诫却显得特别重要。近几十年来,世界已经发生了许多变化。对我而言,最深切的感受就是,世界变得更加喧闹了。在通常情况下,喧闹是活力的表征,喧闹总比死寂,比万马齐喑要好。但是,置身于过分喧闹的环境中,我们也失去了许多。首先,失去了倾听的耐心。实际上,我们总是说得多,听得少。可是,在我们这样一个时代,到处都吵吵嚷嚷,有什么值得一听的呢?每一个人都在说,彼此不能听见,甚至要大声叫嚣,以自己的声音压倒其他的声音,让别人听见。在世界喧嚣的表面,澎湃着话语的泡沫,看上去飞珠溅玉,拍岸滔天,然而,我们依旧是聋人。但文学言说总是试图让人听见。它向历史深处的幽灵,向意识深处的本我,向想象中的读者诉说和交谈。但更为重要的是,真正的作家应该首先是一个好的倾听者,倾听古远历史的呐喊,倾听内在的心声,倾听来自高远处那唯一者的召唤。
如果我们把通过话语层面所表达出来的文学性的文本,而不是某个具体的作家及其作品,看成是文学史的主体的话,那么,文学就有其独立的自我意志和内在精神,文学在说话,作家反而成了倾听者,成了某个更高意志诉说的记录者。但语言的变迁,却使得这种倾听和记录的载体发生了变化,写作者有时会陷于“遗忘”的焦虑当中。整个文学史,尤其是现代汉语文学史,始终存在着这样一条隐秘的“焦虑”传统。我们这个时代的优秀诗人和作家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为这一令人不安的传统作见证。
对于一个孤单的个体来说,静听也是必不可少的日课。当人的灵魂体处于某种终极性的境遇的时候,当人要独自面对无边的黑暗的时候,我们软弱、跌倒,终归无助,“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罗马书》8章26节)这种微妙的叹息,只有在万籁俱静的时分,悉心谛听,方可听见。
思想随笔的写作,是在时代的喧闹声中,倾听来自历史深处之秘响和高远之处无限启示的一种尝试,在日复一日的时间流逝中,近乎机械重复的学术和教学的生涯中,这种能唤醒青春时代的诗意梦想,让我感受到生命的存在。在这样一种写作中,我感到慰藉和充实,也是对写作的罪与罚在某种程度上的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