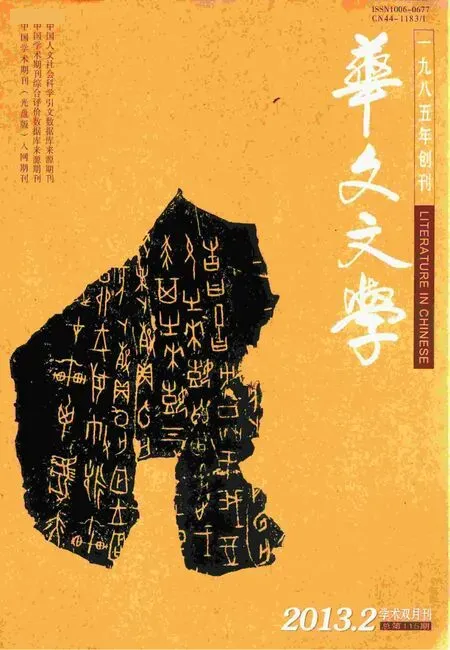向“内”看的灵魂:陈谦小说新论
[美国]陈瑞琳
此为“新论”,是相对于2004年1月2日发表在美国《侨报副刊》上的《灵魂变奏的沧海之歌——读“白领作家”陈谦的小说》。这个“新”的含义里还包括陈谦又给我们提供了一系列新的作品。当然,最重要的“新”,是关于陈谦的小说正在形成一些新的结论。
一、陈谦的小说:一个奇异的存在
蓦然回首,海外新移民文学的发展已经超过了30年。如果说上世纪的八十年代为发轫期,先有周励为《曼哈顿的中国女人》撰写传奇,后有曹桂林在《北京人在纽约》里书写着海外“伤痕”。一“喜”一“悲”,却都是以切入“现实”为基点。到了九十年代,顺应时势,出现了以查建英的《丛林下的冰河》、苏炜的《远行人》、闫真的《白雪红尘》等为代表的“大陆留学生文学”,亦开始有严歌苓《少女小渔》、《女房东》等大量新移民题材的小说作品出现,构成了双部轮唱的混合交响。在九十年代后期,海外新移民文学创作大量增多,形成主导之势,其中以严歌苓、张翎、虹影等作品为突出代表,创作倾向遂开始从“现实”回朔“历史”,由此奠定海外华文文学走向“反思”及“寻根”的新特质。进入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完整的十年正是海外新移民文学纵深发展的十年,在文学的形态上,大部分作家虽然是继续沿袭着前二十年的两种走向:或正面书写着异域生活的文化冲突,或站在新的时空角度,重新回归到“中国书写”,但他们在精神内涵上已大步跨越了对外部世界的现实性关注,从而进入到了“人”的“内世界”的探掘和反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看到了陈谦的“灵魂小说”,这个“奇异的存在”或者说就是陈谦带给文坛的一种方向。
在2012年第10期的《人民文学》卷首语上有这样一段话:关于“新海外华人小说,我们发现,在这一区域,中国上世纪八十年代‘伤痕/反思’文学的遗痕较深,‘我从哪里来’、‘我遭受了什么’那种质询式的外部叙事之上,或许还需‘人是怎样的’、‘人何以如此’这种根本性的内视探究。无论叙事技法还是人文观照,我们都热切期待着这样的小说能够充分地与经典型的当代世界文学交互关联,陈谦的《繁枝》,让这一形态的呈现由可能变成了事实。”《繁枝》是陈谦最新发表的小说,但不仅仅是《繁枝》,陈谦在新世纪创作的系列作品,都是在回答着“人是怎样的”、“人何以如此”这样的内诘,她的笔无论如何变奏,都是在人的“灵魂”这个浴场上飞翔穿越。
在海外华文文坛上,陈谦的小说出现得相对比较晚,而且多不是鸿篇巨制,但是她总能带给读者意外的惊喜和震撼。她好像是一个熟练的穿岩走壁的行者,从不在大路上步步为营,而是先一步攀援到雾障重重的山峦,给我们看那远处幽深的风景。如果把她的作品也比作“奇葩”,这“奇葩”显然并不硕大,也不绚烂,但却是摇曳着非常独特的风姿,若将目光停留,就无法离开,因为她的色彩实在有些复杂,而且她似乎并不按着季节生长绽放,甚至就是开放在时间的前面。
陈谦,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九十年代即开始写作,但她早期是以“啸尘”的笔名在海外网站上撰写随笔,她的“海上心情”专栏曾在北美知名的文化网站《国风》上点击率高居榜首。她的小说创作始于新世纪之初,处女长篇《爱在无爱的硅谷》2002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为此推出小说连播,美国旧金山湾区中文电视台特别专访,陈谦的名字一举为人所知。但真正展现她创作才华和文学功力的则是她稍后创作的系列中篇:《覆水》、《特蕾莎的流氓犯》、《望断南飞雁》,再到《繁枝》,可说是篇篇让文坛为之惊艳。
回顾新世纪之初,很多海外作家还在写移民生活的“身份追求”、“五子登科”的时候,陈谦小说《爱在无爱的硅谷》里的主人公苏菊早已丰衣足食了,但是她却要抛弃掉这得来的一切,而去追求另一种“人生之梦”。当海外作家普遍热衷于表现中西异质文化的交融与冲突时,陈谦小说《覆水》里的依群思考的却是人性深处永无弥合的悲怆。当国内作家开始对“文革”厌倦、对“历史”感到疲惫的时候,陈谦笔下的“特蕾莎”却是在海外开始了对“自我灵魂”的救赎和忏悔。还有,在《望断南飞雁》中,她让自己的人物突然离家出走。在《繁枝》中,血脉的手足竟然就是那“杀人的凶手”。这一切的故事,陈谦真正要表达的并非是曾经的历史或是当下的现实,而是生存在这个世界的一个个苦痛的灵魂。在她看来,灵魂才是一种最真实的存在,这个存在只有她的主人知道,那就是无法遗忘的“疼痛”和“叹息”,它像蛇一样一直盘踞在每个人的心里,咬蚀着灵魂里的血肉,而所有的历史或现实的故事只是这些灵魂的陪衬而已。
关于陈谦何以对人的灵魂和命运感兴趣,她说这与自己多年的美国经历有关。因为在西方的基督文化中,讲的是每个人都有使命,要去发现它,努力完成它,这就是寻找的过程,即搞清楚自己的来龙去脉,自我认识、自我完善、自我完成。此外,陈谦说她真正感兴趣的还是在形而上的,即灵魂上的思考。她说:“这是我个性的一个方面,我比较关注内心,是往心的深处去,是往内走的小说而不是往外走的。因为我觉得世界五彩缤纷就是因为人的心理千差万别,因为这,就导致很多很多事情。我就特别想知道外部世界发生的事件是由什么导致的。我发现,外部的所有冲突冲击都是因我们内心的东西发生的,这是我的理解。我跟别人交流的时候,言行举止都是我心里面思维的一种折射。”“这个世界不管多么缤纷离奇,其实百孔千疮,而且都是从心理出来的。每个人都有病,所以现在我很悲观。真的,就像张爱玲说的,华丽的旗袍下全是那种虱子。我是说人的内心非常重要,所以我的小说自然走这种方式。我就是想寻找‘故事为什么会发生’。我的小说想回答这个问题,而不是‘发生’、‘怎么发生’,不是how,what,而是why,那肯定就要走到人的心灵里去。”(引自2009年11月9日《对话黄伟林:我的小说就是要寻找Wh y》)
解析陈谦的小说,会发现她具有着一种天赋的功力,这功力一方面是来自理科学者特有的缜密逻辑,另一方面则是女性作家特有的抽丝剥茧的形象与细腻,而她突出的智慧是在于对“人性”奥秘的探照。在她的笔下,喜欢写红尘男女,让悲剧与激情同歌,让得到与失去共存,让苍凉与沧桑共舞,让苦涩与忧伤交响。但她最终要表达的就是人的灵魂在本质上无法逃脱的苦痛。这些灵魂的浴场,虽然如梦如烟,但只要轻轻触摸,就能丝丝见血。这正是“人”的内部存在方式,是在心理意义上如何活着的那种方式。这个方式充满欲望,充满梦想,也充满挣扎和绝望。
二、女性的命运:通向“灵魂”的载体
显然,陈谦小说的主旨是关心人为什么会痛苦。在这个寻找“Wh y”的过程中,她为小说中的灵魂找到了最重要的载体,就是“女性的命运”。关于她早期的作品,我曾经概括为海外“丽人行”。今天看来,“丽人”其实是陈谦通向灵魂的一个载体,一个桥梁,她希望通过女性主体的叙说,来完成她对人类灵魂的解剖认知。
关于女人,陈谦说她一直有偏爱。她有这样的话:“走过万水千山,每个人都走过很难的路,就这么连根拔起,移植到异国他乡。我身边的女生都很厉害,没有那种很强的意志力,你走不远的,也无法存活的。用一句很俗的话讲,她们都是自强不息的那种人,我喜欢那样的女生,所以就总是写那样的女孩。”(引自2009年11月9日《对话黄伟林:我的小说就是要寻找Wh y》)
在陈谦看来,揭示女性的存在就是对人类生存本质的一种揭露,因为在女性身上更多地保留着人类原本具有的各种特质,最自然,最原始,也最激烈,比如“情”,因为只有“情”,才是真正属于个人的,也是属于“人”的核心本质。所以,在陈谦小说中,我们看到主宰人物灵魂的关键就是“情”。由此可见,陈谦借助了所谓的爱情叙事、女性叙事、跨文化的移民生活叙事、留学生叙事、文革叙事等等。从而进入到个体生命的深层内视。
在这些个体生命的女性故事里,作者究竟揭示了怎样不同的灵魂,请看下列作品的具体呈现:
1.苏菊:梦想就是一种献身,哪怕是毁灭!
出版于2002年的长篇《爱在无爱的硅谷》,其意义除了证明陈谦架构长篇的能力,最重要是奠定了她小说创作的精神基调,即以女性的故事写灵魂穿越的历程。这个灵魂,并非一般意义的灵魂,而是那种“逆流而上”的灵魂,挣扎,跳跃,献身而悲壮。
小说写的是一个叫苏菊的女子为了反抗“丰衣足食”后的平庸而舍身寻梦的故事。落脚在北美的新一代移民,用智慧的血汗赢得了自己生存的位置,然而,在他们获得了财富上的保障时,精神上却陷入了深深的迷惘。显然,物质的拥有绝不是人生梦想的全部,他们开始思考怎样才是真正富有“灵性”的生活,他们开始寻找让“激情”充分得到燃烧的生命之路。虽然现实的冷酷和人性的弱点最后还是将苏菊的梦想毫不怜惜地彻底击破和打碎。但是,苏菊的故事悲怆但不悲哀,她让自己终于走过了一段生命之途的绚烂,犹如悲壮的飞蛾扑火,虽败犹荣,因为她证明了生命本应具有的火焰激情。
在海外,一代“改革开放”后造就的新移民,只在短暂的瞬间就完成了从“留学生”到“移民”这样的身份转换,生存的重压只是他们最初的闸门。但是,那些走进了稳定富足的“工薪白领”,实现了所谓的物质“梦求”,他们的灵魂又将安置何处?他们的“职业”人生从此就真的“安定”了吗?陈谦的作品,正是以这样一个独特的视角,为我们打开了“移民世界”最牵心动魄的一角。国内著名文学评论家曾镇南先生赞誉她的作品是“以深刻展示旅美华人中的高科技人员的感情缺憾和心灵悲剧独树一帜”。
2.依群:情与理的二律背反
2002年发表在《小说界》上的中篇小说《覆水》,是陈谦早期最重要的作品,她不再追求篇幅上的份量,而是走向灵魂上的深度,可惜当时的学界未能给予足够的关注,今天看来,依然令人震撼。故事写的是一个年轻的中国女子在命运的网中与一个相当父亲年龄的美籍男人生活在一起的挣扎无奈。年轻的依群嫁给了“老德”,是出于复杂的“报恩”情感,但在这个跨国老少的婚姻里,寒心的苦闷不仅仅来自于“东风无力”的痛楚,更来自于那犹如亲情般的束缚与桎梏。依群的灵魂是哑的,她哭不出,她的生命只能在谙哑的深夜里默默地消蚀。后来,她虽然有幸遇到了一个自己想“要”的男人,但生命已如“水”,在“错误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情与理的背叛又怎能在依群的手中把握?《覆水》的寓意是极深刻的,人生常常无解,选择里就包涵着无法衡量的得与失。“覆水”难收,生命不可逆转,即使是重新开始,但那已不是生命的原点,苍然的心早已过了青春的驿站。这是怎样的一种悲悯情怀?是对人的生存状态、人性的挣扎、命运的无奈深层意义的体现,正是这样的大悲境界,使陈谦比一般的情爱小说家走得更高更远。
3.特蕾莎:为人性的弱点忏悔
2006年,陈谦前往重庆,因为她读到很多关于重庆文革墓群的故事,想去看看。于是,“文革”四十周年后的这次重庆之行,孕育出了《特蕾莎的流氓犯》这部沉甸甸的中篇。
在这部烟尘弥漫、扑朔迷离的小说中,陈谦以缜密老道的文字,沉郁忧伤的格调,书写了一对男女走过“文革”的心灵史,以及他们为自己的灵魂赎罪而进行的痛苦挣扎。作品先是在《收获》2008年第2期发表,同年入选中国小说学会年度中篇小说的排行榜,并荣获首届“郁达夫小说奖”的中篇小说提名奖。
小说中的特蕾莎是中国南宁一个叫静梅的女孩,那时她不叫特蕾莎,1975年的静梅只有十三岁,那一年,她喜欢上了学院军代表家的小儿子王旭东。在一个偶然的午后,她竟看到了自己的女同学正在与王旭东搂抱在一起接吻。因为那可怕可恨的一瞬间,十三岁的静梅成了陷害他人的“凶手”。很多年之后,静梅长大成人,明白了嫉妒和爱,也懂得了人性的弱点就是罪的起源。后来的静梅浪迹天涯,从欧洲到美洲,并成为英特尔芯片质控研究的一线科学家。但她的心从来不敢回忆,也从来没有过平静,盘踞在她心里的负罪感,犹如一条沉默的蛇,一直在噬咬着她。然而,小说的深刻之处更在于,静梅后来遇到了一个以研究“文革”为己任的史学家王旭东,却并不是她当年揭发的那个流氓犯,在这个王旭东的故事里,装的却是来自广西的另一个小梅。眼前的这个人,也是一个充满了赎罪心情的人。
很多人称赞这篇作品的主题是关于“文革暴力”的救赎,但我更愿意认为它是一篇为人性弱点忏悔的作品。陈谦在这里表达的依然是灵魂里的苦痛,只是这苦痛与曾经的历史有关,而她真正着眼的是心灵创伤的治疗。在中国,人们经历了太多的心灵创伤,正是因为缺乏这种创伤的心理治疗,所以人们才宁愿选择遗忘。
从崇尚个体生命追求到打捞历史沉钩,正视“文革”给人们带来的心灵创伤,寻找灵魂的拯救之途,陈谦不但成功地开拓了创作视野,还给作品赋予了更为丰厚的内涵,显示了她不断超越自我的艺术品质。
4.南雁:绝望主妇的希望与决绝
发表于《人民文学》杂志2009年12期“海外华人作家专号”的《望断南飞雁》,曾荣获2010年度“茅台杯”人民文学奖,是陈谦又一部探索女性命运的感人作品。被评论界誉为一百年后再写“娜拉走后怎样”。这个关于“绝望主妇”的梦想故事,陈谦说是为了“献给生命中的纠结与决绝”。
上世纪八十年代赴美陪读的女子南雁,已经熬成了两个孩子的母亲,丈夫又是美国名校的生化教授,而她自己也经过努力成为了康奈尔大学的资深生化技师。在这样的世俗美满幸福家庭里,忽然有一天,她留下了一张寥寥数语的字条,带了三千美金,抛夫别雏离家出走了。小说告诉我们:南雁的丈夫沛宁是一个目标明确、不懈奋斗的知识分子。在打拼事业的过程中,家庭的担子主要是落在了“陪读”太太南雁的身上。而在南雁的心底,却一直有着自己的梦想,只是被这样的生活束缚着,压抑着,让她感到窒息。但是梦想并没有死去,那是“人”渴望寻找自己的一种最强大的力量,正是这力量最终让南雁踏上了一条抛夫弃子去完成梦想的道路。这显然是一个冲破女性困境,渴望为自我生命价值做最后一搏的故事,但小说的深刻则在于南雁依然爱着她的丈夫沛宁,爱着她的孩子,她的离去,她的放弃,与爱无关,而是与“人”的灵魂自由有关。
《望断南飞雁》表面上看是写了一个女人突然离家出走的故事,实际上是作者对我们每个人发出的有关精神困境的拷问,故事中的“沛宁”与“南雁”也许正是我们自己。这对夫妻所展示出的对于生活的无力与无奈,其实就是我们每个人每个家庭正在或者曾经甚至未来将要经历的那种心灵上的挣扎与煎熬。但希望正在绝望之中,读者从南雁身上看到了一种勇气,看到了“人”想要成为自己的那种力量。
5.爱与恨:剪不断的“繁枝”
中篇小说《繁枝》发表于2012年第10期《人民文学》。主编在卷首语中如此评述:“关乎族亲血脉、成长、爱和隐痛,中篇小说《繁枝》,正如题目所示,铺叙着繁复的层面,也探寻着清晰的线索。必然和蹊跷、爱的拥有和爱的伤害,都绕不过成长史中繁枝般的元素,它们或浸染或裂变在几代人、不同国度的生活里,可能秉持常态也可能生长异果。对故事的节奏、人物的命运与性格,需要专注阅读和耐心揣摩,才更能体察出真髓妙处。”
《繁枝》里讲述的是一对家族树上有着某种复杂血缘的两个女子彼此间探寻的故事。小说的第一主人公是女化学博士锦芯,她深爱的丈夫回到大陆创业后却发生了情感上的背叛,在苦劝未果的情况之下女博士蒙生了惩罚之意。没想到丈夫却在她的“过量惩罚”中死去,陷入绝望的她选择自杀。但是,被抢救过来的锦芯,不仅要承受着器官衰竭和精神抑郁的双重折磨,还要面对F B I对她的追查。锦芯已走到生命的绝境,在无奈的结局中她选择了悄然而逝。透过这些惊心动魄的情节,作者要表达的其实是爱情在不可考验之下的分裂与残酷。
在这篇侦探般的小说中,陈谦用她的行云流水之笔,把家庭关系、身份意识、寻根意识、爱情命运、女性悲剧等一系列本质性的问题有效地融合在一起。故事的结构非常巧妙,从一个美国孩子的一篇家庭作业——介绍自己的家庭组成和来历开始,牵出了女主人公立蕙对自己的身份和家庭的追寻。她在寻找的过程中,联系上了三十多年没有音讯的同父异母的姐姐锦芯。在立蕙的引领下,读者一步步走进了锦芯的爱情悲剧和生存困境,直到最后的谜底。在这里,“繁枝”的意义不仅是一棵复杂的家庭大树,更是人性的不断分叉,枝枝蔓蔓地无限扩展出去。
喜欢《繁枝》,除了故事的悬念十足,语言的魅力也令人拍案。且看下面一段:
“何叔叔已经在前年春天离世了——叶阿姨的声音飘过来,风一样,极轻。立蕙看到那只蜂鸟‘啪’地一击,尖小的长嘴定在铁网间的草叶里,摇落下的指甲花瓣星散而下,让人想到雪花。她靠到椅背上,感觉后背抽紧了,不响。叶阿姨凑近了,看着她轻唤:立蕙?立蕙回过神来,很轻地说:啊,怎么会是这样?何叔叔年纪并没有很大——她侧过脸,看到自己走出暨大学生食堂的大门,去寻何叔叔白色的身影。她十九岁了,那时。十九岁的她,竟没有留何叔叔吃顿学生食堂的午餐,现在看回去,那竟是他们的第一面,也是最后一面。何叔叔身板挺直地藏在白色的确良短袖衬衣里,慢慢走远。”
就是这样一个在轻描淡写中“慢慢走远”的何叔叔,却正是造就了小说中两个女子非常命运的关键人物。品读《繁枝》,感觉它实在是内力充足,技巧上的很多预兆都隐含其中不断显出故事的张力。小说的节奏含蓄却快捷,直通人物最终的命运,一切都得到了解释,却让人无法平静。《繁枝》里所表达的婚姻与爱情,既是过去的历史,又是活生生的现在,更跨越了东西方的时空。尤其是作者在“爱与恨”的把握上准而狠,从而将人性的“被迫分裂”得到了充分展现。
三、结语
陈谦曾坦言:“如果不来美国,我不会写作。”显然,是海外生活的激荡,诱发了这个理科女生用文字寻梦的激情,文学的殿堂,走进了一位意外的女儿。因为“通过文学,她找到了一扇通向心灵世界的门。”
与北美其她的女作家相比,她追求的不是大格局,她的笔力主要放在一个小切口,再一路探掘下去。陈谦写小说,完全是一种爆发型的状态。一旦冲刺,她就赋予了自己神奇的能量。她的作品,绝没有专业作家的雕琢,遣词的技巧也并不在意,但是她似乎天然地具有着一种抽丝剥茧的逻辑细腻,同时又灌注着丰沛的情感血肉。她对“生活的暗流”有着超乎寻常的感知,只要她的敏感触觉与自我内心的纤细灵性碰撞,就会熔铸出一道夺目的文学火焰。
经过了中西文化的鏖战,陈谦达到了一种新的人生境界,这也是她小说的境界。她这样说:“我终于明白了一点:事实上,无论我是来了美国,或是留在中国,我所要面临的人生挑战其实都是一样的,那就是永远必须在梦想与现实之间作一抉择。而这种抉择的结果,有时是美梦成真,尽管有些成真的美梦并不一定是我殷殷期盼过的;有时则是深深的挫折、无奈的妥协、或是心有不甘的放弃。站到了这个角度上,美国与中国的不同,就仅仅是相同的挑战而其所表现的形式不同罢了。”“正因为梦想和现实之间永远不可能有完美的统一,我生命的织锦上就必然会反反复复交织着追求与放弃,执着与妥协,成功与失败。而在这不断的反复之间,我经历着一种生命中最自然的成长。值得庆幸的是,这成长的结果,就是终于有一天,我学会了不再以成败论英雄。”(2005年“在美国的一种成长”)
“不再以成败论英雄”的陈谦,此刻正在构筑她新的长篇。她在摇曳,她在沉淀,她在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