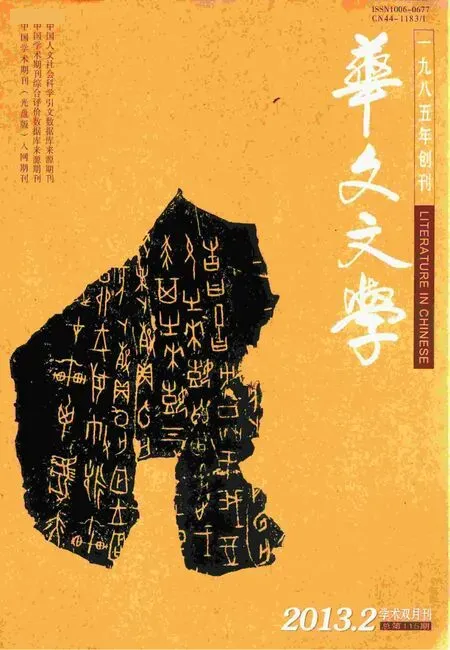在澳门大学研讨莫言和诺贝尔文学奖
荒 林 主持
参加者:商金林、荒 林、杨青泉、张丽凤、
白鹿鸣、张明明、李 昂、戎 琦、李 杰、
刘 勇、黄 静、霍 然、冯佳杭、杨宝宝、

石 琳、马蓓欣、贺欣欣、张 烨、郭永真等
地 点:澳门大学王宽诚楼
时 间:2012.11.14晚
荒林:一个月前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喜讯传来,大家都很兴奋。一周前王蒙先生应邀来澳门大学做驻校作家,王蒙先生的驻校演讲为《莫言与诺贝尔文学奖》,揭开了校园讨论莫言与诺贝尔文学奖的序幕。今晚,我们文学博士沙龙专题研讨莫言与诺贝尔文学奖,请大家自由踊跃表达,希望总结之前的经验,从研究方法、阅读体验、比较视野各种角度,深化研讨。
一、研究莫言的路径
杨青泉:首先我想谈谈研究莫言的路径。许多当代作家是从军队出来,莫言没有上过大学,他后来在解放军艺术学院进修。军队是很锻炼人的,培养政治、军事、文化等等人才。莫言认为《高山下的花环》写得不好,于是写了《透明的红萝卜》,大家可以去了解这段历史。怎么去了解历史?其实很简单,通过阅读文学期刊,我们做文学史研究,必须去接触一些活生生的、有现场感的材料,才能够感悟到当时的文学的现实。因为有许多我们后来的文史学的东西,会遮蔽、或者说掩盖掉一些东西,比如说阅读八十年代最有名的《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像这样的期刊,你去研究,如果一年一年按顺序读下来,你就能写一部文学史,那跟我们现在的这种文学史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觉得这是研究的一个路径,研究莫言,包括和莫言类似的这些军旅作家,我们可以看他作品发表的最原始的期刊,看这些活生生的材料的话,可能比看后来的文学史、或者他后来结集出版的小说更加有感触。
还有就是我想提醒大家的一点,莫言大概在198 4年成名,那八十年代末莫言在干什么?我相信很多人都不清楚,包括文学史也不会提。这个事我小时候有很深刻的印象,当时莫言的脑子里生了一个瘤,他在开刀。当时有一个期刊,叫《海南纪实》,现在已经没有了,这个刊物反映了很多当年的文学啊、生活啊、包括政治啊这些现实。这个期刊现在可能还有一些港台地区的人收藏,那上面登了一张莫言的照片,他当时头部做了手术。我不知道这个事件会不会对莫言有一定的影响,可能是天意吧,因为这个事情,让他疏离了很多的漩涡,一些需要站队的东西。开刀好像对他个体是一种伤害,但反而是一个不坏的事情。但这个我没有考证啊,我只是有这样一个想法。
然后我想讲的是关于莫言的研究。莫言这样的作家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值得研究的东西。像朱栋霖先生在演讲中讲到经典,经典是什么,就是可以不断被人阐述啊、不断地生发出意义,这种能称之为经典。我觉得莫言的文本可以成为当代小说的经典。我们在读很多当代文学作品的时候会发现,莫言是很独特的,包括贾平凹、张承志,都是我们喜欢的。从八十年代以来,莫言一路走来都没有中断过文学的创作,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很多丰富的文学作品,甚至在他脑部开过刀之后还在坚持文学创作,这是非常可贵的。相反我最近看一个报道,不知道是不是真实的事情,就是张贤亮有很多情妇,这是网上的报道,大家可能都看到。像张贤亮这样的作家,我们也很喜欢看他的作品,像《绿化树》、《灵与肉》,这些作品当时很能打动人心,但是后来我就发现他不搞创作了,他去搞宁夏的西部影视城去了。把张贤亮拿来和莫言相比,通过这几十年我们可以看出来,张贤亮比莫言少得很多,至少他后来没有给我们提供更多的有价值的文学作品。从文学史里我们可以知道,莫言最初是学习魔幻现实主义,学习马尔克斯的,文学史把他归类到寻根文学,转向对中国文化的挖掘。然后,借用陈思和的话来说,莫言还有一种自觉的民间文学的立场,我们看他的很多小说都需要到山东高密县去寻找他的行迹。我觉得莫言这个作家的高明之处在于,因为他在体制内,他的身份、他的一些头衔、光环都是体制赋予他的,但他能够在体制内写出、或者说揭露不好的、或者说叙述一些不好的社会现实,这点还是很值得我们钦佩的,至少他不是写完全随大流的、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那些作品。这点我觉得莫言的探索精神还是非常好的。所以,我们可以从很多角度去研究莫言,从西方魔幻现实主义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这个角度去解读莫言,也可以从我们传统文化的寻根的角度去阐述莫言的文学价值,也可以从民间文学的立场去挖掘他的作品的乡土性,所以他的文学的阐释角度是非常丰富的。
第三点我想讲诺贝尔奖和莫言的关系。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还是很值得我们称颂的。不管别人说诺贝尔文学奖怎么样,托尔斯泰没有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等等,它毕竟是全世界范围内很重要的文学奖。莫言获得这个奖对现在的文学是非常有好处的,起码对当下没落的文学现实、倍受冷落的文学注入了强心剂,让大家关注文学,关注当代文学作品。这点是非常有积极意义的。但我们也不应该过度去消费莫言得诺贝尔奖这个事件,比如现在网络上有非常多的传言,莫言的家乡搞一些宣传活动,他的家搞成故居,开发成旅游景点,等等。这些事情莫言也身不由己,他也无法抗拒。
诺贝尔文学奖颁奖的当天晚上,我和我的师兄有一些讨论,他们有一些看法,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提到了莫言跟韩寒,一个是纯文学作家,一个是偶像作家,分属两类作家;然后莫言跟赵本山,更是井水不犯河水。现在网络上关注度的变化更像是一种应激反应,从最初人们不知道莫言是谁,到人们对莫言趋之若鹜、前倨后恭的态度,却真实地反映了我们今天的文化现场和文化现状,人们对于莫言的态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今天中国人真实的对于文学的审美趣味,特别是对于具有精神探索性的文学艺术的真实态度,也从一个侧面解释了纯文学萎靡现实的原因。在这场狂欢化的大众礼赞中,人们各取所需,似乎每个人都得到了满足。至于莫言的作品中更深层次的内涵的挖掘,恐怕没有多少人真正去关心,这也是很可悲的。我们作为中文系的学生,应该承担起这个责任。我们应该多写点不限于莫言的、从中国当代文学的发生、发展的问题出发,去真正做一些有用的研究。这是我最后想说的,我今天就讲这些,谢谢!
荒林:青泉讲述了研究方法,我来描述一下莫言的写作吧。莫言的作品中充满了暴力和苦难,这和他自身经历有很大关系。他的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写一个小男孩,是有自传的因素的,有着莫言小时候饥饿的痛苦记忆。作品中小男孩叫黑孩,没有爹妈,作家把主要笔墨用于描写他饿的那种感觉,那个萝卜之所以那么好看就是因为他很饥饿,想吃这个萝卜,而别人不给他吃还扔到水里去了。莫言独特的经验是别人所没有的,莫言建立于独特经验之上的想象力,也出人意料,也许饥肠辘辘唤醒了他生命中天才的感觉和想象力。作家需要天分,就是说你不知道你会成为一个作家,你的经验有那个时代特别重要的独特性,生命的渴望得到天才的表达,再坚持下来。其实莫言就是这样。
莫言说他写的很多东西别人都不相信是真的呀,比方说他写《丰乳肥臀》,这部长篇得了“大家文学奖”,里面也有他母亲的传记成分,他是为纪念自己的母亲而写。作品中的母亲把吃下去的东西吐出来给孩子们吃。莫言说这都是他亲身经历过看到过的生活真实,没人相信,因为超出了正常经验范围。小时候他妈妈去生产队劳动,那时候生产队管得很严,下工需要搜身的。但是大家都很饿,他妈妈偷偷地把东西吃到肚子里,回家后再想办法吐出来。他说队里的母亲全都是这么干的,为了孩子。这些都是他经历的真实的经验,他把真实再现出来,充满了对于荒谬时代的批判,对于人的奇迹般的生存能力,也自有惊叹。而给我们的阅读体验,可用上震惊两字。
《生死疲劳》一落笔就写一个地主被枪决,灵魂落入地狱,他在地狱喊冤,说是不想来到这个地狱,要回人间讨公正。后来不耐烦的阎王把他送去再投胎。一再投胎,变驴变猪变狗,变来变去,看到的都是人间疾苦,承受的动物命运也与人的命运息息相关。表面上,这完全是想象出来的,但想象如此之奇特悲壮,让人又悲又乐,尽写出苦难经验的万般无奈滋味。只有经历并深刻认识过苦难的莫言,才能对生死疲劳有轮回想象力的表达。借助佛教中轮回观念,通过一个个生命对于命运的承担,揭露残酷的生存现实,反思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诺贝尔文学奖称莫言小说是魔幻现实主义,并说有着中国乡土世界的根子,相当深刻。
莫言总共有三部作品翻译为瑞典文,它们是《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和《生死疲劳》。这些作品中他的经验,以及他对中国社会深刻的批判性,都有着乡土的、地域的和个人的经验特色。莫言得奖是当之无愧的。
二、阅读莫言的角度
张丽凤:我在读本科的时候阅读了莫言的一些作品,最近又回顾了一下。先说说莫言得诺贝尔奖的事儿,然后再讲讲我读莫言作品的读后感吧。我比较喜欢他早期的《白沟秋千架》和《透明的红萝卜》,后期的作品比如获得茅盾文学奖的《蛙》等等少了早期作品的平实,多了一种浮躁、不恰当地说甚至有点儿轻浮。但是要肯定的是,莫言弥补了中国文学上的一块缺失,包括《生死疲劳》和他写的很多东西。我也是山东人,他在《蛙》里写的东西,都是生活中非常现实的东西。后来人们贴上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的标签,只是因为我们乡村中国一直没有能够表达自己生存状况的一种技巧。我自己的感受是,莫言最大的贡献是把乡村中国的面貌呈现出来了。他和鲁迅的乡土文学不同,和马尔克斯——他对那片土地也理解得非常深,他看到了外面的东西,反过来能够比较自由地反映出来他非常熟悉的这片土地,莫言也是这样的。中国文化传统的一部分,包括轮回转世,在我们山东,经常会说谁谁是什么投身转世。比如我大姑家的表姐,天资聪颖,但是从小身体特别不好,一直看不好,然后就说她是花童转世。所以说,在乡村中国,有很多东西解释不了的时候,不知道该如何解读,痛苦需要安抚的时候,这种文化历代一直传承了下来。但是新中国之后这种文化就被抹煞了。现在莫言出来,让我们意识到,这种文化是中国的,而且是一直存在的,不会因为一个制度或者一时的政策将这种文化基因断阻掉。大家可以看一下《乌合之众》,勒庞在里面讲到,文化这种东西,经过改朝换代貌似变了,但是回想一下,这种最基本的文化基因其实是一直延续着的。另外,我觉得莫言是一个特别会讲故事的人。我自己就觉得听过身边那么多事情,传奇的事情,但是一直都找不到方法来表达,而莫言能够通过很多细节让人感受到故事的真实性,甚至比你自己亲临现场更能体验到一种真切感,这一点可能是他和其他作家不一样的。《白沟秋千架》写农村妇女背高粱叶的细节,还有后来的《红高粱家族》,《檀香刑》里他对那些酷刑的描写,它呈现出来的让你觉得你能看到,所以说我觉得他的作品被改编成电影也是非常有画面感的。应该说,关于魔幻现实主义,他是藉由马尔克斯然后忽然开窍了,找到了自己的非常自由的表达方式。我就讲这些,谢谢大家。
荒林:谢谢丽凤和我们分享你们家乡的经验,使我们对莫言的理解更加地道。我觉得你的想法很好,就是借西方来开窍,这句话真的说得很好。
莫言的写作基于扎实的生活经验,也基于对写作技巧的驾驭。有时候他很有趣地把他的写作奥妙告诉读者。比如,他的小说里写一个人死掉的场景,他莫言作为作家自己出场来说话了,他说,不知道该怎么写一个人过于古怪的死亡,他列举了马尔克斯会怎么写,托尔斯泰怎么写,并把人家怎么写都列一通,然后说真不知道该怎么写,别人都写过了,就不写了吧。读起来非常神奇有趣,却让人反思,当已经没有什么语言可以表达人类的死亡痛苦,人类到底发生什么了?!一种荒诞美学也就在莫言的作品中诞生了。
莫言写荒诞很深刻。《蛙》里面不断地给外国人写信,《丰乳肥臀》里男主人公的父亲也是一个外国人,而且还是个瑞典人,传教士,会说高密话,会念《圣经》,却不会说瑞典语,他临死的时候稀里哗啦说了一堆瑞典话。怎么会有一个瑞典的传教士呢,什么国家都可能,就是没有瑞典的可能,而莫言写的是没有可能的可能。而且他的小说里会出现“莫言这小子怎么怎么写的,都是骗人的假话”,在小说中就插这么一段,写作人忽然跳出来说这个,很搞笑。所以你看他在作品中调侃西方,只有中国足够强大了才会有这样的自信,这一点也值得研究,很有意思。
白鹿鸣:多年前,我在北京,我见过莫言,40多岁的样子,特别挫。那时我们学校的老师都特别牛,当时我就想这个人怎么混的啊,我们学校还有这么挫的人。别的老师都是坐豪车走的,这个人还和学生一起坐车。当时我们去开会,领导颁一个叫“文华奖”的奖项,鼓励大家创作。莫言没有发言,也没有任何表示。所以我觉得莫言在得诺贝尔奖之前是特别不如意的,他在我们学校也没有人照顾他。不过,那时,也许是我个人的印象。
荒林:莫言非常有才,表面木讷,内心非常自信。我看过他到德国的一个演讲。说,我本来不想来的,但是我老婆一直说让我来。好男人不都是要听老婆的话嘛,所以我就只好来了。来了之后我就发现对了,要是我不来就会背上一个黑锅。我老婆说你给我带个锅回来。因为德国的锅是特别好的。然后我就去买了一个锅,德国的锅真是很漂亮的。他描述了锅的厚度啊质量等等。然后给老婆打电话,她说再买一个。但是我说过关只能一个的。我听老婆的就是对了,我回去给德国推销锅子。德国人听了之后都笑了,狂鼓掌。他接着又说,要是我不来,就会背回去一个黑锅,就真的是两个锅了。然后德国人都想知道为什么,但他说了一大堆都没说到这个,直到最后他才说,我这次来什么事情都不重要,但是我这个人是不想背黑锅的。因为我还没有来,你们记者就说莫言会来,而且莫言是讨厌谁、不想跟谁住的。他说,我都没来,你们就写成这样,我讨厌谁,传到中国这可怎么得了。然后大家狂鼓掌。他是非常有趣的一个人,很会讲故事,他的批判力和讲故事能力都非常强。我讲的都没有他讲的有意思,我看了这个故事,但是再叙述时就没有他那样有天才了。
今天中午的时候,商教授请王蒙先生吃饭,王蒙先生也是很会讲故事的人,说了莫言一些有趣的故事,下面请商教授跟大家分享一下。
商金林:我是让荒林给诓来的,她说今天晚上是朱老师(朱寿桐教授)的课,讨论莫言,让我来列席旁听。是这样的吧,荒林?现在逼着我发言,真为难我了。
王蒙先生的演讲大家都听了吧,他讲得非常深刻、睿智、幽默。对王蒙先生,我是非常敬仰的。他这次来澳大演讲,第一讲就从莫言得奖讲起,对莫言有一个很准确的定位。莫言获奖,我并不惊讶,以前也参与过评奖,我认为得奖的作品都是好的,可得奖的作品不一定就是最好的。莫言得奖的重要意义有很多,其中有一点就在于这个奖提示我们要重视对中国当代作家的研究,我们当代作家写作的水平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准。过去有些人轻视当代文学和当代作家,认为现代作家知名度再怎么小也是一座大山,当代作家名气再怎么大也只是一尊土丘。莫言得获,就郑重其事地告诉我们要认真阅读和欣赏当代作家的作品,对他们的评价绝对不能简单轻率。莫言得奖也让我们打破了对诺贝尔文学奖的迷信。以后,我们中国再有人得诺贝尔奖的时候,我们也就不会惊讶了。莫言得奖,使得我们以平常心对待这个奖项。
莫言得奖的第二天,记者采访他的爸爸。他老人家八十多岁了,满手的老茧,拿着镰刀,还去地里干活呢,那场面真让人感动。仅从这一点看,莫言这个人就非常了不起,他出身在一个农民家庭,他的家乡至今还不那么富裕。莫言是在艰难的奋进中成长起来的。莫言得奖,也使得我们对于家乡,对养育我们的大地增加了一份感激和敬畏的心情。
王蒙先生演讲时说到,莫言应该得奖,但是我们还有很多作家:王安忆、张抗抗、铁凝、余华,等等,差不多有十位吧,也应该得奖。王蒙先生还说到记者采访刘震云的事。记者问刘震云“莫言得诺贝尔奖了你有什么感想”。刘震云回答说:“莫言得奖,你应该去采访莫言呀,怎么来采访我呢?这就好比我哥哥结婚了,你们问我‘哥哥结婚’有什么感想,你们要问我哥哥呀,我哪知道。”这个幽默的回答,大概也透露出我们国家像莫言这样水平的作家,还有不少。这让我们感到格外高兴。莫言很了不起,但就我之前的阅读感受而言,我更喜欢陈忠实、贾平凹、余华一些作家,这当然也与我没有好好研读莫言的作品有关,以后一定找机会好好看几部。
就作家如何描写中国社会而言,我总觉得不能把中国社会描绘得太丑陋,这是第一。第二,作品最好要能给人以美的享受,要能给人以知识和智慧的享受。中国社会太复杂了,写中国社会,要相对的客观、公允,回到当时的历史语境中来写。前天看电视,看到有记者采访莫言,莫言说“魔幻现实主义”这个翻译不准确,他的作品也不能叫“魔幻现实主义”,而叫“幻想现实主义”。莫言的作品文笔好,感觉细腻,想象力丰富。当然,诺贝尔奖为什么颁给莫言,这个问题同样值得研究。王蒙先生说中国达到莫言这个水平的作家大约有十人,为什么把奖颁给了莫言了呢?在庆贺莫言得奖的同时,我们来思考这个问题,这对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是有意义的。
张明明:我想就前面老师和同学们谈到的观点做一些互动吧。首先我想谈莫言获奖的问题,他获奖后得到非常两极的评价,评价不是过高就是过低。我们应该以较为平和的一个态度来看待这个事。还有一点我很同意青泉刚才说的,通过莫言,很多普通人开始读小说,开始重新进入文学世界,这是对我们来说最有现实意义的一件事。从我的角度来说,我的妈妈没有上过大学,在我印象中她从来没有主动读小说的习惯。但有两次。一次是她让我给她找一本萧红的小说,我问她为什么,她说萧红是黑龙江的作家,作为一个黑龙江人应该了解一下她的作品。还有一次是前一阵子,莫言获奖了,她让我在网上给她买莫言的小说。所以,从普通人的角度,莫言获奖是有很积极的意义的。另外一个,我想谈一下刚才丽凤谈到的,乡村中国这个概念。很多人评他是魔幻现实主义。我问我妈妈,你觉得他写得怎么样。她说,他写出了很多人不敢说的话。因为她只读了《蛙》,写计划生育的,至少现在很多人不敢写这个题材。我妈妈接触过很多从山东来的农民,他写的跟他们讲的真的是差不多的,他写的就是那一段时期中国的现实,她能看懂,因为是事实,他让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有共鸣。他写的也是一种现实,很多比如轮回啊、鸟仙儿啊、大仙儿啊,其实现实生活中很普遍的。包括现在在农村,至少东北农村是很普遍的现象。可能不了解这种现实生活的人就觉得他是一种魔幻,但是有那种生活经验的人就知道写的就是现实生活的经验。昨天我问一个采访对象,觉得莫言写得怎么样,他说莫言写得挺好的。他的想法和商老师差不多,莫言并不是最好的。他的成功之处是,把普通人的生活故事讲得很生动。他很有语言天赋,有时候甚至觉得他在炫技。别人不敢写的他写了,不敢触及的他触及了,作为一个先锋作家他是当之无愧的。另外,他的语言天分和文学才华是很高的。基于这两点,对于普通读者来说他是非常优秀的作家。
李昂:就着刚才明明讲到她妈妈读莫言小说的问题,我想接着说。我们要知道明明的妈妈不是普通的妈妈呀,她是一位中文系博士的妈妈。莫言得奖这个事情,能让中国文学地位上升么,恐怕是有限的。莫言得奖的时候,我也很兴奋,这些作家作为我的研究对象,我一直在接触他们。我举两个很有意思的例子。我的一个师姐,当时把Q Q签名改成“莫言得奖,兴奋得睡不着!”我们在座的,会觉得一个中国作家得到世界级的大奖,都会很兴奋,然而这是通俗地说——圈内人的态度。我妈妈学校的一个老师,知道莫言得奖的时候问“啊,这是哪个班的学生?”所以影响这个问题是值得怀疑的。文学,在今天,它的很多功能已经被别的艺术形式取代了,电影啊、电视剧啊。很多人最初了解莫言,难道不是他作品改编的电影《红高粱》么。从网络购书的角度看,他的书的销售量,毕竟也没有达到洛阳纸贵的水平。所以我认为他获奖对文学地位的提升,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平时大家会选择看看电视剧、电影等等别的消遣方式。
最近我在研究经典型的问题。本来我们看待莫言,他是那一类作家中的一个,并没有单独列出来。有的作家风格也差不多。就像他的血腥或别的,我们可以在余华的作品中找到,他对文革的书写,比如严歌苓等等,都可以找到这一类的书写。他得奖对当代文学经典型地位的确立有一定帮助。古代、现代文学的经典性已经确立了,而当代文学离我们太近,难以定位。甚至我们一度消极地认为,当代文学已经死了,只有偶像作家才能畅销,而莫言、余华这些先锋作家是非常小众的,很少人去读的。而莫言获奖对经典的建构是有帮助的,他的作品有内在的质量,也有外在建构的力量。当然这也是十分可悲的,说明我们没有这样的能力,而需要藉助外来肯定才能建构自己的经典。
自埃塞加入国际竹藤组织以来,国际竹藤组织在埃塞执行了15个项目,资助方包括中国、加拿大、美国、欧盟、联合国及世界银行等。项目内容涵盖竹林栽培、管理和加工利用。2018年国际竹藤组织发布了与清华大学合作的埃塞竹子资源清查结果,主办了竹林碳汇和竹子标准培训班。
当然这也是好事,我觉得莫言挺淡定的。电视采访他大哥和村里的人,他们说他就是我们这最普通的农民,把他放人堆里就找不着了。他和所有的农民都一样,他有农民的质量。
我记得大学课本里把莫言作为魔幻现实主义的代表,但我认为魔幻现实主义不是一种“主义”,而是一种叙事技巧,主义有点太大了。莫言有的时候用它,有的时候不用它。大二的时候,我特别迷《红高粱家族》,但后来我忽然生厌了,觉得烦了。刚才我在大家的讨论里忽然明白过来,就是因为他不断地使用这种技巧,让我厌倦了他。像刚才丽凤说的,他写的是真实的生活状态,只是那种生活离我们很远;还有一种可能,他在叙事过程中,将现实生活做了陌生化的处理。我认为莫言最打动我的,是他将现实生活作了陌生化处理,而不是他的魔幻现实主义的技巧。
三、获奖、翻译、比较的视野及其他
戎琦:莫言作品很多,我又没有看完,不敢妄言。我就谈谈为什么西方将诺贝尔文学奖颁给莫言啊。就像王蒙先生说的,西方倾向于颁奖给社会主义的叛徒。莫言他是一个怎样程度上的“叛徒”呢?我认为他的态度还是比较客观的,他的《生死疲劳》写很多中国的现实,但好像也没有太多的反思的力度,能够提供给人们反思的经验。我看《生死疲劳》,感觉到的是他凭借着他的经验,以及娴熟的写作技巧,有点概念化,再加上他的魔幻现实主义的笔法。他获奖以后,国内对他的很多质疑是他对中国现实的揭露、批判并没有达到如何的程度,很多质疑的声音都是这样的。没有担负起一个严肃作家、一个知识分子的作家该做的。好多的声音都是这样。可能西方不想开罪中国政府,不想再颁给高行健这样的呢。
李杰:我就说一说前段时间重读《檀香刑》的感受,其中千刀万剐的残酷刑罚,看着令人极度恶心,将刀手的心理、受刑者的心理,以及围观的群众的欢呼、官府对刀手神乎其技的赞叹,都写得令人脊背发冷。我觉得莫言的写作成就不及余华,从个人感受来说,我更中意余华在对苦难的叙述中间保持冷峻的批判,而不是莫言这样偶尔在文本里“出戏”的技巧,这会破坏他所酝酿的、文本的张力。莫言这样的作家获得诺奖,能够让我们对当代作家群体的成就的定位更清晰。莫言的作品中是否将一些丑恶的东西做为他炫耀写作技法的素材了呢,值得我们各位深入思考。
荒林:戎琦的观点是诺奖的公正性是令人质疑的,西方人似乎更喜欢看到中国的那些丑陋的东西。李杰讲到看《檀香刑》的恶心感受。我也说说我看《檀香刑》的感受。有一段时间北京特别风行,书摊都是《檀香刑》,我就绕道而行,因为太暴力了。生活在北京已经有强烈的暴力感受了,还要去看这么暴力的东西,我就一直没看它。直到来到澳门听老师聊起,说台湾人很喜欢《檀香刑》,我很不解,然后不得不去看这个书。台湾是一个非常开放的社会,他们看《檀香刑》持一种对中国文化的象征意义的观点,认为中国文化在百年中的苦难,就类似《檀香刑》的这种极其难受、极其恶心的感受,一点点细致地展示给人看。这里面对西方文化是有很深刻的批判的,并不是说展示给西方人看。因为受到西方人的挤压,中国才会发生这么恐怖的事情。因为故事的背景是德国人在胶州修铁路,中国人起来抗议德国人。这个领头的人被抓了,德国人坚持处死这个人。我在看这个小说之前查阅了一些清朝末年的数据,发现清朝末年就是这样的,然后再看《檀香刑》,才发现他还没有写得足够的恐怖呀。莫言写的时候他已经很有象征意义了,近代中国深刻的苦难是笔下难以书写的,他对那样的恐怖主义、不人道、反人性的制度的反思和批判。所以我是不同意莫言是向西方展示的观点的。他有很强烈的象征性,从人性的角度来看,《檀香刑》的展示本身就有很强的批判性。
刘勇:我特别同意前面学姐说的乡村中国的这个观点。我的毕业论文写过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马尔克斯本人也特别不认同魔幻现实主义的观点,他使用当地人的视角在看待世界。比如里面写到黄色代表不祥,当地居民都是这样认为的,当地的文化中就是这样的,这是很独特的体验。他写出来让外面世界的人来看,就很魔幻。莫言和他是异曲同工。余华说他第一次看马尔克斯的小说,感叹道原来小说可以这样写。我觉得莫言应该有相似的感受。他把看到的、感受到的、想的写出来,就是很好的小说,就可以讲出很精彩的故事。还有他小说语言的问题,普通人会觉得他的语言有炫耀的成份。这也是他的特色,他能够写出很细腻的感受,从艺术的角度说,那就是非常好的艺术品。另外,《生死疲劳》四十九万字,展示了六十年的历史,他展示了历史的横截面,把他知道的写出来。他在体制内有很多话不能说,但他敢说真话,这就够了。他到底有没有把中国人丑化?中国人丑不丑,大家都是中国人,都知道。他写出来,西方人爱不爱看,肯定是有的。我觉得,丑陋既然是有,为什么不能写呢,我们为什么要粉饰呢,为什么不能展示出来。《檀香刑》里也有中国人很美好的东西啊。我觉得没有丑化,只是呈现而已。还有诺贝尔奖的公正性,有各种各样的质疑,是否有倾向性。我觉得重要的是莫言完全具有获得该奖的水平,我觉得他够得上诺奖,诺奖也会因为颁发给他更添光彩,这就够了。
黄静:我也谈一下我的母亲给我电话,说莫言获奖了,问我看没看过他的书,我说看过三部。我妈是计生办主任,她看了《蛙》。她说这书太真实了。特别是农村计划生育这些事,此中种种,特别真实。我很敬佩莫言的一点是,莫言敢讲真话,他对现实丑陋的表现问题,我相信他创作的时候本着文学该担当揭露现实丑态的责任,而不是歌功颂德的工具。然后谈到诺奖的问题,我觉得大家想得太过于复杂,王蒙先生转述刘震云的当代作家里至少有十位水平和莫言相当的说法,他们为何没有得奖。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很简单,诺奖是瑞典人评的,他们不懂中国字吧,需要翻译吧,那翻译的水平就决定了评委对这个作品的认识,莫言作品的翻译可能更好,对作品的内在表达准确转化为另一种语言了。总的来说,对于莫言获奖,我是很支持的。之前我在网上看到莫言新书的发布会,出版社把郭敬明请去了,莫言自嘲了一把,说自己写了这么多年书,按照赚钱来评价,远远不如郭敬明。这让我思考到了文学的受众群体,现在的娱乐方式这么丰富,电影、电视,等等,还有多少人看文学作品?有多少人看比较深刻的作品,而不是进行肤浅的快餐式的文学消费?从这个角度,我很高兴莫言获奖,会挽回一些看深刻文学的心灵。
荒林:刚才这位同学谈到翻译问题。莫言的作品是当代被翻译到外国最多的作家。一方面,莫言比较重视他的作品的翻译;另一方面,他作品的文学性非常强,西方人喜欢看,有文学趣味,这涉及到文学的功能。
霍然:之前提到过贾平凹,我觉得莫言和贾平凹的作品在很多情况下有共通之处,对社会现实的反思性是共同的。但是莫言的语言、艺术上更让我难以接受,而贾平凹的相对趋于平和。莫言得奖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两方面,一个是作品中艺术方式的运用,他把情绪、情感、内心体验都放在了故事情节和结构之下,表达非常到位。在批评社会现实方面,他采用的是一种含蓄的手法,他的终极指向表达得非常完美,是批评与手法的完美结合。他讲了大家都知道但是没有讲出来的东西。我本科是学传媒的,我认为莫言获奖这个事情的关注度是非常高的,可以带动那些有文学理想但是没有很多阅读经验的人投入到文学的阅读中来。
冯佳杭:我非常赞同之前学姐说的莫言的作品的魔幻现实主义是将现实生活进行陌生化处理的观点。《红高粱》更多的是莫言的理想世界,是现实中很难达到的。文学作品本身就是虚构大于真实。他在虚构中构建真实,用理想化的笔调写现实,产生距离美;但同时不是完美的,又有缺陷,从而产生奇异的美感。
杨宝宝:现在对莫言作品的深刻性存在着很多争议,很多人说诺贝尔奖是对中国主流话语的一种妥协。在微博上很多人认为莫言的作品不能深刻地反映中国腐败的现实。例如莫言曾表示对刘晓波获奖“没有看法”,于是很多人认为他对中国现实的反映是不够的。但是作为搞文学的人来说,文学的意义是否必须落脚在它的政治意义上呢?《蛙》有反映社会的大胆,这是一方面,在别的方面也是成功的。比如它的语言、西方写作技巧的借鉴。我们应该重视作品的政治意义,但还应该结合别的艺术方面来看待、评价作品。落实到在文学史的评价上,陈思和提出过应该重写文学史的概念,在之前我们对现代文学史的看法都过多局限于左翼文学,走了一个极端,排斥了很多东西。朱栋霖老师说他写的文学史要重新为莫言设立专章,北大的那一版文学史也要马上重新修订,《透明的红萝卜》也马上要进入高中课本。我认为这是走了另一个极端,过度地放大一个作家,将他神话。他不是当代唯一的一个,不应该被神化的。做研究者应该保持对他持一个什么态度,这也是很值得研究的。我很喜欢余华的小说,有一个学者曾经将余华和莫言做过比较。余华早期的作品里也有很多表现暴力的东西,他的作品既保持了先锋性,又有很多大众读者喜欢他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他的作品里做的是减法,削去了作品中很华丽的部份,语言很简单,最大限度地保持思想的精髓;而莫言做的是语言的加法,有炫技的倾向,也是很好,他们各有特色。
陈家杰:莫言得奖了,他的作品是好作品,但不一定是最好的,我们不要把他过于神话,我是不会特地去看他的作品。
尤坤:我非常认同他的看法。莫言获奖对我的生活没有太多改变,虽然那天我去银禧楼二楼的那个书店,畅销书价上摆满莫言的作品,我才意识到随着诺奖的公布,莫言的风潮确实席卷来了。我记得本科的时候,我的老师说当下比小说更精彩的是社会。虽然我们已经预计到莫言的风潮会到来,但是真的来到、甚至比我们的想象还要夸张,不得不感叹获奖的影响力之大。但谁在读获奖的书、谁在读畅销书?文学的受众由于自身阅历、修养的不同,他们读的书会相同么?文学的意义,一个是质疑,寻找精神的家园;另一个在于提示我们去反思。他的书把六十年挖出来,让不同的人,军人、农民、领导,大家从里面读出不同的东西来。我们常看到内地的书店里,很多农民工坐在那里看书,对他们来说是精神家园,同时想一想生活经验中没有的、或者已经麻木的东西。另外,我们不能靠着一股浪潮去读书,阅读应该是终身培养的习惯。
谭思维:我的疑惑在于,诺奖评审看到莫言的作品,是经过翻译的,那是不是说,翻译决定了一部作品呢?翻译能不能全面地代表莫言所写的所有的东西呢?他们看的是莫言的作品,还是翻译之后的实质是另一个作品呢?
杨青泉:评审里的马悦然是汉学家,他看的是中文文本,其他人看的是翻译的文本。翻译不可能做到完全的等值,现代汉语和瑞典语的差异非常大。他的内容是可以传达的,但是艺术性的传达能做到百分百是不可能的,甚至百分之六十也做不到。(谭思维补充:我说的是作品的思想。)内容是每个人都能看到的,但是作品的思想是每个人的理解都不一样的。
李子涵:我浅浅地看了他的《透明的红萝卜》、《檀香刑》等几个作品,给我的感觉是他的作品千篇一面。语言上,有人说他是语言上有炫耀。他的作品给我的感觉特别 嗦,色彩、感官给人的冲击很强烈,但是太累赘了。还有一点,他的作品的乡土气息给我一种亲切感。这一点他和陈忠实的《白鹿原》都让我很喜欢,虽然写的是不同的地域,但是都是乡村的感觉,真实的存在,比如民间迷信的部分。我就说这些。
许玥:我在高中的时候读过语文读本上选的他的一个短篇小说,《枯河》。当时看了之后特别震撼,一直在我脑海里萦绕了很久。写的是文革时候的故事,他写的这个题材和语言上的冲击感,是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的。但就像李子涵说的那样,他的有些描写确实是比较嗦的,有些环境描写为了渲染,铺陈很多笔墨,有时候我觉得不是很有必要,他洋洋洒洒会写很多。另外我想谈他为什么会获得诺贝尔奖,之前好像是朱老师说的,西方人比较喜欢纯粹的中国味儿的东西。从他们的审美来看,特别有东方感觉的。他的文本的内容,对于中国乡间的描写,打动了评审,看到了最中国的一面。他触碰到计划生育这些,还写得不错,所以他被青睐吧。而关于畅销书的问题,比如现在流行的《盗墓笔记》等等,而莫言的书没有一个让你看完之后,放下书,还能够想起来的、令人印象深刻的主人公。前面有师姐提到莫言作品前后期风格不同的问题,我想是不是他写《透明的红萝卜》的时候是憋着一口气要写好作品,后来则是为了写让编辑们喜欢、而不是为了读者写呢?还有他很欣赏张悦然这样想象力很好的作家。
石琳:我的本科毕业论文写的是贾平凹的作品。我觉得这两个作家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在幻想上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讲动物的精怪,如《檀香刑》或《蛙》里面对动物的想象,和贾平凹的《怀念狼》,和《聊斋志异》里面都是很像的。另一方面,我觉得他们对于历史、生殖历史都非常关注,《蛙》、贾平凹对于阉割的历史的讨论。青泉师兄之前讲到莫言做过手术,其实贾平凹也是得了肝病,经受了很多病痛的一个作家。病痛对作家的创作是不是有影响的呢,他的身体会促发他的想象力的迸发。大家说莫言的语言 嗦,其实贾平凹更 嗦。他们俩在身份上都是农民。莫言的作品中包含了更多的现代性的技巧,流行的元素,很能抓住读者的心。同时他对乡土的感受,是非常真实的。他把精怪的故事跟生活故意拉开了距离,让我们觉得想象力很丰富啊。而贾平凹讲这些精怪传说的时候更加真实,他会把人的生活和传说故事结合起来,而不是单独拎出来,做夸大、做流行元素的包装。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更支持贾平凹。当然莫言获奖我也是很高兴的。
荒林:贾平凹和莫言确实有很多人拿来讨论。有人说贾平凹被人翻译得太少了。还有一种说法,贾平凹的作品翻译出来后,西方人不能体会到文人传统的味道。但通常来说,贾平凹和莫言被认为是同样级别的作家。有人说莫言是暴力、色情、传奇结合得很好的作家。而贾平凹把传奇用得更多,他文气、文人味儿更重一些。
马蓓欣:我觉得莫言和高行健很像。高的《灵山》和《一个人的圣经》很值得一读,但一直找不到。后来我在我们澳大读到了这两本书,读了以后我才知道他为什么会被禁。他虽然是法国籍的作家,但写的内容是中国的回忆录。他获奖在国内得到的响应非常冷淡,我认为这对高行健是不公平的。朱老师在谈到汉语新文学的时候说,用汉语来划分新文学,是非常可观的,而不是按照国际划分。莫言和他很像,《灵山》很神秘,莫言的作品也非常神秘,都是魔幻现实嘛,瑞典的颁奖其实延续了高行健的那种神秘的传统。还有一点是对政治的否定,莫言的否定比较隐秘,大家分析后才知道他批判什么。冲这一点上,其实莫言对共产党也不是很喜欢。一个写得非常直面,一个需要我们揭露出来。高行健非常努力,很多领域都颇有建树,《一个人的圣经》比《灵山》后发表,而更精彩,从这一点我看到了他的努力。而莫言身上我没有看到这种努力,我只喜欢他前期的《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家族》,后来的《檀香刑》写得越来越现实,我没有看到他写得越来越好。他作品给我们的是一种印象、一种风格,这样一方面他形成了自己的语言风格,但是他达到这个高度之后没有更大的突破。比如沈从文、老舍,他们的风格是多变的,让我们看到风采各异、驾驭有余,而莫言没有做到,还欠火候。
贺欣欣:听了很多讲座和大家的发言,我也产生了很多想法。从一个小点出发,看《檀香刑》素材的选择,檀香这么美好的事物和这么残酷的刑罚结合在一起,给我的感觉是有一种变态的美感在里面。莫言选择这个题材很有创意。他其实取了历史的侧面,人们不甚熟悉的一个题材,进行了深入挖掘,来演绎一部小说。他的小说是揭露了一种丑陋,这种丑陋是不是要揭露出来?更重要的是他对这个刑罚有没有一种反思和同情的态度在里面。我从他小说中对刑罚的描述和众人的心理出发,比如描述人头落地像一颗颗球滚在地上,那种调侃的态度让我觉得作者对于这个刑罚并没有表现出同情和理解。他的态度是很让人质疑的。通过他对这个刑罚的叙述和刽子手的享受被观看的快感,我是觉得作者的态度很让人反思,也让我觉得这个作品有一种痛快的刺激和变态的美感。这种暴力和变态是值得别的小说家思考的,把残酷挖掘出来让我们享受感官的刺激。
张烨:我原先喜欢感性的美感,在《高山下的花环》的崇高中得到感动,而随着阅读经验的深入,我现在可以接受贺欣欣所说的变态的美感。看到丑陋的东西,一方面压抑的心理得到释放;另一方面,像《蛙》这种恐怖是审丑的真实,让我们看到离我们不是很远,但是已经看不到的记忆了。上一代人的记忆,对内容的理解更亲切。对于诺奖的风潮,我觉得这是传媒的胜利,不是文学的胜利。很多人都没有听过莫言,通过传媒,大家才认识到,这是挺悲哀的。
郭永真:刚才金林教授和各位同学的发言全面而且深刻。我现在想从侧面讨论一下莫言。我认为,瑞典文学院之所以愿意将诺贝尔文学奖颁给莫言先生,不全是因为他的“魔幻现实主义”,也不全是因为他曾在自己的小说中构造过一个瑞典人的形象,我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莫言在他的作品中记录了中国相当长一段时期,中国最广大的老百姓的生活和思想状况。因此,可以说莫言肩负起了作为一个作家的最崇高的责任之一:即见证和记录一段历史。我认为,瑞典文学院应该正是基于这样一点才给莫言先生颁了奖。我们应该注意到,莫言先生的小说都是以自身切身经历为背景的,这不仅使得他肩负起了作家见证和记录历史的使命,同时也使得莫言的小说形象生动,言而有话。而且我们也应该注意到,我国的一位著名导演张艺谋先生之所以能把他的电影《红高粱》拍得那么出彩,也是因为张艺谋曾经在农村生活过一段时期。他和莫言都是因为以自己的切身经历为背景来进行各自的作品的创作,才各自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就。所以,我们在今后的文学创作的道路上,一定要保持住自己最本真和最朴实的东西,秉承并且坚持自己擅长的东西,不要忘本,方能取得最大的成就!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