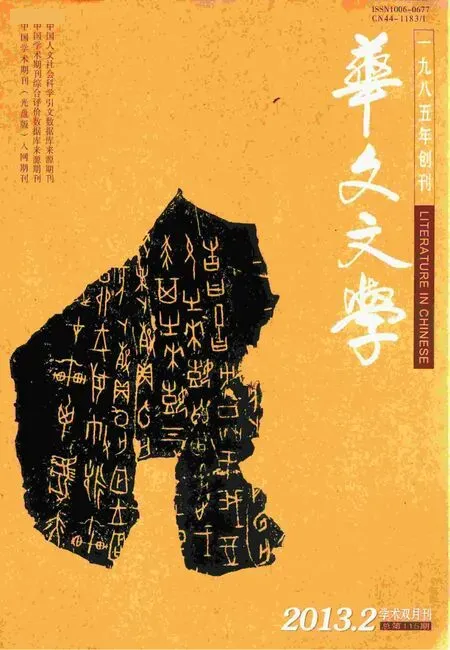梁秉钧:重量级香港作家
古远清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湖北武汉430070)
从三封信谈到彼此间的误会
惊悉梁秉钧先生于2013年1月5日不幸去世后,我连忙检阅还末付梓的《古远清所藏书信选》有关梁氏的三封手写信:
远清教授:多谢你的论文,我先寄上《梁秉钧卷》。我从事评论工作,确在赴美前,在报馆刊物工作时已开始。比较有系统有理论方向的评论,则大概在七八——八四在美写论文时以及八四年回港后。我的论文主要在西方文学的论介等六个方面。祝春安!
梁秉钧9 6,3
我第一次和也斯(梁秉钧)见面是在1997年初夏。那时我和北京大学谢冕教授一起在香港岭南学院做客座研究员,有一天我和谢先生一起到香港大学去看他,那时他在冷气房里赠了我们两人不少自己的著作,其中有他的处女诗集《雷声与蝉鸣》。后来我写了一篇评论他的文学评论文章,上面一封信便是他的回复。
我由于研究香港文学,在内地很难找到港版著作,便向也斯索要,下面便是他寄书时附的短简——
古先生:遵嘱寄上《香港文化空间与文学》一书,是从文化角度探讨香港文化的尝试,其中后面一些论点,或可解释我当时对杨世彭先生的批评,并非“排外”,实是为香港文化的不健康发展担忧。多谢上次对《书与城市》的评论。谨祝著安
梁秉钧9 6,4
我在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香港当代文学批评史》中,曾设有专节《也斯:细察现象,剖析本质》写他,其他各章节也经常提到他的名字。后来听说他主持“香港文学的定位、论题及发展研讨会”,便给他写了一封信。但由于我与他不是至交,因而他回信时只说了一些客套话:
古远清先生:艺发局资助香港文学研讨会,由香港大学承办。我们当然希望广邀国内、台湾、本港及海外学者参与。我们会集中在有关香港文学论题部分,而香港大学会集中在个别年代的作品。希望通过扎实的历史资料和讨论方法,为将来的文学史定下基础。
阁下对香港文学的评论和新诗下了不少功夫,我们当然希望你能赴会,发表一篇重要论文。敬祝文安
梁秉钧2007,5
这次会议于2007年12月20~22日在岭南大学举行,我之所以未能与会,大概和彼此产生过的误会有关。在冯伟才先生主编的香港《读书人》1997年终刊号上有篇文章叫《问题多多的〈香港文学节研讨会讲稿汇编〉》,据一位香港资深作家考证,此文署名“张文林”即是梁氏的笔名。作者时任香港大学讲师,便站在香港大学的立场,以我的论文为例认为首届香港文学节的主旋律是在歌颂香港中文大学的学者,还以台湾诗坛批评过笔者的《台港朦胧诗赏析》和《台湾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为理由,证明港英政府邀请我参加香港首届文学节是一种错误的选择,并将我在文学节宣读的论文定位为“典型的国内研究香港文学的例子”。他称内地为“国内”,潜台词香港似乎属于“国外”,这是香港回归前的流行说法,其意识形态上的差异不辩也罢,但他怀疑我做香港文学节的主讲嘉宾是与他“交恶”的中文大学某教授运作的,其实是当时香港文化界票选的结果。那时被提名的内地作家和学者有20多名,谢冕得票第一,笔者第二。台湾的余光中,美国的张错倒是指名邀请的。我读后曾写了一篇《关于首届香港文学节的“主旋律”》的文章回应他,未能在香港找到地方发表,后收入我于2009年在台湾秀威科技出版公司出版的《古远清文艺争鸣集》中。
我在《关于〈香港当代新诗史〉写作答客问》中有云:“作为评论家,必须坚守严肃的学术立场。不管自己相识或不相识的诗人,相识是亲近还是疏远的作家,也不管是自己喜欢的作品还是不符合自己审美要求的作品,都要去读,都要去评。不看刊物编辑的眼光行事,不看被评对象的脸色,写自己想写的东西,说自己想说的话,这需要气量,需要胸怀,需要学识,需要勇气,更需要睿智。哪怕是挖苦讽刺批判过我的人,只要他的文本优秀,还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我照样欣赏他,照样将其写进文学史,而且给的篇幅还不会少。”我这段话,基本上是针对也斯即梁秉钧讲的。我说到做到,在香港人民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拙著《香港当代新诗史》中,整整写了他两节,其中一节的标题是《也斯:颇具现代色彩的诗人》,是把他当作香港诗坛重镇向读者推荐的。在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另一本拙著《当代台港文学概论》中,我对他的评价也不低。
出入于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诗人
不管怎么样,我最敬佩的是作为香港诗人的也斯,他和戴天一样属重量级的本土诗人。他的学养深厚,视野开阔,经常出入于中西文化、现代与后现代之间。他在题材、形式和语言上作多种现代实验,在咏物诗、颂诗及都市诗的探索方面取得骄人的成绩。
崛起于1970年代的也斯,他翻译介卜·狄伦、彼德·西嘉等人的作品,既是他阅读的延续,也是他美学上的声援,对其日后的创作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他最早的作品《夜与歌》、《夏日与烟》、《裸街》、《未升》等,就是“向往新电影那种冷冽优雅的美感,以意象和气氛代替叙事的手法,用以抒发我当时隐约而难以界定的感情。”
作为本土诗人,也斯对香港有一种特殊的情感,对本地的变迁尤为关注。他自称是“城市的闯荡者、观察者、陋巷摊子旁的游击队员”。这反映在他的处女诗集《雷声与蝉鸣》中,有众多题目均嵌进香港的地区及街道名称,如《傍晚时,路经都爹利街》、《五月二十八日在柴湾坟场》、《巴伐斯街的公寓》、《罗素街》、《北角汽车渡海码头》、《新蒲岗的雨天》……他不用浓墨重彩,而用有真意、去粉饰的白描手法,并注意口语的节奏感,表现平静的城市如何在骨子里翻腾着各式各样的幻想和挣扎,用诙谐的笔法写芸芸众生的日常生活。诗人用摄影机拍下街景,用寻常的市井生活与读者谈心,用故事性的演绎写香港街头巷尾的变化,其中《抽奖》还用魔幻现实主义手法,但作者并没有照搬西方,而是借舶来手法展现东方自然诗的风韵。
或叙事,或咏物,或写景,或寄情的《雷声与蝉鸣》,体现了也斯早期的艺术追求,并为他中期写出《游诗》——并非狭义的旅游诗奠定基础。这类诗,不是以游客的身份游山玩水,而是离开原先稔熟的地方去看另一种事物,通过城市与山水反省文化和语言,以及比较各地异同。即是说,作者借周游世界各地抒写放逐的哀愁和发现的喜悦,在彼此相遇的文化中穿梭,其最终目的是落实本土——反思香港的文化问题。这些作品比早期放得开,大至宇宙,小至街道,还有历史电影,都进入他的视野。这与远赴美国加州留学的异国环境与内心探索多于外部观察有关。《乐海崖的月亮》、《大马镇的颂诗》等作品,均是从华人角度或侨民的身份,去思考西方与东方、都市与乡村、生活与艺术的关系,辨识香港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差异。在表现方法上,不再用凝固的白描手法,而是用难以界说的联想、对话启发读者想象。不再像过去那样过分强调意象和氛围的创造,而是由热变冷,由抒情转向描写;不再以谢灵运、王维式的山水诗写作,而是以较暖的轻快节奏写都市的人情。这其中虽然有立体派及超现实主义绘画的影响,但其情感形态完全不同于西方。
“游诗”的另一种含义是脱离文字媒介,去借鉴其他艺术媒介,或将文字媒介“游”进艺术媒介之中。也斯将《游诗》与骆笑平的铜板画配搭展出,《形象香港》和摄影对唱,《寻找一个诗人》用戏剧的形式演出。这种多媒体的运用,使也斯成了一个极具现代色彩的诗人。
1987~199 4年间,也斯不仅写了堪称精品的《游诗》,而且还写了从《诗经》开始就有到后来几乎被人遗忘的“颂诗”。这里讲的“颂诗”,不是内地1950、1960年代流行的政治抒情诗,更不是对某一党派的颂歌或赞歌,而是解构传统的价值观念,质疑歌功颂德的人生观与艺术观,借用颂歌的形式歌颂日常生活中的人和事,歌颂文艺家的献身精神和美好品德,反思历史文化,调整以往要么高耸入云要么打入地狱的标准,“在田畦甜腻的合唱里/坚持另一种口味。”《给苦瓜的颂诗》,写的是蔬菜,实质上是由物及人,赞颂那些看到太多虚假的阳光后“把苦涩藏在心中”的清醒精神。诗中写道:尽管人们不喜欢苦瓜“皱眉的样子”,但“我”本来就不奢望从苦瓜的脸上寻找平坦的风景。作者就这样通过苦瓜的赞颂,令读者一个个清心明目,重新细细咀嚼这个充满“邪热”的世界。
在香港诗坛,很难找到像也斯这样精通外国文艺理论的学者。他在美国几年,读了俄国形式主义和布拉格语言学派的书,也跟米高·大卫信等修过“后现代主义”、“当代美国诗”、“诗与画”等课,这对他后来的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不过,从基本倾向看,也斯并不是典型的后现代诗人。后现代的定义有多种,也斯对此有所选择。他不赞成反历史反意义的态度,更不会无条件拥抱后现代世界。在《大角嘴填海区》中,他明显地不信任“什么都可以,什么都无所谓”的后现代主义面对世界的基本信条。
也斯的创作,融合了后现代与现代主义的长处。“他的许多诗,抒情和叙事的界限常常既被确立又被拆毁,界限十分模糊。许多诗的形象,既不是现代主义的‘大写’和‘单数’,也不是后现代主义的‘小写’和‘复数’,而是缩小的‘大写’和放大的‘单数’。读也斯的诗,常常感到这一首中有‘黑山派’的‘客观主义’,那首诗有‘纽约派’的绘画式描述,另一首诗里又有‘跨掉派’那种‘像告诉朋友一样告诉谬斯’的生动口语。”他学来的后现代诗观,只帮他理解和反省当代作家的视野,在立体的变幻、意旨与意符不确定的关系方面处理得更富艺术性。也斯把自己的写作方式概括为:“并不强调把内心意识笼罩在万物上,而是走入万物,观看感受所遇的一切,发现他们的道理。”这种审美方式也斯称之为“发现的诗学”,以和“诗人所感已整理为一独立自存的内心世界,对外在世界的所遇因而觉得不重要,有什么也只是割截扭拗作为投射内心世界的象征符号”的“象征的诗学”加以区隔。像《从现代美术博物馆出来》,在一些人看来根本不像诗,可也斯认为,写诗并不一定非要用象征手法,也可以把自己亲眼见到的东西老老实实告诉读者。表面看来,字句没有深奥之处,事物也司空见惯,可诗中笼罩着一种不平凡的气氛。对也斯来说,写诗是一种发现的过程,而对读者来说,读诗也是一种发现过程,即通过这首诗“发现”作者不仅从现代美术博物馆出来,“也从一种主流的文学观念走了出来,往更自由亦更凌乱的方向寻找新的可能性。”
徜徉在香港文化空间的评论家
梁秉钧是著名的小说家、诗人、散文家,同时又是文艺评论家,出版有《香港文化空间与文学》、《香港文化》等。
至少有两个梁秉钧:一个是在各报刊发表文学创作的也斯,一个是从事严肃文学研究和比较文学研究的梁秉钧。在他那里,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互为促进,双向成长。
作为香港长大、长期生活在混杂文化中间的梁秉钧,身受不少偏见的误解,即使这样,他仍坚持研究香港文化。针对香港被英国人统治多年,他认为必须用重整香港文化历史的行动,去抗衡殖民时期的话语。在《形象香港》中,他谈到香港殖民地过去对自己有何意义时说:
我把它与不能够讲出自己的过去、不能够表达自己对身份的混淆以及不能够说出自己对这个地方的感受这几方面一起思考。我把它与教育、不平衡的文化政策、沉默与压制、以及对自己环境的无知这几方面一起思考。但这个过去的意义并不止于此;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我们所作的一切的背景。很讽刺地,作为一个殖民地,香港给予了中国人和中国文化一个存在的另类空间,一个让人反思“纯正”和“原本”状态的问题的混合体。
它亦很大程度上是我的背景的一部分。它的存在,阻碍着我而又慰勉着我,令我不安,警惕我注意自己不足之处,催迫我在年轻的时候已开始去怀疑一些很容易被以为理所当然的事情。
他这里认为,不能简单地认为殖民统治就只会压制乃至消灭中华文化。香港作家与内地、台湾作家的不同,在于身份上的暧昧或混淆。“曾经有人以在港居住多少年、在什么地方成长、在什么地方发表东西、写给哪些读者看等作为界定作者标准,但这些标准也未必完全可以解释清楚那些含混性和边缘性。”这含混性诚然阻碍作家的文化追求,但又慰勉作家在中西文化撞击中找出新的出路。香港诗人正是在被压迫的种种日常经验中,寻找到新的表现方式,求索出不同于海峡两岸的艺术个性。如昆南的《旗向》:
之故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噫花天兮花天兮
TO WHOM IT MAY CONCERN
This is to certify that
阁下诚咭片者股票者
毕生掷毫于忘寝之文字
与气候寒暄(公历年月日星期)
“诘旦Luckic参与赛事”
电话器之近安与咖啡或茶
成阁下之材料——飞黄腾达之材料敬启者阁下梦梦中国否
汝之肌革黄乎眼瞳黑乎
梁秉钧对此评论道:诗中这段文字是由古文、商业信札用语、歌曲、英文公函、赛马报道等的语气糅合而成,嘲弄中未尝没有辛酸。如果说这是都市文化的产品,那不仅是因为写及的世界是充满了咭片、股票、寒暄、赛事、电话、近安、材料、飞黄腾达等商业社会的用语,更是利用拼贴和陌生化的效果,突出主要由这种文字构成的世界的荒谬。在谐谑与怪异底下,作者的文字从这现代化的都市文化里面作出颠覆。
香港通俗文学发达,严肃文学被其挤到壁角。雅和俗的对峙,是香港文化的一大特征。梁秉钧认为,雅俗文学的关系不能简单地看待。它们虽然有对立的一面,但也有交融的一面,如被誉为中国第一部意识流小说的《酒徒》,就不是发表在严肃文学刊物上,而是登在流行报刊上。其作者刘以鬯并没有因此向流行报纸感恩而替通俗文化鼓吹,反而在作品中批评商品文化。“现代派的技巧与报刊的现实互相调整,转化出创新而又有所关怀的新篇。以这作品为例,可见香港现代文学的淑世性质,始终与商俗世界有所商量。报刊的商品世界,有时亦可淡化意识形态对峙的疆界,打开新的空间。”梁秉钧对香港文化“淑世性质”的论述,发人之未发。
从地理位置上来说,香港地处边陲,因而香港文化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边缘文化。梁秉钧不满足于这边缘化,而力图改变它,使其逐步向中心靠拢。他还认为,生活在边缘文化中的人,不见得思想都开放,“只有自觉地利用其他文化去反省自身文化(当然边缘性也许令这种反省来得较容易),才会慢慢产生出一种二元或多元的文化意识:‘我并不认为香港的特殊情况足以使它的艺术工作者自动地变成双文化或多文化性……只有当一个人以另外一个文化来反省自己的文化时,才会最终发展出一种双文化醒觉。’”梁秉钧的创作,便处在边缘与过渡之间。他常常以中国文化来反省香港文化,让这两种文化互相交融,让中西文化互补,故才发展出这种“双文化”的新鲜事物。现在回归了,但如只认为自己是殖民文化的受害者,而不看到受害者也可以变为殖民文化的传播者,即不将结束殖民性的工作进行下去,殖民性便会永远残留在心中。
梁秉钧评论新诗时提倡并深化香港文化研究的实践,使人们必须同时面对香港文化发展的必然和回归后香港文化仍保持其主体性、独立性的必然。人们大可不必因回归这一重大事件就认为香港文学会在大的时空中与深圳特区文学迭合,但仍必须警惕某些人将殖民心智带进新世纪。
我最近连续买了梁秉钧先生在内地出版的《香港文化十论》等研究专著,算是我对这位重量级的香港作家的纪念。
①羁魂、梁秉钧:《诗·越界·文化探索》,香港,《诗双月刊》,1997年10月,总36期,第39页。
②陈实:《风格与灵魂——香港诗人简论》,香港,《诗双月刊》,199 8年8月,总41期,第91页。
③梁秉钧:《〈游诗〉后记》,载《梁秉钧卷》,香港: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27页。
④罗贵祥:《后现代主义与梁秉钧的〈游诗〉》,香港,《文艺》季刊,198 6年6月,第18期,第24页。
⑤香港,青文书屋,1995年。
⑥香港艺术中心,1995年。
⑦⑫ 梁秉钧:《形象香港》(英译诗集),香港,曙光版,1993年,第18 2、161页。
⑧⑩也斯:《都市文化·香港文学·文化评论》,载张美君、朱耀伟编《香港文学@文化研究》,香港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香港文化及社会研究计划出版,2002年,第387-389页。
⑨香港,《好望角》,1963年5月,第6期,第3页。
⑪梁秉钧:《都市文学的形成——以六零年代的香港文化与香港小说为例》,载《第二届香港文学节“香港文学多面体”研讨会讲稿汇编》,香港:临时市政局公共图书馆199 8年版,第106页。
⑬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