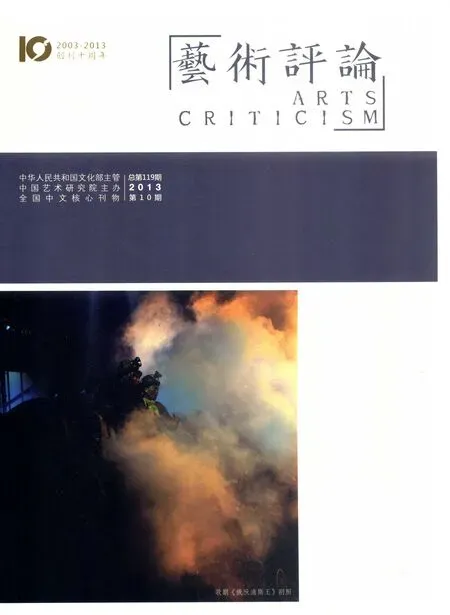补缀那一方坍塌的文化天空(上)
盛和煜
现在戏剧、影视的创作状态很令人担忧,包括我们湖南的状态也是如此。湖南人原来那种敢为天下先,不服输、不信邪的精神,在戏剧、影视创作这一块,反而成了我们的精神包袱:不服输、不信邪变成了不服行[hán],坐井观天、夜郎自大,总以为湖南人了不起,倔强。这个倔强用得不是地方,变成了倔强地不承认别人的长处。这从我们舞台剧的创作中可以看出来,近两届湖南艺术节,比较惭愧,一、二名都被我拿了,上届艺术节第一名、第二名都是我的剧本;这届艺术节第一名是我学生的剧本。我在戏剧、影视界都是边缘人物,特别在家乡,多少年没有回湖南参加戏剧活动了。拿到这第一第二名,说心里话我并不高兴。为什么呢?这说明我们湖南的戏剧创作进步不大。如果在座的能像我们当年“谷雨社”那样,我就高兴了。我多少次给家乡的领导、同行说外面的进步,可惜听者寥寥。再一个,影视创作也好,戏剧创作也好,有很多错误的方向和令人担忧的问题,有的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前不久有记者采访张黎导演,他有一句话,“要求接地气是可耻的”,说是从我这里来的。事实上,因为要求接地气,有了多少庸俗的作品。这些作品开始还有一点现实主义的东西,后来完全成了伪现实主义的东西。以接地气来掩盖他的庸俗、空乏苍白和令人发指的胡编乱造。如果真要接地气,就应该是敢于直面社会、直面人生、直面苦难。我人微言轻,但每次谈创作我都愿意来,我希望把自己的观念提供给大家。我是中国人,是中华民族的一员,就要有责任、有使命感、有这么一点很微弱的声音发出来。我希望我的作品,成为一颗颗色彩斑斓的女娲补天的小石子,来补缀我们中华民族已经坍塌了的那方文化天空。这是我的梦想。
在我们湖南,曾经有原来的“谷雨社”、戏剧湘军。当时中国有三个戏剧窝子:四川自贡、福建莆田、湖南常德,那时候我经常说,单打独斗,我们还没有特别有影响力的剧作家,但是拿出我们整体实力,我们一个常德地区就有200多个编剧,48个专业编剧,多少人都能够写,打团体赛我们能打冠军。我刚才讲了我的几个担忧:一个,是所谓的接地气;一个,是伪现实主义;再一个,是过度娱乐化。我觉得对我们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走向,对我们青少年的培养,严重地来说是个戕害。所以我希望发出我的这种声音,我们要写真正的黄钟大吕式的(小桥流水也行)具有民族特色的带着时代精神的又真正能够感染人的电视剧、舞台剧去影响大家,奋起抵抗卷地而来的庸俗化浪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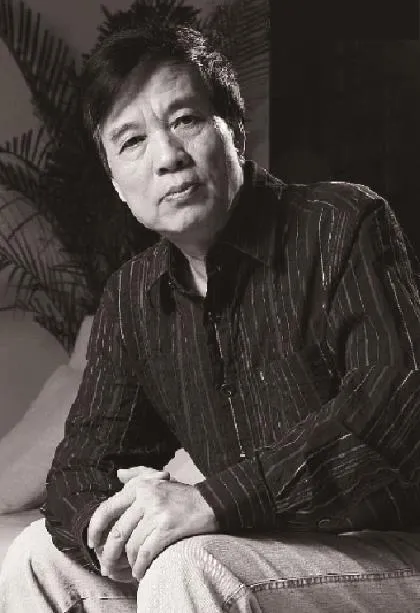
盛和煜近照/本人提供
下面讲我的“老三篇”。所谓“老三篇”,是我从事创作这么多年来的三点心得。我为什么不说是经验而说是心得呢?因为经验是成熟的,而一旦成熟,离腐朽也就不远了。我当“知青”的时候当了公社文化辅导员,等于群艺馆的编外工作人员。第一次我写了一个叫作《搬家》的戏。内容是要修水库了,要把这个地方搬迁,大家克服了自己的一些自私的思想、服从大局,最后就搬了。我准备把它写成一个小话剧。写了“搬家”这题目,然后写场景,那时候我们没有受到这么多的技术教育,就开始想怎么写场景。我想写一张桌子,这张桌子上面贴的是旧报纸,我就想写出那种感觉来,但怎么都写不出那种感觉。还有,这桌子是放在舞台的左侧还是右侧,靠观众近一点还是远一点,我在心目中有那么一个位置,但是我始终表达不出来。就为这个桌子怎么摆,我用文字要怎么表现,三天没有写出一个字。所以说创作,先天应该有些东西,创作天赋是第一重要的,但是后天的训练,技术性的问题必须要学习。它和写诗不同,所以作为编剧要有一定的生活阅历。这是我一个感觉。后来这个戏还是写成了。写成以后,就到县里去汇演,当时老师讲评这次汇演的剧本时,我坐在后面,好想听到老师能提到我的名字,但老师整个就没提我的。我以为我写的好得不得了,但是老师却对我那剧本根本没有印象。所以我太理解我们作为文学青年往上努力时的那种心态,直到今天还有这种心理。
好了,现在就开始我的“老三篇”,题目还是那样,《艺术创作中的逆向思维》,分为一个导言和三个部分:第一、主题的提炼,第二、人物陌生化,第三、独特的叙述框架。
导言两句话,第一句话:一切纪录都是为打破而存在的。跳高的纪录,刘翔跨栏的纪录,这些纪录是为打破而存在的。当初刘翔打破纪录是多么高兴,但是刘翔的纪录还是被古巴小将打破了,所以一切纪录都是为打破而存在的。我当初调到湖南省湘剧院,准备了两个题材,一个就是准备用来写广播剧的《屈原》,一个就是《夹山钟声》,写李自成在我家乡所属的石门县夹山寺出家当和尚的故事。考虑了很久,写《夹山钟声》相对来说比较容易,戏剧结构、内容都比较充实。但是一个朋友对我说,要写就写别人没看到过的,这句话对我意义重大,我决定了写《屈原》,也就是后来的《山鬼》。创作《山鬼》的时候,是上世纪80年代,正是好戏多得不得了的时候。我把当时最好的剧本都摆在我案头,很虔诚地学习,怀着崇敬的心情,很仔细地看这些剧本。看着看着就觉得还有些问题,看着看着就觉得我也能写出来,再看下去就觉得我能写得比它好。这就是纪录是可以打破的。我就看着它们、学习它们、然后希望超越它们。就是这样,如此而已,没有任何别的东西,但是你学的时候要真地学,不是说一上来就要掀翻它们。好的东西摆在那里是希望你超越它,我创作的时候从来不以任何蓝本为我的蓝本,我从来不照抄人家的,包括改编都极少。
第二句话,当一项艺术方案出来,百分之六十的人赞成,为时已晚。我们党和国家的政策方针,要得到绝大多数人的拥护。但是我们的艺术方案拿出来,所有的人都叫好,这个作品的品质就值得怀疑。因为人的个性是有差异的。都说这个不错时,为时已晚,已经就有很多庸俗的东西在里面了。我的《十二月等郎》写出来以后,他们拿去评奖。我是第一届曹禺剧作奖第一名的获得者,但是后来我老是评不上了,为什么呢?大家平时看惯了两万多字的剧本,一看到这八千多字的剧本,他怎么看都觉得有点单薄。
我这两个(导言的内容)都是解释逆向思维的,我写剧本从来不把任何一种成功模式当成我的蓝本。这就是逆向思维的导言。逆向思维贯穿在整个创作之中。
现在讲第一个问题:主题的提炼。如果用个通俗的说法,我叫它鹤立鸡群法。下午讲评的时候我会问在座的这几个剧作者,你们写的时候,想表现一个什么东西?这是很重要的。比如说,电视剧京汉大铁路要我写,江南造船厂要我写,开滦煤矿、首钢都要我写,都是老总们出面,因为写了《走向共和》,所以他们就让我写。我就想,你们要我表现什么东西?叶剑英也要我写,贺龙元帅也要我写。就是说,你拿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你要问自己。贺龙很传奇,故事很好听,为什么不写?贺龙元帅和叶剑英如果同样两部电视剧作品,你要写的时候,你要表现什么?不是表现他个性的不同、故事的不同,那不是目的,那只是另外讲了一个故事。一样的故事你要提炼出你的主题,你想干嘛?你想表现什么?这主题的提炼就决定了我们拿到一个题材以后这个戏的品质,鹤立鸡群,立意很高。取法乎上则得其中,取法乎中则得其下。你的立意高,你的作品才与众不同。我拿着一个题材,我首先想的就是怎么样才不重复前人的窠臼,怎样不同凡响,怎样就算是在同类题材中也高出人家一筹。一定要有这个想法,否则糊里糊涂,这个故事好听、人物有味就这样写下去,当然这也都重要。我们的文艺概论教导我们主题要多元化,是不错。文艺概论还教育我们,不要主题先行,主题是露在海面上的冰山,只能露出1/7,其余的要深深留在海面以下,都不错,都是真理。主题要隐蔽好,这都是不错的。但是在创作的时候,心中没有个高人一筹的主题和目标,这个不行。
《走向共和》的主题是什么?写《走向共和》的时候,有关戊戌变法、民国风云这样的文艺作品从小说到戏剧不胜枚举。但是我在写这个的时候,我就要想,我们的主题是什么。他们的主题大多是表现什么袁世凯、什么奸雄或者创业的艰难什么的,不对。我在写的时候,我和大家商量,主题是什么?我们提炼出:找出路。李鸿章也好,谁谁谁也好,他们都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他们绝对不是什么卖国贼,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出路。洋务派也好,君主立宪派也好,革命派也好,都是找出路,只是方式不同而已。没有谁是天生的卖国贼,没有谁从娘胎里出来就口含天宪,一贯正确。这是《走向共和》,因为定了这个主题,这也成了它的贯穿行动线,“找出路”贯穿我们这部电视剧的始终。这主题出来了,起点一下就高了。

京剧《梅兰芳》剧照

湖北花鼓戏《十二月等郎》剧照
再就是,《恰同学少年》,它的主题是什么?《恰同学少年》是欧阳常林台长的创意,叫我们写的,为了写这个才把我从湘剧院调到湖南电视台去。我最后的主题是为中华崛起而读书。
京剧《梅兰芳》是一个著名的剧作家写的,要我去讨论。我本来是不去的,后来他们说过士行去了,我就去了。为什么呢?因为你看每次《剧本》月刊发表作品,总是话剧摆在最前面,你戏曲写得再好也是摆在第二、第三,话剧写得再孬,也是头版头条。我们国家对话剧、歌剧的重视总比对戏曲高一筹,我就不服这个气。其实在中国戏曲学院高端演讲那次我就说了,“我们戏曲文学是我们母语中的精髓,我们不能这样糟践它,不能这样瞧不起它”。因为过士行兄是话剧大腕,他去了,我也去,我就是为表现自己去的,要让你们知道戏剧界还有能够和你们抗衡的人。在座诸位都对京剧剧本发表了一通言辞,好,说到我饭碗里来了,我就接着侃了一通,侃得他们瞠目结舌。由于我这一番耍表现,编剧就落在我头上了,推都推不掉。我说这剧本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出在主题的提炼上。它把梅先生塑造成一个爱国者,塑造成一个政治人物,而且是当时左联的那种政治人物。它把梅先生完全塑造成一个是三、四十年代的、左联的、政治的、爱国的人物,我就觉得这主题出现了问题。我觉得梅先生是可以和上天对话的人,他不仅是中华文化,他是人类的文化,要这样认识这个问题,所以我就提炼这个主题。梅先生是演女人的,女人是什么?不是说女人是水吗?由此我想到我们中华民族性格。世界上多少彪悍的民族都随着历史灰飞烟灭,它们曾经比中华民族强悍得多。中华民族的性格逆来顺受,就像水一样,你打一拳会缩回去,你不打了,他又上来了。上善若水是什么意思,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它藏污纳垢,能够包涵一切、容纳一切、最后澄明澄清一切,这才是上善若水,和厚德载物一个意思。我们的大地母亲,承载着世界上的一切物品,有恶的、有善的、有好的、有坏的,这才是厚德,才能载物。我就提炼出我们的民族性体现在梅先生身上,他以一个人的抗战,打败了整个日本军国主义,这就是上善若水,这就是主题体现,这就是我在创作之前和创作之中反复考虑的,提炼出来的。提炼出上善若水这个主题,就有别于一切写梅先生的粉墨春秋的作品,就到达了一个新的境地。张和平局长、陈薪伊导演他们非常高兴,在哪个地方都讲,都一直对这个主题认可,因为这样一来就大不一样了。
《山鬼》大家讨论的很多,在座的老朋友们也看过这个戏,都是很赞赏的。《山鬼》演出的时候,很有争议,甚至争议到国外去了。在北京首演的时候,影响非常大,丹麦、日本、美国、德国等11个国家的大使馆都要票,都没有票了,组委会临时调的票,那时候在北京演出,影响也很大。但《山鬼》刚出来的时候,遭到很多人的怀疑,“屈原能这样写吗?”,我说屈原是中国知识分子两千年集体生存心理的一种表现,屈原的主题今天我自己来说是“人是在不断追求完美的,唯其追求完美达不到,才不断地追求”,后来有人解释说两种文化冲突,见仁见智,反正我是有自己的想法的,这是山鬼的主题。
《十二月等郎》的主题,这是一个写农村留守女人的戏,不仅仅是关注农民工,更重要的是关注“千百年来中国女人的等待究竟是为什么?”这个问题,我自己也不能回答,所以这个戏很多人看了以后又感动又惆怅。
《李贞回乡》的主题是什么?最早的剧本是“反封建”,但是十年以后重新拿出来的时候,就觉得这个主题不对了。我原来的主题是“反封建的战士最后又被封建所束缚”。后来的主题是“共产党搞斗争是为人民谋幸福,而不是为了斗争人民”,这种主题是需要勇气的,最后还是被容纳了。
在说主题提炼的时候,还有一个最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的编剧不是政治家,而是思想者。我们不要在自己的作品中去回答什么问题。比如股份制改革的时候说股份制好,然后好像这就能够解决一切,这都是从人家那里批发来的一些观念。作为编剧,要有自己独立的思想,为什么要从人家那里批发一些观念来呢?改革开放,邓小平都要摸着石头过河,你编剧有那么大的能耐,在你的剧本中提供现成的答案和灵丹妙药?但是我们很多编剧仍然以为自己在作品中能够回答或解决我国种种社会问题并且以此自豪,这就有点黑色幽默了。你可以提出问题,一个作品能提出一个问题引人深思、给人启迪就行了。我们真的不是政治家,政治家解决问题有时候也解决得不尽人意嘛!一个作品最高的、最好的品质就是能够提出问题。请大家记住,我们不是政治家,我们是思想者。(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