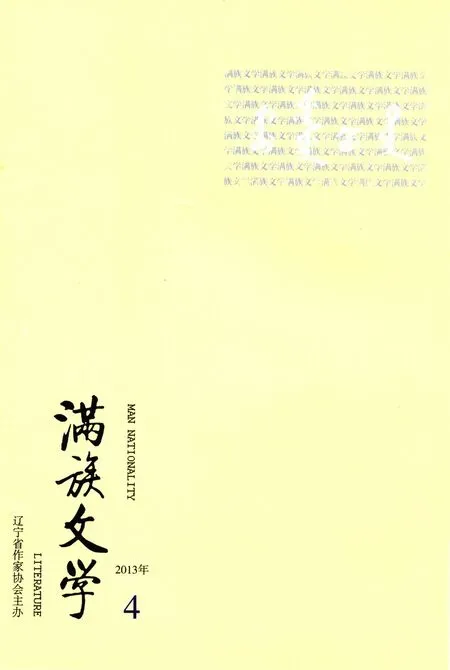父亲母亲[组诗]
崔益稳
手 机
在第二次中风和八十岁生日来临之际
父亲终于有了心爱的手机
以及这个世界上唯一的号码
15138012558
我常常在夜晚悄悄拨通,这个
传递生命信息的号码,低沉的老声
从手机那端传来,仿佛告诉我
这个地下工作者,组织还在
组织无非是我欲罢不能的家
三月草头青八月桂花黄
冷风暖雨层次分明,父亲的
声音衰退得更层次分明
我是娘身上掉下的一块肉
父亲如今却成了我身上一块赘肉
鸡肋般用处全无,真正剐掉又一定很疼
父亲的声音在手机那端,一旦不响起
这端声音的性质随之骤变,我辈
人生标尺,也向终点移动了一大截
今年以来手机那端的声音
话语渐次变短,阳气渐次变弱
无人应答的那一天,正一天天逼近
拨打这生命的密码如履薄冰
生怕不小心拨错一个数字
一下子拨达另一个世界
三百公里外的春天
一条河流劈开两岸菜花
春天随即一分为二,一片春色
就变成了两片,河流村庄作乘数
菜花作被乘数,老家做乘法的春天
一下子扩大到难以想像的规模
菜苔一夜之间把春天拔高几寸
却将我怀念比下去好几丈
三百公里外的春天
大于六百公里内的怀念
那么多雄雌激素竞相膨胀的花
蚕豆花豇豆花荞麦花洋槐花
卑微的花,养人性命的花
把金钱的空气挤得乱颤
最关键的是菜花横空出世
老家的春天才高人一头呀
有空隙的菜芯都渴望被填充
水能沿着风向站起来
风继而将勃起的状态嫁接到
千奇百怪风景的菜地里
嘻嘻真怪,怀孕的青菜
将婴儿挺在身肚之外
真像我的心跳藏在三百公里外
眺望啊眺望,三百公里外的
那个瘦挑男孩,正在用沉默的微笑
迎接从春天坟头爬归的母亲
忙里偷闲的母亲腋下夹着
一截青黄不接的菜花胎
开灯睡觉
母亲走后,日复一日
老父渐渐养成开灯睡觉的习惯
一辈子精打细算的他
年暮惟一不吝啬的举动
无所谓浪费什么电费了
惨白灯光映照下的父亲
依然老嘴张开鼾声如雷
狰狞中隐藏着安详
我随手关了一下灯
老父瞬间一骨碌惊醒
指着灯泡对我怒吼
它就是你娘
呵,灯亮着
娘就在
梦里梦外心里踏实
桃花的笑脸
大地与天空夹缝间
仰望或者俯视一朵灼灼桃花
不外乎正面反面
一面活像金币造型
一面活像母亲笑脸
财富和亲人同时出现
思恋一下子抵达春天的心脏部位
神魂痴迷看桃花
将一面设定为正面
该死的一面常常不是反面
桃花升仙高空或潜入地层
向上能绑住行云的步伐
向下可铆住逝去亲人的心跳
我有时想一杆子捅下头顶白云
有时想一锹挖出桃树千年老根
新城高层公寓十九层窗口
赝品青花瓷瓶内一朵桃花
无论怎么欣赏
正面反面均是亡母的笑脸
光鲜欲滴的桃花光泽
罩不住整座高楼投来的灰色阴影
这样虚幻的春天
生死距离约等于零
两种宿命的苹果
我的母亲,中国一位普通农妇
乔布斯,美国苹果公司总裁
他们竟因同样的毛病
2011年同月同日辞世
一个在长江苏北平原的五架梁瓦屋
一个在美国帕拉奥图的乡间别墅
母亲的葬礼可比乔布斯的葬礼高调
吹吹打打全村上百号人马自发集合
祭在灵前的两只土疙瘩苹果
就摘自门前树上
多像我瞪着白多黑少的大眼睛
母亲肯定不懂牛顿的苹果
更不懂乔布斯的苹果
但母亲的苹果树长得又高又旺
假如她看到门前树上挂满乔布斯的苹果
一定会心疼得反复啰嗦
谁把好端端的苹果咬豁了口唉
迎着阳光打开苹果电脑或手机
每次我都恍惚可见
家乡树上的苹果全长满牙齿
大街水果摊上的苹果全在哭泣
谁又能在苹果另侧再咬一个豁口
让我的痛苦在母亲与乔布斯之间
保持相对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