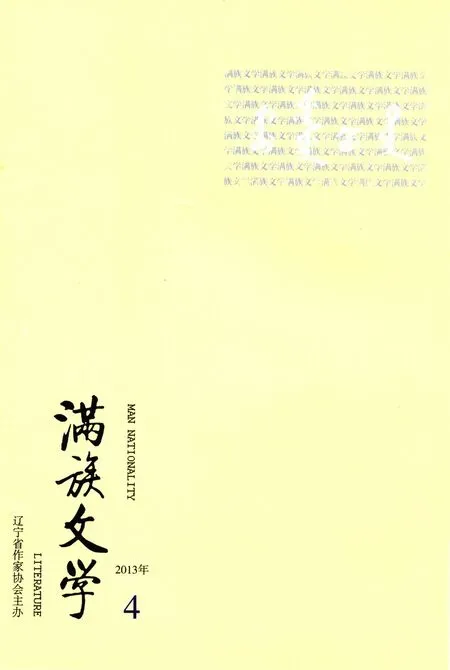放生船
张全友
如果太行山脉是座城,大泉山峰是个乡,巉岩就是一个村。
正是黎明时候,天空的薄雾后面隐藏着几颗星,耳边不时传来几声狗吠。我跟在表哥身后,紧紧地跟着他。因为天色尚早,又是雾天,脚下不时会有小石头磕碰着脚掌。我们走的不是平路,是朝巉岩往上攀的崎岖山路。不知不觉间,二十里山路已经被我们甩在身后了。我不知道表哥怎么样,我的身子都湿透了。两个裤脚像水袋,那是被露水打湿的。背上既痒又爬满了汗渍,胸腔呼哧呼哧像一个风箱,把脑门上的汗珠儿吹落又掉到了鼻子尖儿,滚进嘴里,还很咸,撒了把盐似的。表哥说,快点走,再走不了多一会儿,就到岩下了,到了你在下边等着,那时候你要缓上一整天呢。
表哥的腰间斜挎着一把小劈刀,末梢带着一个鹰隼似的勾。他穿着攀山服,肘子膝盖都是大片的补巴。表哥留了坛盖子头,白天看上去很滑稽。好像电影里旧上海滩没戴帽子的黄包车夫。现在有雾看不到,主要是天气还早,太阳还没有起床呢。
表哥说,你硬要跟了我来,又怕累,真是个软骨头。我说,我不怕,走你的吧。
现在正是七月,早上异常清爽,虽说雾天山涧没有小风儿吹,鼻息间却尽是些舒缓的气流。天色开始蒙蒙放亮时,我们就看到了一地的小草,偶尔还有点点的粉花。雾下的小草很青翠,旖旎的一茎茎,挂满了碎小的珍珠串儿。我们走过去,带动了它们,它们随即一抖,更加翠绿了。
我心里想着一件事,想着那只小帆船。白白的藤骨做架子,有好高好大。我心里想了下,大概最小也够那么大。我笑了,那么大是多大?我也不知道,反正够姑母的一只鹅大小。可惜,表哥太偏心,把它给了小秀了。听说小秀把小船放进了天河,表哥说小秀娘病了,小船到了天河,会给她娘祈福的。我又想,闹不好表哥抓过小秀的毛辫子了?这个也说不定。那女子,清秀的面颊上,一双富有灵气的眼睛,似乎在和你说话。莫说表哥喜欢她,谁看着也会多想一想的。我也想过她。
太阳开始伸懒腰了,它睡了一晚上,脸睡得红扑扑的。我们隔着纱一样的雾气看到它,它也不害羞,只是脑袋周围长了些雾毛儿。
我和表哥距离拉得远了些。他埋怨我跟不上他。他不能慢,他有一大背荆条的任务呢。那是给队里的。他还有一小捆任务,那是给自己家里的。表哥悄悄对我说过,家里没盐了,你来了,吃菜不能没有盐,寡淡淡的不好吃。
我知道,表哥喜欢我。他没个兄弟,家里就他一个孩子,多孤单。我还知道,他不上学了,做了队上的小社员。其实,他很想上学,所以到了假期,我就来了,来给他送书,都是我不喜欢看的课本儿,他却去油灯下看,一看就是大半夜,疼得姑母直骂他费灯油。表哥才很不情愿地睡下了。
所以我在他跟前,就会得到些偏袒。我说我也想要一个那样的小帆船,表哥不会不答应。我说我也要去那个巉岩看看,表哥问我你敢去?我说有什么不敢?我胸脯一挺,肚脐子都瞪成了一只眼。表哥说那里可是有不少蛇,甚至还有狼。我说你不怕我也不怕。所以,我就跟他来了。现在可好,我的脚后跟好像磨起了泡,微微作疼。跟在表哥的身后走着走着,就掉了路,拉开那么远的距离了。
“快点走就要到了!”
山谷里回荡着表哥的喊声。我也说:“哎——”
可是,我却一屁股坐下来,抹一把汗。太累了。心想:早知道这么远才不来呢。
哇!真高啊!我说。表哥不理我,自顾着给腰上拴一根绳子。
我不知道那是做什么用的,傻傻地看着他。
你就在这里等着我,不要乱跑。我说我知道,你早吓过我,有狼和蛇嘛。
表哥鬼脸了一下,就走了。
那巉岩真够陡峭。悬在半山腰的晨雾早已融化在朝霞里,现在天上有一些薄云。它就高高的耸到了那云尖上,看去都有些头晕。不过这个巉岩高是高,山的褶子里,却碧绿如玉。我看着表哥身子轻捷而又熟练地沿着石壁往上攀,一步紧接一步,看得我脖颈子都酸了,他却像一粒黑豆儿,在那光溜溜的岩壁滑来滑去。
“嗖——”一枝青嫩的荆条飞了来,还有些苦煎的茎杆脂味儿一同也飞了来。
我在下边急忙忙地给他收拾着。
大约黄昏,这壁巉岩所展示出的神采,是最令人陶醉的。天际,放火一般燃了起来。那云,像铺上去的一层花瓣儿,被落日的余晖浸上一层浅浅的金色。成群的云燕儿,也去那里飞舞起来,把歌唱在近似绝壁的回响之中。夕阳下,绿也呈黄,山体石躯像表哥身上的肌肉,涌动着它的健壮。
表哥把大大的一背荆条扎好,很娴熟专业地拴成活扣儿,放到恰好能背起的石坎子上,劈刀又挎回腰间。仅有的一小捆,属于我。那是特别精心才挑拣出来的。
这些给你编小船,你带着。
这么多?
余了还能再扎个鸟笼。
那当然好。
不早啦,回去了。
晚上,我问油灯下编筐的表哥,你为什么哭?我看见他明显用腾出的肘子在抹眼泪。
没什么。
姑呢?
过一会她就回来了。
那一晚,我姑回家很晚,我本来躺进了梦里,后来是他们抱在一处的哭声扰醒了我。我没有去劝他们。我知道他们光景不好过,可到底够多难?是早被他们刚强性烈的母子瞒在五里云外了。
他们没咋地你吧?
没咋地,不就进几天学习班嘛。
这筐,还能不能再卖了?
咋地不能?咱先避避风,过了这阵子,咱再卖。
六叔他们说什么?
他们说这叫尾巴,是尾巴就要割,人不能长尾巴。
我编几只筐,咋成了尾巴?他们才长了尾巴!
后来我知道,表哥赶夜工编好的筐,姑去镇市上卖,想换些钱贴补生活,却被队长六叔发现了。姑夫当过国军的连副,多年后被人揭发进了大牢,姑和表哥被村里管制,这样没收他们的“尾巴”不是三回两回了。
又一天,天气暖洋洋。姑和表哥的心情同样暖洋洋,昨晚的事似乎根本没发生过。
表哥不仅攀岩身手快,手也确实巧。阳光下,他蹴在三间窑的拱檐前,去了皮的雪白荆条股子在表哥的手里自由地左右翻飞,没出两小时,一艘白鹅般大小的双帆小船就成了。
给你。
你跟我去河湾放船吗?
去就去。
正是水暖的七月,我们都穿着裤衩子。清新欢乐的阳光洒在我们脸上,我们在水里嬉戏打闹,清凉的河水在我们指间化为一朵朵莹白的花儿。累了,飘来一缕缕梦幻般的小风儿,我们就要放船了。
表哥说,你愿意它去更远的地方不?我说愿意。
我去水里摆弄着。可是它老要倒,立不起来。
还是我帮你吧。表哥扶正了小船,又给它舱底插几片树叶,还吹了几口气在上面。
这是一条不太宽的小河,来玩的村孩儿不多。听说河连海,海连洋,洋连天。天有多远?一定是很远很远吧?
表哥站到河心儿,双手托着小船,弯下腰小心翼翼地将小船放到水面上。
小船起航了,两个小帆儿的小船,银滟的水浪跳跃着拥在船头和船尾。表哥和我看着它远去,直到飘向与天相连的地方。
天河。表哥说咱这个船一定是飘到了天河去的。
天河是哪里?
我也不知道,就听老人们说过,天河那头是个极乐世界,没有大牢,人人都好,更不办学习班。
那咱们也去那里吧?
要去的,我叫小船儿先去,它会飞,飞去了给咱托梦来,咱们再去。
带上姑,也带上我爹跟我娘。
不行,我要等我爹回来一起去。
对呀,还有姑夫呢。
……
我正准备吃晚饭,老婆晚饭一般做得早,这时候突然来了个电话,让我不能再吃了。电话那头不是别人,是我的老板,也是我的表哥。那会儿正是鸟儿归巢的时候,天空,太阳射出了女人月红般的红光,红光泼到了一朵朵白花似的白云上,白云就被染成了红云。蚊蝇似的鸟儿成群结队,在那红云下翻飞。大概它们此刻实在是应该去欢乐的时刻。一天就要过去了,作为一只鸟儿,也累,也困,巢,总是令它们神往并感到温暖的。
表哥电话没有多少内容,就一句话。他说你到国宇大酒店,今天我那里有一桌。
我“嗯”了一声。我的这声“嗯”,是别无选择的。
老婆问我,饭都好了,你现在去哪里?如此风风火火?
老婆的话中有关心和埋怨,也有某些不放心的内涵。如今男人,令女人放心的不多了。
我说,表哥有事喊,他的话我不敢不听。
我这样一说,她也就无可奈何。没错,现在我们一家全靠我在表哥石料厂做事生活,领人家薪水人家有事发话,哪有不听的道理?她只是低声嘟囔一句,谁知道是不是你表哥?就独自吃饭去了。
我这个表哥很横,他的脾气厂子里无人不晓。他已不再是二十年前那个留着坛盖头去巉岩砍荆条回来编那些筐篓的糟小子。二十年,足以让人和这个世界一起,变得面目全非了。
表哥现在有一套二百四十平米的别墅,家里有大学毕业的专职娇妻,谁知道外面还有没有他的情人?他还给我姑去县城单独购一套五间宽敞明亮的平房。我姑喜欢住平房,表哥当然满足她,还给她雇了个工厂下岗后无业的少妇做保姆。
表哥家里还养着三条风格不同的狗。一条国产藏獒,听说是纯粹的二代,花了五十万。一条祖籍为英国的金毛寻回犬,花了两千元。再一条同样是英国户籍的彭布罗克威尔士柯基犬,给姑家买的,也值两千多元。
说狗风格不同,这是表哥的话,他文化水平低,可往往这样的人语出惊人。本来是狗的种类不同,他要说成风格。奇怪的是,他这一说,石料厂底下那些人还一致赞赏,大夸特夸他的三条狗好。底下人也形容不出个哪里好,就是一股劲地夸。好啊好,这种狗,就是好,三条狗一起,都很好。表哥觉出了他们的马屁味道,说好什么好?你们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底下人一下惊讶了,口半张半合,眼吧嗒吧嗒,都哑了。
富平,你可要好好给我服侍它们啊,它们吃饭后,你才能去吃饭,它们睡觉后,你才能够去睡觉,它们拉屎,你要用卫生纸给它们擦屁股,每一个星期天,最少洗一次澡,身上绝对不能有异味,要是它们哪个有了病,你可要及时抱着去看病,如果哪个死了,除了你的工资奖金没有了,还要赔我一半的损失。你乐意做这个狗服务员吗?
我乐意,乐意。叫富平的人,一脸憨气地笑着,鬼才知道他心里想什么,尽然乐不迭地去狗窝前做起了去服侍那些狗的事情了。
表哥说过这些话,看着富平积极的身影,眼里有了些满意的神色。他又从衣兜里摸出一只白金做得很精巧的牙签去剔起了牙。那天他吃了不少鸡肉。他的牙不好,一颗与另一颗之间总是不够亲密无间,有着很不小的距离。他在努力嚼碎午餐中那些鸡肉的时候,一部分却逃脱了他的嚼力,钻了牙的空子。表哥特气这些肉,他一块一块把它们剔出来,狠狠吐到地上。
表哥这样剔着牙,看着富平给狗挠背,心里却想着富平的老婆。富平的老婆不是别人,正是表哥当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还是没有搞到手做他媳妇的小秀。表哥想起来一句话: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了。
我驾着一辆摩托,飞也似地疾驰在到国宇大酒店的路上。已是六月的黄昏,公路两边的庄稼地成片的玉米向后倾覆着倒下。一片片倒下。唯独表哥那张长满了杏核儿似的粉刺的脸,在我脑袋里面挥之不去。
不是一张脸,是两张脸。一张是顶着坛盖儿头的,一张是长满了杏仁儿似的粉刺的。
我记得表哥叫我去喝酒,喝他的酒总是有些故事内容。这是第二次了吧?上一次也是那个国宇大酒店,也是近黄昏,表哥说是叫去了一桌人,喝酒,拉闲呱。其实就三个人,表哥,我,六叔。那一次他请了当年做过他队长的六叔,那个当年腰板挺得直直的人,却把头低得像一个秋后的茄子样,一言不发,只顾吃菜,喝酒。
表哥说,六叔,你老了。
老头的头发确实白了不少,他说,嗯。他重重地点了一下头,继续吃菜,喝酒。
表哥说,六叔,你慢点吃,慢点喝,小心噎着了。
老头说,嗯。去夹菜的筷子就停到了半空中一会,缓缓又伸向一个菜碟子。
表哥说,六叔,前几天我把你丢到了路上的事,你不会忌恨我吧?
老头说,不会不会。头点的像鸡子啄米。一头白发,就晃出了不少白光。
我坐在一边,吃着,喝着,听着,看着,心里想着。
国宇大酒店的女服务员个个很漂亮,都像木偶似的立着,双手交叉在那个最吸引人的地方,堆着满脸的笑。
表哥说,来一块湿巾,稍稍凉点的。
一个年纪稍小些的女服务员哎了一声,急忙回头去储物间拿来了一块湿巾,递给表哥。
表哥却不接,头示意对面坐着的六叔,说,给他吧。
表哥说,六叔,你擦擦脸,屋里太热了。
六叔看了看服务员双手捧过来的湿巾,煞白的湿巾,像一道闪电晃进六叔眼里。他不知怎么,身子颤抖了一下。可能是突然想起来当年生产队地里种植的白萝卜了?要么就是当年如何将姑母去卖的那些筐篓烧掉的情景?不知道是不是?
我说,服务员,你们没有空调吗?干嘛不开?
表哥狠狠冷眼看了我一下,说你好好吃你的饭,操什么心?
马屁踢在了牛腚上,我急忙低下头,只顾吃菜喝酒去了,至席散,我也没有再吭一声。
那天喝的是八百一瓶的“竹叶青”。表哥请六叔喝酒,向他道歉,实际我知道,六叔喝那些酒下肚,比喝毒药还难受。但他还是一杯一杯地往肚子里灌酒,大口大口的。
我知道事情的原委,原来是几天前六婶急性阑尾炎发作,疼得要死,乡下没办法处理,非得进县城医院不可。可是那么远的山路,到哪里搞到一辆车?六叔无奈,想到了表哥。表哥很仗义,二话没说,就来了。医院送的及时,六婶很快康复出院。表哥又来接他们回家。不料车行在那壁巉岩下时候,表哥车子停住了,说六叔,你下车,自己走路回家,我就能拉你到这里了。
六婶也要下,却被表哥按住了她。你不要下,我送你回家。
我心里想象着那个六叔走在回家山路的心境,那是一种什么味道?时过境迁?实在想不出。然而后来表哥却还要设宴为他道歉?还非要叫上我?我算什么?大概就算他的一个物证?或者什么东西?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什么了。
成片的玉米继续朝我身子后边倾倒,那个头发白白的六叔的难堪的脸,也朝着我的身后一张张倾倒。头顶上,已经飞出了一朵朵晚霞,血红血红的颜色,它们不倾倒,它们在追逐我,叫我快点赶路,别误了表哥的酒宴。
关于表哥跟那个小秀的事情,我也略略听说过一些。小秀嫁给富平,没有嫁表哥,原因他们是邻居,从小耍大的,所谓狗屁青梅竹马,在当时,六叔做队长光景也好过。而我表哥,家庭成分不好,穷得就剩下姑母跟他两个干人了,小秀怎么会找他?不料真的会时过境迁,死在大牢里的姑夫给平反了,政府还给了他们一些补偿金。姑夫的那些当年的战友们,还有专程赶来看望他们母子的。有的给他们钱,有的给他们物。其中一个做建筑的人,就鼓捣着要帮助他们母子,叫表哥去做建筑。可惜表哥什么都不会,最后就做起了石料生意。
你来我厂子干吧?表哥说我。
那年我只种地,没有多少收入拿回家。我老婆一听表哥要叫我到他的石料厂干活,当然高兴了。二话没说,把我本来不想离开家里的想法给絮絮叨叨的说动了。谁知一干,就是好几年。
你他娘的怎么这么笨?一块石头落了地,你干嘛非要让它去砸你自己的脚?
表哥很横,他每天最少要骂人五百句话,却从来没有骂过我。
他从乱石堆走过,遇到一干工人,就看着不顺眼,挨个骂他们几句,骂过了一圈,再转回来,继续着骂骂咧咧。石料厂,就是他的一个骂人舞台,他巡回往复,一天的工作就是骂骂骂。我知道,他心里有气,不就是人家小秀不理他吗?他就把厂子往大了扩展,村里的劳力几乎都是他的工人了,小秀还是不想叫她男人富平去表哥这里做。表哥就继续扩展。他把村里的土地买下来,开发农场。小秀家里的地周围,已经都是表哥农场的地了,他们却依然自己耕种着。富平就说,要不我也去石料厂上班吧?小秀说,你没有骨气。
可是后来,不知道怎么想的,富平还是来了表哥这里上起班。表哥一开始叫他下夜,就是看门防贼做保安工作的性质。我还听说过,表哥夜里去过富平家,他想和小秀好。他家里放着大学生的娇妻,还想着这个小秀?可是小秀没有答应他,好像还听说把多年前表哥给她精心编织的那个小船归还了他。真是怪了,不是听说小秀把表哥给她的那个小船,早在二十几年前就放进天河里了吗?怎么会又出来了一个小船儿?莫非它会再游回来?游到小秀手中,再还给我的表哥?
摩托车上坡,速度明显放慢了。我去石料厂上班,每天必经这条路。十几里路程,我都回家了,这个表哥却非要我去赴个什么宴?
一只流浪狗从路的一侧鬼鬼祟祟跑过去。它很邋遢,其实它皮毛的原色貌似白色,现在却一身污泥滚成了沙和尚项上念珠似的溜子,一走哗啦啦作响。我又想起来姑母怀中的那条彭布罗克威尔士柯基狗。我姑母第一次听过这名字后,觉得太长了,不好叫,干脆简化叫它彭彭。“彭彭?过来我抱抱。”那狗毛色花白,亮得像丝绸似的一团儿跑过来,钻入姑母的怀里撒起来娇。我姑母经常用嘴去亲吻它。没准真和它进行过深吻?富平两头跑,给表嫂家里服侍好了两条狗后,还要过姑母家再服侍这一条。做了一个时期的下夜工,富平被表哥又安排做他家的狗服务员,工资自然给他涨了几十块。他很乐意做。他内心难道真的乐意吗?我不知道。我看着那条流浪狗远去的影子,想起了富平。我觉得他们多么相似?活在和表哥和我一个世界里,邋里邋遢,几乎没有什么尊严,形同走肉。我又想起来表哥和我的过去,那些到巉岩下砍荆条的日子。许多年以后,虽然那一壁巉岩早快被表哥的石料厂给吃光喝净了,唯独乱石堆上茂密的荆莽丛,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县城就在前边,很快就要到了。我猜测表哥今天叫我,一定又要有什么动静?可是我猜不出。
国宇大酒店气宇非凡,那是许多富人商户们交际聚餐的地方。黄昏下的县城,县城里的国宇大酒店,已经翩然骚动起来。我找下一个停车地,放好摩托车。表哥已经早到了,我很惊讶地看到,今天仍然是三人组合:表哥、我,另一个却竟然是富平。
表哥什么也没有说,他挥挥手,示意服务员上酒菜。
他的肚子现在很大,虽说不是特别大,也算发福的那种。
而富平却精瘦精瘦的,一双手来回搓麻着,显得很规矩。
我心里犯嘀咕,不知道他们都想什么。当然了,主要是表哥在想什么才是主要的。
表哥挥手让服务员为我们都倒满了一杯酒,他站起来了。我们自然都跟着站起来。
表哥说,富平啊,你还是要走了。今天我在这里备下薄酒,就算为你送行吧。
富平端着酒杯,眼看着晃荡的杯中之酒,低声说,主要是我老婆,她非叫我去外面打工。她说世界很大……
表哥说,富平啊,你不及小秀,她那叫骨气。来,不说这些了,干杯!
表哥使劲和我们碰了一下,一扬脖喝下去一满杯。
等服务员倒满了第二杯酒后,表哥再站起来,说,原本我想请小秀来,可是,我现在请不动她了。这一杯酒,就由你富平代她喝下,也给我带话回去,说我对不起她。对不起你们了。
表哥又使劲和我们碰了一下,一扬脖喝下去一满杯。
完毕,他说,常言道酒过三巡,可是我今天就能跟你们喝这两下,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我和富平都眼吧嗒吧嗒的,弄不懂他到底什么意思。
表哥说,告诉你们吧,酒过三巡那是要遇到知己,你们不是我的知己,所以到此为止。
表哥起身披起衣服,临走把一个小包递给了富平。里边是你几个月的工资,我加了倍。出去好好干,什么时候混不下去了,回来继续伺候我。
我一下蒙了头,看看满满一桌菜,连筷子都没有动,就这样散了,觉得表哥是在耍我。大老远把我叫来了,原来就为了这个?那我是不是他的一个道具?或者摆设?我实在不知道此刻自己是个什么东西了。
前后也就几十分钟,我走出了这家国宇大酒店。富平已经踏自行车走了,表哥却没有开车走。他在我拿钥匙开摩托车的时候,一把将我拉住了。你今天不要回去了,我还找你有事。上车。
表哥总是这样武断。他叫酒店保安帮我照看好摩托车,我们就坐进了他的轿车。
成片的玉米又开始朝我来时的反方向倾倒下去。天色已经要黑掉了,一朵朵晚霞,也像燃尽油的灯,挣扎着最后的那一束束血色。
我们一路无话。我猜不出表哥到底还有什么事情要我去办?
车子很快,一会就来到了石料厂附近。表哥却戛然停下来车,说到了。
“喔呵呵——”
傍晚的山谷里,回荡着表哥的喊声。“喔呵呵——”
我不知他要干什么?后边跟着他。
一会儿,表哥回头说,兄弟啊,你还记得吗?这条路,就是我们当年进山砍荆条走过的老路啊!我一抓头皮,说,好像是。
什么叫好像是?就是,没有错。表哥说,可惜了,这里叫我的石料厂炸得不像样子了。
我看到表哥少见地笑了一下,继续朝着前边走去。表哥一边走,一边回头和我说,真是往事不堪回首,我多么希望能再回到那个幼稚的年龄啊!
我也被他的话所感染,心里一时又想起了那巉岩陡峭的半山腰,那晨雾下身子轻捷而又熟练地沿着石壁往上攀爬的一个小人儿。
“嗖——”一枝青嫩的荆条飞了来,那是年轻的苦涩青脂味儿。
“轰隆——”一声。石料厂那边,有开山的炮声传来。
表哥发福的身影又折回来了。
走,咱们再到一个地方去看看。
天河?
对,天河。
六月的傍晚,天河当年的容颜已经不在。一条枯竭的河床长满了杂草,河床上空只有随意飘移正在黑下去的云丝,连一只当年欢快着咿呀低叫的云燕儿也没有了。表哥的黑色轿车停到了那些杂草上,他打开了后背箱,小心地取出一只白色小帆船。
我说,那里边水都没有,你放这个干什么?
表哥说,为什么没有?这河床里流淌的水,你难道看不到?
表哥又说,哦,你不懂,也难怪你。
表哥走进了杂草里,轻轻把那只小船放下来。小船要倒下,他又将它扶正了。
他立在那里,看着远方,喃喃自语,去吧……
忽然间,他双膝跪下去,抱头痛哭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