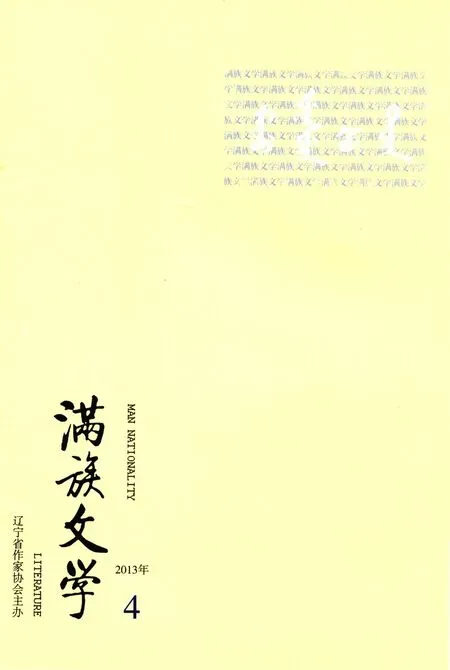一地炊烟
冯金彦
家谱的余辉
家谱是一个家族的历史,不管来自何方,生活在辽东大山里的这些普通的百姓,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对根的认同。
根是一个家族的源,对于根的表达,只有两种形式,一是祖坟,二是家谱。
祖坟总是会选在一个风水好的地方,以便恩泽后代。这不仅仅是一种迷信,还是一种祈盼。人在走得疲乏时,是会找一根精神的木棍子拄着,以便自己不会倒下去。
家谱却不是这样。
家族仿佛是一棵树,一对夫妻如一粒子,从土地里萌生伸长出有力的树干,每一个枝干都是一个新的家族。
家谱发黄的纸页上,总会有一对夫妻的名字。
从他们的名字伸长出的枝干,形成了一条生命的河。
从家谱中,你会很快的知道你是谁,你从哪里来。尽管你不会知道你将来是谁,会向何处去。
家谱是家族的历史。
历史就是这样,不是谁都会有一页文字的叙述,社会前进的规律就是这样,总是忘掉一些人的名字,以便记住一些新的名字。
家谱亦是。
能够被家谱浓墨重彩的,一定是族中人杰,那些有成就的人会被作为一个家族的光荣、骄傲,作为家族的榜样,耸立在家谱中。他们是家族的脸面,是家族的一个标志,一个分界线,除此而外的家族人,都会以他作为分界,是他的八世祖或几代孙。
这个世界从来就是成功者的世界,这个世界的历史也从来都是为成功者写的,一个民族如是,一个家族也如是。
而那些背离祖训的人,是不会在家谱中找到自己位置的,他们的名字只是一个符号,他们的劣迹是一个家族的污点,是会被家族的人涂掉的,他们甚至都不准被葬入祖坟。这是家族对一个人最大的审判或者说惩罚,它显示的是家族的力量,家族的力量是一种道德的力量,一种善的力量,它不是制度却超越制度,是一个家族凝聚力的表现和前行的动力。
被家族的耻辱柱钉上的人,不仅他的一生暗淡了,甚至他的后人,他生命之河的下游,从此再无清明的日子。
但这份耻辱与荣誉,又常常不能脱俗,常常与社会有关,与世俗的评价标准有关。成功者常常是用家族的标准亮出来的,难免带有一些功利的色彩,因而,家谱常常被改写,但这丝毫不影响家谱的庄重。抖开那些发黄甚至斑驳的纸页,一些朴素的人就鲜活起来了,一些平凡的人就生动起来了。他们在历史里走动的脚步声,远远地就从岁月的山坡上滚下来。
石碾上的牵牛花
圆圆的小道,几乎被村里的每一条小毛驴都走过的小道,已看不出驴的蹄印。
石碾盘边,当年谁不小心丢下的山楂籽,如今已经长成了一棵大树了,一到春天就开红红的花,一到秋天就结红红的果,秋风一起,叶就落满了一碾盘。
红红的果就落满了一碾盘。
想当年,石匠姥爷是从几十里外的一撮毛山上,用几头牛拉的爬犁,把这块上好的大青石拉回来,堆在院子里,石上面盖上一层层厚厚的玉米秸,从来就没有动过。那年母亲才六岁,从此之后,尽管也有人出高价买这块青石,姥爷却一直没有动心。
听姥姥说,姥爷这一生,除了他作为一个石匠谋生的工具外,他只在意这两件东西。三十五岁时,从山上拉下来的这块青石,后来他把青石造成石碾送给女儿作嫁妆了。六十五岁时,在停放过青石的地方,姥爷为自己准备了一副寿材,山桃木做的,一备就是二十年,每年他都精心的里里外外的刷上一遍油,二十年后,八十五岁的他把自己装进了这里,像一本合上的书,不准人们再打开阅读。
母亲不会领会当年姥爷这一副石碾陪嫁的意义,在她婆家破旧的三间草屋旁,人们精心地修整出一块地方,安置好了这座石碾,这是这个小村的第一个石碾。石碾隆隆的滚动声,让一个小村有了活力。
村里的人于是习惯在石碾上,加工粮食。每一个加工粮食的人,在离开时,都会给母亲留下点馈赠,或一把米,或一瓢面,母亲的日子就暖暖的温热。
这样的日子维持了四十多年了,四十多年后村里的电磨开始轰鸣,便没有人再用石碾推压粮食了,村里的驴也都杀光了,石碾留给村人的只有吱吱呀呀绕圈儿的记忆。
母亲就有一些不适应,喧闹的人生一下子宁静下来,母亲仿佛一个被冲上海滩的贝壳,只能听听海的声音,却感受不到海的湿润。
生活就是这样,得到一些就要失去一些,但遗憾的是,得到的,有时并不是我们想要,但失去的却是最珍贵,这是无奈的遗憾。
石碾就这样遗落在这里,风吹雨淋,那些木制的框架都腐烂掉了,只剩下它孤零零地蹲在这里打盹,直到有一天,一个城里的人想买走它,做什么用,城里人没有说。
母亲犹豫了一夜,最终还是没有卖,她说这东西留着就是一个念想。
有许多东西,我们留着都是一个念想。
有许多东西,我们留着也只是一个念想。
只是岁月并不这么想,一株牵牛花借着雨的指引,风的煽情,一点一点的爬满了石碾,浅浅的淡淡的花开得热热闹闹,轰轰烈烈。
铁匠铺的火光
铁匠炉是工业文明溅落在小村的一个火星,小小的一直没有熄灭,并没有成燎原之火,便如一颗星,孤冷地挂在村头。
铁匠铺选址在村头,在村头上的二间草屋里。草屋依山而建,屋边一条小溪流过。当初选在这里,一来图这里是进村的必经之路,人们来来往往送活、取活方便,二来离村子稍远一些,以便叮叮当当的捶打声扰了小村的宁静。却想不到山下,水边再加上一炉火光,使得小屋成为小村的一景,成为铁匠生命中的一景。
铁匠非常满足这样的日子,靠力气吃饭,靠手艺吃饭。日子平淡却也有滋有味,有滋味的日子就是好日子,就叫铁匠恋着,想着。没活的时候,铁匠喜欢坐下来抽一袋烟,胸前总是挂着皮围裙,那皮围裙被火星溅得斑斑点点,屋里的火星明明灭灭,铁匠的烟袋锅也明明灭灭。
平静的日子并没有多少。
铁匠不安份的儿子跟着抗联走了,成为一名抗联枪械修理的专家,而这一直是铁匠的心病。
有一天,他听说只要去县里领一张良民证,儿子就无事了,他走了四十里山路去了县里的警察署。
他走去了,就再也没有走回来。
他不知道,所有人都不知道那只是日本人的一个阴谋,当他们一个接一个被捆上,拉到县城边的浑江,一个又一个被塞进了砸开的冰窟窿时,他们才明白。然而明白也晚了,一个个生命悄然的凋落了,成为了浑江惨案的一个数字,成为历史的一滴眼泪。
铁匠于是消失了,甚至连尸体都没有找到,铁匠炉后面的山坡上的那座土坟里,埋着的只是铁匠的那件皮围裙。
炉火于是灭了,风箱抽动声也一下成了过去,只有偶尔落在屋檐上的鸟儿,证明这里曾经活过。
许多年之后,铁匠的儿子回来了,是从抗美援朝战场上回来的,只是少了一条腿,额头的皱纹留下岁月的痕迹,身上的伤痕留着战争的痕迹。
儿子此时才知道父亲的事。他一条腿跪在山地上,跪了整整一天,仿佛是祈求父亲的原谅,仿佛在叙说自己的内疚。
后来,儿子推掉了县里安排的工作,把父亲的铁匠炉收拾了一下,又开业了。
儿子的手艺比铁匠还好,价格也便宜,远远近近的人都来找他,有时没有钱,挎一袋土豆,拎几个鸡蛋,也可以充当工钱。儿子的小日子过得还算滋润。
那时,他的年龄已经大了,村里没有适当的对象,就有人把邻村的一个刚死了丈夫的女人说给了他,就把铁匠炉旁的房子买下来,那女人知冷知热,小日子过得也热热乎乎。第二年还生了一个儿子。
儿子手艺好,手巧,是在部队上炼就的,在这里就没什么用武之地,闲暇的时候,他就打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玩。儿子的自行车就是自己用锤子砸出的,尽管很重,但在山路上骑起来,驮点东西,比买的还适用。
儿子打得最好的是老人过世封棺用的棺钉,普通的铁匠只会打一个一般的钉子,铁匠的儿子却会在钉上面打出一个寿字,还不要钱,远远近近的老人过世都是用儿子打的棺钉,封闭了与这个世界的最后一扇门。
铁匠炉一直就这么开着,红红的碳火,在岁月里明明灭灭,直到有一天,铁匠的儿子倒在了门前。
那个时刻,铁匠的小孙子已经离开村子去上大学了。
铁匠的木棺,钉上他留给自己的棺钉之后,他的一生就结束了,一座曾经温暖过小村的炉火也熄灭了。
只是在我的记忆深处,那风箱的抽动声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