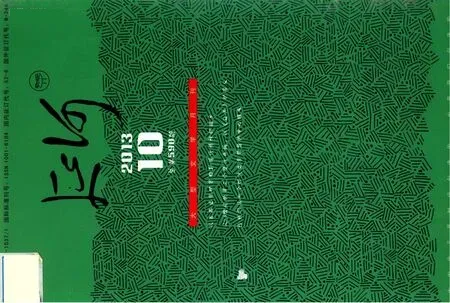神话“重述”的集体溃败
朱嫣然
《碧奴》是苏童为“‘重述神话’写作计划”而作的长篇小说。“重述神话”是全球包括英、美、中、法、德、日、韩等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知名出版社参与的全球首个跨国出版合作项目。由英国坎农格特出版社著名出版人杰米•拜恩发起,委托世界各国作家各自选择一个神话进行改写,内容和范围不限。
这是一个颇具意义的写作项目,已加盟的丛书作者包括诺贝尔奖、布克奖获得者及畅销书作家,如简妮特•温特森、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斯蒂芬•金等。中国作家中,苏童、李锐、叶兆言、阿来等受到邀请,用自己的方式对中国神话进行了重新解构。遗憾的是,在这一系列的神话写作中,先锋作家们保留了自己的语言优势和叙事能力,同时也暴露出其根深蒂固的无神论意识形态。用无神论去书写神话,导致了这些作品中“神性”的集体缺失,直接抛却了神话写作的灵魂。
相比于李锐的《人间》、叶兆言的《后羿》和阿来的《格萨尔王》,“人气作家”苏童的《碧奴》受到了更多的批评与关注。苏童用优美的语言打造了一个神话,如同打造一个华丽的神殿。但是神的缺席制止这场神话叙事,这是一个致命的缺陷,犹如“碧奴”背负的那块顽石,压垮了整部作品的精神指向。
眼泪的生存哲学
《碧奴》故事的叙述是由眼泪开始的,最终又由眼泪结束。极具想象力的“眼泪叙事”,是这部小说最引人入胜,却也是唯一精绝的地方,构成了整部小说虚无而苍白的支架。
一个叫信桃君的贵族来到了北山,对他的叙述,却从遗忘开始。“人们已经不记得信桃君隐居北山时的模样了,他的草庐早就被火焚毁,留下几根发黑的木桩,堆在一片荒芜的菜地里。”显然,信桃君是开头时一个模糊而黯淡的影子,苏童用了煞有介事的语气,将这个孱弱的落魄贵族焚烧成一团黑色的记忆。整个故事的背景,因此被放置在了一片鬼魅而疏离的土地上。将死的信桃君,他隐居到了北山,同时也把死亡的宿命带到了这里。北山的人们因为为他“哭灵”,而遭遇了一次残忍的集体谋杀。这是“眼泪”在故事中的首次出场,它的出场带来了与死亡有关的恐怖记忆。从此,“北山下的人们至今不能哭泣”,哭泣不被允许,它成了死亡的图腾。要生存,就不能哭泣,这成了北山下人们的生存哲学。
“眼泪等同死亡”的哲学观第一次被打破,是碧奴出现在五谷城时。她的眼泪被城门口的官兵发现,并被认为极具药引价值,可以奉献给达官詹刺史的药炉。泪水在关键时刻救了将死的碧奴一命,将象征着死亡的外衣成功脱下,被赋予了与生存有关的星火希望。这是一次依赖“眼泪”的互救,詹刺史需要用眼泪入药救活老母,碧奴需要将眼泪交出以换得生存。
苏童当然不会让碧奴在这种情况下流泪,如我料想的一样,在面对着接泪的坛子时,碧奴一滴眼泪也无法流出。我们无法乐观地认为,她是有精神洁癖或某种觉悟。这个美丽而愚蠢的村妇,她暂时离开了与苦难无关的情境,以至于失去了反应。这是一次遗憾而尴尬的转折,眼泪并没有摆脱自身的宿命。
眼泪最后一次大规模出场,是在故事的结尾。大燕岭上搬砖的男人们,他们同北山下的人们一样,不被允许哭泣。而碧奴的哭声像风一样回荡在大燕岭的上空,坚硬的城墙外,是灰黄而空旷的远方。苏童用优美精致的语言,着力刻画了碧奴这最后一次的哭泣。这哭泣是如此宏大而悲伤,整个天地都因此荒芜。在这次哭泣中,碧奴终于抛却了桃村的女儿经,放肆地改用眼睛哭泣。她的哭泣有了作用,山崩地裂中,长城塌了。
眼泪至此完成了它的三次主要出场,苏童也通过这三场“眼泪”完成了叙事。在故事的叙述中,眼泪始终与恐惧和死亡有关,直到一个看似乐观的结局到来。但这结局又是如此牵强,它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新问题,碧奴是如何靠着最后的眼泪,哭倒长城的?仅仅是因为她抛却了眼泪带来的死亡恐惧,向“不能用眼睛哭泣”发起了反抗?
被忽略的心脏
哭泣本身是一种情感表达的方式,北山的人们显然失去了这种直接表达情感的权利。但是苏童给了他们全新的排泪秘方,桃村女孩的眼泪,从眼睛以外的手指和脚趾、头发、乳房、阴部等所有孔窍流出,漫过苍凉的大地,成为小说的章鱼式结构的逻辑支点。
“耳朵大的女孩从母亲那里学会了用耳朵哭泣的方法,那眼睛和耳朵之间的秘密通道被豁然打开,眼泪便流到耳朵里去了,大耳朵是容纳眼泪天然的好容器,即使有女孩耳孔浅,溢出的泪也是滴到脖颈上,脖颈虽然潮了,脸上是干的。厚嘴唇的女孩大多学的是用嘴唇排泪的方法,那样的女孩子嘴上经常湿漉漉的……”显然,只有身体最饱满的部位,才会流出丰富的眼泪。苏童给碧奴的,是一头乌黑浓密的长发,碧奴从那里流出眼泪,流得比所有其他女孩儿都多。在她背着冬衣寻夫的途中,她的脚趾也新增了流泪的功能。这大抵可以推断出,长途的跋涉,让碧奴的双脚也变得更加厚实有力。
但是,奇异的是,在苏童笔下,眼泪可以从所有孔窍流出,唯独没有心。在故事的开头,北山的人们由于为信桃君哭灵而纷纷葬送性命,因此得出“哭灵人都死于一颗感恩之心”的结论。当北山下的人们为了生存不再流泪时,他们也就放弃了有心灵有关的事物。
这是一处绝佳的隐喻,可惜的是,苏童似乎刻意地将其忽略了。在之后的叙述中,从身体各处流出的眼泪汹涌不绝,而心脏依旧保持着被忽略的姿态。我原本以外,在碧奴流亡的途中,被忽略的心脏会被重新唤起,流出清澈透明的眼泪,完成“眼泪叙事”与“神话叙事”的双重转化与升华。遗憾的是,直至结尾,碧奴以及苏童本人都没有从中苏醒。他们沿着“眼泪叙事”的奇诡开端渐行渐远,终于走向不归的末路。
故事在哭倒长城处戛然而止,似乎暗示了眼泪和碧奴的最终胜利,却因此让整个故事显得苍白而虚弱。没有心的眼泪,如同没有灵魂的肉身。因此,碧奴的眼泪是没有精神指向的,它无法支撑起这则神话的价值与信仰体系。眼泪在苏童的笔下,如同一个刻意打造的、极具神秘感的仪式,却最终成了一个虚晃的影子,在碧奴一路的流亡中,逐渐黯淡下去。
受虐与施虐的狂欢
在“眼泪叙事”的主线之外,“自虐与他虐”的母题,如同一条暗夜里的蛇,固执地爬行在浑浊叙述的表层。碧奴在给丈夫送冬衣的流亡途中经受的种种,看起来像是一场纷繁吵嚷的苦难汇演,和不可思议的虐待狂欢。
碧奴如同一个旧式的自虐英雄,悲情泛滥,自我凌迟,享受着浸淫其中的快感。她行走在充斥着血和泪的路途上,遍尝人间苦难,却似乎并不自知。苏童的叙事保持了先锋小说家一贯的冷淡,却在《碧奴》中得到了极为失败的效果——如同没有心的“眼泪”,碧奴成了一个没有心的殉道者。
在自虐以外,一系列更严重的他虐事件混入了小说的叙事中。碧奴一路上从未遇见善意的人事,在树林中,她被一群年轻的男孩猥亵,随后被钉在死人棺木上为陌生男子哭丧……施虐的高潮发生在碧奴被当做刺客,被关在铁笼里示众的时刻。那是一场真正的嗜血狂欢,在苏童冷酷却又沉湎的描述中,其场面的暴虐程度令人发指。“人们转过了脸,很自然地去看笼子里碧奴的手,她的手被套在木枷洞里,看不清楚,她的发髻已经散成乱发,乱发滴着雨水披散下来,遮住了她的脸,她的脸也看不清楚……”这是一个瘦削而苍白的女子,但人们关心的,只是她的脸看不清楚,影响了自己的窥视。而碧奴本人呢,在肮脏的囚车和滂沱的大雨中,她安然入睡,对一切命运的不幸坦然接受。这或者就是苏童在序言中所说的“乐观的故事”,我们甚至可以由此推断,苏童本人也陷入了这种施虐的狂欢中,不能自拔。
苏童是一个模糊的影子,隐藏在看似冷漠实则兴奋的叙述背后。他与碧奴之间,构成了精准而对立的“受与施”关系。对碧奴施暴者,正是苏童本人。他用了一场又一场的暴力狂欢,蓄意打造出一个女子的悲惨形象,如同在腐烂伤口上雕刻出的精美繁花。
苦难的巨大筹码,推动着苏童小说的叙事。一个女子的眼泪和痛苦,通过极端的虐待和摧残,赤裸裸地呈现在了读者面前,从而唤得震动和同情。这是一种笨拙的方式,它使故事本身失去了一个饱满的精神内核。
缺乏说服力的出走者
碧奴是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出走的,在那个温暖的季节里,她固执地要去为丈夫送一件冬衣。碧奴出行的目的是如此单薄,单薄得有些愚笨。当然,在故事的开头,碧奴的这种愚笨是可爱的,至少她是带着顽强的信念离开桃村的。我们可以期待,这模糊的信念,会随着这场固执的出走,而逐渐清晰和明朗起来。
从出走的层面来说,碧奴身上具有反抗者的精神气质。她的愚笨和固执,使她充满了一往无前的勇气。与惧怕眼泪的北山人不同,碧奴似乎是不忌惮死亡的,她试图用一只青翠的葫芦,提前埋葬自己的肉身,像埋葬一件冰冷的器物。她对待自身是冷漠的,这种冷漠反衬出她在出走时的坚决,以及后来路途中的热情。在这场漫长而痛苦的行走中,碧奴对自己遭遇的一切磨难选择了盲视,没有任何痛感,同时,她又有着不可思议的,不抵达大燕岭绝不罢休的坚韧信念。对肉体的极端漠视,和对目的地的极端狂热,构成了一个精神分裂的女性形象。
碧奴出走的唯一目的,就是为她远在大燕岭的丈夫万岂梁送一件冬衣。如此我们便可以看出,整部小说就是在讲述中国古代,一个极其普通的“千里寻夫”的故事,其本身不具备任何新意。苏童利用了神秘主义和传奇性等工具,为整部小说编织了一个巨大的圈套,以掩盖故事本身的单薄。如同一件高贵柔软的外衣,勉强地遮掩着空洞的内核。
作为出走者,碧奴是缺乏说服力的。碧奴没有自己的守护神,也没有自己信仰的教义。她惟一的跟班是一只同她一样愚顽的盲眼青蛙。这是一种苦行僧的姿态,需要用身体语言去表达信念。但是,在《碧奴》中,我们无法找到支撑这种苦行的精神力量。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究竟什么东西在支撑碧奴承受如此巨大的苦难。是爱?宗教信念?还是某种神奇的巫术?苏童在叙述中没有给出有力的解答。
这一切使得碧奴的出走变得毫无说服力,她不是一个朝圣者,而作为殉道者,她又是没有光环的。碧奴整个人,连同她的故事,都是如此黯淡而单薄。她是一个缺乏说服力的出走者,从另一个方面折射出中国男权文化的阴郁一面。
苏童用一部长篇小说的笔墨描写了碧奴这样一个女人,美丽,愚笨,隐忍,同时有着无可救药的痴心与贞洁。这显然是苏童心中华夏女性的最高典范。整个故事的主线是这个叫碧奴的女人,而男性角色则是故事中一个个轮番出现却又面目模糊的配角,男主甚至只是一个与名字有关的苍白代号,它看上去很像是一份女性主义文本,实则完全相反。那些面目模糊的男人们,凶狠、狡诈、对碧奴的苦难境遇毫无怜悯,反而更加肆虐地加以践踏,而碧奴却对此毫无知觉,继续圣母般地对他们表现出天真的良善。碧奴穿越了所有非人的苦难,只为完成对丈夫的坚贞。而她是否爱自己的丈夫呢?在苏童的小说中,对此似乎丝毫没有涉及。
传统的中国男权文化,要求女人成为模范的受虐者,这一受虐伦理,从贞节牌坊开始,一路浩浩荡荡地延伸下去,最终凝结在先锋小说家的笔尖上。苏童肯定并讴歌了碧奴的胜利,重塑了传统的贞操美学。而面对孟姜女故事中可能包含的儒教歧视女性因素,苏童并没有给出必要的质疑或批判。《碧奴》的整个叙事,就如同一曲高昂的女性受虐之歌,从两千多年前的秦汉,一直回荡到今天,如同碧奴那风一般的哭泣。
“神”与“性”的双重缺失
作为神话写作文本,《碧奴》在处理最关键的“神性”时遭遇了惨败。整部小说用华丽的语言打造了一个精美的神殿,却连冠冕堂皇的神像都不曾塑起,只留下空荡荡的阅读现场。“神”与“性”的双重缺失,暴露了苏童根深蒂固的无神论意识形态,同时宣告了这则神话写作的失败。
小说没有任何直接的性描写,这从侧面衬托出爱的退场。“他们守在溪边,隔水谈论着信桃君状如孩童的生殖器官,躲在岩石后面的牧羊人说王公贵族就是不一样,连那东西也长得那么精致文雅,灌木丛里的樵夫则怀疑那样的器官是否能够传宗接代……”这是小说中为数不多的对生殖器官的直接描摹,它是纤细而脆弱的,仿佛随时可以被折断。某种意义上,信桃君的死亡,暗示了“性”,或者是男性的阳具在整部小说中的缺场。这也许是苏童刻意打造出的贞节。在后文中,即使碧奴被一群年轻的男孩猥亵,苏童的语言也控制得干净节制,一笔带过,有着不可思议的纤弱美感。
而在碧奴与丈夫万岂梁之间,也没有太多的情感描摹。只有一段描述碧奴对丈夫的回忆,涉及隐秘而欢愉的性爱,短暂而甜蜜。可是这段追忆是如此单薄,根本无力支撑碧奴出走背后的强大精神信念。
脱离了性和爱的根基,《碧奴》故事中的情感变得单薄起来,经不起任何推敲。而整个故事中,我看不到神的存在。除了结尾处出现的山神淡弱的影子,冷漠地看着背着重石上山的碧奴。那些亡灵变成的青蛙、百春台河五谷城外的马人和鹿人等,生硬而软弱,失去了神话叙事的透明和清澈,也与神话应具有的神性毫无瓜葛。
苏童在序言中说,“神话是飞翔的现实,沉重的现实飞翔起来,也许仍然沉重。但人们籍此短暂地脱离现实,却是一次愉快的解脱,我们都需要这种解脱。”遗憾的是,读完《碧奴》全篇,我并没有得到解脱,甚至更加沉重。我们并没有从碧奴的眼泪中,寻找到解决人类普遍困境的终极方法,反而陷入到一种更无力的绝望中。神的缺失,让读者和碧奴一样,最终只能走向神话的穷途末路。
苏童妄图通过对民间神话的瑰丽想象,建造一套自己的情感哲学。但是毫无疑问,他失败了。在这次“重述神话”的尝试中,中国作家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包括李锐的《人间》、叶兆言的《后羿》和阿来的《格萨尔王》在内。一群心中无神的作家,无法正确阐释神话遗产。碧奴的道德眼泪,摧毁了孟姜女的伟大信念,同时宣告了这次神话重述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