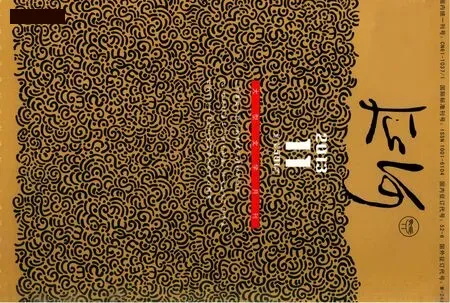我玩过的死亡
冯学起
1
我一直以为,世界上最刺激的事情是和死亡玩耍。认识我的人都知道,27岁那年,我和胃癌玩耍过,38岁那年,我和窒息玩耍过,前年,我和醉酒驾驶玩耍过。我几次和死亡玩耍,虽然玩得你死我活,甚至被黑白无常押解过,被阎王殿喜欢吃人的小鬼们垂涎过,但只觉其乐融融,未曾尽兴,所以一直惦记着继续和死亡玩耍。
前些日子,我又和死亡玩了一次。这次跟我玩的那个家伙叫脑死亡,医学上称脑梗死。
那天,我坐在办公桌上埋头改我的中篇小说,突然觉得房子里一片漆黑。沉沉的漆黑里抽动着数条金黄色的丝线。丝线弯弯曲曲地附带着或长或短的分叉,活像我们经常见到的天上打雷时从云彩底部射出来的电光。不同的是,那些丝线一样的东西虽然也带着亮光,但亮光是独立于漆黑之外的闪烁,漆黑与闪烁的亮光互不相干,各行已事,黑得无所顾忌,亮得唯我独尊。现实中根本无法想象出这样的情境。你可能认为漆黑是因为丝线不够亮的原因,其实根本不是那回事。因为只要你瞅一眼那些丝线,就会有针刺和视网膜被撕扯的感觉。不一会,那些丝线又打弯成圈,或远或近,或多或少地套在一起,圆圈在逐渐收缩,原来散漫的刺激被集中得越来越紧密,最后像许多把烧得通红的匕首一样的血腥恐惧。闭着眼睛,依然能“看见”它们飘来飘去,活像在水中游荡的吐着信子的毒蛇。一旦你瞄上一眼,它们又变成了匕首的尖锐,直直地向你刺来,你的脑部瞬间就产生了被剜的疼痛,身体也产生了被抽了筋一样支离破碎的感觉。
闪着亮光的匕首退去后,房子里反倒不再漆黑,昏昏黄黄地像一片汪洋。汪洋没有水的密集,却像烟团一样散漫而抽离,间隙里翻腾着各式各样的造型,有黑压压的山,有巨浪翻腾的洪水,还有怪模怪样的图像,让人有身处无际苍茫的感觉。就在我稍未留神之际,无边无际的苍茫中忽然间挤来一个肥头肥脑的家伙,塞满了我周围的所有空间。那个肥头肥脑的家伙虚晃着,看上去像一个捉摸不定的人影,但我的眼前却堆满了山一样的脸面,有鼻子有眼,就是分不清鼻子在哪里,眼睛在哪里。伸手触摸,却是空荡荡的感觉,什么也摸不到。我感到眼花缭乱,身如筛糠,每个细胞都在不停地分裂。分裂后的细胞像空气中被蒸发的水分子一样不再回落,飘得不知去向。我觉得意志和肉体都在逐渐虚脱。不一会,我又感到浑身的肉在剥离,在骨头瞬间就变成了粉末,不停地散发着燃烧的焦味。
我以为自己累了,只好停下手里的活。我趴在桌子上,想闭着眼睛休息一会。
“你就是那个喜欢跟我们玩的冯先生吧?”一个妖里妖气的声音,但让人感觉那声音的底盘很重,另外好像还带着交叉十字步走路的怪味。
“哦,我是冯学起。你是个什么怪物?怎么铺天盖地的就进来了?你们又是谁啊?”
“啊哈,我们是死亡家族成员,我是脑死亡。听说你耍的大,多年前把我的几个朋友都玩得一塌糊涂。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对你这样的硬汉情有独钟。我这次找你,也想跟你玩玩。”
唉,原来是这么个烂事——死神来了!
看阵势,这家伙不是个软货。“哦,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你不说,我早就忘了。”我对他说。我想起了以前几次和胃癌、窒息、危险驾驶等死亡玩耍的经历。
“忘了?你是不是有点太洒脱了?这个世界上,有的人喜欢玩物,有的人喜欢玩钱,有的人喜欢玩女人,有的人喜欢玩毒品,更有把玩人作为最高境界的人。玩物的人乐此不疲,玩钱的人矢志不移,玩毒品的人死不改悔,玩人的人临死都有‘万水千山只等闲’的美妙记忆和‘登泰山而小天下’的自豪,即使是和女人玩一夜情的人,也会对曾经的幸福终身难忘。你跟我们几个死亡大佬玩得撕心裂肺、响彻云天,现在竟然忘了?”
“哦,对不起!我从小就这脾性,虽然喜欢跟死亡玩耍,玩的时候也有过心跳,但玩过就不再刻骨铭心了。”
“这么说你是一个钟情于刺激的家伙,那么,你肯定对跟我玩也很感兴趣了?”
“哦,玩得多了,再玩玩也不推辞,兴趣么,很一般。”
“那好!请抽一支我的烟,好吗?”
“好啊!烟是我的宝贝。你看!几十年来我抽烟不断,半夜起来上厕所还要抽一支。现在依然如故。烟启发了我的智慧和灵感。”我伸出右手被烟熏得焦黄的指头,左手又端着桌子上盛着满满烟蒂的烟灰缸让他看。接着,又点燃了它递给我的一支烟,有滋有味地抽了起来。
“嗯,很好。我们一起喝酒,你不介意吧?”
“笑话!酒是我有生以来的最大挚爱。它让我激情荡漾,勇往直前。没有酒,我便没有了做事的激情,更没有了做人的胆量和勇气。年轻时,瓶子不倒我不倒,瓶子倒了,我自岿然不动;现在,我不再年轻,虽然浩气不再,但每顿半斤八两能奈我何?”于是,我们又开始喝酒。
“好啊!有酒就得有肉呀!来碗红烧肉咋样?”
“红烧肉啊!红烧肉是我的命呀!三日不吃,便觉神魂颠倒,说话吐字不清,走路下脚不稳。”我们伴着大杯喝酒,又开始大块地吃肉。
“很好!那你好自为之。我们改日见。”吃完喝完,结束了欢快后,他走了。
2
房子里又恢复了以往的模样。数日里不再有什么异常情况打扰我,我也便心安于以往的孤独之中。于是,我便继续我以往的习惯,埋头写作,一根接一根地抽烟,隔三差五地狂饮至醉,常有不省人事的表演,坚持着“宁可居无竹,不可食无肉”的生活。不一样的是,从那以后,一个美丽的红衣少女成天带着妩媚的笑颜和母亲对婴儿一样的关怀围绕着我,一会递烟,一会端茶,时刻提醒着我肉的美味和酒的醇香。在她的鼓励下,我每天消耗的烟酒肉数量在直线上升。消耗越来越多,心理依赖越来越严重,思想上越来越不堪舍弃。没有烟,我无法写作;没有肉,我提不起走路的精神;两天不喝酒,便万箭穿心般的难受。
过了一段时间,我开车在去单位路上,突然觉得上下肢激动不已,手不停地到处乱抓,脚腿兴奋地要把车踢翻,觉得好像谁用一个超级针管给我注射了经常听人说的那种令人兴奋的东西。一开始,我并没有意识到我遭遇了脑死亡的挑战,也许是前几次跟死亡玩得太痛快淋漓了,早已忽视了死亡对我的威胁,忘记了前些日子我和脑死亡的那个约定。
坐在副驾驶座位上我的一个同事吃惊地问我:“你怎么啦?为什么一边开车,一边手舞足蹈?”
“没事!只是觉得想爆发,觉得力大无比,特别想跳迪斯科。”我说。
“不对呀!你是不是什么地方有毛病了?应该去医院检查一下。王宏学上次就出现过你这样的情况,结果是让脑梗死缠住了,他把钱都兑换好了,做好了到另一个世界的准备。”他很认真地提醒我,脸变成害怕了的白颜色。他说的王宏学我认得,也是我们一个单位的。
“对呀!”我突然想到应该是脑死亡来了。但我害怕我那同事继续害怕,没敢说出前些日子的那个遭遇。毕竟那个事情有点虚无缥缈,说给谁听,都会让人觉得你是在虚张声势,故弄玄虚。但我的内心已经在构思和脑死亡玩耍的情景,心急火燎地想体验玩它的快感。
接着,我便看见上次脑死亡跟我约会时的场景,眼前抽动着的金色丝线又往一起靠拢,周围包裹着一片黑压压的雾霾。哦,这场景我见过,应该是那家伙早已设计好的玩耍氛围。我突然意识到我得停车。于是,我把车停在了路边。
令我没想到的是,还没见到脑死亡,停车后的瞬间,我就昏迷不醒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觉得自己被放进了一个像棺材一样的空间里。“棺材”在自我移动,我被送在一个地窖一样的地方。但那地方虽然形状酷似地窖,里面却不是地窖那般黑暗,偶尔还有特别刺人的光。我还听见“哐当”、“嗡嗡”和一些“吱吱呀呀”的声音。我的灵魂告诉我,这个地方是阎王殿,那亮光是阎王殿堂大油锅下面的火光,那声音是阎王殿内那些小鬼们在磨刀的声音,他们还在为如何把我生吞活剥而争吵。奇怪!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呀?难道脑死亡这家伙有隔山打牛的本领?
我感觉我那七十公斤的肉体已经被平摊在阎王殿堂的大案板上了。一群吸血蝙蝠一样的小鬼吱吱呀呀地围在我身旁,他们渴得要命,他们饿得难活。面对我平日里好酒好肉滋养出的肥美肉体,谁还能无动于衷?我知道,只要阎王一声令下,他们便会蜂拥而上,用他们手里磨得闪闪发光的牛耳尖刀剥开我的皮,抽出我的筋,挖出我的五脏六腑。他们平时连误闯殿里的一只老鼠都会吃得一干二净,何况我这样的一个大块头肉体?这次他们就只拣好的吃,只吃内脏和筋。内脏营养丰富,吃饱一次,可以支撑他们半年多的日子。筋像人类钟爱的海参鱿鱼一样,对他们有同样的吸引力,不仅口感很好,吃了会给他们增添无穷的力量。
与此同时,我隐隐约约感到几个嗜好窥探别人隐私的家伙已经开始翻腾我的脑子了。他们要把我的脑子切成山里农民晾晒苹果干一样的碎片,一片一片地晒在那个大案板上。晒干后,再用一种叫做还魂汤的液体把脑片泡在一个很像玻璃瓶子的容器里。一段时间后,玻璃瓶子上就会像放电影一样,把我一生干过的事情播放出来。从光屁股的形象到几个小时前开车的样子,在题目是《冯学起的一生》的统领下,我所经历的事情会被一点不漏地呈现在众鬼睽睽之下;有让我欣慰的,也有令我死不瞑目的,一切隐私皆将大白于阴司。
我还知道,我被脑切片,被剥皮抽筋,被分食内脏后,就会被投入那口大油锅里进行煎炸。那个冒着热气,翻着滚滚油花的油锅在接纳了我的肉体后,便含蓄内敛地冒一会悠然的小泡泡,就会老练地把我煎煮成他们预想中的样子。用不了多久,我的骨头便会被炸得焦黄酥脆,里面的骨髓就会顺着缝隙主动流出来。那些拿着吸管在一旁等待的小鬼将毫不费力地吸到我隐藏最深的美味。
我马上就要变成一只黄而脆的酥鸡了!我该咋么办呀?
奇怪!天大的奇怪!怎么这么快我就被运到了这个地步?
我很想抽支烟!
3
我觉得我的灵魂已经游离到我的身体之外,但还在恋恋不舍地张望着我。它想离我而去,但好像又于心不忍。我能猜到它此时的心思,必定它的本质还算善良!
“哈哈,你这个冯耍大呀!我们又见面了。这下你玩到头了吧?看你还显能不?”是那个肥头肥脑的家伙。脑死亡终于出现了!
它飘在我的上面,居高临下地看着我,悠闲的臭嘴一边还吹着胜利在握的口哨,放松的身体带着幅度不大的街舞一样的动作,肥腻的厚嘴唇在气流的掀动看上去肥猪大便一样的恶心。我又有了那种天翻地覆的感觉了。
“果真又是你。哼,你这个厚颜无耻之徒,偷袭我,算什么英雄好汉?”我终于又看见他丑恶的嘴脸。他那吸血蝙蝠一样的口哨声,令我有一种憋尿的痛感。但我和以前跟死亡玩,知道不能表现出丝毫的胆怯。
“偷袭?我数月前就告知你了,从那时起,我们就开始玩了。”
“胡说!那次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你这副丑恶的嘴脸呀!我们还没有开始呢!”
“哼哼,谁在胡说?我没有胡说。我的影子一直在你身旁,一刻也没有离开过,日夜侍候你抽烟,喝酒,吃肉。抽烟喝酒吃肉的时候,你那么心满意足,那么贪得无厌;烟酒肉超量,你又那么恬不知耻无怨无悔。现在你难道忘了?”
“那个红衣少女是你的影子?是你派来的卧底?抽烟,喝酒,吃肉是你的武器?这就算是我们在玩了?”
“当然了。哈哈……没有想到吧?都什么年月了,谁还和你玩阵地战?游击战也早已过时了。我不策划个她,你就不可能尽情地抽烟,喝酒,吃肉;你不享用那么多的烟酒肉,始终头脑清楚,我打不坏你的生理系统,怎么可能玩得过你呢?”
美人计!我中了这家伙的美人计了——哦,还有欲擒故纵计。唉!我一个小小之人都能被美人瞄准,难怪那么多智商高,意志坚的高官被美女跟踪,瞄准,侍候得断送了前程。“美女”和毒品一样毒啊!
我还没有出手,不知不觉中就被人家玩了个稀里哗啦。这家伙谙熟《孙子兵法》。恐怕我不是他的对手。怎么办呢?我想到了保命要紧的道理。
“你不能走!你是我生命的一个重要部分。你不走,我坚信能胜利;你走了,我就玩完了。”我只好看着我的灵魂,自我努力。我的灵魂看着我日落西山的样子,表现出了从未有过的犹豫。
“你早该走了,跟着他一个书生有什么意思?现在谁还成天玩弄文字?随便找一个肉身附体,你就会有不一样的感觉,你肯定就能在滚滚红尘中享受荣华极乐,何必成天在孤独中忍受贫穷呢?”脑死亡又开始对我的灵魂下手了。
“嗯。我也有这样的感觉,早不想跟他这样一个书呆子混,过那种充满煎熬的日子了。”他们两个的看法一致。
完了,完了,这下我全完了。我后悔啊!平白无故地和这么个没心没肺的家伙较劲,现在被玩完不说,自己有生以来无人知晓的隐私也将在生命终结的时候暴露无遗。他们马上就会知道我小时候经常给人家水泉子里撒尿,知道我第一次性交时笨手笨脚的丑态;我成天想着和女性缠绵却屡屡被骗的画面必将笑掉他们的大牙;我被彩票中大奖诱惑得几近破产的情形,势必会让他们说我是一个笨无极。还有,我曾经日谋夜算着踩着别人往上爬,曾经准备把单位里一大笔钱据为己有,曾经诅咒上司不得好死,曾经一年四季不回家看望父母,曾经开着大排量的私家车回家给家里人做工作,让他们省吃,曾经……唉……我还有两部长篇小说没有完稿。
“你不能走,看在咱们一起生活了几十年的份上,请你留下来。”我对灵魂乞求道。只要灵魂不离我而去,我还有希望。听了我的话,我的灵魂还在犹豫,但好像不由自主地向我跟前靠了靠。
“不能!坚决不能!现在是什么时光了,懦弱都懂得跟着坚强混,混混都知道跟着大佬蹭,女人都傍着大款高官的膀子。一个至高无上的灵魂怎么就不能舍弃一滩行尸走肉呢?”
“嗯。对着了。”
“不要!不要那么认为。你是灵魂,你可是我的主心骨。自从我们在一起,我让你抽烟,吃肉,喝酒;我经常写作,愤世嫉俗,思想高雅,肉体没有污染,所以你才获得一个纯洁的名声。别处你不可能找到这样的待遇。”
“不要相信他的鬼话。他们早已没有灵魂了,也不要灵魂了。再说,坚持清白,追随高雅早就变成了过眼烟云。”脑死亡戳我的老底,千方百计地劝说我的灵魂。
“嗯,是那么回事!我还是想纯洁啊,但他从来也没有好好地待我。‘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是强词夺理的恶意炒作,写小说是一种自我清高的标榜。其实,他时刻忘不了红尘滚滚,花花世界。他的说辞和所作所为不过是狐狸吃不上葡萄说葡萄酸的真实写照。”
“对对对,他就是这么个人!”脑死亡高兴地笑了。
完了,完了,我的灵魂能不了解我?最害怕的事马上就要发生了。我的灵魂要离我而去了。我也得兑换钱,做好移民的准备了。我看见一群手里拿着尖刀的小鬼向我走来,他们准备剥我的皮抽我的筋;那些拿着吸管的小鬼心急火燎地要把吸管插入我的骨头。
4
就在我觉得在劫难逃,想做出最后一搏的时候,白无常站在我的身边。我知道白无常是最讲道理的。我听见他说:“这个人虽然死相斑斑可见,脑部也已经出现了多处死亡,但关键部位没有问题,意志还很清楚,是不是没有喝奈何桥上的孟婆汤?”
“嗯。没有喝。我们让他喝时,他把盛孟婆汤的碗给砸了。”一个小鬼回应道。
哈哈!我真高兴我意志坚定,虽然曾被那么多的诱惑所招安,但我拒绝了有可能是人生的最后一个诱惑,没有喝那该死的孟婆汤。尽管当时那个给我送来孟婆汤的小鬼说的天花乱坠,吸引力远远超越过以前遭遇的所有诱惑。
“没有喝?没有喝,怎么就按照已死亡处理呢?抬出去!进一步诊断后,再作处理。”白无常放下了手中的脑部切片说。
“有人让这么处理的。我们也是听从指挥嘛。”那个小鬼嘟囔道。
“胡闹!”白无常生气了。
咦,我看到了不死的可能。
我感觉被摇晃着推离了那个地窖。那些原来准备把我作为大餐享用的小鬼们,叽叽喳喳地表示强烈反对,活像一群反对拆迁的居民,要死要活地拉开造反的阵势,但他们知道在阎王殿的威严面前,任何挣扎都只能是虚张声势。闹腾了一会,便鸟雀散了。脑死亡更是气急败坏地发怒道:“不能让这家伙逃脱,我们正在玩死呢。他都死到临头了。”
没有人理他。我心里得到些许安慰。他只好对着我愤怒地说:“即使阎王放过你,我还要玩死你。你就等着瞧吧!”
没过多久,我就被置于奈何桥旁的沙滩上了。四周昏昏黄黄的,没有一点生命的迹象。但我坚信,这下我死不了了。我迷迷糊糊地听见天上有一大群寻找腐肉的乌鸦在忽高忽低的盘旋着。我生怕它们把我当成一个死尸。我还没有死啊!我的内心呼喊着。我感到口渴难耐,很想喝一大杯,不,一小杯就满足的凉爽啤酒;我也觉得饥肠辘辘,要是有一碗,不,哪怕是一块红烧肉,该有多好啊!
“啊呀,你这个该死的家伙怎么跑到这里啦!让我找了好久!嘿嘿……就是这个家伙。”
我听见脑死亡锲而不舍地追来了,在和一个人说话。接着,我看见一个漆黑如墨的家伙来到了我旁边,是黑无常!我认识他,以前我们见过面。那个可恶的脑死亡又搬救兵了。
“查一下他的脑子,看还有没有生命迹象。”黑无常命令旁边的小鬼道。
“我检查过了,他没有死亡。”白无常在对黑无常说,我明显感到白无常脸上挂满了不可思议的表情。
“那不一定准确,以精确的事实为依据吧!”黑无常说完,就走了。
“嘿嘿”,脑死亡笑得汗流浃背,尖锐的哨声像天空那群饥饿的乌鸦一样刺耳。他令我恶心得想大便。
接着,我又被推上一个像那个大案板一样的平台。他们扒光了我的衣服,有人在我大腿根部的一根大血管上划了个口子,另外一个人拿着一根长长的铁丝从那里穿入我的血管。我感到好像一群蚯蚓沿着我的大腿、胸部、脖颈劈荆斩棘地走着,不一会就到了我的脑子里了。它们到了我的大脑后,探头探脑地四处走动,仿佛进入了一个迷彩世界。我不知道它们在找什么。过了一会,我感到好像那些蚯蚓在我的大脑里撒了一泡尿,顿时觉得头晕得不得了,嘴唇发麻,四肢轻飘飘的,宛若电击。我终于没有忍住大便,稀里哗啦地拉了半个台子,也是热的。
“你们看哪,他都大便失禁了。猪羊临死的时候,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无法控制大小便。”脑死亡在旁边争取道。
“恶心!”黑无常面对着脑死亡。脑死亡耷拉下脑袋,我想他心里肯定在恶毒地骂着黑无常。
感觉不晕了后,我听见旁边一个人说:“没有什么!跟脑切片反映的结果一样。”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他抽了那么多烟,喝了那么多酒,吃了那么多肉,怎么可能还会一尘不染,两袖清风呢?”气急败坏的脑死亡已经土崩瓦解,我再也听不到他得意的口哨声了。
黑无常瞪了脑死亡一眼,双手抱拳,给白无常道歉。白无常笑了笑,什么也没有说。脑死亡晕得找不到东南西北了——我知道他不是头里面的脑子在发晕,而是他的意志受到打击后产生的不知所措。他蹲在一旁面色惨淡,形容枯槁,原来那副耀武扬威的嘴脸既没有了宽度,也没有了厚度,尽管躯体上的肉还在挣扎,但整体形象缩小成了一个木偶。没有了脑死亡那压抑的阴影,我感到了阳光和空气的存在,尽管我还能听到脑死亡在一旁嘀咕道:“不就少喝了个孟婆汤吗?”
他们都走了后,我被安置在一个白色的房子里。我终于被当活人对待了。原来,是连日来围绕在我身旁的医生。我的灵魂又悄悄地回到我的身上。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呀!我敢埋怨他吗?能埋怨他什么呢?
脑死亡被挡在了房子外面。三四天时间里,它很不甘心地爬在窗户外和我对骂,夜里还常常走进我的梦里。我知道它上厕所时一定是一边使劲地往出拉大便,一边用同样的力气在诅咒我。但无论它怎么诅咒我,我的灵魂回来后,我再也没有看见过那个诱惑我的红衣少女,虽然我一刻没有停止过对烟酒肉的思念。
5
快一周了,按照医生的说法,我仍然没有完全脱离死亡,期间还有几次似乎意识到我就要死去了。我想这可能既有医生的刻薄,也有和脑死亡玩的时候那刻骨铭心的记忆在作怪。
这次和脑死亡玩,虽然他蓄谋已久,准备充足,来势凶猛,大大地伤了我的元气,但毕竟他最终没有赢我。时至今日,想起和他玩的过程,我简直无法阻挡特别想哭的心情。我想哭,并不是想表达后怕或疼痛或难过的心情,也不是对脑死亡心狠手辣的痛恨。因为我想到了我那可耻的灵魂。我怎么有这么一个可耻的灵魂呢?想当年,我在跟那几个死亡玩耍时,他是那么坚定地和我站在一起。唉,看来在这个世界上很难有真正的天长地久了!
我静静地躺在床上打点滴。脑死亡失望地放弃了窗外的骚扰。然而,他走了后,我便觉得想抽烟喝酒般的无聊。我只好盯着那根细塑料管数里很有节奏的点滴,数着数着,就睡着了;醒来后,不想数了,但翻来覆去尽是无聊,又不由得不数,就又继续数着。打点滴本是一种受罪,现在似乎成为了我无法离开的乐趣,正像我跟死亡玩耍一样。难道我今后无聊的时候,还得继续跟死亡玩耍吗?人究竟是个什么东西?灵魂是怎么一回事呢?
一只饥饿的蚊子悄悄地爬在我扎点滴针的胳膊上。瘦骨嶙峋的,像一个缩小了的阎王殿里的小鬼,细长细长的腿像肉体风干了的神经末梢。任凭你瞪大眼睛寻找,几乎看不出它身上带着生命迹象。怎么看,它就是一块在秋风中飘落的黄叶碎片。
又来了一个跟我玩死亡的家伙!就它那身体情况,显然没有脑死亡的威力。我心里这样想。
它好像来顾不得思考自己到了一个什么地方,就拉开阵势准备从我的身上吸吮血液保命。我知道它在做出这个决定之前,在我的周围考察了好长时间,也费了不少脑筋。它怎么可能没有认识到我是一个会让它死亡的厉害角色呢?它之所以毅然决然地冒风险,是因为它是一种靠玩死亡活着的生命,玩命是它生存的本质,向来都不得不这样做。我和死亡玩,玩的是刺激,它玩的是命。只要我不无聊,我可以不玩,它再不无聊,能不玩吗?想到这里,我放下了抬在空中的另外一只手,没有理会它。它便像护士一样给我扎起了针。尽管我清楚护士扎针是为了我好,它扎针会给我制造难受,但我选择了忍受。
一阵痒痒的感觉过后,我看见它精神焕发地飞走了。望着它那沉甸甸的背影,我看见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一个个虚晃地走过我的眼前。
我喜欢与死亡玩耍,能与它们没关系吗?
27岁那年,我活在一个猪年里;38岁那年,我醉酒窒息,那年是一个虎年;前年是一个马年,我醉酒驾车,想着日行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