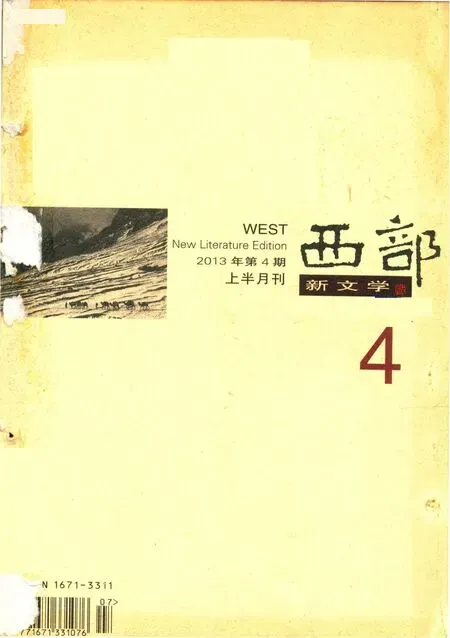明天以后
西洲
李一平那次发作之后,她算是彻底明白了他的感情。他对她终究是厌倦了。她只是觉得他过于可笑,明明是自己理亏,却做出一副受害者的样子,有什么意思呢?
努力想一想,她已经记不起来他掌心的那颗痣究竟是在哪一只手掌,左手还是右手?大约是左手吧,从前他牵着她走在路上的时候,就用左手拉着她,他说你要永远走在我的左边,我的心永远属于你。她可以感受到那颗暗红色的痣在她的手心摩挲,温柔热情又蠢蠢欲动。那颗痣和手心的皮肤是一体的,哪里能摸得到?这样一想,她又实在不能确定,那颗痣到底在哪里。是啊,从前她以为,他们必定会相爱到老的,他掌心的痣,就像歌里唱的那样,她“永远记得在哪里”,但那时的她实在不懂,那歌词为什么如此矫情:“恨不得一夜之间白头。”如今,她已经完全了解。一夜白头,这一夜就是地老天荒,就是海枯石烂,中间再也没有变故,没有分离背叛,没有仇恨痛苦,没有相逢陌路……可是已经太迟了。
女人的敏感是与生俱来的,但是有些人,会渐渐地在平淡或者热情中,悄悄地、一点一点地收敛起自己的敏感,不再轻易地把自己放在敏感的位置,这是无数次受到伤害之后总结出来的经验,叫自己的心稍稍麻木一些,再麻木一些,就不那么容易受到伤害。她其实早就知道他有了别人,她只是不想说出来,她不想像个审判者,看着他被拆穿后狼狈的样子,她只是等他告诉自己,等他有勇气说:“碧珠,我们分手吧;碧珠,我不爱你了,我爱上了别人。”她等着他这样说出来,而不是偷偷地出去,不回家。
但有时,她又觉得自己就输在了这样的冷静上。这种冷静仿佛不是一个被背叛的妻子所应该拥有的,也许这就是她的缺点。她本应该大吵大闹,捕风捉影;她本应该像个真正的妻子那样,盯紧丈夫的一举一动,留心他身边的各色人等……但是,那样太累了,那样的生活是她想也不敢想的,而且她也不愿意想。感情的事情,怎么说呢?如果真的靠这样才能继续维持两人的生活,那该是多么痛苦!
黄昏的时候,她看向窗外,天气好得不像话。他在书房里“啪嗒啪嗒”地敲着键盘。她进去后,他有点慌乱,不自然地笑着,又站起来抱了一下她。她有些尴尬,仿佛自己闯入了别人的领地。她挣脱他的怀抱:“我来找本书。”他才放开了,又坐到电脑旁边。她面朝书架,眼睛盯着一排一排的书,一本本地触摸着,那些书许久没有拿出来,上面都有一层灰了。房间里空气凝重,他的键盘不响了,一些文件和书页被翻来翻去,发出杂乱的声响,有些焦躁不安。她叹了口气,随便抽出一本书,没有再看他一眼,走了出去。
天色突然就暗了下来。黄昏的光影消失得那么快,好像有什么期待的大事情还没有发生,就已经入夜了。她不记得在哪里看到过:我最爱这苍茫的黄昏,唯有在这时刻,我才会感到有什么伟大的事情可能要发生。
可是从来都是什么也没有发生,日子就一天天过去了。从黄昏到深夜,到清晨,时光倏忽而逝,一天复制一天,一天重复一天,唯一不同的是那些她没有醒着的时刻。
唯有梦是不同的。
但是不止一次,她梦见那场大雨,相同的雨却落在不同的地方,有时候是站满旅客的站台,有时候是人来人往的天桥,有时候是无人的旷野。还有一次,是在湖边,一个她从来没有到过的湖边,而那湖水幽蓝,天色泛着只有晴天时才有的光泽。所有大雨的场景里都没有一张熟悉的脸。她也不觉得惊恐,在梦中,她清晰地知道这是梦,她镇定自若,一遍遍告诉自己,这只不过是梦罢了。直到她看见她的丈夫李一平。她看见他面带微笑从遥远的对面走来,从拥挤的站台上,从天桥的另一端,从旷野的地平线,从湖水的最深处……他微笑,像一个孩子般朝她走来。她也笑,张开双臂迎接他,还准备向他诉苦向他埋怨:“你到哪里去了?”一定要带着某种撒娇般的蛮横。但是她的准备没用上,她的双臂扑了空。李一平微笑不改,却目不斜视地从她身旁交错而过。她的笑容僵在脸上,双手还做着拥抱的准备。她回头,看见一个模糊不清的影子扑进了他的怀抱。
总是在这个时候醒来。她有些不甘心。她想看清楚那个人的脸,她是不是更年轻一些、漂亮一些,有哪些是自己不曾拥有的。遇到这种情况,她总是想知道那个人是怎么样的。他与那个人是怎么开始的呢?
她不知道。
但是,她相信很多事情不需要理由。她尝试着说服自己: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亲爱的,每个人都有红白两朵玫瑰,娶了的,和仍在园中的,没有什么大不了。
李一平也和别人一样。她告诉自己。她无端想起来从前,她去他的城市看他的那些时光,那时候怎么就不知疲倦呢?她问自己。如果现在,两人仍旧分居两地,她还愿不愿意每个周末搭火车跑七百公里的路风雨无阻地去看他?她不能确定。
周末,她任由他去开他的“会”,自己坐火车去了从前她待过的城市。那个城市与此处相距七百公里。那时候,他们分隔两地,每逢小假期,她都去看他,甚至某些周末她也要去。夜班车,夕发朝至。周五晚上去,周日晚上回,回来之后,顾不得梳洗下了车就直奔单位,刚好赶上上班。
辛苦呀,怎么不辛苦,但是比起相见的喜悦,辛苦又算得了什么呢!
李一平爱喝酒,但是绝不嗜酒,每次到了他的城市——也就是如今的这个地方——他们一起做饭,他总要开一小瓶白酒,一开始是他一个人自斟自饮,后来渐渐地叫她也喝。她喝酒的时候,他就看着她笑。她渐渐地爱上了喝酒的感觉。长夜漫漫,一个人的回程是如此寂寞,李一平就买一小瓶白酒、一只烧鸡,叫她在路上吃喝。车一开,她就打开酒瓶,就着烧鸡,吃肉喝酒,酒足饭饱之后,她倒在铺位上就睡,一觉醒来,正好到站。清晨的风吹醒她,真是叫人舒爽,一个人在那没有爱人的城市里所有的不安和孤寂都随着夏天初始的风四散而去。
李一平是不是爱过她,从前她是肯定的,可现在却有些恍惚了。那个婚是怎么结的呢?她现在想起来都有点心酸:他甚至都没有向她求婚。但是,那算不了什么,那个时候,两个人都是真心的,只是,谁也没有想到以后的变化。
她有时候也会想,究竟为了什么才留在这个城市里呢?爱情?婚姻?从前人们提到,总会说:“嘿,你这家伙,一定是为了爱情才留到这个城市的。”她想解释,可解释又觉得无从说起,她最怕人们这样想,为了所谓的青春、爱情、理想……诸如此类。一定需要一个理由才能在一个不相干的城市里待么?当那些支撑着整个生活的所谓理由崩塌了,不在了,还要怎么留下来呢?还要再找什么样的理由呢?她不愿意为了什么特定的理由留在某处,即使是曾经叫她那么幸福的爱情。
待在这里只是因为习惯。是的,只是因为习惯,虽然那些习惯背后,是她脆弱的爱情。
如今想一想,从前的那些想法倒像是给自己留了条后路:如果爱情没有了,我还是可以光明正大地待在这个我已经习惯了的城市的。她这样想想,不禁微微地露出了笑意。
这一次出门,她没有像往常那样坐夜班车,她买了上午的票,天气阴沉着,一朵灰色的云飘在站台上。
进站的时候,一个女孩哭着从楼梯上下来,周围的人向她投去讶异的目光,一个男孩亦步亦趋地跟在后面。她狠狠地看了他一眼,那男孩看见了,想说点什么又没好意思开口。小情侣吵架呢,她心里想,但是关自己什么事呢,她还莫名其妙地瞪了人家一眼。上了车,她坐在窗子边往外看。
恍惚中,她看见李一平更年轻的身影,跟在一个哭泣的姑娘身后,亦步亦趋。她看见他蹲在那女孩身边,什么也不说,只是看着她哭。那女孩哭啊哭啊,他递了一张纸巾给她,那女孩接着了,继续哭,不知道哭了多久,车站里又有人要进站台了,她才起身往人群走来的方向走去。李一平跟在后面,远远的,仍旧是什么也没有说。
一直跟着那个哭得昏天暗地的女孩到了火车站外面,他凑到跟前说:“同学,我家就是这里的,你要去哪儿我送你去吧,你别哭了。”
他自顾自地说:“你看,我不是坏人,这是我的学生证,我是理工大的学生。”他一边说一边把学生证从包里掏出来,递到她眼睛下面。
那个女孩还是在哭。
她眼睛酸酸的。那是多久之前的事了?
那时候她正沉浸在一场注定没有结果的爱情中,那个人对她说:“这是最后一次见面了,以后再也别见面了。”她上了火车,又跳下来,想在那个她再也不能来的城市里多留几分钟。她就在那里哭,一直哭一直哭,李一平就是那个时候出现的,他一直跟在她后面,直到她跟他说话。
在候车室里,他请她吃了一份盒饭。不知道还说了些什么,终于她笑了。当时并没有交换联系方式,出于礼貌,她说了自己的名字和学校。
毕业之后的一天,她登陆校友网,看见他给她留的信息。那时候李一平已留在学校所在的城市,而她远隔七百公里之外。但是不知怎么的,两个人渐渐地走在了一起。
车子快开的时候,一个人满头大汗地跑了进来,坐在了她对面的座位上。她抬眼一看,发现这个人就是跟在那哭泣小姑娘后面的男孩。
那男孩一看是她,就连忙解释说,我不认识那个女孩。她牵动了嘴角,但是没有说什么话。她还是看着窗外。
男孩尴尬地擦着汗,她看见他映在窗玻璃上的脸,幼稚而诚实,真的很像李一平从前的模样。
窗外一片昏暗,像是大雨要来的样子。过了一会儿,她轻轻地问:“那个女孩怎么了?”
他有点受宠若惊地说:“我,我在站台上看见她哭得很伤心——我去站台送一个朋友——她上了火车,又下来了,一直坐在站台边上哭。火车开了,她还在哭,我就问问她怎么了,她什么话也不说,坐在那里哭了快半个小时。后来,后来她站起来要走,我怕,怕她出什么事,就跟在后面看看……”
他说得着急,有点磕磕巴巴,语无伦次。她看着他。他接着说:“我跟她说,我不是坏人,你要去什么地方我送你去吧,反正我的火车还没开。我怕她不相信,就把学生证掏出来递给她,还给她瞧我的挎包。你瞧,”说着他把他的挎包拿到台桌上给她看,“我是理工大学的。”她轻轻地笑了。
男孩也笑了。他说:“我倒不是想英雄救美,只是觉得她哭得很伤心,万一遇到什么坏人就遭了,反正我离学校近,这趟车坐不成,就坐下趟呗。”
她看着窗外,大雨已经下起来了,豆大的雨点打在窗玻璃上,“啪啪”地像是什么东西敲着她的心。他们都没有再说话,那男孩到了站,跟她说再见,她微笑地跟他挥挥手,但是她脑海里只想着那个哭泣的女孩。后来呢,后来怎么样了?她竟忘了问他。
窗外的雨越来越大了,天黑得厉害,车厢里的灯都亮了。她看着窗外大雨中模糊的影子。这里是一片山,她记得,有一次春天的时候坐白班车,看见山上到处都是开满花朵的玉兰树,那硕大的没有叶子的花树,将初春的天空衬得一片明媚,就像爱情最初洁白的样子。她忽然矫情地想到这个比喻。但是后来呢,那些花朵,叫风一吹就落了,一点儿风雨也不能经历,只一小阵儿初春的小雨,那花朵就黄恹恹的,耷拉着,树下说话的声音都会将它们震落。
雨是阵雨,渐渐地就止住了,风将天空的黑云撕开一大块,外面瞬时亮了起来。
可是那个在火车站独自哭泣的女孩呢,她怎么样了?
她不知道为什么叫她在这个时候碰见这样一件事。她觉得那个男孩真是个好小伙,有难得的善良。但是,也许以后他会令自己的女朋友在陌生的地方,为他们的感情而哭泣,尽管他善良依旧。一个善良的人在爱情中也会伤害太多的人。
火车慢吞吞地经过一个叫凉风镇的小站,站台上人很少,一个穿白色连衣裙的姑娘依偎在一个男孩怀里,不停地晃着脑袋。刻着站名的石碑边,一株合欢树正吐着淡红的花蕊,风轻轻地吹着。
她不忍看下去。她想起那些年轻的时光,他们在火车的另一头分别的时候,那些留恋,那些不舍,那些眼泪和真挚的情意……那是谁也不能否认的啊。她的眼泪不由地掉了下来。
最近她总是爱哭,一个人的时候,看电视、听歌、看见一朵花从树上落下来,甚至一阵风吹过,她内心一动,眼泪就随之落了下来。但是她从来不让李一平看见。叫他看见了不好,他一定要问问为什么。但是为什么呢?
她一个人坐在窗前,觉得这趟火车实在太漫长了,怎么走了这么久,叫她有这么多时间来回想曾经发生的事情。
但是此刻她没有想他,倒是想起了一个叫冯德伦的演员。确切地说,是想起一部电影。在电影里,他演一个著名的诗人,他黑白分明的眼睛里闪着某种叫人迷恋的天真,他的声音、他的神态简直叫人无法拒绝,他爱的人是莫文蔚,可是后来,她唱《他不爱我》的时候,他正牵着别人的手,诉说崭新的情爱。终究还是没有走到最后。
也许真的没有人能一起走到最后,死亡会让不管是相爱的还是仇恨的人们彻底分离,那时候,每个人都要独自面对最不能拒绝最不能逃避的孤独。但是,人们竟然情愿是死亡让人最后孤独,也许,在潜意识里,只是想,没有人变心,没有人背叛,我们还继续相爱着,只是,亲爱的人啊,我们都无法阻挡死亡的来临。
火车进入了隧道,耳边一阵轰鸣,她本能地堵住了耳朵。一瞬间,火车又呼啸着携裹着不知名的热情闪出了隧道,带着从来没有这么锋利的风声,用从来没有这么飞快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