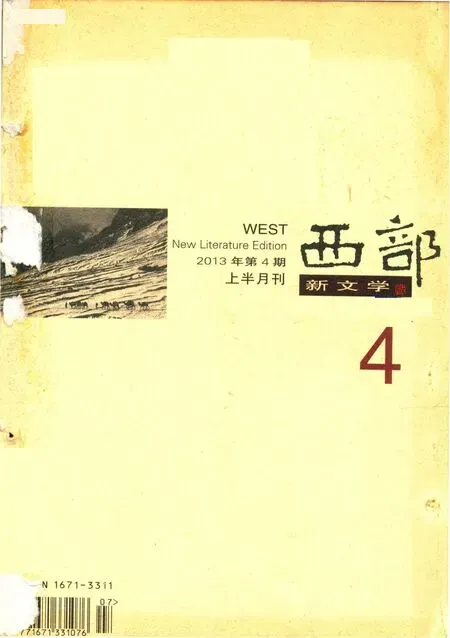怀念与致敬
陈漠
诗人张侠先生离开我们已七年了。七年,恍若一梦啊!
总觉得,张侠一直没有离开我们。我经常可以梦到他。读他的诗歌或散文的时候,仿佛他就在我们身旁,在同我们说话,与我们一起探讨文学或人生。每次坐车去昌吉的时候,我都觉得马上就可以见到他了。他就在这个城市里,在某幢住宅楼里,只要站在楼下的马路上大声喊他的名字,他就会下楼和我们见面。要不了多久,他就会从延安路或北京路的某个巷道中走出来,依然那么谦和憨厚地冲我们笑一笑,建议我们一起到他家或陈友胜家去喝酒吃马肉。只是——我们很久没有聚会了。因为,他在世时,我们也经常是过了好久才见一次面的。
是的,张侠兄一直都和我们在一起!
也许他出了趟远门,办完事,现在又回来了!我们又可以把酒言欢,共叙兄弟情谊了。
那么,没有张侠的时光是如何流逝的?这七年里,我们都做了些什么?七年前和七年后,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人都有哪些不同?在另一个世界里,张侠先生过得好吗?
也许,这是一些难以追问的问题。唯一可以诉说的,就是这七年里我们对逝者不尽的追忆与尊敬。
张侠,祖籍山东巨野,笔名西岛,网名画柳野鹤。一生共出版四部诗集,分别是《神箭》、《飞翔的叶子》、《淡蓝的诱惑》和 《和生命对视》。生前担任新疆昌吉州作家协会副主席、昌吉州文联创研室主任,2006年8月30日不幸因病去世,享年五十四岁。
尽管他出版的诗集均署本名张侠,但在文坛上,西岛这个名字远比其他的名字响亮。很多时候,人们并不知道张侠和画柳野鹤,只知道新疆诗人西岛。这个笔名充分昭示诗人充沛的生命激情和巨大的创作雄心,体现了他无可更改的文学视线和执著的浪漫主义情怀。同时,也彰显了他的文学理想、才华与个性:岛——西岛——西部文学之岛!
有媒体约我写一段介绍西岛的文字,我是这样写的:“西岛是一个悲情的理想主义者,一个用纸和笔、用诗歌、用苦难的人生和坚强的个性,与生命对视终生的人。也许,他终其一生也没有赢得梦想和期待中的荣光,但他不懈的诗歌追求表明了人类应有的生命境界和精神向度。”
事实上,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以及90年代初期,张侠都不遗余力地进行着西部现代诗歌的探索与试验。他同其他诗人一起创办《博格达诗报》,同时举办 “西部现代诗歌大展”,成为当时中国诗歌界最活跃的诗群之一。
那时候,我们共同生活在新疆昌吉市。
昌吉市当时的诗歌繁荣景象,是今天的很多人难以想象的。也许是距首府乌鲁木齐市较近的缘故,也许因为当地文化底蕴深厚,民风淳良,人心闲逸,因此,昌吉市的诗歌创作呈井喷状发展。几万人口的小城,诗人和诗歌爱好者达数百人。一位外地诗人的到来,就可以成为全城文化人的节日,诗歌写作者蜂拥而至。诗歌笔会、诗歌朗诵会、诗歌讲座此起彼伏,以诗歌的名义聚餐、饮酒成为极其寻常的生活方式。仿佛每棵小树和每块地砖都充满了诗意。诗歌的光芒覆盖全城,覆盖每个人的生活细节。小城完全变成了诗城。
直到今天,除张侠外,我随口就能叫出名字的昌吉作家诗人就有二三十位:陈友胜、钱世林、邱华栋、白梦、徐庄、姚金海、王新德、樊荣、江涛、李明、刘河山、周琳娜、陈亚洲、孟颖、马玉梅、张永和、毛眉……那真是一个诗歌的时代呀,是昌吉历史上辉煌灿烂的时期。作家、诗人群星闪耀,好作品层出不穷。即使是二十多年以后的现在,他们中的很多人仍活跃在昌吉、新疆乃至中国文坛。
张侠是其中的佼佼者,曾被称为昌吉诗歌界“三剑客”之一。他以自己持续的诗歌探索与表达,赢得了人们的广泛尊重。
张侠的诗歌创作中,有两部代表性的作品必须关注,即《飞翔的叶子》和《和生命对视》。前者出版于1995年5月,后者出版于十年后的2005年10月,是他一生中的最后一本书,也是他所有诗作中价值最高的作品。该书出版十个月后,他离开了阳世。
对张侠来说,1995年是个特殊的年份,是人生和写作的分水岭。当年5月出版了其重要诗集《飞翔的叶子》后,11月他即患上了哮喘病,几度因呼吸困难而险些丧命。
诗人自己也认识到了这一年对他的可怕影响。他说:“1995年11月,我触摸了死神的手指。死神的手冰冷而滑腻。我们互相对视,死神的背后是黑暗的深渊。我知道,只要我向前一步,就会永远消失在黑暗里。”
疾病使他变得深沉和敏感,也擦亮了他的思想。他开始深度思索人生的意义与方向,思索生与死的现实挑战及美学价值,思索尘世间的爱与温暖等普遍意义上的问题。
他住进了医院。他说:“病榻上,我像一部废弃的机器,每一个部件都已锈蚀。此刻,等待修理是我唯一的选择。窗外的天空就像一块肮脏的抹布,我看不到一只鸟的影子……我的空间落满药品和诗歌的尸体。我和死神相持很久,都无法将对方击倒。这是我生命中最强硬的对手。我们已对峙了十年,彼此成为对方生命的一部分。死神让我不仅感受到生命的脆弱,也让我领悟到生命的宝贵和意义。”
十年的抗病史,加深了他对生活的理解与体悟,也加强了他对人生的体察与发现。
有一年春节,我们去他家拜年时,他兴致勃勃地讲起芦荟之妙。他领着我们到阳台一看,那里上上下下种满了生机旺盛的芦荟。他大讲这种肉质肥厚的常绿植物的通经、健胃功效,建议大家都多种多吃。同时,他还说自己学会打太极拳了,并承诺要找机会打一套绝佳的陈氏太极拳让大家看。
患哮喘病后,他再也不像往日那样狂饮豪喝了。一次,在很节制地喝了几杯“伊力老窖”后,他突然动情地说:“你们都记住,只有当你躺在医院的病床上的时候,才会发现,所有对你海誓山盟的女人都不见了,全世界只有一个女人仍对你好——这个人就是你的老婆。你老婆会在最困难的时候陪你的。这个妹妹那个妹妹——全是假的!”我们问他,《那花》一诗中,“我们在一条很短的路上/重复地行走”,除了广阔深远的人生意义外,是否还有色情的寓意?他嘿嘿嘿地憨笑着,说:“你们自己想吧!想到啥就是啥。”
还有一次,张侠愤愤不平地抱怨说,由于遗传的原因,他们家族的男人全部短命。他父亲活五十三岁就走了。他这一辈子最大的理想是要活过父亲。结果,他赢了——活到了五十四岁!
去世前不久,张侠半开玩笑地问女儿张雅茹和张雅菲:“我走了以后,你们准备把我的骨灰埋在哪里?”
雅茹笑着说:“爸,我把你埋在客厅的花盆里——天天看着你,给你浇水!”
诗人想了一下,摇头说:“不行,骨灰太脏了,不能埋在家里。”他看着窗外的花池说,“埋在院子里的大树下不错,还能增加树的营养……”
最终,他带着女儿到昌吉市西郊选了一块墓地。辞世后,女儿们把他埋到了他自己挑选的地方。
显然,经过生与死的持续对视,他对生死问题平和了,淡然了,可以轻松面对了。
诗人在最后一篇总结自己创作历程的文章中说:“1995年后,是我由青年步向中年的交汇口。这是我生命过程中的一次革命。这场革命是极端痛苦的,生理和心理的转折几乎将我置于绝境。我本能的反应是恐惧、烦躁、抗争。我突然发现,身下的土地正在塌陷……这场我抗击了十年的疾病,改变了我的人生,也改变了我对诗歌的理解。”
张侠尤其佩服诗人沈苇对他诗歌的阅读和洞悉的目光。沈苇在《和生命对视》的序言中说:“在早期的诗作中,我看到了一个忧心忡忡的张侠。诗中常流露出个人化的愤懑情绪。由于缺乏向着普遍性的提升,愤懑没有转向为一种扎实的尖锐性,而成为一阵阵寒意的暧昧和闪烁……进入21世纪的这几年,张侠的诗风有了一定的改变。譬如情绪的克制,语言的加倍节约,还有叙事与场景的出现增加了诗的可感性和真实性……”
近期,我仔细阅读了张侠的所有诗歌作品和相关评论文章。这种重读与回望是有意义的,也是必需的。这里有怀念与敬意,更有对逝者生命与情感质量的再度仰望和发现。
有一阵子,我觉得自己正在同诗人交谈。他的每一行诗,都是兄长对兄弟的崭新叮嘱与安慰。
我格外喜爱诗人的最后一部诗集《和生命对视》。这本诗集的前半部分诗作明显好于后一部分。这部作品中,诗人的诗风更加质朴、简洁和流畅,诗意、哲思与人生感悟熔于一炉,从而使其诗歌创作水平达到了应有的高度。
2003年后,张侠出任新疆门户网站——新丝路“丝路文苑”栏目总版主。除在网上发表个人作品外,他还积极扶持文学新人,广泛组织参与新疆各项网络文学活动,努力倡导成立新疆网络作家协会。
由于他的骤然离世,新疆网络作家协会成立事宜就此搁置,直到今天仍无人问津。这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悲哀的事情。与此同时,新疆网络文学创作活动也因张侠的离世而遭受沉重打击。
张侠任“丝路文苑”栏目总版主那几年,我是新丝路网站的艺术顾问和文化、新闻频道的主编。我俩同新丝路网站年轻优秀的总经理杨戈先生商定,由张侠先生编辑一部《新疆网络文学作品选》,准备出版。岂料,书稿刚编好,张侠就走了。
更为不幸的是,就在张侠离世四年后的2010年10月8日,杨戈先生在攀登青海省境内海拔五千六百米的玉珠峰时,因高山脑水肿也不幸遇难,年仅四十六岁。
现在,《新疆网络文学作品选》的书稿落在我一个人手里,沉重又非同一般。每次收拾房子时,我都会打开书稿,翻一翻,读一读。我在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找个适当的机会出版此书,以了却两位兄长的遗愿。
最后一次见张侠的时间是他离世前二十多天的2006年8月7日。当时,我们共同参加了奇台县古城酒厂组织的作家笔会。该活动正是由张侠等人倡导举办的。我们参观酒厂,并到江布拉克景区刀条岭的巨大帐篷里饮酒居住。半夜,一场倾盆大雨把帐篷和整个刀条岭都浇湿了。天未亮,我和张侠兄就乘坐一辆小车下山。我们赶到乌鲁木齐南湖广场附近的新丝路网站参加座谈会。会后,我回单位上班,他回昌吉。自此,我们再也没机会说话了。
2007年1月31日,新疆作家协会、昌吉州文联、新丝路网站共同在乌鲁木齐市的新疆大酒店举办新丝路新年诗歌朗诵会,隆重纪念诗人张侠。很多作家、诗人、网友以及张侠的亲人们参加了朗诵会。新疆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著名作家董立勃把各族作家捐助的一万多元钱,捐赠给了张侠的亲人。
这个朗诵会,既是对张侠的纪念,也是向诗人致敬。朗诵会让每一位作家、诗人们都深感欣慰和安慰。
七年了,唯愿张侠兄在另一个世界里安详。愿生者一路花开,平安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