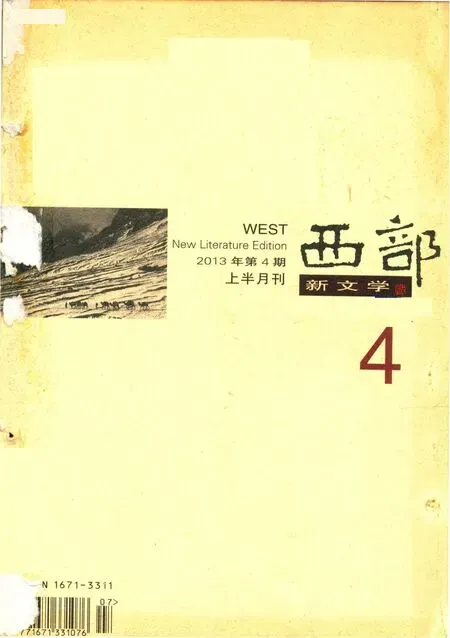和生命对视
张侠
下午五点在旧书摊上
这时是下午5点06分,我在一条街上毫无目的地行走。喧哗的街市,遮蔽在物质的阴影里,到处都是没有表情的面孔,很像一幅陈年的旧画。
我的目光在大楼的缝隙里毫无目的地翻找,一束阳光落在拥挤的街道上,形形色色的鞋子从它身上踩过,大大小小的车辆从它身上碾过,它依然灿烂在街心。也许是它的存在,反衬出更多的污秽。
在一个旧书摊上,我沉没在发黄的岁月里,想和孔丘同志聊聊文人的自尊。我的鲁国老乡,依然靠干肉生活,一件遍是污渍的长袍,裹紧疯长的思想。老孔同志在多国的风尘里奔走,总想弄套官服穿穿,再体验一回杀少正卯的快感。老爷子最终没能如愿,还得在乡村的屋檐下,用思想换取干肉。
得志的文人又能如何?商鞅也曾威风一时,砸了多少人的饭碗,最终叫人家五马分尸;司马迁更惨,让人家割了卵子,弄得连男人都做不成。说到底还是庄子聪明,压根就不和权贵搭边,落得清闲自在。纵观古今,中国知识分子天生贱骨,读几本破书,就以为可以拯救天下,为一展抱负,不惜奴颜婢膝,巴结权贵,一旦碰得头破血流就灰心丧气,把一腔大志泡进酒杯,以名士自居。
反观自己,又何尝不是。本是一介武夫,偏要跻身知识分子堆里,想给自家祖坟添几分书香。我查过族谱,我们老张家三十代内都是农夫,就我曾祖念过几年私塾,算是我们家族里学历最高的,按今天的知识分子标准,顶多算一个摘帽文盲。在我这个年纪以上的,我算是家族第一个可以称为知识分子的人(有知识分子补贴作证)。
这个知识分子头衔除了每月给我带来十二块五毛的经济实惠,还让我活得比一般人体面,我应该知足了。可是它给我带来的痛苦也让我无法忍受,这种痛苦主要来自心灵,知识让我对社会对人生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对这个社会的种种虚伪和欺骗看得过于清楚,而自己对一个失去公平的社会又无能为力。我常常看到我被自己的影子击倒,口吐鲜血,胸前的伤口绽开成玫瑰。我总是看到一排牙齿,当我发现潜伏其后的舌,就已中箭。
我已习惯在黑夜行走,我只辨认路口,而无须辨认面孔。我知道自己原本就是一只蝙蝠,投靠太阳是我最大的失误,因此而失去会飞的翅膀。我将自己置于刑架之上,让炼狱之火焚烧。我听见良知痛苦的嘶鸣和灵魂的抽泣。
我站在这一堆书之间,突然发现自己变成一条软体小虫,似蚕非蚕。我听见有人叫我书虫,我觉得很委屈。我拼命地啃书,想使自己强壮起来。没有人注意到我的破坏力,我在他们眼中始终是一条虫。
在夜晚的街道行走
我从十几岁就在乌市街道上行走,但对这个城市,我总是爱不起来。有个朋友说,主要是这个城市没有你的情人。的确,我的爱情最初发生在它西边的那个城市,直到今天我还认为那是新疆最美的城市,那个城市的一草一木都让我感到亲切。而眼下的这个城市,带给我的只是嘈杂和烦恼。八十年代前,这里更像一个煤矿,到处灰不拉几,就连鸟都像是刚从烟囱里爬出来的。这些年,乌市虽然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仍然对它爱不起来。
昨晚,从“海德”走出,我让老李把车开回去,自个在街上毫无目的地走着。晚风顺着大街吹来,扑到脸上,挺爽的。新疆的城市就这点好,即便最炎热的日子,到了晚上也像秋天一样凉爽。我突然想起一个喜欢黑夜的小姑娘,也许是她这种黑夜性格,让我记住了她。风高月黑,花前月下,同样是夜晚,前者是强盗的天地,而后者却是情人的梦境。很长一段时间,我被一种黑夜意识折磨着,我认为,我从一出生,就背负着沉重的黑夜,欲望和现实之间总是无法平衡,无休止的欲望,就像一只无法抗拒的巨手,将我推向无边的深渊,而残酷的现实总是将我的欲望一次次毁灭,于是,我被生活折磨得伤痕累累。我便沉没在痛苦的黑夜之中。
我在黑夜里独行,我喜欢上了蝙蝠,我觉得它是这个世界唯一可以沟通的生命。蝙蝠的形象充满了我的诗句:痛苦如哀鸿的羽毛/从自由的天空纷纷跌落/思想的鳞片化成高昂的帆影/向着没有遮拦的宇宙出征。有一次,我患了严重的支气管炎,差点儿要了老命,一个战友特意捉了一只蝙蝠,说是能治我的病,一定叫我吃了它。我望着罐头瓶里的蝙蝠,突然觉得那就是我自己,我抱起那瓶子,跪在病床上,泪流满面地乞求我的家人把它放掉。所有的人都感到惊奇,大家以为我发烧烧得神经出了毛病,谁也不肯动。那时我已发了四天高烧,浑身一点儿力气也没有,我见他们无动于衷,不知哪来的力气,我竟从病床上爬下来,抱起瓶子就往外跑。手腕上的吊针猛地脱落,鲜血从针孔里流出来。大家赶紧把我按住,答应一定把蝙蝠放掉。至今谁也不明白,我为什么要保护那只蝙蝠。说也怪,那只蝙蝠一连几天在我的窗前飞,有时它飞得很低,好像怕我看不到似的。大家都觉得奇怪。其实,任何动物都有灵性,尤其这种来自黑夜的动物。
我想,那个喜欢黑夜的女孩,一定有她的道理。这个世界丑陋的东西太多,黑夜可以掩去许多我们不愿看到的东西。夜晚的城市,烦人的喧嚣退去,喜欢在太阳下表演的人们像鸟一样回到那些楼型的树林。我的头顶是智慧的星星,一群苏醒的灵魂。我沿着大街走着,路灯在我的前方列队,此时,我想如果蓦然回首,那人会在哪里?
和父亲的灵魂对话
我打开稿纸,想走近诗歌。窗外是一个被假象遮掩的城市,一些弯曲的脊梁在汽车的夹缝里行走,一些人微笑,一些人痛苦。我的眼前一片苍白,我突然怀念起父亲粗野的呵斥和一只布鞋击打屁股的温暖。
我的父亲是一个让我敬重而又很难理解的人,他十八岁的时候就在东北的密林里和小日本打仗。父亲最初是一个伐木工人,他以强悍的体魄和胆气受到工友的拥戴,成为他们的老大,林场主让他做了把头(可能相当于现在的工头)。这个职务在“文化大革命”中给他带来了致命的麻烦。
后来林场被日本人抢占,日本人的残暴惹怒了血气方刚的父亲,他和几个工友在老林子里弄死了一个日本伍长,之后连夜逃到一个叫烟筒山的地方,准备往关内走。父亲在那里遇到一支抗日队伍,为首的叫韩义顺。其实他们原是占山为王的“胡子”,说白了就是土匪,东北沦陷后,不少有血气的土匪将枪口对准了日本人,也有不少借抗日的名义扩充实力。父亲说老韩最初也是想借机扩充地盘,后来他在乡下的妹妹被日本人糟践了,含辱而死,老韩才真恨起日本人。
老韩得知父亲杀过日本人,对父亲特别器重,他们很快成为知己,并委任父亲为二当家。“文化大革命”中父亲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就是缘于这段所谓当土匪的经历。
这是一支仅有三十多人的队伍,一共有十八支步枪,四把驳壳枪,其余的是大刀片和红缨枪。这点儿装备用于打家劫舍足可以雄霸一方,可是要打日本就显得势单力薄。在父亲的策划下,他们袭击了父亲工作过的那个林场,那是这支队伍最辉煌的一次胜利。他们打死了六个日本人,缴获了一挺轻机枪和一些枪支弹药。这次成功的袭击,不但队伍士气大振,也使他们的名气大增,附近的几小股土匪和一些走投无路的农民要求加入,队伍一下子扩充到近百人。他们起了个番号叫“长白山抗日救国旅”,老韩任司令,父亲任副司令兼参谋长。
不久,日本人就派兵围剿他们,父亲建议先躲起来,再伺机行动。老韩坚持要和日本人拼一次,他说上次袭击林场,偷偷摸摸不过瘾,要和日本人面对面地干一次。那次行动,他们差一点儿全军覆没,有六十七个兄弟永远躺在了那个山头,老韩也死在那次行动中。父亲凭着在森林的生活经验,带着十几个兄弟逃出日本人的魔爪。父亲后来回忆说,那简直是场噩梦,他们连日本人的影子还没看到,许多兄弟就死在日本人的小钢炮下,老韩被一块弹片击穿了胸部,他临死时只骂了一句:我操你娘小日本!老韩死后眼睛一直睁着,他死不瞑目。
父亲后来领着他的残部参加了东北抗日义勇军,参加了大大小小上百次战斗。他没有死在日本人的枪口下,却死在“文化大革命”的批斗会上。他死后,身上没有党旗,他是带着一顶“匪首”的帽子离开人世的。我记得,那是1971年初,正好大年初四,患有严重肺心病的父亲已被没完没了的批斗折磨得奄奄一息,我哥哥突然又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关进了监狱。起初,我们都瞒着父亲,可是那些人却押着哥哥在我家门口喊口号。父亲在一片激昂的口号声中含恨而去,他死时和老韩一样,眼睛也一直睁着。那双眼睛里有一种我永远也读不懂的东西,它一直在我灵魂里,让我无法忘记。
父亲没给我留下任何遗产。我们兄妹六人谁也没有从他那里得到过福荫。我十五岁就远离故土,浪迹天涯。可我们都敬爱父亲,父亲在我们心目中的形象很伟大。不久前,有一部叫《激情燃烧的岁月》的电视剧,妹妹说那个石光荣有点儿像父亲,真的,那性格、那品质,甚至那体形都像。我想,石光荣也许代表了那一代人。
我一直想为父亲写部传记,但是,我无法对他这代人做出一种更合乎人性的评价。尤其在价值观发生了重大变化的今天,我们将怎样评价那代人的生命价值。我一直在苦苦思考,想找到一种非表象的、概念化的理解。我不能简单地将石光荣身上那些愚昧的东西作为民族精神,作为优秀品质去歌颂,去发扬。我必须从他们的精神生活中滤去那些被异化的东西。
我和父亲进行过无数次灵魂对话,我发现,我和父亲之间有一条很难逾越的鸿沟。有时我想,也许我的灵魂已被污染,商业社会的价值观念已经潜入我的血液。是的,我们很难摆脱一个时代的烙印。我和父亲属于两代人,就像我和我的女儿。但是,一个民族,必然有一种共性的东西可供延续,那是维系一个民族血缘的链条。那个东西就是我们用几千年的苦难打造出的民族精神,那种精神是无形的,是在我们民族血液里世代流淌的遗传基因。当民族遇到危难,民族利益受到伤害的时候,这种精神就会迸发出排山倒海的力量。
父亲作为一个普通的伐木工,他有一万个理由让自己沉默,他完全可以像大多数人一样选择逆来顺受,可是,他偏偏选择了以生命为代价的保家卫国的道路。父亲对日本侵略者的反抗,完全出于一种本能的民族自尊,就是那种不灭的民族精神激励了他。
去年,我一个非常崇拜赵薇的学生,就因为赵薇日本军旗事件,一怒烧毁了积攒了几年的赵薇的图片和磁碟,从此她对赵薇持非常蔑视的态度。我不想评价这件事的对错,但她让我看到了我们民族气节、民族精神在下一代的延续,让我看到了我们民族未来的希望。还有,这几天的论坛里,人们对于“昭和”一词的敏感和愤慨,都让我感到欣慰。我相信维系我们民族血缘的链条一定会延续下去。
故乡在母亲的皱纹里
上个月,我从北京回到故乡,在妹妹的农家小院里,守着年迈的母亲,和一群鸡为伴,过着和网络隔绝的日子。城市的喧嚣虽已遥远,我却像一个刚卸装的演员,从熟悉的舞台上走下,思维仍留在扮演过的情节里。
黄昏的时刻,偏瘫的母亲坐在屋檐下的竹椅上,暗淡的天空写满她无奈的目光,一只燕子在对面的树上鸣叫。我读着母亲沧桑的面孔,突然感到一种孤独和悲凉。
在返乡的火车上,满脑子都是儿时故乡的影子。儿时的回忆就像一部永远也放不完的旧电影,模糊的,久远的,却是无比亲切温馨的。那些记忆是烙在内心最深处的,你不用经常去触摸,它会永远在那个内心最柔软的角落里,当你最脆弱的时候,它会给你的心灵最平静的抚慰。
刚刚踏上火车,熟悉的乡音就扑面而来,让我感到触手可及的亲切。那会儿,我很久不说的乡音突然自然欢快地蹦出来。有人说乡音是心中最难忘的童谣,即便岁月年久,但是当别人唱起来的时候,你也会很快地回忆起来。
我最先想起的是三爷那片杏林,那是我儿时的“百草园”,给我留下过许多乐趣。我小时候常常一个人躲在那里玩一些在别人看来很古怪的游戏。我最喜欢玩“蚂蚁过桥”,在离蚂蚁窝边一尺远的地方挖一道沟,在沟里尿一泡尿,然后用麦草搭一座桥,让蚂蚁从桥上列队走过。我事先把蚂蚁捉到沟这边,用樟脑球封锁所有的通道,逼着蚂蚁从桥上爬过。当我指挥这些蚂蚁的时候,幻想着这就是我的军队,心里有种拥有权力的快感。
我发现,我立足的所谓故乡,就像个穿西装的农民,现代文明在传统的废墟上蔓延。三爷的杏林像一个久远的故事消失在一条街市中。在一个卡拉OK练歌房里,一群年轻人正用浓重的乡音唱着周杰伦的歌曲。在我的记忆里,乡音里都是高昂的山东梆子,戏文里那些关于秦琼、武松之类的故事,让我从小就有一种做山东人的自豪感。不知怎的,听到用乡音唱出来的流行歌曲,总觉得很别扭。
在我的家乡,黄牛曾是衡量贫富的重要标志,“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是故乡人世代追求的一个梦。我祖上是贫农,从我爷爷那辈就没有过牛。解放以后,据说我们家分过一头小母牛,大概上世纪五十年代就进了生产队的牛棚。在我记事以后,牛棚就成了村里的文化中心,因为那时的人太穷,油灯都点不起,牛棚是公家的,全村最亮的灯在牛棚,牛棚里的灯光吸引了许多不爱早睡的人。人们聚在这里,互相传播村里村外的新闻,讲着那些老掉牙又百听不厌的故事。我最喜欢的是听闲书,就是由一个人读,大家听,内容多是《七侠五义》、《包公案》、《水浒》、《三国》之类。这也许是中国最早的读书会。我应该感谢这种“读书会”,美丽的故事和牛粪味孵化了我的文学梦。
然而,祖祖辈辈陪伴我们的黄牛在我的家乡绝迹了,在一个多月里,我没见过一头黄牛。我问过妹夫,他竟觉得我的问题很可笑。是啊,几乎家家都有拖拉机和农用车,谁还用牛?二牛抬杠式的生产方式作为一个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农机、农药、化肥这些现代科技的产物,使中国农业进入了集约化生产模式,粮食产量几乎增长了六倍。
农业的科技进步使农民远离了饥饿的威胁,伴随而来的环境污染也让我触目惊心,单纯地依靠化肥,不但日益加重农业成本,而且让土地严重退化;过量的使用农药,使农产品的农药残留量严重超标,给人的健康造成严重威胁,作物病虫害非但没有被遏制,反而年年加重。一些城市现代病开始在这里蔓延,就在我呆的一个月里,一个一万多人的镇子,先后六个人患脑溢血和脑梗塞。我妹妹刚过四十,就患了这种病,差点儿丧命。也许苦难和幸福是一对冤家,他们总是形影不离。
离开家的时候,我还是个不知道愁滋味的少年,而今将到知天命之年,可是山东人那种独有的性格印记,仍在我血液里流淌,就连乡音也无法彻底改变,即便普通话说得如何标准,可时不时地还是能流露出山东人的音质,尤其是心情激动的时候,那乡音更浓。无论如何地掩饰深藏自己,山东人那种疾恶如仇的火爆总会在最后的时刻暴露。
当我回到故乡的怀抱,却发现我已经成了一个外人,我很难再融入他们的文化中,几乎有九成的人用陌生的眼光看我。一个和我同窗了十年的女同学,一个小时都没认出我。那个当年我曾暗恋过的柔情似水的小女孩,如今已是珠光宝气的商人妇,一条粗大的金链子,在她的脖子上闪闪发光,当年的那种感觉再也无法找到。
夕阳慢慢地落下,那只燕子还在暮色里鸣叫,我感到一种孤单。一抹余晖映在母亲沧桑的脸上,岁月在她的脸上一轮轮展开,我突然感到,我记忆中的那个村庄已收藏在母亲的皱纹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