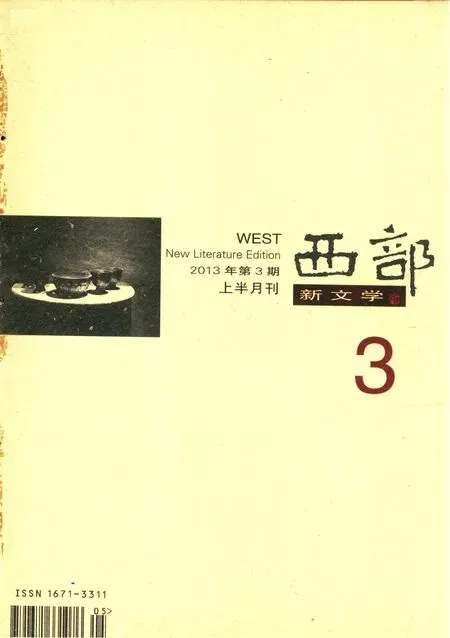我的盗贼生涯(外一篇)
安歌
写《小偷日记》的法国著名作家让·热内,是个职业的小偷,当然他的偷也不是天生的,问他为什么要偷,他回答说“最简单的动机就是要吃饭”。我想大多数人偷东西,都是从吃开始的。
少时的我贪食,也挑食。记得在尘土里跳了一下午方格子之后,我又饿又累地跑回家,打开碗柜,本色略黄的柜层上,一只白的瓷碟里卧着的几个圆圆的玉米面窝头,寂寂地黄着,一看之下,饿意也全消了。零食也只有定量配给的硬糖块,却被妈妈装进布袋吊在高高的墙上那枚孤零零的铁钉上。在我童年的仰望里,布袋里缤纷的糖果热闹的甜简直就是一面天堂景象。记得有一次妈妈上班,把我和哥哥反锁在房间里,我曾出主意让哥哥站在木凳上偷糖果,被他胆怯地拒绝了。作为家里的老大,哥哥比我更早接受了“服从”这个习惯而巨大的词。后来他向妈妈告发了我,也许是出于更积极主动的服从。我也没太沉湎于被出卖的痛苦里,更多地是心里在抵抗地想,我也没吃上。当然,后来也有吃上的。
奶奶买了一包黑枣,分给我们几粒后就装进那个放米面干菜的木箱里了。想来奶奶就是没有妈妈高明,她以为放进箱子我们看不见的东西就不存在了,哪里像妈妈,把它光明正大高高在上地挂着,意味着这是你根本达不到的高度。放东西的方式其实也显示了一个人的性格,说来话又远了,还是回到黑枣。那是我一生中吃过的最好的东西了,这可能不只在于它的滋味,还在于秘吃的忐忑的快乐;还有打开木箱时,米、干菜、枣混合的扑面而来的隐秘气味、黑枣落入口中时所想的:绝不再偷吃了!那种诀别的心境;以及奶奶最后抖出空空的布口袋时感到的对奶奶的剥夺——那是奶奶每次分给我们几粒枣时脸上蓄满的满足和微笑及这微笑中所蕴含的对自己价值的一点肯定——是这些组成了我的黑枣,我的记忆里最好吃的黑枣。
馋是万恶之源,有时候好奇也是。
很小时候,大概是三四岁吧,还不知道钱是用来做什么的,只感觉它好像很重要。妈妈爸爸有时候会为它争吵,有时候会郑重地商量着什么,然后才能拿出花花绿绿的它来。在那些缺少色彩的时代,我不知道自己是被什么所吸引去偷钱的。也许是想让父母停止争吵,也许只是因为它重要,或者只因为它的色彩。那时的我还太小,还不明白钱是可以换来物质甚或生活的某些幸福的。
家里的抽屉是从来不上锁的,从笨重的红漆木桌的抽屉里偷出几张花花绿绿的钞票,怀着秘密的忐忑和激动,却不知道应该用它做什么,把它放在哪儿。那是人们午睡的时间,单位大院阳光灿烂,白杨树空寂地站在那里,邻居家的院门关着,世界好像和阳光一起停在那儿不动了。小小的我,四处找可以藏刚刚偷得的钱的地方,后来我选择了邻居家的木台级。那个木台级很大,邻居家原来在里面养了几只鸡,后来不知道为什么不养了。在正午的阳光下,因为曾经热闹过,台级便显得格外的寂寞和安全,我把钱小心地塞在里面,就安然回家睡午觉去了。心里一丝忐忑也没有,可能只是感觉好玩,是游戏着的,并没有连带着欲望,有了欲望才会有忐忑吧。
但正如海明威所说,如果你的小说的开头,写到墙上挂着一枝枪,这枝枪一定要在后面打响。用在我偷钱上也是适用的。藏在邻居家木台级里的钱,成了我的一桩心事:如果邻居家突然又想起用它来养鸡怎么办?或者是,如果他们认为里面有一个鸡蛋没有拿,去拿时发现里面的钱又怎么办?虽然不知道钱的正确用途,但知道那是家里重要的东西,不能让别人拿走了,而如果我自己把它拿回来,放回抽屉里,无论如何,感觉好像都不对,但钱一定要回到家里倒是极认真的想法。
偷出去东西固然难,再把它们拿回来有时更难。
我想到的人,自然还是奶奶。或者是因为我爱她,或者是因为她善良到无欺,而善良到无欺往往会成为被欺的对象,虽然当时我并不想欺她。
我先把钱转移到单位土打的围墙缝里:土墙色彩斑斓,把钱卷成细小的一团塞在里面,根本是看不出来的,在我看来,这比起鸡窝来更安全。当我拉着奶奶的手,远远地给她指着那面墙,说看到了一团东西,走近发现是塞在里面的一团钱时,奶奶也丝毫没有怀疑我。许是她认为她孙女的眼睛是雪亮的,在她看来,她孙女的什么都是雪亮的。钱好像是十元一张的,在当时就是大钞了,但我不认识大钞小钞的分别。因为是我发现的,奶奶理所当然地认为应该属于我。也许奶奶是怕三四岁的我根本无法正确使用这钱,也许奶奶也是有着私心的,她用口袋里的小钞说要和我换。我自然是答应而且高兴的,因为这钱变成了奶奶给我的,而不是我偷来的。即使我那么小,也知道,什么东西是让人放心的。
后来妈妈自然发现了钱丢的事情。我记得奶奶拿出了那些钱。我已不记得奶奶是如何解释这一切的,也不记得自己是如何承认这一切的,也不知道妈妈相信不相信奶奶和我的解释——也许那么幼小的我,还没有替大人解释的能力,只知道家里从来不上锁的枣红色的抽屉,自那以后上了锁。
现在想来,这件事带给奶奶的委屈一定是有口难言的。而我能够感到羞愧时,事情已过去多年,这事已无法提起,自然也无法道歉。
写《小偷日记》,几乎当了一辈子小偷,后来成了法国著名作家的让·热内开始偷东西只是因为饥饿。后来,就在他成名的关键时刻,他还是忍不住去偷,那就不是贫困和饥饿可以解释的了。在漫长贫穷和饥饿的岁月里,他充分体验了绝望中的欢愉,禁锢中的解脱,耻辱中的神圣,污垢中的圣洁。他甚至把自己的小偷生涯和征服欧洲的恺撒大帝相提并论:我也横跨了整个欧洲,只是我的办法和他们的赫赫战功相反相成,正在为我谱写一段珍贵的秘史,情节之离奇足以与伟大的征服者相媲美。著名作家萨特和很多法国作家不仅成了他的营救者,还为他的《小偷日记》写了序:他们使我们大吃一惊,也使我们心荡神驰。
这个心荡神驰用得真是好,有待月西厢记里的那句词之妙: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那种隐秘的快乐,是一种心领神会,是看到别人在实现着自己想做但无法做到的事情的一种心荡神驰,是看到自己生命的另一种可能,也是对真诚的敬意,哪怕是邪恶,到了真诚的地步也有其迷人之处。
谁又能否认自己内心的邪恶呢?
小时候偷苹果,倒不完全是因为深知邪恶真诚之类的智慧,那尚属本能,因为馋,也因为小伙伴们都在偷。作为小孩子,如果你一个人不偷,是让人不齿的。那时候,根本不懂得屈原说的什么,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什么境界。好在那时候不懂,有时候不懂一些事情真是很幸福的事情:大家一起醉而不要那个独醒的人又有什么不好呢。
小时候每家都有一块自留地,自留地是要浇水的,所有人家浇水的渠沟都通过单位的果园。我们常常是通过某个小伙伴家的渠沟钻到果园里去的。至今还记得,心惊肉跳地爬上果树,或者把小伙伴从树上扔下来的苹果从浸水的草丛中拣出来,放进束紧腰带的背心里,苹果冰凉的皮面贴着肚皮那种沁凉的感觉。还有时时等着放哨的孩子喊“老汉来了”准备急急逃跑的忐忑。
也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把所有看院子的人都称为“老汉“,不管他年轻、年老,是什么族别。许是偷苹果偷得多了,老汉,就变成了看果园人的专称。
有一次,在“老汉来了”的叫声中,一群孩子鱼贯着逃跑,最前面一个孩子的皮带松开了,边跑苹果边一个一个往下掉。后面的孩子看见了,也从脖颈中掏出苹果一个一个往外扔。等穿过渠沟的小洞,坐在自家的菜院里,深深地喘着气,等着数战利品时,才发现,偷到的苹果所剩无几:是皮带松的孩子没掉完的,还有扔苹果的孩子没扔完的。几个孩子坐在那里,沮丧极了,但现在想起来,那次偷苹果的所剩无几的成果成了记忆里最深的一次。所谓得失寸心,这也算是了吧。
当然也有被老汉抓住的时候。如果是在自己父母的单位,人们都知道偷苹果是孩子都做的事情,被抓也只是骂几句,给家长告一下状,并无什么大痛。记得有一次是到并不很熟的同学家附近的果园偷苹果,被抓了,那个老汉不是一个平善之人,他把我们几个孩子排成一排,罚站,似乎还打了我们,让交出苹果还不算完,还一定要我们报出学校的名字,要通报我们学校。我们自然是死也不肯说——通报学校,这对孩子来说,是最可怕的事情。而平常的我们,并不把偷苹果这事当偷的,仿佛它只是游戏的一部分,而且偷来的苹果比用钱买来的更好吃,或者也是有这游戏的味道在里面。但这次的被抓,却让我们变成了真正的小偷。至今我还记得那次那个老汉终于肯放我们回家去时的深夜,一步一步向家走着,内心的沮丧和夜色一起更深更黑,好多个白天也无法说服我。从此也知道,偷东西本身的难过,和被抓住的难过比起来,根本不算什么。从那以后,偷苹果,就不算一件纯粹快乐的事情了,那里面已有了悲伤。
人说,艺高人胆大,其实胆怯也可以让人胆大的。
单位院子里的梨树是那种又高又直的梨树,并没有长在果园里,但一般孩子也不去偷,因为树太高了,而且周围也没有遮挡。不知为什么,那天平常极胆小的我,竟然敢爬到梨树上去偷梨。紧挨着梨树的也是一面墙,可爬到有梨的地方,地面和那墙看起来就好像高处的深渊。当下面的小伙伴叫“老汉来了”,作为一个小姑娘的我,情急之下,从五六米高的梨树上直接跳到了墙上,竟然没有摔倒,从墙上顺利逃跑了。
梨有没有偷到是记不得了,只记得自己纵身一掷时,那种顿得解脱的心。
以此看来,我是不如让·热内的,他因为生活的困顿,而且想写作,常常宁愿被抓到警察局里去,因为那里起码有饭吃,有相对安定的环境,可以让他好好写字。耻辱,比起这些来说,对他根本不算什么。他也根本不想解脱,倒是当他成了自由人、名作家,在高级公寓里写《小偷日记》时,却感觉到浑身不舒服,感觉到自己要和主流社会同流合污了。正如他自己对记者说的:一旦自由了,我却迷茫了。
但热内毕竟是个真正的天才小偷,一个可以在地狱里发现天堂的人,也可以在天堂发现地狱。虽然在高级公寓里写颠沛流离的《小偷日记》多少证明了萨特所说:世界是荒诞的,人生是痛苦的。
但让·热内所感觉到的世界,是真正的小偷的世界,是“虱子是我们(叫花子)繁荣昌盛的唯一标志,也是我们穷困潦倒的象征”,他还说:“有理由认为,当我们根据我们的现状对这一标志做出正确的评估之时,也就是对我们的现状做出了正确评价的时候。”
比起彻底的热内,我只算个伪小偷,不可能对这一职业的任何现状做出正确的评估,这种不彻底,真是让人心酸。
当然,为不彻底悲哀这事,并不是特指小偷的,平常的人生,大多是不彻底、不真诚的。
曾经爱过一个人,很多事情都忘记了,还清楚地记得他给我讲过,有一次进银行,出门发现单车让人偷了,偷车的贼并没有走远,还可以看见他在椰树下推着单车匆匆地跑。他和银行的保安一起去追,追到一半,他突然停下来了:如果那个小偷被抓住他怎么办呢?
唯这一点体贴的善意,回想起来,感觉就没白白爱他一场。这善,也如英国散文家查尔斯·兰姆所说,我不是因为一个杀人犯改过了就原谅他,当我知道他和我一样喜欢吃羊肉,我就原谅了他。
人不单对善,对恶亦是有着体贴的。卡夫卡在和古斯塔夫的《谈话录》中,一次,他们进了布拉格最长的教堂——雅各布教堂,那里面有一条铁链,上面挂着一只手,这是一根熏黑的、残留着干枯的肌肉和筋的骨头,它在一千四百年前被留在了这里。据古老的编年史和不断更新的口头传说,这件可怕的事情过程大致如此:
雅各布教堂两侧有许多小祭坛,其中一个祭坛上有一尊圣母玛丽亚的木雕像,雕像上挂满一串串金银币。一个退休的雇佣兵看到这笔财富手痒难忍,当他在黑暗和烛光中终于伸出手,想抓住雕像上的金银首饰时,他的手变得僵硬了。这个第一次潜入教堂的窃贼以为圣母玛丽亚紧紧抓住了他,他使出了全身的力气,想把手抽回来,可是一点儿用也没有。第二天早晨,教堂司事发现他筋疲力尽地站在凳子上,脸色苍白,惊恐万状。
祈祷的人群来了,教堂的元老来了,甚至市长也来了。教堂司事和修道士想尽办法想把窃贼的手从圣母玛丽亚雕像手中拽下来,他们也没成功。于是市长叫来了刽子手,他一刀就把窃贼的手砍断了,这时“雕像也松了手”。这个雇佣兵在刑满后,加入方济会当了杂役。
卡夫卡认为圣母的奇迹是一种强直性痉挛:盗贼渴望得到圣母的装饰,被这种欲望所掩盖的宗教感情在他伸出手的那刻,突然被震醒了,而他的宗教感情比他想象的强烈得多,因此他的手僵硬了。——对神圣的渴望,伴随而来的亵渎圣物的羞怯以及人所具有的正义感,这一切是强大的不可战胜的力量。要犯罪,总是要在心灵上先肢解自己。卡夫卡说。他还说,刽子手的那一刀并不像人们认为得那样可怕。相反,惊恐之后肉体的痛苦给他带来的是解脱,灵魂的肢解为刽子手对他的肉体伤害所取代,这样,这个可怜的雇佣兵就从良心的痉挛中解放出来,他可以继续做人了。
古斯塔夫疑惑教堂的故事在今天还会不会再发生。
卡夫卡肯定地说,不会,今天,人们对上帝的思念和对罪孽的惧怕大大地淡薄了,他们会把圣母像整个偷走。——这时僵硬的不再是手臂,而是灵魂。
而偷兰姆的书,却不必去教堂,甚至是有意为之的。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深喜兰姆,这种深爱之后的相遇,甚至可以上升到对上帝的思念的同一套伦理学里去:当时想,如果我能在书店拿到兰姆的书,而不用付钱,仿佛可以证明冥冥之中的一种缘分——人与人是有缘分的,这缘分,有时候近在咫尺也会视而不见,远隔千里也是在的。
去书店也是和L一起去的,但兰姆的书的事情,却没有告诉L。并不是不信任,只是感觉这是我一个人的事情。也买了一大堆书,全部付了钱,唯兰姆的那本,我把它夹在腋下了。许是售货员看我像个斯文人,以为是我自己带来的书,并没有怀疑我。本来交了钱就算完事了。书店的外层是卖画册书法的,当看到高更梵高米勒们的画册,我自然又是移不动步了。拿了几本准备去交钱,把买好的书交L的手里。就在售票员旁边,L翻着书,突然说,咦,你的这本兰姆的《伊利亚特》怎么没有盖交款的章?
当时的我真是心惊肉跳,真正恨死L了。L哪里知道我对这本书的一番情思如同对恋人的一见钟情,是无言相对亦有知,更是仰慕已久的爱,是不肯用钱来得的。奇怪的是,每每心惊肉跳的时候,我却会显得格外镇定自若。只是静静对L说,哦,可能是售票员忘记盖了,我让她补盖。因为买的是一沓书,外面卖画册的售票员并没有多疑。从L手里夺了《伊利亚特》,和几本画册一起去交费处。但我心知,我根本不会为兰姆交钱,而且我坚定地相信,兰姆会支持我的。不仅仅因为他在他的《退休者》开篇引用了奥·基福的诗:“在繁华的伦敦市/我是个小小的职员”。他还说,每每在繁华的伦敦街头,看到车流人走,都会泪流满面。他哪里会肯让我因为惜缘到如此紧张的地步,而不肯给我这个缘呢?
最后书的钱自然没有交,对此我没有丝毫的羞愧,也不是因为这个书店多年来从我这里赚了不少钱。因为L的不解揭发——那种和兰姆心意相通的得意虽然稍稍减弱了些,但心里的暗喜是在的。因为兰姆,因为心里的暗合,因为深爱成为可能。
我也没有和L说这本书最后有没有交钱,因为这是我个人的事情,是我和兰姆的事情。
这是几年前的事情了。这几年没有偷什么东西,也可能是因为没有什么东西值得我偷。想来也是遗憾的事情。
双声——至少你是懂得我的
看我喜欢的女友写的一个帖子,说有段时间,她在BBS上疯狂地找另一个女子的帖子。那个女子的签名是:又是乌鸦的炸酱面,又是乌鸦的炸酱面……是鲁迅先生文章里的一句话。女友看了,当下就笑,也不由感慨而感动:竟然还有人在这样读鲁迅,这样记得鲁迅。然后又看到她跟在一篇文章后面的回帖:好□□□□□□□□□□□□□□烂的帖子。女友说她忍不住“哗”地笑出来。后来有空就去那个BBS,专门看她。她自己有时候觉得有点儿好笑,然后自嘲:幸好这是网络,没有人看得到她成天屁颠屁颠跟在她后面。
那个女子在网络里逛来逛去,也不发什么长篇大论,看到喜欢的就扑上去,看到好玩的就大笑,促狭鬼的那种笑法。有一天,在别人的帖子后面,她忽然写了一句很不相干的话:陌上花开,可缓缓醉矣。
女友下结论说:我渐渐爱上了她。
我知道她说的那种爱,是相知的欢喜,是两个有趣味和品位的女性在交换着自己的花香——没有共同品位的女性也是花,是没有香气的花。而没有香气的花要交换,那就换的不是花香而是花瓣,就可能有碎了的危险。
我也爱我的女友,她问我为什么。我说,我知道你会喜欢那个乌鸦的炸酱面的。——但对她这样公开表示爱别人女子,心里虽不能说特别开心,但也不会是铿锵的愤怒——女人爱女人,是一朵花在找另一朵相悦的花,一种香气在寻找另一种香气;而女人爱男人,就是花在找那个摘下她的人。花与花之间是不可能有什么铿锵和愤怒的。
说到花,便想到亚历山大·罗斯一幅让我过目难忘的水彩画。画的题目是《姐妹》。钴蓝的底色一笔一笔的画得可以看出笔触来,那一对裸体的女子就在这片钴蓝中,不甚清晰的肉粉色的身体,像是刚刚午睡过后,还没有从梦里走出来。一个女子已经坐了起来,另一个还在开放地睡着。她们的身体上、床的周围甚至呼吸的空气里围绕着粉红的、熏黄的花,在花中的她们仿佛是其中最大的花了。这幅画绝对没有同性恋的味道,只让人看到花与花相伴,可以美到绚烂——那一块一块的颜色和落在其上的光,是真的绚烂啊。而如果换一男一女在这幅画里,那就应该是一个人,拥着一束花了。这个亚历山大·罗斯多少是懂得女人的。懂得,那种滋味也是张爱玲和她的女友炎樱坐在咖啡厅里聊天时溢出来的。
胡兰成在《今生今世》里说,张爱玲说她真正哭过两回,其中一回就是炎樱离开香港而没有等她,她跑回寝室,扑倒在床上哭得不能自抑——以为炎樱是弃她而去了。
炎樱在上海的咖啡厅里对她的张爱玲说:“我不大能够想象,如果有一天我发现我的丈夫在吻你,我怎么办——口吐白沫大闹一场呢,还是像那英国人似的非常窘,悄悄躲出去。——还有一点奇怪的,如果我发现我丈夫在吻你,我妒忌的是你而不是他——”
爱玲的态度是:“我总觉得一个男人有充分的理由要吻你。不过原谅归原谅,这到底是不行的。”
炎樱:“当然!堂堂正正走进来说:‘喂,这是不行的!’”
爱玲:“在我们之间可以这样,换了一个别的女人就行不通。发作一场,又做朋友了,人家要说是神经病……”
张爱玲、炎樱彼此喜欢,因为她们可以一起谈日本风景画;可以一起谈埃及的艺术,那样天高地厚的沉默;谈古中国文化的厚道含蓄,一起喜欢这种含蓄的空……那清空的谈里,只是一朵花看着另一朵花的平和。就是有动静,也是轻风过隙的那种动静,是细雨湿衣看不见,更是闲花落地听无声——然而,花并没有真的落地,只是在交换花气——炎樱假想看到自己的丈夫亲了爱玲,虽然会生气,但也离不开。理由也如炎樱所说:现在我同你说话,至少我知道你是懂得的……你还是不要走开罢。
这是相知的女人之间真正的不舍。
虽然张爱玲给胡兰成的信中说,因为懂得,所以慈悲,但我想真正彼此懂得的,倒并不一定是胡兰成。有人说,女人和男人的区别比人和猿猴的区别还要大。退一步说,就算人与猿猴一样了,他们如何彼此懂得?但一般情况,人只会疯狂地爱自己所没有的东西,自己不懂得的东西。这就好象左派其实是爱右派的,要不他们为什么天天找右派来斗争?斗争,也是爱的一种变种,正如英国散文家兰姆在对新来的女佣客气相加时,却时时忆起与前女佣之间种种的怨,得出结论:怨和爱是从一家来的。这与男女之爱相类——性的区别如火焰照亮了爱的面孔,用中国的老话,那叫锦上添花、热火烹油。而女人爱女人,至艳也就是《诗经》里说的桃之夭夭,或者中国民间所说的蜜里调油。——不知为什么后者我感觉一定不好吃。
桃之夭夭——虽然我明白它的意思是桃花开得非常艳丽的样子,但看着,就联想到逃跑:一朵艳红的桃花在逃跑,那点儿艳丽越跑越小,快活地……如果逃跑的是两朵桃花,那就是在黑暗里烁烁着的一对桃花的眼——这可能就是女人之间的爱了。
说到逃跑,不由得想到顾城和那个逃跑的英子,当然还有没有逃掉的雷米。顾城在激流岛上想建的其实是一个女儿国,看着英子和雷米在那里走动,做家务,说话,相爱,他就感觉着好。好,原本也是由“女子”合成的,顾城深喜这点,也是他内里有着女儿的心,仿佛《红楼梦》里的宝玉,只是他没有大观园,此顾城之不幸也。——他不肯让儿子小木耳回到家里生活——小木耳于他,是意料之外的出现,是一个嘲讽——儿子的出现让悲哀变成了泥浆(杨子诗)——他内心的乌托邦。是想他自己在两个女孩子之中,成为另一个“女孩儿”,爱她们,让她们爱他。但他毕竟是一个男人,有着正常的,甚至是强烈的欲望,有时候他深恨自己的欲望,恨到想要自戕的地步。而那两个女子,也并不是因彼此的喜欢而走到一起的,她们在一起的理由却是顾城这个男人——她们爱着的。所以也会有后来的悲剧。说到底,顾城其实不是死于哪个女人,而是死于他自己的乌托邦的毁灭。他不明白《圣经》所言:人是不可以寄寓希望的。而且,他人永远都是他自己的意外,是不可能永远被别人建设的。但毕竟,顾城是一个有梦想就敢于去实现的人,同时,他是深明着女孩子一起相亲相爱的美景的——《倾城之恋》里,柳园和流苏战火纷飞中那一个紧紧的拥抱,张爱玲说,虽然彼此把对方看得透亮透亮,便只是这一个拥抱里的谅解,就能让他们在日常里安稳地过上十年八年。——或者顾城并不需要这个他不接纳的世界的谅解,更不可能接受拥抱了,哪怕你同样来自他所喜爱的女性世界。
虽然张爱玲爱胡兰成爱到发疯,平常斤斤计较的钱也不计较了,分手时给他三百万元。但那种分手是决绝的: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早是已经不喜欢我了……你不要来找我,即或写信来,我亦是不看了。这是男女之爱的大结局之一种。她倒是和炎樱计较着几十元钱,和炎樱在各自回家的车上一路算着车钱:炎樱应当出八十五,我借了她二百元做车钱,下次要记着还她一百一十五元。她们的钱向来是还来还去,很少有清账的时候。
或者正因为这种斤斤计较,才正是合了女人之间的情意,而不清账,就永远会有下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