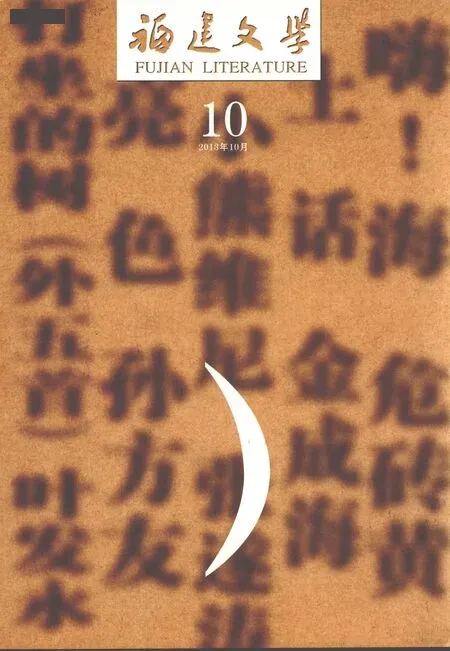我的母亲赵与琰
□修 武
壬辰年农历十一月,我在挂历“十二月十一”所处的位置上做了一个记号。这是一个扎眼的日子,每年的这一天,我都会想起已经走远的母亲,她是空的,但光线中总能没来由地摸到她的身影。去年,因为忙碌,我竟然错过了祭母之日,那一天就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为此,我特别提醒自己及家人,要做好祭母的准备。
母亲出身于书香门第。母亲的祖父姓赵,家住福州三坊七巷衣锦坊三官堂,办过私塾学堂,是很有名气的私塾先生;母亲的父亲也是私塾先生,但他不甘寂寞,后到上海经商去了。母亲是家中的独生女,比父亲小十三岁。我的奶奶是林则徐的外玄孙女,奶奶的舅舅是林则徐的长曾孙,名叫林源渼,字清畲。清末民初年间,先后驻德国、法国参赞,之后升任其他要职。奶奶娘家住福州宫巷25号,她父亲是清朝举人,而祖父家住福州光禄坊,两家人都很熟悉,你来我往,正所谓门当户对,遂结成亲家。我在家排行老二,原名修武。
一九九四年一月二十二日,母亲悄然离世。我不知冥冥之中上苍是否早有安排,这一天是我正式获得通知将被选调省政府办公厅挂职之日,一边是天大的噩耗,一边是突如其来的佳音,我夹在其间,哭泣无声。我的家人和邻居都很清楚,没有母亲赵与琰,就没有我们一家。母亲走后,我的内心世界黯然失色。母亲至今已去世十八年了,去世时年仅六十二岁。十八年来,每逢“清明时节雨纷纷”,便是我断魂时。如今,我的女儿出落得亭亭玉立,也当上了母亲,而我已进入天凉好个秋的生命时节,每当有人提起“母亲”这个字眼,我总思绪万千,那些和母亲有关的人与事历历在目,挥不去,也抹不掉;每当我的家人聚会欢乐时,背地里,我总想起母亲的身影,她孤孤单单,无法享受天伦之乐,同时深感对母亲的养育之恩无以报答,纠结得很。
九十五岁的老舅奶曾告诉我,母亲生我之前差一点就和我一起离开这个世界了。母亲快临产时,为了养家糊口,她起早贪黑,每天乘公交车,停站后再走上一段砂土路,然后搭乘轮船到仓山麻袋厂上班。有一天,大雨滂沱,江上水势凶猛,母亲挺着大大的肚子(离临产只有一星期),那搭乘的渡船左右摇摆,上下起伏,母亲孤身一人,无依无靠,几乎葬身在江河之中。我出生后,家里口粮不多,可为了全家人的生计母亲还坚持上班,母亲没什么奶水,四十五天后,我就断奶了。母亲是家里的顶梁柱,她不仅要养活刚生下来的我,她还要养活家中的另外几口人——曾外祖母、外婆、我的哥哥,还有生病住在家中的表舅,还要救济在狱中的我的父亲,为生计她日夜奔波劳碌着,从未喊疼,从未喊苦,我的母亲,在那样的一个年代里,她像一根火烛,照着那个偌大的家庭避开了黑暗的吞噬。
其时,母亲娘家已家道中落,嫁给父亲后,我们这边的家境也很差,她连寻求帮助的勇气也没有。直到我懂事后,我才时断时续地听到,那时的母亲除了卖力工作,她什么也不去想,她觉得在那样的一个年代,每个家庭都有着自己的苦难,而在我们家,她正好就是那个可以直面苦难的人。我的母亲,整整几年,舍不得为自己买几尺布,剪裁一套衣裳,为了节省路费,她每天要花一个多小时,徒步从城里走到仓山,做完工后,她要花费近三个小时才能回到家里。我的母亲,她每个月只有二十九元九角的薪水,套用她自己的话说,“这钱抓在手里,怎如冬日里的雪米粒,又轻又薄”。我的母亲总会告诉我,要听长辈的话,要好好读书,有了知识,就能改变不幸的命运;要学会做人,多做好事多积德,福分都是养出来的,而不是吐出来的。我的母亲,她说这话时,我还够不着她的腰身,但我知道,她在那样的时刻是幸福的,她的幸福就埋藏在我的身体里,圆鼓鼓的,比那瘦削的日子要来得更有分量。
一直以来,母亲就没有多少说话的时间,她用的更多的是手,是脚,这是那样的年代可以看到的真正意义上的劳动的样子。劳动大于一切,因为只有劳动,只有让身体忙碌起来,母亲才觉得自己还活着。每当我看到母亲慈祥的双眸,我就想说话,可我太小,我还不能明白一个母亲在她的眼神里所能包容的爱意。好多年后,我长高了,长大了,我才看见母亲的眼神开始变得呆滞,一些事物到了她眼里已经不再闪烁。最让我揪心的就是母亲去天堂之前,那是一九九三年底(当时我在三明工作)我回家与她聊家常时,她神态有些恍惚,她指着我说:“三个子女中数你们家最困难了,前些日子在台湾的二姨丈(台师大教授)刚刚寄来一点钱给我看病,我准备拿它把这‘房改房’买下来,以后你们如果回家,或者能调到福州工作,也有个宽敞的地方住,即便是二姨丈、姨妈春节回来时,也有个像模像样的落脚的地方,不至于那么寒酸!”母亲说这些话时,声音很正常,但表情有些异样,原来在我返回三明临别之前,她已悄悄地在我口袋里塞了三佰元钱,我回家换衣服时才发现。妻子指责我怎么能拿走母亲的“救命钱”啊!我不知回答什么,那钱攥在手中,犹如掰不开的锤子。我的妻子开始有些许不祥的预感,虽然她没说,而事实是福州的这一次见面已成了我与母亲永远的诀别!当我领着一家人赶回家中,直奔灵堂前,呼天抢地号啕大哭,俯身用脸紧贴着母亲,而母亲的脸还是微热的,她身体中最后一丝的力量都凝结在了那儿,我知道,这是母亲给我的最后的温暖了。
我六岁前,从没见过我的父亲,母亲也很少说起父亲。有时,我会缠着她,要找父亲,母亲只是轻声说:“健健,你的父亲在外地工作,过段时间他就会回来了。”一九六0年春天,父亲在我6岁那年才回家,他是被“左”倾路线冤枉,而后被送进了监狱。父亲回来后,母亲还是一样的忙,忙里忙外,父亲劝她要休息,母亲却说:“你在监狱受苦了,要休息的是你。”父亲的老部下到我家时说父亲,“他在狱中可以读报纸,拉京胡,过着‘逍遥’的狱中生活”,母亲就笑。那笑,无声无息,只能看见母亲那两排白得雪亮雪亮的牙齿。
有一回,家中好像来了客人,客人走完后,我看到桌子上摆着两瓶鱼肝油、两罐牛奶膏、一瓶钙片。我嚷嚷着想吃,母亲很严肃地说:“孩子,这不是你吃的,是寄给我们家‘亲戚’的。”我感到很奇怪,是什么亲戚呀,母亲对他比对我还好?后来,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曾外祖母才悄悄告诉我,那些我爱吃的东西,是亲戚寄给我父亲的营养补品,我的父亲,他的身体已经很虚弱了……
那个夜晚,我躲在被窝里一个人想着,这个所谓的“亲戚”我并没见过,可我的母亲,她在生活面前,在亲人面前,她那操劳持家的样子,我如何也挥不去、抹不掉,难道母亲就不怕自己的身体垮了吗?这件事直到我上小学二年级才知道,原来,我只看到了母亲粗糙的手、弯曲的背、睡梦里偶尔发出的沉重的呻吟,对于父亲,她所给予的爱是多么真挚!本来,这些补品母亲应该第一个享用,一家人生活的重担全压在她身上,她还有冠心病,可她从未发出只言片语,唯独把劳累、辛苦揽在自己身上,她心里装的总是身边的亲人。
一九八三年,我没有辜负母亲对我的悉心栽培和殷殷期盼,骄傲地坐在了大学教室里聆听老师的授课。那是我工作若干年后,很努力才跨进了大学之门,而且还考上了冷门的作曲专业。我常想:如果没有母亲的含辛茹苦,没有她的血汗哺育,我岂能茁壮成长?岂有我今天美好的日子?
屈指算来,母亲已离开整整十八年了,有很多亲戚前辈们聚在一起还会提到我的母亲,说她善良的、说她本分的、说她坚强的、说她白皙漂亮的、说她端庄贤淑的、说她任劳任怨的、说她勤俭持家的,说母亲的手掌如何有力,说母亲的眼神多么刚毅,说从未见过母亲掉泪,说母亲是世上少有的女人。我都听到了,不同的场合,不同的表情,在他们眼里,我的母亲赵与琰好像仍还活在这个世上,可我摸不到,可我喊不出声,对着空气也好,对着人群也好,但我能感觉得到,我的母亲就在身边,在朝阳中,在落日里,在那数也数不清的光线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