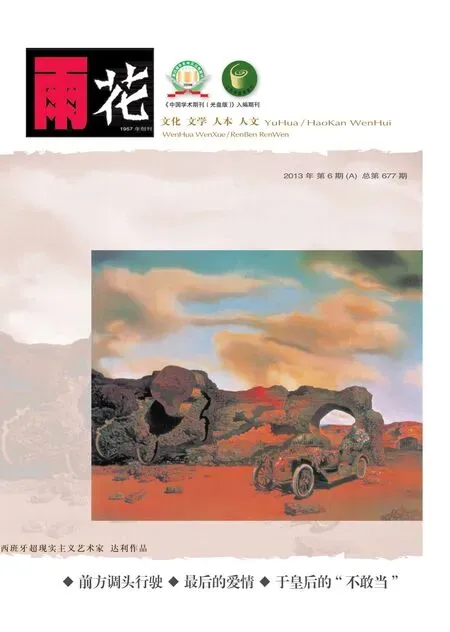青 铜(外一篇)
● 浅 蓝
静穆高阔的博物馆厅,三千年前结着绿锈的青铜器,还那么方是方圆是圆,纹饰清晰,硬骨棱棱,手没有触到,沉甸甸的粗糙和沁凉,全都有了。
好像它只是埋进土里睡了一觉,翻个身,几个千年刷地就划过去了,它就老了。而且比老还老,是古老,就从此饥饿地空着,只能像化石一样被人参观、评点和研究,没人敢用它,没人想用它,也没人舍得把它当普通器皿使用了。被闲置的青铜们多了个神秘的名字叫文物,多了身美丽的绿锈花,就跟人老了会披一头白发一样。其实绿锈是死去的时间碎屑,把时间击败是光荣的,这锈蚀无损它的威风,反添了华彩与持重。
原本郁热的下午,一看到安静的青铜,四周的光线都暗了下来,就有凉意隐隐袭来,就想起权倾朝野、酒林肉宴、阴谋权变与血雨腥风的厮杀。那个时代,青铜是贵族的专属。傲慢地摆在高屋华堂之上,从整套的祭祀礼器到日常生活的各类酒器、食器、乐器,还有兵器,是钟鸣鼎食之家的排场,是攻城略地的工具,也是残酷的刑具。
浑厚凝重的造型,繁多的品类,或简单的,或精美,或狞厉的铭纹,都显出它的尊贵、庄重,还有雄性和权利的符号特质。青铜时代,是段男性雄风震烁天下的历史。虽然那段史书上偶尔有个婉媚的名字出现,也多是做盛世浮华或悲剧变故的点缀,女人轻飘飘的,是男人衣带上的一块玉佩,可以随手弃掷,辗转在那青铜林立的器物中,可以随时碎裂。
我没有兴趣区分什么爵、角、斝、觚,也总是记不住鼎、鬲、簋、盨、豆的各自作用。只是对这冷漠坚硬的金属,对那神秘遥远,痕迹模糊的历史,充满了好奇。这些作为身份象征的器皿,一定也像金银珠玉一样,曾从一个人的手里,流转到另一些人手里吧,或者赐予,或者从血腥的杀戮中获取。面前这只线条流畅的爵,颜色格外深重些,它是否装过传说中的鸩毒,被递至某大臣颤抖的唇边?它是否装满了浇愁的佳酿,又被滴落的眼泪浸染?它是庆过功,也杀过人,它祭过神灵,也参与过阴谋。它的样子就像极了一个身着甲胄仰首问天的将军,一只酒杯,尤其是这样一只结实耐用的青铜杯子,它见识过的往事,肯定并不比一个人的一生少。
那只笨重威严的四足大鼎,上面深刻粗描的图文看起来令人生畏。它究竟是宗庙祭器,饮宴时的调味之皿,还是用来烹人的刑具,没有见到明确的资料说明。这柄青铜剑,花纹精细,剑身平整光亮,该是国王或贵族的佩剑吧。而那堆锈蚀严重,又有明显磨损痕迹的戈矛,不知曾吮吸过多少人的血,斩断过多少人的骨。冷兵器时代的短兵相接,搏杀的场面肯定更加惨烈,用一把会钝的武器去砍杀生命力顽强的人,医学又不发达,那伤者赴死的过程肯定相当痛苦。漫长的历史也是漫长的征战史,哪一寸土地没有被鲜血沃浇呢!
耳边忽然响起了编钟与编磬相互配合的古乐声。悠场的乐音中,朝代飞快更迭,江山频繁易主,整个青铜时代的风云变幻,像茫茫荡荡的黄河水一样,随着铁器时代的到来,终于呼啸流过,成了沧桑历史中一抹暗色,只剩余了断片残简,和这些以殉葬方式保留下来的青铜记忆。
青铜累了,就躺在土地中睡着了。这一梦就是三千年,这中间又发生了多少青铜所不了解的事情呢?
青铜或许不这么认为。它看惯了繁华与没落,知道历史与历史都是相似的,知道贪婪与仇恨的心是相似的,流血与流泪的战争是相似的,所有的胜利与失败也是相似的,还有爱情。无论是铁器时代,还是后来有文字详细记载的文明时代,夹杂在历史中的爱情,悲欢离合,辜负与恩爱无不是相似的。
那么,几千年的时间,也都是天上急驰而过的云烟。事了拂衣去,深藏身和名。醒了的青铜在了悟之后,除了沉默还是沉默。博物馆的蓝色玻璃幕墙在阳光下冷冷地倒下天上疾驰而过的云影,这居住着许多青铜的馆舍,远远望去就像吸纳收藏时间的宝盒。
桐
桐。似一声呼唤。从唇齿间跳出时简洁清亮,大方深情,音节介于“空”与“洞”之间,像回声,内虚外实,如指骨叩击木板的脆响,富于音乐美。字也有颜色和性状的,桐,是绿色,重量偏轻,样子挺拔清俊,年龄大约二十岁多些,儒雅,静定,有文化。
印象中,名字里带“桐”的人不多。翠羽黄衫霍青桐,出自金庸的《书剑恩仇录》。她是位智勇双全的女领袖,美丽孤傲、豪爽英气,和她的妹妹香香公主相比,尽管同样姿容绝世,性格多了硬气,让人敬爱,不敢亲昵。桐,是有男性倾向的字眼。和其外形相近,读音相似的字是“铜”。铜乃硬质金属,青铜曾是几千年前冷兵器时代的兵刃、器皿、社稷之鼎。无论是先有“铜”字,还是先有“桐”,铜都以其强悍的存在状态,令几千年后“桐”的读音里,都格外浸淫了硬的味道。
也有叫“雨桐”的。多见于鸳鸯蝴蝶小说,用这个名字的女子,则是寂寞独守的小家碧玉相,命不会好。
桐适合男人的名字。
叫“桐”的男子,其实有点不平凡的味道。该是明末清初张岱那样的人品。有绝世才,不必有经世运,瘦挺,清高,有气节,一点孤傲,半个隐士,磊磊落落,卓尔超群。
民国时代东北的著名道德家,女子义学的兴办者王凤仪先生,字树桐。虽是农民,天生夙慧,懂得在日常生活中格物致知,崇义向善,终于彻悟人生大道,救度百姓,启人慧命,成就了一番不俗的事业。
就是一座城,因名字里有了个“桐”字,也格外地灵人杰。安徽的文化名城——桐城,从明清至今名士辈出,明代有东林党魁方学渐、哲学家方以智、忠毅公左光斗,清代的“桐城派”乃是当世最大的散文文学流派,其如雷贯耳的早期代表人物戴名世、方苞、刘大槲和姚鼐等皆是桐城人,到了近代则有朱光潜等人。真个是人文勃兴,代有英才。
碧梧栖老凤凰枝。“桐”字的不俗,在于它上面栖着凤凰,树下住着高士,它曾被周成王剪叶封弟,也曾伴有情人窗前听雨。梧桐作为植物又名青桐,树身青碧,挺拔通直,叶茂花荣,仪伟气清,扎根在中国文人审美意象中,是优雅、高洁、爱情、离愁与相思的象征,古典又诗意的植物。梧桐也是“桐”字的音义的主要所指。
桐。轻轻一唤,恍惚一片叶子“铿”然落下。一叶知秋说的就是这桐。此外,油桐和泡桐也称桐树。油桐的果实是著名油料作物,读《子夜歌》,桐花万里路,连朝语不息。我认为指的就是油桐夹道的路途,暮春,落花纷纷似雪,像一条香河铺满道路,浪漫唯美,适合恋人漫步游赏,喁喁私语。
但油桐喜热,属于南方,至今不曾亲见。梧桐因能入诗入画,多了贵族闺阁气,生活于穷土僻壤的我,渴慕已久,近年才得一睹芳容,自小伴我长大的是命贱好养的泡桐树。屋宇内外,村头田陇,到处是它娑婆的身影,贴近生活,与人相亲。过去村人若得到一块新宅基,运来石头圈了院墙,会先在院中种几株桐苗。幼桐也似幼童,嫩生生的喜人。树干碧绿通直,中有空芯,顶上几片又大又软的叶子,布满微细的绒毛,叶柄很脆,常被人随手掰下当扇子把玩,又随手弃掷。种泡桐树为着它是速生乔木,高大多荫,耐旱耐贫,不择地理。
泡桐扎下根后就开枝散叶,日夜生长,数天不见就会高一截,三五年长得一搂粗,伐下就能派用场。泡桐木质细白轻软,纹理美丽,可做椽、檩、门窗、箱柜、床板、桌子等,是盖房子做家具的必用木料。平时遇急缺钱,也可随时伐倒来卖。种桐树,比养牛养羊还要经济与省事得多,栽活后不需要特别照料,沐日月光华,靠天风时雨,假以年月,即可成材。
乡下到处桐阴匝地,村人视之也不甚惜。随意弃置,并不知道它原来和梧桐一样,是可做琴的良木。只是乡间没有懂音律的蔡邕,竟不知有多少可供做琴的奇木被埋没于岁月的尘埃,误了终身。树之遇亦同人之遇,通达或蹇滞,也是一时一运,或一世一命。
桐是速生有用之木,也决定了它不会享百年或千年之寿。世间古木,多是松柏榆槐之类的硬木,与庄子提到的“树无用,不求有为而免遭斤斧”中的树相反,桐树总因才质美而早夭。鞠躬尽瘁,正是桐的高标品格的呈现。
“桐”字也因此,显得音响韵清,风骨凛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