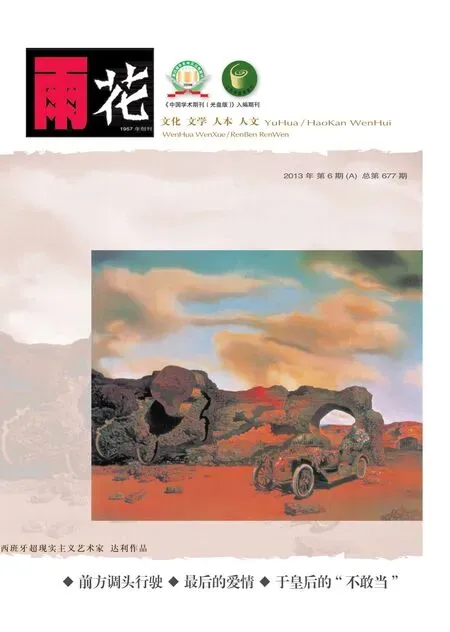城之南,之南
● 刘萌萌
那样的时刻,远行的冲动像一波波海浪,温柔而疼痛地拍打上我单薄的胸腔。从固有的生活中挣脱并消失,是我心底潜藏已久的欲望。
一道立交桥将小城一分两半儿:城南,城北。但“城北”一说罕有提及,当地人多唤“北窖儿”。尤其老辈人,掌纹里盛满秘密的青苔。在他们四面漏风的言语里,小城葆有另一番样貌——缓慢、从容、明净的沟渠里流淌着活泼的水流,土坡上的蒿草遮掩着旧时典故。早年的风声呼啸在耳,寒冬腊月时节。远远有人隔街相呼:“去哪儿啦?”这边扯起嗓门儿喊:“北窖儿。”抬抬袖管,各自走出好远。
现在,“北窖儿”一说似已不大分明。县城的街道区域被重新划分命名,代之以碣阳大街、韩愈大街这类更为响亮的名号。我家从前便住在北窖儿。我自幼在小城长大,完完全全称得上本地“土著”,然而,我在内心从未将此处认作故乡。呵,故乡,故乡在父辈的回忆中缓缓呈现——辽宁省,一处盛产苹果的城市,纵横错落着古塔区、小凌河、女儿河……一面幽深的铜镜,映射出时光之远。多么辽远呐,隔着半生的时光,故乡一动未动,连季节都忘记了更替,红色的果子依然垂悬枝头,繁密的枝叶里藏着灼人的日影与蝉鸣。遍地洒落大把的青春与故土风物。但是,这样的故乡,两鬓繁霜的父母已然无法回去,何况作为他们的孩子,一个自幼在异乡成长起来的我?然而,安身于此,我又多么地心有嫌隙。这些年,各式各样的表格上,不止一次填写过籍贯一栏。那样的时刻,我总能轻松落笔,内心毫无波澜。籍贯能代表什么呢?苍茫人世,一个人很难说清自己的来路和去向,籍贯不能,身份证不能,户口簿也不能。内心深处,我早已洞悉自己,此生注定是一个没有故乡的人。倘若必定要对自己加以注脚,那么,我只能说,我的故乡一直镌刻在灵魂的内里,既是来处,亦是去向。
我要说的,是城南。城南是我现在的落脚点。当地人习惯以“城南”或者“铁道南”称呼立交桥以南的这片生活区域。火车站的确坐落城南,在我童年时期它就在那里,直到现在。变化并非没有,候车室由过去的简陋平房改建成明亮的候车大厅,可以容纳更多的旅客。站前广场修葺一新,平整的水泥地面更适合拉杆行李箱轻松滑过。然而,在广场的背面,火车铁轨无限深入之地,仍然暗藏着破旧低矮的民居。只有一个从火车车窗里向外好奇打望的旅人,在陌生的光线里,才会发现那些散发陈腐气味的平房,如同即将倾颓的梦境,遗落在时间的荒野里。在低矮的灌木丛和高高的蒿草后,在夏日的草气与冬日的荒寒里,这些陈旧的房舍似乎已经睡了过去,它们被时间遗忘,也就无须醒来。有时候,我甚至相信自己已经看到它们一百年一千年以后的样子——腐朽、遗弃,在一天又一天的日子上缓慢而迅疾地死去。
在深处,有些事物,从未改变。
冬天的傍晚,我从立交桥下经过,目光透过桥上的护栏,偶尔会看到一列满载的火车,飞驶向远天的残阳。瞬间,车轮的巨大鸣响仿佛被什么过滤掉了,行驶中的火车成为黄昏里一个安静而辽远的意象。我总是无法看清车窗里那些一闪而过的面孔,只有一扇扇车窗,像一幕幕倏忽即逝的往事,从眼前一晃而过。一列火车是一个巨大的谜语,从铁轨上、立交桥上、从一个傍晚的光线里,带着诱人的意味永远地消失了。那样的时刻,远行的冲动像一波波海浪,温柔而疼痛地拍打上我单薄的胸腔。从固有的生活中挣脱并消失,是我心底潜藏已久的欲望。
很多年过去,我仍在同一条街道的同一幢房子里出没,过着早出晚归的世俗生活。家门前的街道也像我十年前刚刚搬到这里一样,安静、无言,默默承受着人们带来的喧嚣和树叶掸落的寂寞。这是一条狭长的街巷,一边住满了人家,门前清一色栽满了树木。无外乎椿树、杨树、梧桐,这些习见的树种。某个初夏,我发现有一棵树上居然开满了粉红的合欢花,在午后的微风里,温柔又旖旎。仅此一棵,也足以愉悦眼目。就像生活中那些稀罕的快乐,少少的一点,却实实在在慰藉了孤独的心灵。道路的另一侧,原是一处工厂。不晓得生产什么,只看见过那些年轻的女工,她们是一群正值青春的女孩,中午的时候,会从厂门里走出来,像一群喜鹊,叽叽喳喳地,很快就飞远了。没有什么快得过时间。说不清哪一天,这家工厂忽然关了大门,那些年轻的女孩子一个不剩地消失了。只留下一个昏昏欲睡的老者,终年守在传达室里。有时候,他会走出来,坐在大门旁,斜倚着,在木椅里睡着了。再后来,守门人也不知去向,厂房被推平,成了楼盘,现在,这里矗立起一座快捷宾馆。隔着茶色玻璃门,我隐约看见前台服务员,有时一个有时两个三个,无聊地坐在那里,表情空洞。我也见过宾馆里的住宿者,在这些异乡人那里,我并未嗅到令人迷醉蛊惑的新鲜气息。我倒是看到男人肥胖女人庸俗,有时低声私语有时高声叫喊,而我从未听清一句。他们的神情和隐藏在背后的身份一样,温吞而含糊。
一年当中,总有那么一些时候,我会拐出这条街巷,向着小城南部的更深处游走——城南之南。沿着这条道路,会一直走到饮马河边。那里有一片密集的树林,林子深处有一条渊源颇久的河流。据说,即使现在,那里仍聚集着四百多种鸟类。很难想象,数百种鸟儿济济一堂,共同发声,该是一部怎样悠扬宏丽的合唱。然而,我一直不曾去过那么远,那片传说中的小树林也就一直在我的想象里,闭合起蓊郁的枝叶与沉静的倒影。事实上,我的脚步仅仅在半途就已停转,我要去往一座教师家属楼,最北边的一栋,住着D老师。认识D老师已有多年,他爱人是我中学时的老师。我们的联系时断时续。中学时,我曾和别人一起,去县文联里见过他,那时,D老师还年轻,黑黝黝的中年男子,戴着黑色镜框的眼镜,坐在满屋子的报刊杂志中间,微笑。直到现在,那股浓郁的油墨味道,仍在记忆中弥散。那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我见到办公室里的D老师。再次见面,D老师已是年逾60的老人,而我,也不复昔日的青涩。然而,彼此也不觉得诧异,似乎这些年,不曾有过生疏和失散。通常,我们的会晤正值盛夏。坐在老师的书房里,二面墙壁皆为书所掩,低头,书桌下也码放着成撂的书籍。老师就坐在这些书籍当中,絮絮地,和我闲散说话。数年下来,我的位置一成不变,永远是书桌侧面的一张几凳。有时候,我在凳子上坐定,恍惚觉得上次来这儿,也不过昨天的事儿,如何也不像时隔一年之久。话题大多离不开我的文字,总是有一些困惑和烦恼,与写作相随相生。老师多是倾听,言辞散淡,寥寥数语,却可拨云见日。这间房间的书桌正对阳台,背后则是一台日日敲打文档的电脑。去年,阳台上挂着一只鸟笼,里面有两只珍珠鸟。一雄一雌,身体不比一只钢笔帽更长,在笼间跳跃鸣啭,颇为可爱。今年再去,两只鸟笼空空荡荡。老师说,雄的那只去年冬天时冻死,而另一只雌鸟,则因那几日赶稿子忘记喂食,生生饿死。文痴之恶劣,至此可以窥见。师生二人皆笑。走时,看到电脑桌旁的众多书籍之上,搁置一只瓷碗,盛放着刀功粗糙的咸菜。可以想见,无人到访的早餐甚至午餐桌上,这个老人就是如此搪塞着自己的胃。我忽然记起,在书桌一角,堆放着的几只药瓶。我特别拿起其中一个,瞄了一眼,是“莨菪片”,有平息胃痛之功效。那一刻,竟然有些心酸。灵魂与肉体,犹如光洁脆弱的瓷钵,你更勤于拂拭哪一个?繁琐冗长的生活里,我们总是难以将二者并置共举。
初时,老师尚问及我的私人生活,流露长者的隐忧。时间久了,便也避而不谈。他一定是觉察了我内心的躲闪,或者,他渐渐看出我的冥顽不化,一个彻头彻尾的务虚者。生活于我,不过是通往写作的一扇门。我站在自己的伤口上埋葬往昔,借以歌唱腐朽中重生的明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