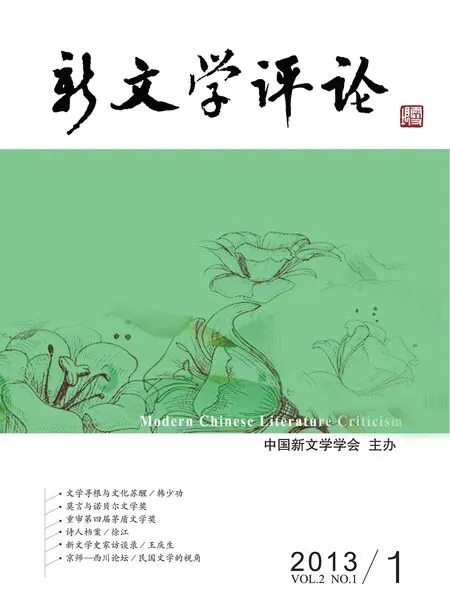思维的简单与批评的粗暴
◆李明军 熊元义
思维的简单既是当代文艺批评容易粗暴的根本原因,也是制约当代文艺批评有次序发展的重要原因。这种思维的简单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种理论的不彻底。这种理论的不彻底可以说是当代文艺批评界出现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来回折腾现象的理论根源。当代文艺批评界教条主义文艺批评和反教条主义文艺批评都存在这种思维简单化的弊病。
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文艺批评界猛烈地批判了教条主义文艺批评,认为教条主义文艺批评是文艺批评的歧路,是一种只有“批评”而无“文艺”的简单而粗暴的文艺批评,严重损害了批评家和作家的正常关系。《中国新文学大系》(1949—1976)第2集文艺理论卷收录的关于文学批评的论文,近一半是从理论上批判和讨伐教条主义文艺批评的。这些反教条主义文艺批评虽然看到了教条主义文艺批评的缺陷,但是没有真正把握教条主义文艺批评的失误之处,和教条主义文艺批评一样存在思维简单化的弊病。
侯金镜(《试谈〈腹地〉的主要缺点以及企霞对它的批评》)在批判教条主义文艺批评时指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中存在一种教条主义倾向,“这一教条主义倾向曾经有多种表现形态,其中之一,就是向简单化、庸俗化的极端上去发展,和武断、粗暴的批评方法相溶合,形成一种专横的批评风气,在文坛上高视阔步、四处冲击。”这种教条主义文艺批评从教条出发,给英雄人物规定了若干不能违反的条件,在文学艺术创作的广阔天地里划出了这么多禁区,宣布了这样那样的禁令。这种教条主义文艺批评阉割千差万别的英雄人物的个性,阉割丰富复杂而多彩的生活,然后又用这种框子去衡量文艺作品,适合于这种框子的就通过,不适合这框子的就抹煞。而于晴即唐因(《文艺批评的歧路》)则概括了教条主义文艺批评的程序和方法,认为这种教条主义文艺批评先有几个“主要矛盾”、“本质”等等的绝对观念,或者自己创造出来的某种违背常情的原理,并从这种观念和原理出发,然后把作品割成许许多多的碎片,甚至割成一字一句,再来两相对照,看后者是否符合于前者,并从而做出结论。这种教条主义文艺批评是一种绝对主义的思想方法,它制造出“一个阶级一个典型”、“一种生活一个题材”、“一个题材一个主题”等等烦琐公式,从而在实际上否认和取消了文学艺术所以存在的基础,是造成文艺创作公式化、概念化倾向的重要原因。萧殷等(《文艺批评的歧路》)认为教条主义文艺批评在评论文艺作品的时候,离开了自己研究对象的具体实际,忽略了文艺作品的艺术整体的互相联系,忽略了文艺作品的内在规律,往往从主观出发,用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观点来观察生活和认识作品;或者用一般的抽象原则和概念来硬套作品,以“代表”否定典型,以一般否定个别,以理想否定现实;或者寻章摘句地肢解作品,把个别人物、个别情节从作品的艺术整体中割裂开来,然后攻其一点,以局部掩盖全部,用单个否定整体。这种主观片面的批评方法不单违背了文艺认识与反映现实的特性,也背离了主观与客观的辩证统一的原则。其结果,当然是离开了辩证唯物主义而陷入形而上学的泥坑。这些反教条主义文艺批评虽然是结合文艺批评实践进行的,但是它们在为具体文艺作品辩护时只是看到教条主义文艺批评在批评具体文艺作品的失,而没有看到教条主义文艺批评在批评具体文艺作品的得。因而,这些反教条主义文艺批评对教条主义文艺批评进行了彻底否定,而不是在否定之否定中前进。其结果,反教条主义文艺批评与教条主义文艺批评互不接受对方的批评,没有在扬弃各自的局限中形成中国当代文艺批评有次序的发展进程。
这些反教条主义文艺批评指出,教条主义文艺批评要求在正面人物身上集中一切最先进、最理想的特征,要求艺术典型成为某一客观事物的全部特征的总和,并以这些框框来和文艺作品中的人物两相对照,凡是对不上的,就断定为“失败”或“不典型”;教条主义文艺批评不是从个别认识一般、从具体认识抽象,而是从一般的观念、从现成的结论或从社会科学的公式或规律出发,用一般去代替个别,用规律去代替生活。这不但不能正确地认识生活、理解社会,反而只会把纷纭复杂的现实生活绝对化和简单化;教条主义文艺批评用众多文艺作品所达到的成就的总和或对一个时代文学艺术的总的要求和总的精神,来强求一部文艺作品和文艺作品中的正面人物。其实,教条主义文艺批评要求在正面人物身上集中一切最先进、最理想的特征,要求艺术典型成为某一客观事物的全部特征的总和,并以这些框框来和文艺作品中的人物两相对照,从一般的观念、从社会科学的公式或规律出发衡量社会生活,用对一个时代文学艺术的总的要求和总的精神来强求一部文艺作品和文艺作品中的正面人物,这种思维方法并没有错。这就是文艺批评的宿命。鲁迅尖锐地指出:“我们曾经在文艺批评史上见过没有一定圈子的批评家吗?都有的,或者是美的圈,或者是真实的圈,或者是前进的圈。没有一定的圈子的批评家,那才是怪汉子呢。”在这个基础上,鲁迅认为:“我们不能责备他有圈子,我们只能批评他这圈子对不对。”既然文艺批评家在文艺批评时须有一定的圈子,那么,他就不能不从圈子出发。因此,首先,我们不能责备文艺批评家有圈子,只能批评他这圈子对不对;其次,我们在判断文艺批评家的圈子对不对后,还要看他把握了圈子与文艺作品的辩证关系与否。在这两者之间,文艺批评家的圈子固然重要,但把握圈子与文艺作品的辩证关系更重要。在文艺批评史上,不少重要的文艺批评家的圈子虽然早已遭到扬弃,但是他们对文艺作品的精妙批评却仍然闪耀着思想的光芒。这就是说,中国当代教条主义文艺批评的错误不在于它搬用了完美的圈子,而在于它只看到了这个完美的圈子与具体的文艺作品的差别,而没有看到它们之间的联系。文艺批评针对作家艺术家创作提出某种理想要求,与作家艺术家在创作中实现这种理想时达到了什么程度是两回事。这是绝不能混淆的。文艺批评绝不能因为作家艺术家没有完全达到这种理想要求,就全盘否定他们在创作中所取得的成就。也就是说,教条主义文艺批评在出发点上没有犯错,而在批评具体文艺作品上因为看不到尺度与具体文艺作品的联系而陷入了虚无主义的泥淖。
当代虚无存在观文艺批评虽然不是教条主义文艺批评,但它在思维方法上犯了和教条主义文艺批评同样的错误。这种虚无存在观文艺批评所追求的文艺的理想境界虽然没有教条主义文艺批评那样具体,但也是从人类的某种完美理想状态出发,彻底否认现实的存在。它只看到了现实和理想的差距,没有看到它们之间的辩证联系,这实质上无异于取消了多样的存在。这种虚无存在观文艺批评推崇伟大文艺作品的观念,认为“真正美的、优秀的、伟大的作品不可能只是一种存在的自发的显现,它总是这样那样地体现作家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和梦想,而使得人生因有梦而变得美丽。尽管这种美好生活离现实人生还十分遥远,但它可以使我们在经验生活中看到一个经验生活之上的世界,在实是的人生中看到一个应是的人生愿景,从而使得我们不论在怎样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对生活始终怀有一种美好的心愿,而促使自己奋发进取;在不论怎样幸福安逸的生活中始终不忘人生的忧患,而不至于走向沉沦。”它坚决而彻底地批判和否定了那些只是供人娱乐消遣的文艺作品,认为“并非那些轰动一时、人人争读的作品都可以称作是文艺的。克尔凯戈尔在谈到什么是人时说:‘人是什么?只能就人的理念而言……那些庸庸碌碌的千百万人不过是一种假象、一种幻觉、一种骚动、一种噪声、一种喧嚣等等,从理论的角度看他们等于零,甚至连零也不如,因为这些人不能以自己的生命去通达理念。’这‘理念’以我的理解就是‘本体观’。这话同样适合于我们看待文艺。”如果只是承认那些充分体现文艺的理想境界的文艺作品是文艺,那么,这个世界上的文艺作品就所剩无几了。可见,虚无存在观文艺批评在文艺批评实践中只是看到了文艺世界的差别而没有看到文艺世界的联系,因而彻底地批判和否定了文艺的多样存在。
不过,虚无存在观文艺批评虽然在思维方法上犯了和教条主义文艺批评同样的错误,但它重视文艺理论的指导作用却是对的。这种虚无存在观文艺批评认为:“虽然由于文艺理论与文艺现象之间所固有的内在联系,使得在文艺理论研究中这种演绎不像数学推算那样,仅凭抽象的逻辑思辨开展,而必须时时返回到对经验现象的分析和归纳;但是若要发现本质与现象以及现象与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而使它们成为一个知识的有机整体,仅仅凭经验的归类和归纳而没有一定的理论思维的能力是绝对不能完成的。”这无疑是正确的。然而,当代文艺批评界在猛烈批判教条主义文艺批评和虚无存在观文艺批评的过程中,只是集中批判了它的出发点即圈子,而没有深入地解剖它在把握圈子与文艺作品的辩证关系上的失误,不但没有真正有效地克服教条主义文艺批评和虚无存在观文艺批评的缺陷,反而滋生出另一种极端,即重视文艺批评的审美感悟而拒绝文艺理论的科学指导。这种拒绝理论指导的倾向提出了所谓的“理论控”,认为理论控执意要用理论把艺术肢解成概念的载体,是反艺术的。“理论何重,批评何轻?意义的阐释怎么就优于审美的体验和心灵的对话?类型何重,个例何轻?难道艺术不是用来描写精神生活的例外,不是通过个体的感受最终来刺痛或者温暖心灵的么?理论控从来不肯相信眼前的东西,也从来不听从审美感悟的导向,他们太崇拜理性对于人的作用,导致彻底放弃了那些通往理性之外的和到达理性之前的混沌、幽暗,同时也是神秘、空灵的‘另一重世界’。说得严重点,这样的文艺评论读多了,只会阉割人们对艺术的感受和神往,渐渐变成‘艺无能’。所以,从根本上说来,理论控是反艺术的。”在这个基础上,有些文艺批评家甚至认为,应该是文艺作品给文艺立法,而不是文艺批评给文艺立法。文艺作品无限丰富,作家艺术家的每一次创作都是一个挑战,所以文艺批评家要更多地尊重文艺作品,尊重作家艺术家,尊重原创。这些拒绝文艺理论的论调没有看到,尽管独创是艺术的第一特性,但是,这种独创既有可能是有意义的,也有可能是无意义的。如果盲目崇拜精神生活的例外、个体的审美感受,那么,就无法区别有意义的文艺创新和无意义的文艺创新。其实,这种文艺批评观不过是克罗齐派文艺批评观的翻版。中国现代美学家朱光潜扼要地概括了克罗齐派文艺批评观,这就是创造的批评,即艺术作品的精神方面时时在“创化”中,创造欣赏都不是复演。“真正的艺术的境界永远是新鲜的,永远是每个人凭着自己的性格和经验所创造出来的。”朱光潜在介绍克罗齐派文艺批评观时曾尖锐地指出这种文艺批评观存在难以克服的困难,这就是它忽略了艺术价值的高下判断,自然对于文艺批评是一种困难。文艺的多样化的发展是有价值高下的,而不是等量齐观的。正如毛泽东所说的:“文艺家几乎没有不以为自己的作品是美的,我们的批评,也应该容许各种各色艺术品的自由竞争;但是按照艺术科学的标准给以正确的批判,使较低级的艺术逐渐提高成为较高级的艺术,使不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改变到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也是完全必要的。”在文艺家都以为自己的作品是美的情况下,文艺批评不能不严格甄别较低级的艺术与较高级的艺术,并促使较低级的艺术逐渐提高成为较高级的艺术。如果只是由文艺作品给文艺立法,那么,文艺批评家将只有拜倒在作家作品的脚下,而不可能引领文学有序而健康的发展。
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界这些拒绝理论指导的倾向在一定程度上重拾了朱光潜早已抛弃的思想糟粕。在中国现代文艺批评史上,朱光潜虽然倾向印象派文艺批评和克罗齐派文艺批评,但他却清醒地看到这些文艺批评流派的根本缺陷,并在文艺理论上对这种缺陷有所克服。朱光潜认为印象派文艺批评往往把快感误认为美感。在文艺方面,各人的趣味本来有高低。印象派批评没有区分这种趣味的高低;文艺虽无普遍的纪律,而美丑的好恶却有一个道理。印象派批评没有深入探究美丑的好恶的道理。而克罗齐派文艺批评同样也存在显而易见的缺陷,一、从艺术传达上,克罗齐否认艺术传达是艺术活动。艺术家同时是一种社会动物,他有意无意之间总不免受社会环境影响。真正的艺术家尽管不求虚名,却很少有人不希望有知音同情者;尽管鄙视当时社会趣味低,却很少有人不悬一种未来的理想的同情者。钟期死后,伯牙不复鼓琴,这真是艺术家的坦白。有些人知道“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所以把作品“藏诸名山,传之其人”。人是社会动物,没有不需要同情的。同情心最原始的表现是语言,没有传达的需要就不会有语言。艺术本来也是语言的一种,没有传达的需要也就不会有艺术。艺术的风格改变往往起于社会的背景。我们不能否认传达可以影响艺术本身。二、从艺术价值上,克罗齐否认了美与丑的分别。克罗齐认为,美是绝对的,没有程度的分别。凡是直觉都是表现,都是艺术,也都是美的。大艺术家的直觉和一般人的直觉虽在分量上有差别,在性质上却并无二致。我们不能说这个艺术作品比那一个美。如果《红楼梦》是完美的表现,《桃花源记》也是完美的表现,它们就是同样的美,我们不能说这个比那个伟大,虽然它们的篇幅长短广狭都相差很远。这样,克罗齐只能承认艺术与非艺术的分别,而在艺术范围之内不能承认美与丑的分别。朱光潜在探讨文学的趣味时进一步地反省了这种偏颇的文艺批评观。这就是朱光潜不但认为文艺的趣味是有高下的,而且承认文艺标准的存在,认为“文艺自有是非标准,但是这个标准不是古典,不是‘耐久’和‘普及’,而是从极偏走到极不偏,能凭空俯视一切门户派别者的趣味;换句话说,文艺标准是修养出来的纯正的趣味”。这就是说,如果盲目崇拜精神生活的例外和个体的审美感受,就是在文艺的低级趣味流行时无所作为。可见,当代文艺批评界没有在朱光潜已达到的思想高度上继续前进,而是退回到朱光潜早已扬弃的印象派文艺批评和克罗齐派文艺批评那里。中国当代文艺批评之所以进展不大,与这种来回“折腾”不无关系。
注释:
①鲁迅:《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28页。
②鲁迅:《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28~429页。
③[丹麦]彼德·罗德选编:《克尔凯戈尔日记选》,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129页。
④参见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8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378页。
⑤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9页。
⑥参见朱光潜:《朱光潜美学文集》(第1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482页。
⑦参见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8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381~383页。
⑧参见朱光潜:《朱光潜美学文集》(第2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4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