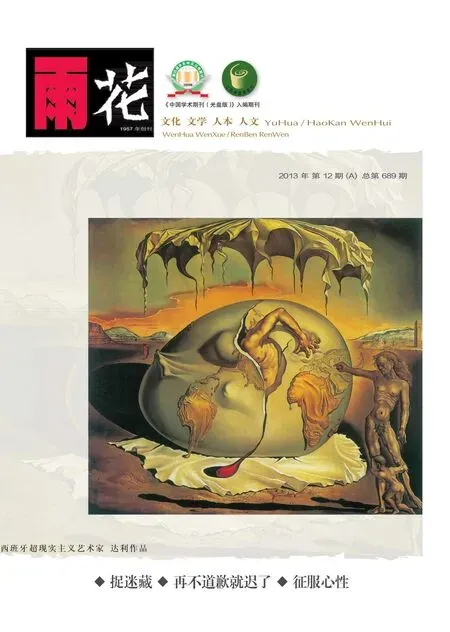桨声
●刘鹏程
想我娘想得厉害的时候,我就沿刘屋垄跑到麻林咀去,去坐渡船,到大姐家去。一坐上渡船,桨声开始以后,我就仿佛娘在身边。
自从搬到刘屋垄来住,我的耳朵里似乎常常听见桨声,最近的频率越来越高。
其实刘屋垄现在只是一个虚拟的村庄了。这个被城市吞并并快速同化了的村庄,越来越不真实。到我搬来这儿居住的时候,只剩下了门前一洼规划为松兹菜市场的水田还没有开发。这也是刘屋垄仅存的一点关于村庄的痕迹。
但是,我自从住进这个小区来以后,晚上躺在床上,听见那洼水田里咕呱呱的蛙声;或者站在四楼的阳台上,看雨在田洼里积水成塘,我就把它当成了一个真实的村庄。
我老家的村庄名叫刘屋,门前一直延伸到泊湖边的一大片田垄也叫刘屋垄。
这个刘屋垄的水最终也是流到泊湖。一直就是这样,从鲤鱼山上下来的泉水,终年灌溉了刘屋垄,然后经过白洋河,九曲十八弯最终流到泊湖里。
大概我老幻听桨声就是因为这个——现在,我总是喜欢把此刘屋垄和彼刘屋垄划上等号。在我的潜意识里,刘屋垄下面就是那个名叫高家赛的湖汊。小时候我曾经无数次走刘屋垄,到水边乘坐小木船渡过高家赛。我大姐家和外婆家就在高家赛对岸的鳖壶嘴。
娘回娘家时带我走刘屋垄,上麻林咀,去过渡。湖上静悄悄,只有桨声徐徐,和随着桨声有节奏的划行。偶有一两只跳鱼儿跃出湖面的声音,安静极了。后来的回忆,包括现在听到的假想的桨声,就变成了安宁,变成了缓慢……
对岸的那两棵大枫树后面就是大姐的村庄。早晨的阳光从大枫树的叶隙间透过来,照在湖面,湖水像一面偌大的镜子。大姐正好就在对岸的湖边上洗衣,远远地喊我和我娘。喊声是从棒槌声的间歇里传过来的,和着桨声,在湖面上亲切地荡漾。
外婆家是在大姐家后面的那个村子。我出生就没见过外婆,倒是常去大姐家。大姐在我出生前就嫁到那儿了,她比我大20岁,像娘。小时候娘的奶水不足的时候,我喝过大姐的奶水,所以我总是喜欢渡湖往大姐家跑。通往大姐家的路充满亲切而幸福的桨声。
我也能够想象,早年我娘从鳖壶嘴嫁过来,嫁到我父亲的村庄;以及后来大姐嫁到高家赛对岸去,都是走刘屋垄,在桨声里完成的,沿途同样充满了安宁与幸福的桨声。
直到有一次,在梦里我梦见一只桨断了,我乘坐的渡船在湖面上飘摇,没了方向。那个时候,我娘正得了个叫做食道癌的毛病,我不知道这是个什么毛病,但是这个梦不久她就死了。那时候我13岁。之后我一直纠结于这个该死的梦,以为是我的这个噩梦让我娘死的。
我娘死后,我总是整日烦躁不安,无心念书。有时候我就逃学,从学校往家里跑,快跑到村口的时候,又不想回去了,就一个人在村头的麦地坝上坐会,无聊之极就发发呆,掐掐地上的草,等其他孩子放学了再一起回家。
想我娘想得厉害的时候,我就沿刘屋垄跑到麻林咀去,去坐渡船,到大姐家去。一坐上渡船,桨声开始以后,我就仿佛娘在身边。我就集中精力去听这个桨声,烦躁之心就在这桨声里舒缓下来,平静下来。
以至后来,我有些依赖这个桨声了。当我在自己的城市生活里,被白天呼啸的汽车声,夜间歌厅里刺耳的尖叫声,以及钢筋水泥坚硬的碰撞声弄得烦躁不安的时候,就会梦见桨声,这个桨声就载我到达安宁的彼岸……
现在,我回到刘屋垄来居住。剩下的时光,从刘屋垄出发,离桨声就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