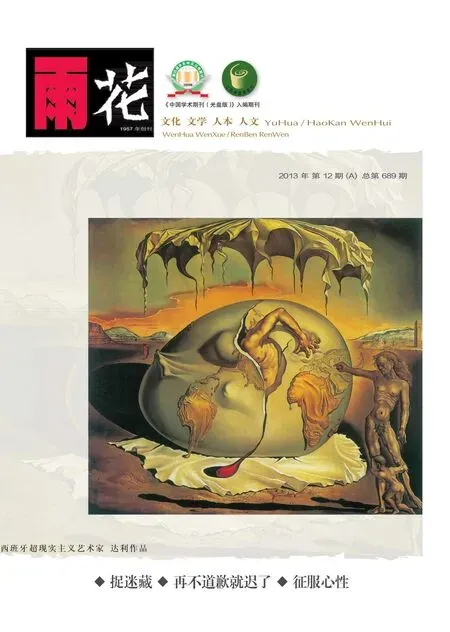最后的漂泊
●张寄寒
父亲病中一直想吃母亲做的乳腐卤烧肉,母亲去买了肋条肉,去酱园里要了乳腐卤,烧了乳腐卤红烧肉,母亲端到父亲病床前,父亲只看了一眼,叹息地摇摇头,两眼落下两滴混沌的老泪。
一
父亲从上海做殡葬行业生意失败回到了母亲所在的故乡小镇,他依然念念不忘当年他在上海生意场上的朋友,他相信他们会向他伸出援助之手。刚刚回掉一个朋友介绍的一笔钢笔生意,又收到另外一个朋友来信,介绍一笔火油生意,取货时付现金,父亲堆着一脸诚恳的笑意和妈妈商量,妈妈只好去借了本钿,让父亲去上海取货。
父亲乘航船去当班回来,我在航船码头上远望西边的港湾,只见熟悉的黑色的上海航船笃悠悠地摇了进来,航船靠码头,父亲叫两个脚夫把两箱火油扛回家。
父亲一到家,乐乎乎地对妈说,两箱火油朋友按最低价卖给我们,我们按市场价格卖出去,这个差价可不少哩!
“我们放在哪儿去卖?”
“我早就想好了,去桥头栈房门口卖,你和栈房老板娘不是老姐妹?这点忙总可以帮吧!”父亲胸有成竹地说。
“你带没带上海的糖果?”
“时间紧没有买,卖火油的朋友送我一盒奶油咸味糖,我想给孩子吃,你要做人情,你就拿去吧!”
我跟着妈妈去桥头栈房找到老板娘,老板娘性格直爽,一见妈妈便说,无事不登三宝殿!
“真的有事相求,一包小糖不成敬意!”
“有啥事尽管说,送东西,你就见外了!”
妈妈一五一十如实相告。
“这点小事还商量什么,你尽管来摆嘛,我们还好做个伴哩!”
次日一早,我和父亲扛了一箱火油去桥头栈房,火油箱上放了白铁皮漏斗和勺子。父亲从栈房里借了一把椅子,口袋里掏出一本练习本和红绿铅笔。父亲用铅笔在练习本上写下“零拷火油”四个字,挂在栈房门口。
初夏时节,父亲白衬衫,吊带西装裤,头发虽已谢顶,但仍梳得精光,坐在一张靠板椅里,哪像是做小生意的人,骨子里还是上海大老板的派头。没有生意时,他悠闲地抽他的板烟。中午放学回家,我给父亲送饭,放晚学,我替父亲收摊。
老板娘一直说我父亲是大少爷开店,做小生意,就不能怕难为情,当街吆喝嘛!父亲不要说吆喝,平时话就不多。一个上午没有一个生意,老板娘看不惯,帮我们吆喝起来。放晚学了,老板娘叫我吆喝,我说我也喊不出口,老板娘说,有其父必有其子。
老板娘心直口快,说归说,吆喝归吆喝。打火油的人来了,父亲做成第一笔生意,她拷一斤,父亲一只四两勺子,两勺半,不是小半而是大半。没多久,卖火油的人在门口排队了,父亲依然堆着笑脸按第一笔生意一样贱卖。
第一天的晚上,妈妈帮父亲算账,卖掉一箱火油所收到的钱,就是朋友给父亲按最低价的一箱火油的钱,辛苦了一天,一分也没挣到,妈妈埋怨父亲做小生意大手大脚,妈妈一边翻父亲过去的卖香烟老账,一边说,第二箱火油无论如何不能贱卖了。
第二天早晨,我和父亲扛了第二箱火油去栈房,刚到不久,门口拿着火油瓶的人就在等候了。妈妈急吼吼地也赶到。妈妈让父亲坐在椅子里休息,她做生意,第一个生意是米店小老板阿康拷一斤,妈妈用勺子拷了两勺半,阿康怒气冲冲地对妈说,昨天人家和我一样的火油瓶,一斤齐瓶口,今天怎么齐瓶颈,你克扣斤两不可以的!
“我难得做点小生意也学不会克扣斤两,不像有些人想了自己作他人!我不像有些人卖米把大拇指扣在升箩里!”妈妈指桑骂槐地说。
“你说我克扣斤两,这种缺德的事我不干的。”
“我又没有指你的名字。”
说也奇怪,妈拷火油就没人来拷,妈一回家,顾客蜂拥而至。父亲怕伤了乡邻乡里的和气,依然还是两勺大半。不到半天工夫,第二箱火油销售一空。
入晚,妈妈跟父亲算了一笔细账,两箱火油亏的是父亲来回的盘缠钿,妈妈说父亲,都说千做万做蚀本生意不做,你就是做蚀本生意。
父亲对妈妈笑着说,钱没有挣到,留了个好口碑也值!妈妈朝父亲发出一阵苦笑。
二
照父亲的意思还想去上海拿几箱火油回来卖,可是妈说他劳命伤财犯不着,当然不让他再去,父亲便断了这个想法。有一天下午,父亲又收到上海的一个朋友来信说,有一笔好生意请你做,赶快来上海面谈。父亲满脸笑容和妈商量,妈常说,你父亲的微笑让我的心也软了。妈让父亲快去快回,父亲只带了路费匆匆上路。原班航船回来了,我去航船码头候他,父亲手里只拎着一只纸箱,回到家,父亲欣喜地打开纸箱,哦!十二只锃光闪亮的国光牌口琴,太吸引人,我拿了一只把玩,爱不释手。
“快放好,不要弄脏,你父亲尽捡这些卖不出去的东西!”妈一脸不快地说。
“这一打口琴是朋友用最低价批给我,卖不掉可以退给他,卖得掉再去批!”父亲乐观地说。
“小镇上哪有这么多的人吹口琴,这里是乡镇,不是城市哟!”妈给父亲泼冷水。
吃罢晚饭,父亲和妈商量决定,明天让我和父亲一起去小学推销口琴。入晚,我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想起上一次和父亲一起去小学推销钢笔,父亲被奚落的情景,心中茫然……这回推销口琴我要去找教我们唱歌的王老师。
次日早晨,父亲和我带了一纸箱口琴去学校,我们走进了教师办公室。
“又来推销钢笔?”一个教师高声说,立刻把埋头伏案教师的注意力调动起来,我把父亲带到王老师跟前,我对他说,我父亲从上海带来一打国光牌口琴,我知道你会吹口琴的,先给你看看。父亲打开纸箱,十二只锃亮锃亮的口琴展现在王老师的办公桌上。
“太漂亮的口琴,又是名牌!”王老师赞不绝口。
“你吹吹看好了!”父亲对王老师说。
“我家儿子最喜欢吹口琴!”
“我要给我女儿买一只!”
“国光牌,名牌!”
“王老师,你会吹,吹一曲给大家听听音色。”父亲郑重其事地让王老师吹奏一曲。
“那我吹了……”王老师掏出一块雪白的手帕擦了擦口琴,便放在嘴边,先快速地试了一遍音阶,连声说,不错!不错!
“吹一曲!吹一曲!”众教师起哄地喊。
王老师把口琴放在嘴边,朝天想了想说,吹什么呢?
“就吹《秧歌舞》吧!”
“好,我吹!”王老师吹奏《秧歌舞》曲,明快的节奏,轻松的旋律,有几个教师情不自禁地扭动起舞步。
“吹得太好了,太好了……”众教师赞笑着。
“你父亲卖口琴,肯定也会吹口琴,要不我们请他吹一曲?”王老师突然将了我父亲一军,让我为难得说不出话来。
“说实话,我还真没听过父亲吹口琴哩!”我如实地对众教师说。
“我们鼓掌欢迎,给我们吹一曲!”王老师边说边鼓掌,众教师掌声雷鸣。
父亲在众教师热情邀请下,盛情难却,他沉吟了一会,朝大家微笑,沉稳拿起口琴搁在嘴上,仰起头,鼓起腮,屏气、哈腰、含胸,样子像是自个与自个拗着劲。从口琴里挤出来的音,声如裂帛,有明亮的穿透力,又款款如诉。这是首节奏明快的《游击队之歌》,父亲用熟练的单复音,双复音吹奏,如同一个乐队演奏的气势,教师办公室刹那间成了口琴独奏音乐会的会场,我发现一个个教师的眼睛闪亮,脸上洋溢着欢乐,一双双向我父亲投去敬佩的目光,我的心像灌了蜜一样甜美。
父亲的一曲《游击队之歌》赢得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我买一只!”
“我也买一只!”
“我买两只!”
……
没有想到父亲的一打口琴,一下子顺利地卖掉八只。我和父亲刚跨出办公室门口,立刻被一群高年级的同学团团围住,他们说要买口琴,父亲摊开口琴盒,立刻被他们一抢而空,他们拉着我父亲央求他再吹一遍《游击队之歌》,父亲不拂他们的诚意,就在走廊里边走边吹,又一次博得同学们的一片掌声!
我把父亲送出校门口,心里仿佛觉得,父亲不是来推销口琴,而是来举行一场口琴独奏音乐会。望着父亲远去的背影,油然而生自豪感。眼前抹不去父亲那张和蔼可亲的笑脸。
三
初夏时节,故乡南湖畔城隍庙前古戏台请来了草台班京剧班子做两天两夜的戏,举行一年一度的祭龙仪式。妈和父亲商量,两天的龙戏去做点什么小生意。妈没有想到父亲爽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于是,父亲关在小屋里,一会儿找资料,一会儿找原料,父亲说,他利用阿基米德原理中的水的压力,做成一个小发明,从一只小水箱外面装有一根朝上的水管,水箱里的水满了,水管会喷出一股水柱,让水柱托住一个乒乓球,远远望去,乒乓球像悬在半空旋转,挺抓人眼球。
父亲的小发明得到我和妈妈的喜爱。父亲决定去戏场上卖荷来水,把这个小发明放在小摊旁边。
龙戏的第一天早晨,我和父亲扛着荷来水的小摊,小发明摆到人头济济的戏场上,引人注目的乒乓球在水柱上滚动起来,立刻把过往行人吸引住,没多久,我们这个荷来水小摊被孩子们团团包围。孩子们边看边喝荷来水,一批又一批,一个上午,我们的荷来水,卖掉一百多杯。下午忙得我来回往家里拿荷来水,一个下午卖掉了三百多杯。我和父亲收摊回家,父亲坐在靠椅里悠闲地抽着板烟,妈对他说,隔壁邻居都说你聪明能干,做样像样,父亲的表情淡定,丝毫看不出内心的兴奋。
第二天,我和父亲起了大早,把小摊早早地去戏场上摆好,没多久又被孩子们包围得水泄不通。我发现旁边的几个小摊摊主朝我们吹胡子瞪眼睛。父亲性格沉稳,从不张扬。今天他换上白衬衫戴了黑领带,西装吊带裤、稀疏的头发两边分,头路清晰可见,活脱脱的一个上海人腔调。
龙戏做了两天,我走在街上有的同学见了我都说,他爸是卖荷来水的,有的同学见了我都说,他爸是工程师,我听了喜忧参半。
龙戏结束,妈趁父亲刚做小生意做出了劲,便和他商量继续再做,妈提出去戏院摆小摊卖五香豆、香瓜子,父亲却一口答应了。次日一早,妈便去戏院和戏院陈老板商量,陈老板说,见过我父亲,一口答应了。我回家迫不及待把这个消息告诉父亲。于是家里立刻忙碌起来,又炒瓜子,又烧五香豆。次日中午,我帮父亲去戏院门口摆摊头。父亲坐在门口的小凳上一边看摊,一边和陈老板有说有笑地聊天。
入晚,我在家做完作业,匆匆忙忙地赶到戏院,有时帮爸守摊,有时去戏院看戏。
戏院散场了,我们等戏院里的客人走空了,父子俩扛着小摊子笃悠悠地回家。踏着一片迷离的月色,登上了一座高高的石拱桥,桥楼的翘脊上升起一弯洁白的上弦月,父亲情不自禁地唱起了京剧《武家坡》中一句“一马离了西凉亭”,我不知道父亲是否真正能就此安于现状,还是心猿意马……父亲的脸上依然是永恒定格式的微笑,或是低声呼唤我,还有欲言又止的凝重。
四
早听母亲说,父亲是湖北武昌一所商业大学毕业的,我可百思不解,父亲读了那么多的书怎么会找不到工作。
一天下午,我家来了一个不速之客,不知他从哪里打听到说我父亲是个有文化的人,他便向我父亲说明来意,他是南货店老板,要买别人家的一幢房子,请父亲去写一张卖买房契,我一听说父亲要去写卖买房契,心想父亲常年在城市生活,对于乡下的事不熟悉,我正替父亲为难时,谁知父亲二话不说,爽快地一口答应下来,立刻跟南货店老板说走就走。
隔不多一会,父亲回家了!哦!父亲可神气啦!一手拿着一瓶红葡萄酒,一手拿着两个三角包,脸上绽开了粉红的笑靥,我和小妹欢蹦跳跃地迎了上去,拉着父亲的大衣角回屋。
父亲把两个三角包拆开,一包奶油花生米,一包五香麻雀。父亲一边给自己斟了满满一杯红葡萄酒,一边给我和妹妹一人一只五香麻雀。
我和妹妹坐在我父亲的对面的靠椅里有滋有味地嚼着五香麻雀。今夜父亲心情特别好,刚喝了几口红葡萄酒便对我们说,你们过来!坐在我的膝盖上。我和妹妹分坐在父亲的两个膝盖上,父亲让我们吃着桌上的奶油花生。
“好吃吗?”父亲眯缝着眼睛望着我们,父亲今夜的脸色,分外娇艳,父亲仿佛陶醉在难得的兴奋里。
父亲忽然用筷子蘸着红葡萄酒分别塞在我和妹妹的嘴里,妹妹皱了眉头说苦!苦!我说,好甜的酒!望着眉开眼笑的父亲,小屋里顿时升腾起一股温热的暖意。
暮春时节,我家门前的小河正发春水,石河桥的石级都被春水淹没了。父亲一大早找了一根粗铅丝在一块磨石上“嚓嚓——”地磨着,再用老虎钳把它弯成一只鱼钩。
“爸,你拿鱼钩去钓什么?”
“去钓好吃的东西!”父亲一边神秘地笑着说,一边提了一只小铅桶走向石河桥。
“放学回家吃好小菜!”我背着书包边走边说。
上课时一直走神,想父亲钓鱼。父亲常年生活在上海大城市,从来没有钓过鱼,正如母亲一直谐谑他只会在碗里钓鱼。
中午放学回家,踏进家门便闻到一股浓酽的鱼肉鲜香,想不到客堂里的饭桌上真的摆着一碗浓油赤酱的红烧鳗鲡,这道菜对我们家来说是太奢侈了,我迫不及待问母亲,这鳗鲡是不是父亲钓到的?
“不是你父亲钓到而是它自己游到我们家的?”母亲笑着说。
“真的是父亲钓到的吗?”我用怀疑的目光盯着父亲看。
“都是你父亲一个上午的功劳!”母亲骄傲地替父亲说话。
母亲在餐桌上给我娓娓道来,你父亲大清早便去石河桥下观察,发现石河桥下有鳗鲡出没,便回家做鱼钩,找鱼饵,细磨细相地蹲在石河桥级上钓鳗鲡,半包香烟抽完,半个上午过去了,一条鳗鲡都没钓到,我还埋怨他只会在碗里钓了,我刚离开石河桥,你父亲兴奋地叫我,快来看,一条大鳗鲡!我走去一看,果然是一条又粗又大的白肚皮鳗鲡。说也怪,一条钓牢了,越钓越顺,一个上午钓了半铅桶的鳗鲡。
听完母亲的叙述,我简直难以置信,莫非父亲的鱼钩真是神钩吗?我最喜欢吃的母亲最拿手的红烧鳗鲡,如今真真切切地放在桌上的大碗里,今天能够吃到父亲亲手钓到的鳗鲡,母亲亲手烧煮成的红烧鳗鲡,对我而言,这是一道具有特殊意义的菜肴,也是留在我心中最美最美的美食。
五
星期日的下午,我和邻居家阿羊去镇郊急水江畔玩削水片。走到急水江畔,望着一江春水向东流,我们踏在一片碎瓦片的江滩上,白色的水鸟三成五群,时高时低地在江面上盘桓,我和阿羊用一块块碎瓦片,朝着平静如镜的江面上削水片,碎瓦片在江面上轻盈地扑腾,溅起一朵朵白色的水花。
忽然从江东驶来一艘白色的大轮船,我和阿羊立刻停止了削水片。大轮船靠岸了,轮船上都是高鼻子、蓝眼睛、白皮肤、黄头发的外国人。没多久,镇里的人都闻讯纷至沓来看热闹,急水江畔立刻变得人山人海。可是岸上这么多的人都无法与船上的外国人交流。不知道他们是哪国人?来这儿是干什么的?大家只能面面相觑。
我忽然想起家中的父亲,他身边有许多本砖头一样厚的外文书,他常常全神贯注地读着,按母亲的说法,父亲在上海和外国人做生意,说了几十年的外语,可想而知父亲外语的水平了,想到这里我不顾一切奔回家把父亲拉到急水江畔,父亲丈二和尚摸不着头,一到江畔,我拉着父亲的手挤进了拥挤的人群,父亲发现大轮船上的十几个外国人,他立刻自自然然地用一口流利的英语和他们对话,忽然大轮船上的外国人欢蹦乱跳起来,手忙脚乱地拿了一块长跳板搁到岸上。一个外国人和父亲“叽哩咕噜”地对话,于是,父亲面带笑容,从容地沿着跳板登上大轮船,父亲一到船上,只见父亲与外国人有说有笑地交流。一会儿,一个个外国人都和父亲拥抱,把父亲送上岸。父亲回到岸上对父老乡亲说,他们是一艘英国商船,要去上海,今天迷了路,我给他们指引了方向。
岸上成群结队的围观者站在江畔目送外国大轮船向东远去,父老乡亲们纷纷给我父亲投来一瞥敬佩的目光,我为自己拥有一个懂外语的父亲而自豪。
十二岁那年的一个秋日,我接到县中的录取通知书,当晚父亲特地用我在做龙戏时的戏场头买来的小胡琴为我演奏《欢乐歌》、《喜洋洋》民族乐曲表示庆贺。
父亲在家检查我的作业时发现我的粗心大意和不求甚解的毛病,常对我说,学问,学问,一边学,一边问,学习上千万不能不懂装懂。
带着父亲谆谆的嘱咐,我在学校里刻苦地学习,期末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放寒假回家,我刚踏进家门,母亲悄悄地告诉我,父亲喉咙里生了一个硬块,去上海医院看了医生,医生说,要动手术,但手术费十分昂贵,一直拖着。母亲要把家中唯一的一只铜床卖掉,父亲无论如何不让卖。
父亲病中一直想吃母亲做的乳腐卤烧肉,母亲去买了肋条肉,去酱园里要了乳腐卤,烧了乳腐卤红烧肉,母亲端到父亲病床前,父亲只看了一眼,叹息地摇摇头,两眼落下两滴混沌的老泪。
整个寒假,家中笼着一片阴霾。
转眼开学了,我无奈地告别病重的父亲,怀着沉重的心情踏上去县城的轮船,离开了故乡,离开了我最放心不下的父亲……
没想到开学一个星期后的一天中午,接到家中的一封烧了角的书信,我立刻颤抖地拆开信封,那是哥的手笔,父病亡速归。我急忙告假,踏上冗长的水途,心急火燎赶回故乡,踏进家门,父亲的灵堂已拆除,母亲噙着泪对我说,等不到你回来,让你父亲棺柩早日入土为安吧。
哥把我带到镇郊父亲的坟茔前对我说,父亲临终前一直念叨你的名字,我们说马上来了,他一直忍着病痛的折磨等你,父亲终于没有等到你,阖上眼睛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父亲的棺材里放了他的一副老花眼镜,一只板烟斗,一把小胡琴,一本英汉大词典……
我听着,听着,眼泪禁不住扑簌扑簌地掉下……
父亲走了,我的满眼都是他的影子,我在心中默默祈祷他的这条小船在天堂里找到他停泊的港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