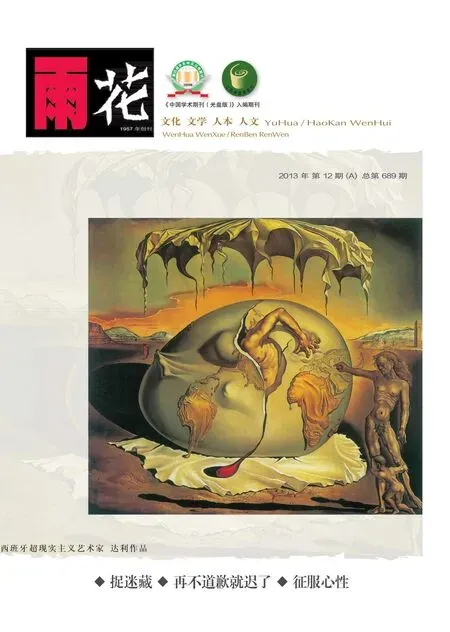能不泪满襟
●李昆华
母亲结满老茧的双手,很早就糙硬似柴,指关节粗大而变形,与那细巧的针工形成偌大的反差!而唯一不变的,是那拈针的手指间始终缠绕着的一种柔柔的亲切而温馨的气息。
位于县郊一隅,父母留下的那座小院和一排老屋,除小弟一家还住着几间,父母的卧室已空了九年了——从母亲也离世时算起。这几年不断传言那一带要被征用、拆迁;此番回乡,传言尤盛。不管是否真确,未雨绸缪实属必要,这更促使我趁机顺带整理一下尚余的父母遗物,以防突如其来时因忙乱而丢失散弃。何况届时我又很难在场呢。
于是与妹妹、弟弟并弟媳来到老屋里查看。只见除了几件油漆斑驳的旧家具,空荡荡的屋子似乎再没有什么值得保留的东西。但到底是女人家心细,弟媳说有只木箱里还盛着咱妈的不少衣服哩!虽无人能穿,扔了怪可惜。妹妹说她也一直惦记着,只是偶然翻捡起那些衣物就免不了一阵伤心,以至搁置到现在。
箱子遂被打开。一阵香料的气息扑面而来,原来箱底放了不少花椒、大茴,是防虫子的,而又没有樟脑的异味,足见母亲生前过日子的心细;而一件件洁净的衣服叠放得那般整整齐齐,更是令人不忍翻动。我们小心地一样样拿出,有母亲的羊毛衫、坎肩、夹袄,更多的是大襟的布褂,都是春秋天与夏季时穿的。不由想起母亲病重是在冬天,这些衣物当是她在入冬前仔细洗晾好收进箱子,准备来年天暖时再穿的。孰知老天无情,从此母亲缠绵病榻,一病不起,直到去世——她是再也没有穿过它们,连开箱再看一眼都不曾啊!
只知道母亲的棉衣好一点的大都送了人,还有的在殡葬时烧掉了,作为贴身遗物,这一箱衣服给我一种意外的慰藉;睹物思亲,更给我强烈的冲击与难以自持的伤感。尤其那些大襟布褂,每一件都是母亲亲手缝制的。虽不过极其普通的布料:七、八十年代后流行的的确良、涤卡、混纺丝棉之类——从我记事起原就没有见过勤俭的母亲穿过什么绫罗绸缎,蓬门未识绮罗香呵!但裁剪之合体,针工之精细,简直与机器做出的如出一辙。那缘口的针脚整齐、细密而匀称,不在亮处仔细瞅,根本看不出来是手缝的!那用碎布条巧妙缝合、盘成的布扣与纽袢儿,扣在一起有如一只只立在花瓣上的小蜻蜓……每件衣服显得那般秀朴、美观而省俭。要知道它们都是母亲年已七旬乃至八旬后缝制的啊!
作为男子,我完全不懂针黹,何曾留意过母亲的案边劳作?但自幼没少听人夸奖过母亲的针线活,没少见过登门向母亲求教的妇女;到伙伴家里玩耍时,身上的褂子鞋子常会引起婶婶姨姨们的惊奇打量与猜测,问是买的还是做的。当时只道是寻常,此刻,我才像妹妹那样,怀着敬畏与伤痛,轻轻抚摸着这凝注心血的每一件遗物。想象着母亲一面满意地穿上它们,一面在右胁下缓缓系扣的身影,不由得泪落满襟!
自然,这些老式的大襟褂子,代表着一个消逝的手工时代。那个时代并不遥远,在我的青少年时期,针黹,还是老百姓最直接的生存之需与持家之本啊!不由想起母亲大半生为我们精心做过的无数的衣物,除了年近九旬时还曾拼着精神,执意用先父的旧棉衣为我改做的那件小棉袄,其余的早就湮埋于岁月的烟尘了。遥想我们兄弟六人加上小妹,在参加工作与自立前,春夏秋冬,从头到脚的全副武装,哪一件不是母亲一针一线缝出来的呢!作为七个孩子的母亲,她那一手绝好的针线活,除了源于做事认真,源自于爱,还来自于今天已很难想象的日夜不辍的劳顿!从我记事起,无论深夜醒来、黎明恋床,总见母亲油灯旁飞针走线、举尺挥剪的身影。白天更不必说了,常常是为了赶制一件衣裳或一双鞋子而凝神提气,忘记了饥饿,以至父亲时常不无心疼地埋怨她:光记着做活不记着做饭!缘此,母亲结满老茧的双手,很早就糙硬似柴,指关节粗大而变形,与那细巧的针工形成偌大的反差!而唯一不变的,是那拈针的手指间始终缠绕着的一种柔柔的亲切而温馨的气息。
可惜这绝活因世道转变,家里媳妇、闺女们都没能传承下来,被到另一世界的母亲永远地带走了!幸而这仅存的衣物还留着母亲的体温与手泽,萦结着母亲的思绪与匠心,供我们虔诚地阅拜。于是我们决定每人保管、收藏几件。
一回到徐州,我即将它们拿给妻子和女儿看,她们都说是难得的民间工艺品。翌日是个大好的晴天,我将它们在阳台上晾晒了——毕竟它们已有十个年头没见天日了啊!当那深黑的、浅灰的、淡黄的、月白的、湛蓝的,细布的、粗布的手工衣物晾满一绳,刹那间,我觉得光阴倒流,多久未见到这样的场景了:恍惚又回到十来年前,回到父母的小院中,素爱洁净的母亲将刚刚漂洗完的衣服挂满铁丝,眼前又出现她清瘦而劬劳的安详身影……眼泪又禁不住流下来了。想起两句不知何人吟下的诗:珠珠泪似针纫处,寸寸肠如结线时。人说针线可称之母亲的艺术,眼前这几件母亲艺术的最好载体,于我岂止是纪念,更是不识字的母亲以针线书写给我的圣虔启示,一笔至昂的精神财富,启悟与勉励我,像她老人家那样生活与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