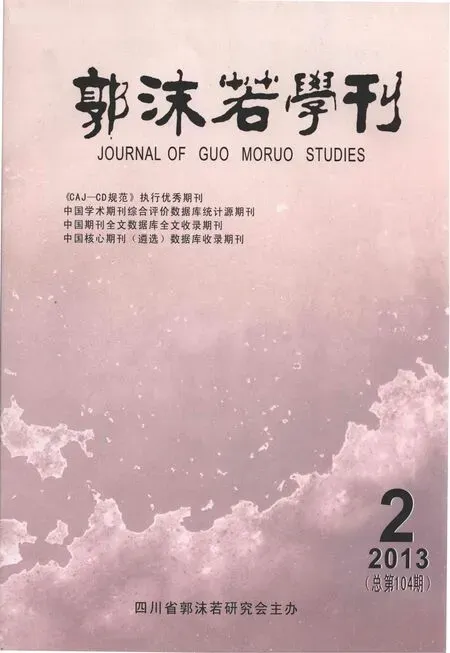文学史阅读中的《女神》版本及文本*
蔡 震
(乐山师范学院 四川郭沫若研究中心,四川 乐山 614000)
《女神》问世已逾九十年,九十余年后的《女神》早已经成为一个关于文学记忆的历史存在。伴随着《女神》成为文学记忆的过程,是对于它的阅读、评说、研究,当然还有出版。这些本身,也已经构成了一个历史存在。回看这个历史存在,有些情况和问题,是需要再行梳理做新的思考的。
一
《女神》问世伊始,即被人们评说,之后又有了研究。那时,人们所评说和研究的对象,的确是诗集《女神》本身。但是随着《女神》进入新文学史叙述与研究的视野和话语中,它作为一个研究对象,就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错位。我们来看一段《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中的文字:
在郭沫若早期诗歌里,我们找不着伤感和绝望的色彩,他有的是朝气,有的是信心和力量,他鼓舞着我们向前迈进。也不同于同时代其他诗人,他不把他的歌奉献给夜莺与无边的静夜,他歌唱的是“日出”,是“春之胎动”,是“大都会的脉搏”,是20世纪的动的精神。
如果不看上下文,这一段文字所论对象,无疑是“郭沫若早期诗歌”,但实际上,它是具体论述《女神》的一段文字。显然,在这里,作者以“郭沫若早期诗歌”置换了,或者说替代了《女神》。局部的研究对象,引出一个全称谓的论断。
在另一部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中,这样写到《女神》:“作者初期的诗大部分都收入《女神》集中,这些诗都充满了上述的思想内容。”言下之意,是谓《女神》收录了郭沫若“初期”的大部分诗作,可以作为郭沫若“初期”诗作的代表。但事实是,《女神》并非收录了郭沫若初期诗作的“大部分”(下文将述及于此)。
这两部文学史,都是新文学史(现代文学史)作为一个学科领域开始形成时期的力作,它们的叙事方式和研究模式基本上就是之后几十年文学史的写法(还有一部王瑶著《新文学史稿》,关于《女神》只有一段很简略的泛论,但叙事方式和研究模式与两部文学史无异)。而文学史的这种叙述和研究的模式,也决定了郭沫若研究,当然包括《女神》研究的方式和路数。所以,在此后的《女神》研究中,将作为一个具体研究对象的诗集《女神》,放大为“郭沫若早期诗歌”创作,或郭沫若《女神》时期诗歌创作的情况,是相当普遍的。《女神》只是郭沫若当时诗歌创作的一个选本,是诗人自己辑录的一个选本,即使诗人以为这五十余首诗可以代表自己那时的创作,但对于文学史的阅读和研究来说,无论如何它们是不可能涵括郭沫若早期诗歌创作的全部内容的。
这是《女神》作为一个研究对象,其历史文化内涵被放大了的问题。与此相关,也即是说《女神》被视为一个关于郭沫若早期新诗创作情况无所不包的考察对象,但对于它的研究在很多时候又只局限于从文本到文本,缺少对于文本之外,对于与创作相关的其它信息的考察和研究。
从学术史的视角看《女神》,还不能不说《女神》集外的佚诗。《女神》是郭沫若从自己留学经历的一段时间内所写作的全部自由体新诗中选录辑成,在这一段时间内他写成的诗作远不止《女神》中那56首。在我所辑录的《〈女神〉及佚诗》中,即收录有郭沫若《女神》时期创作的集外佚诗77篇总计97首。
《女神》何以选这样一些诗篇而不选另外一些诗篇,郭沫若当然会有他的考虑,也是他的自由,但就学术研究的意义——尤其是《女神》研究的涵义实际上是关于郭沫若早期新诗创作的研究——而言,《女神》并不是一个完整的文本研究对象。《女神》集外的佚诗,诗人自己可以弃之不选,研究者却不能视而不见,因为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女神》文本所没有包含的诗歌元素,或是未能传达出来的历史信息:散文诗、宗教题材的诗、口语体诗、写实手法的诗、儿歌形式题材的诗、金字塔形状的诗等等。从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到,郭沫若的创作为新诗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和更大的空间。
在文学史上郭沫若前期的诗歌创作是由《女神》与《星空》两个诗集为代表的,但两者是各自独立的叙述和研究对象,即《女神》的研究不包含《星空》。这种情况值得反思。事实上,两个诗集的作品是密切相关,不应分开来研究的。《星空》中的诗作,是与《女神》中的多数诗作有所不同(思想内容、情感表达),但它们的差异,实不过《女神》中所划分出的三“辑”之间的那种差异而已。张光年就曾提出过这个问题:“拿《星空》说,它基本上是《女神》时代的作品。这两部诗集中的若干首诗,作者在几次编集子的时候,往往彼此互见,连诗人自己也很难划分清楚。”《沫若诗集》的辑录,很清楚地表达了这层意思(应该也是作者的意思)。在该诗集中,《女神》和《星空》两个集子的作品是拆分后混编起来的,分为七辑。《沫若诗集》从第4版开始才增收了《瓶》《前茅》《恢复》三集的诗作,但它们各自以诗集的形式被辑录。对《女神》的研究,也应该包括《星空》的诗作。
总之,缺失了这样多内容的《女神》研究,还不能算是完整的研究,即便已经过去九十余年了。
二
大革命失败后,1927年末,郭沫若从广东回到上海,与创造社朋友们一起继续文学活动。不久,他大病一场。或许是因祸得福,在死里逃生病体痊愈后,郭沫若不但身心上“赢得了一番新生的欢喜”,而且又一次感受到“诗兴的连续不断的侵袭”。这种诗兴喷涌爆发的状态,按郭沫若所说,在他以往的创作经历中有过两次,一次是《女神》时期,一次是写作《瓶》的时候。而这一次“诗兴的连续不断的侵袭”,就是《恢复》的创作过程。从1928年1月初开始的不到两周的时间内,郭沫若几乎每天都有诗作写成,最多时竟有一天写成六首的。
亲身经历了一场血与火的社会革命运动,郭沫若的思想情感发生了巨大变化,所以《恢复》与《女神》《瓶》的内容和风格都大不相同了。就在这样一股创作激情涌动喷发的同时,郭沫若萌生了一个新的想法:“想改编《女神》和《星空》,作一自我清算。”这显然是一个与创作《恢复》联动的文学冲动,他把这样一个想法记在1月28日的日记中,而且似乎立刻就开始在做了,因为31日的日记中记载有“仿吾又送来《女神》和《星空》各一册。校读《女神》”之事。
然而,一个月之后,郭沫若即偕家人东渡日本,开始了他十年的海外流亡生涯。“改编”《女神》和《星空》,应该是没有做成,并且最终放下了。但郭沫若对于《女神》中一些诗篇的内容已经做了重要的修改,这就是收入《沫若诗集》中《女神》文本。
准确地说,《女神》不是以作品集的形式收入《沫若诗集》,《沫若诗集》拆分了《女神》、《星空》两诗集,与若干集外佚诗混编为七辑,《女神》集中有几首诗未编入《沫若诗集》。但《沫若诗集》中收录的《女神》诗篇,无论对于《女神》的文本还是版本衍变,应该都是非常重要的。
从版本变迁看,建国以后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4月版的《女神》和收入1957年3月出版的《沫若文集》第1卷中的《女神》,是初版本后《女神》的两个重要版本,它们都经过作者本人修订。收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卷的《女神》,则依据《沫若文集》的版本。两个经郭沫若自己修订的《女神》版本,除篇目增删的变动、编目结构的易动,最重要的文字内容的修订,基本上依据收入《沫若诗集》的《女神》诗篇文本。从文本的删削修改看,在195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女神》之前,还有收入重庆明天出版社1944年6月版《凤凰》与上海群益出版社1947年3月版《凤凰》中《女神》诗篇的文字修订,但是这些改动,也基本上是依据收入《沫若诗集》的《女神》诗篇文本。
文本是阅读、研究《女神》最基本的,也最重要的对象。从研究的角度而言,《女神》文本需要特别研读的应该有两个:1921年初版本的《女神》和1928年收入《沫若诗集》中《女神》诗篇的文本。它们是不能互相替代的。这一点从一开始的文学史叙述中就没有被提到,也即是说文学史并不包含作品版本文本衍变的内容。当然,一直以来的《女神》研究中,这一点也没有特别被注意,甚至缺乏清晰的认知。
仍以《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为例,该书在评说《女神》中所表达的“诗人的爱国主义精神”时,突出赞扬了诗人“高昂的反抗的、叛逆的呼声”,并以《匪徒颂》的诗句为例说:“他歌颂了‘古今中外的真正的匪徒们’,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歌颂了‘鼓动阶级斗争的谬论,饿不死的马克思’,‘不能克绍箕裘,甘心附逆的恩格斯’,‘亘古的大盗,实行共产主义的列宁’。”作者在这里引用的《匪徒颂》诗句,显然是想要说明郭沫若所表达的“反抗的、叛逆的呼声”,已经具有了无产阶级的观念意识,或者是将其定位于革命民主主义思想这样一个概念之中。
但是,《中国新文学史初稿》的论述,恰恰忽略,应该说是根本没有意识到《女神》的文本是修改过。书中所引用的《匪徒颂》诗句,是郭沫若在1928年修订《女神》文本中改订的文字。在1921年的初版本《女神》中,《匪徒颂》的这几句诗文是:“倡导社会改造的狂生,瘐而不死的罗素呀!/倡导优生学底怪论,妖言惑众的哥尔栋呀!/亘古的大盗,实行‘波尔显维克’的列宁呀!”诗人把英国哲学家罗素、遗传学家哥尔栋(哥尔登),与列宁并称为“一切社会革命底匪徒”。
将两个文本的诗句对比,所表达的思想内涵,即使不说南辕北辙,其差异之大,也是足以改变该书所论的。
《中国现代文学史略》引述了《凤凰涅槃》中“凤凰更生”的一节诗,以此评说该诗“充分表现作者对‘新’的热诚的向往”。其所引用的文字,也是郭沫若修订以后的文本。《凤凰涅槃》在1928年的文本修订中,是改动比较大的一篇。该诗结尾部分的“凤凰和鸣”,原有15小节诗句,改定的文本仅有5小节诗句,除第一小节文字相同,其他4小节文字均有改动。初版本中“凤凰和鸣”的诗文是这样的:
我们更生了!/我们更生了!
一切的一,更生了!
一的一切,更生了!
我们便是“他”,他们便是我!
我中也有你!你中也有我!
我便是你!
你便是我!
火便是凰!
凤便是火!
翱翔!翱翔!
欢唱!欢唱!
我们光明呀!
我们光明呀!
一切的一,光明呀!
一的一切,光明呀!
光明便是你,光明便是我!
光明便是“他”,光明便是火!
火便是你!
火便是我!
火便是“他”!
火便是火!
翱翔!翱翔!
欢唱!欢唱!
我们新鲜呀!
我们新鲜呀!
一切的一,新鲜呀!
一的一切,新鲜呀!
新鲜便是你,新鲜便是我!
新鲜便是“他”,新鲜便是火!
火便是你!
火便是我!
火便是“他”!
火便是火!
翱翔!翱翔!
欢唱!欢唱!
我们华美呀!
我们华美呀!
一切的一,华美呀!
一的一切,华美呀!
华美便是你,华美便是我!
华美便是“他”,华美便是火!
火便是你!
火便是我!
火便是“他”!
火便是火!
翱翔!翱翔!
欢唱!欢唱!
我们芬芳呀!
我们芬芳呀!
一切的一,芬芳呀!
一的一切,芬芳呀!
芬芳便是你,芬芳便是我!
芬芳便是“他”,芬芳便是火!
火便是你!
火便是我!
火便是“他”!
火便是火!
翱翔!翱翔!
欢唱!欢唱!
我们和谐呀!
我们和谐呀!
一切的一,和谐呀!
一的一切,和谐呀!
和谐便是你,和谐便是我!
和谐便是“他”,和谐便是火!
火便是你!
火便是我!
火便是“他”!
火便是火!
翱翔!翱翔!
欢唱!欢唱!
我们欢乐呀!
我们欢乐呀!
一切的一,欢乐呀!
一的一切,欢乐呀!
欢乐便是你,欢乐便是我!
欢乐便是“他”,欢乐便是火!
火便是你!
火便是我!
火便是“他”!
火便是火!
翱翔!翱翔!
欢唱!欢唱!
我们热诚呀!
我们热诚呀!
一切的一,热诚呀!
一的一切,热诚呀!
热诚便是你,热诚便是我!
热诚便是“他”,热诚便是火!
火便是你!
火便是我!
火便是“他”!
火便是火!
翱翔!翱翔!
欢唱!欢唱!
我们雄浑呀!
我们雄浑呀!
一切的一,雄浑呀!
一的一切,雄浑呀!
雄浑便是你,雄浑便是我!
雄浑便是“他”,雄浑便是火!
火便是你!
火便是我!
火便是“他”!
火便是火!
翱翔!翱翔!
欢唱!欢唱!
我们生动呀!
我们生动呀!
一切的一,生动呀!
一的一切,生动呀!
生动便是你,生动便是我!
生动便是“他”,生动便是火!
火便是你!
火便是我!
火便是“他”!
火便是火!
翱翔!翱翔!
欢唱!欢唱!
我们自由呀!
我们自由呀!
一切的一,自由呀!
一的一切,自由呀!
自由便是你,自由便是我!
自由便是“他”,自由便是火!
火便是你!
火便是我!
火便是“他”!
火便是火!
翱翔!翱翔!
欢唱!欢唱!
我们恍惚呀!
我们恍惚呀!
一切的一,恍惚呀!
一的一切,恍惚呀!
恍惚便是你,恍惚便是我!
恍惚便是“他”,恍惚便是火!
火便是你!
火便是我!
火便是“他”!
火便是火!
翱翔!翱翔!
欢唱!欢唱!
我们神秘呀!
我们神秘呀!
一切的一,神秘呀!
一的一切,神秘呀!
神秘便是你,神秘便是我!
神秘便是“他”,神秘便是火!
火便是你!
火便是我!
火便是“他”!
火便是火!
翱翔!翱翔!
欢唱!欢唱!
我们悠久呀!
我们悠久呀!
一切的一,悠久呀!
一的一切,悠久呀!
悠久便是你,悠久便是我!
悠久便是“他”,悠久便是火!
火便是你!
火便是我!
火便是“他”!
火便是火!
翱翔!翱翔!
欢唱!欢唱!
我们欢唱!
我们欢唱!
一切的一,常在欢唱!
一的一切,常在欢唱!
是你在欢唱?是我在欢唱?
是“他”在欢唱?是火在欢唱?
欢唱在欢唱!
只有欢唱!
只有欢唱!
只有欢唱!
欢唱!
欢唱!
欢唱!
对比改定的诗文,作者的修改,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是相当大的。以5节诗文替代15节诗文,其咏唱的节奏、韵律、抒情气势,所具有音乐性,以及作为结尾部分与全诗在形式构成上的协调等等审美特征,两者是难以相提并论的。在内容上,诗人尽量浓缩了自我思想情感的表达,但有些很重要的东西完全被删削了。如“我们恍惚呀”“我们神秘呀”两节诗文,显然更真切地表现了诗人当时在创造新世界的理想憧憬中复杂、纠结的思想情感状态。
这样的文本易动,在研究中应该是重要的关节点、关注点,但罔顾《女神》文本修订变化的情况,在迄今的《女神》研究中仍屡见不鲜(从其引文所用版本即能知晓)。
三
《女神》中的诗作基本上都发表于报刊,但《女神》被大众阅读,被研究者关注,是源自它的出版。在《女神》出版的历史过程中,又经历有版本、文本的衍变,所以,从《女神》出版发行的角度,来看其为社会,为大众,为文学史所阅读和接受,也应该有一些有益的启示。
出版《女神》的上海泰东图书局,原本是个没有什么出版目标、不起眼的小书局,在与郭沫若及创造社结缘后,泰东确定了倚靠新文学作为出版资源的目标。在此之后,泰东图书局有了较好的发展。在这一过程中,1921年8月《女神》的出版是其重要的节点。
当然,对出版机构而言,一本书的利好因素,在于它的印行量。由于出版史料的不完备和缺失,我们今天已经无法统计到泰东书局版的《女神》究竟出版了多少个版次以及发行的数量,但以目前的史料所能见者,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和几个数字:泰东初版本《女神》出版后次年出版了第3版,也即是说一年之内,出版了三个版次。之后,1923年出版第4版,1927年出版第6版,1928年出版第7版、第8版,至1930年,几乎都是以一年为间隔,没有间断地印行新的版次,每一版次印量2000册。再往后到1935年4月出版了第12版。这一版次虽由上海大新书局印行,但版权页仍以泰东图书局为出版者,沿用了泰东的初版本。
这样几个并不完整的、简单的数字,当然不只是针对泰东图书局的图书市场统计学意义上的数据。两三万册发行量的绝对数字,不能说有多么巨大(尽管在那时应该算是不小的数量了),但作为文学体裁之雅部的一部诗歌作品集能够长销不衰这一史实,对于《女神》在新文坛、在社会大众中被关注,被阅读的情形,都是一种很直接的印证。
《女神》部分诗篇的文本修订以后,作为诗集单独出版已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作品出版的情况与50年代之前有了很大不同(可比性当然也就因此而不同),这里暂不考察,那么,与《女神》文本修订有关的就是《沫若诗集》(还有其后的《凤凰》集)的出版。
《沫若诗集》出版的情况要复杂一些。上海创造社出版部于1928年6月印行了初版本,1929年3月再版,之后,《沫若诗集》转到上海现代书局,仍沿用创造社出版部版,从1929年12月起至1932年11月,陆续出版了第3版至第7版各版,每一版次2000册,其中第4版有两个版本(另一版本作《沫若诗全集》)。这是见之于文献记载的(见上海图书馆编《郭沫若著译分类书目》)。但在此之外,《沫若诗集》还有若干种或为盗版或属版次情况不明的版本。以我所见者,至少另有4种署为第3版、2种署为第5版的《沫若诗集》存世。其中署由上海新文艺书店出版的一种《沫若诗集》第5版,版权页上印数已累积至10000册,但是该种版本是否印行了5个版次不得而知。在时间上最晚近的一个版本,是由上海复兴书局于1936年5月出版的复兴版再版本(初版本未见),沿用的文本是现代书局第4版。《凤凰》集则有重庆明天出版社1944年6月版与上海群益出版社1947年3月版两个版本。
《沫若诗集》在那样多的正版本之外还有许多版本情况不明的版本(我们不好冒然断定其为盗版书,但即使是盗版本,它们也仍然能够印证该出版物的市场价值),其实际印行量大概还高于泰东版《女神》。这当然表明其有着很好的社会阅读需求、市场需求。
那么,包括《凤凰》集在内,辑录《女神》修订文本的《沫若诗集》,与初版本《女神》几乎在同一时间段内都各自不间断地再版出版,可谓比肩而立,携手并进。这样的出版史实,是不是也从一个方面解读或提示了《女神》的文学史涵义呢?这是值得《女神》研究、文学史研究思考的。
[1]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M].北京:作家出版社,1956-4.
[2]丁易.中国现代文学史略[M].北京:作家出版社,1955-7.
[3]郭沫若.《女神》及佚诗[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6.
[4]张光年.论郭沫若早期的诗[J].诗刊,1957,(1).
[5]郭沫若.离沪之前[A].海涛[M].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