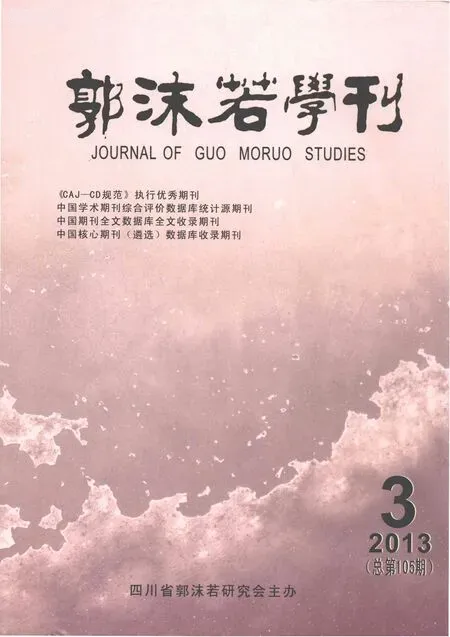“时代意识”与郭沫若的《读随园诗话札记》
曾 平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四川 成都 610071)
一
郭沫若的《读随园诗话札记》于1961年12月12日在广东从化温泉脱稿,《人民日报》从1962年2月28日起陆续刊登,相关学术讨论一直持续到1962年夏。这段时间对中国知识分子而言,是一段平静美好的时光。钱伯城在《1961—1962年:知识分子的短暂春天》一文中回忆说:“1961年的春夏之交,相对前两年绷得紧紧的气氛,上海知识界普遍感到政治空气有了松动,透出了点春意,虽然浓浓淡淡,捉摸不定。……松动的迹象之一:从这时开始到次年夏天,没有搞什么新的政治运动,政治学习也不像前两年那样没完没了,夜以继日了。……松动的迹象之二:报纸上重又宣传起沉寂已久的‘双百’方针,《文汇报》还在理论版上登了个‘百家争鸣’的篆字大图案,组织一些学者发表争鸣的文章。……松动的迹象之三:‘右派’分子摘帽的人数有所增加。……松动迹象之四:1962年3月间,传来了广州会议上周恩来和陈毅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消息,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从《札记》我们也可以感觉到当时宽松自由的学术氛围和作者轻松愉悦的心境,故《札记》更多流露了作者的天性及真实的学术思想、美学趣味。
在愉快的旅途中,郭沫若随身所带的消闲之书是他青少年时代的精神偶像袁枚的《随园诗话》。重读《随园诗话》,当年那个单纯热烈的少年已年届古稀,中国社会半个世纪的急剧动荡与政治风暴在他的精神世界打下了深刻烙印,这些因素均使郭沫若在重新与青少年时代的偶像进行精神对话时产生了迥然不同的感受。在《札记》的《序》中,郭沫若和盘托出了自己的这种变化:“袁枚(1716-1797),二百年前之文学巨子。其《随园诗话》一书曾风靡一世。余少年时尝阅读之,喜其标榜性情,不峻立门户;使人易受启发,能摆脱羁绊。尔来五十有余年矣。近见人民文学出版社铅印出版(1960年5月),殊便携带。旅中作伴,随读随记。其新颖之见已觉无多,而陈腐之谈却为不少。良由代易时移,乾旋坤转,价值倒立,神奇朽化也。兹主要揭出其糟粕而糟粕之,凡得七十有七条。条自为篇,各赋一目。虽无衔接,亦有贯串。贯串者何?今之意识。如果青胜于蓝,时代所赐。万一白倒为黑,识者正之。”曾经仰视的对象如今却发现不过如此,袁子才崇尚性情、不立门户的通达之见在此时的郭沫若看来也并没有太多新颖之处。借助“时代意识”提供的新尺度、新视角,郭沫若从《随园诗话》中看到了少年时代的自己无法洞察的层面,而写作《札记》的根本冲动不是重新向当年的偶像致意,而是亲手消解偶像的光环,将袁枚的《随园诗话》变成批判和审视的对象。这种向权威挑战的革命精神,既源于郭沫若本人争胜好强的个性,更是“时代意识”给予郭沫若的馈赠。比起青年时期的激烈张扬,老年郭沫若已含蓄低调了许多。他虽然十分肯定《札记》所见远在袁枚《随园诗话》之上,但又谦虚地将这一成绩归功于“时代意识”。那么,什么是郭沫若所说的“时代意识”呢?
其实,在涉及诗歌创作的内在艺术规律时,《札记》与袁枚的相通之处比比皆是。谈论艺术创作个中三昧的文字在《札记》中占了不少篇幅,显示了郭沫若作为文学大家的深厚艺术素养。由于这些文字常常与政治见解、时代精神无关,所以,郭沫若与袁枚的此类对话更像是两个老友的灯下对晤、旅途闲聊,虽有见解的差异,却言笑甚欢,时有惺惺相惜之意。而郭沫若采用了类似于中国传统诗话的札记体形式展开此番与袁枚的对话,颇有客随主便、入乡随俗的意思,本身就包含了对袁枚某种程度的尊重。袁枚的《随园诗话》与郭沫若青少年时代关于诗歌的美好记忆联系在一起,重读《随园诗话》,仿佛是在重温自己的青春岁月,尽管时移世改,但有关青春的记忆又如何能够轻易释怀呢?我们看到,当谈论到纯粹的艺术问题时,郭沫若一直保持着平心静气、风趣温和的态度,颇有传统士大夫中正平和的气质,全无当年进行文学论争时的剑拔弩张、盛气凌人。这类札记尽管发表了有关文学创作的精妙见解,但仍然不脱传统诗话的格局与风味,并不能让我们看到有多少迥异于袁枚的特见。可以肯定地说,让郭沫若自信《札记》“青胜于蓝”的地方绝不在此。
二
进入民国以来,采用中国传统诗话的外在形式撰写的学术著作并不多见。最有名的要属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和钱钟书的《谈艺录》。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从外在形式上看与传统诗话并无二致,来自西方的影响只是一股潜流,静静地在地表之下流淌。王国维将叔本华、尼采及康德的思想融入到中国传统诗学之中,使之成为诗话的内在血肉,而不是力图以西学对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造。但是,《人间词话》的内在理路仍然大大逸出了传统诗话的思想疆域,比如强调文学的非功利性,强调文学脱离政治获得独立等等,都与儒家精神背道而驰,是受西方哲学影响的结果。
钱钟书的《谈艺录》则立足于中西贯通的广阔学术视野再次刷新了传统诗话的格局与面貌。从小接受了中西合璧式教育的钱钟书,精通多国语言,又兼具作家与学者的双重身份,一直以全面“打通”不同学科、时空、语言、文化之间的界限壁垒作为自己的学术追求。出版于四十年代的《谈艺录》,将钱钟书的这种学术追求付诸实现。《谈艺录》由典雅古奥的文言写成,是一部研究中国古代诗歌的随笔札记。虽是一部以中国传统诗话形式写作的学术著作,《谈艺灵》却具有明显的现代意识,从容自如地将传统诗学理论与西方文学观念融会在一起,涉及西方哲学、美学、文学大师500余人的观点,其中包括精神分析、俄国形式主义、新批评等20世纪上半叶在西方出现的种种现代理论。《谈艺录》的治学方法深受中国传统学术思维的影响,精于训诂、考据与名物阐释,但它又从根本上颠覆了中国诗话的传统,将中国古典诗歌及传统诗学放在中西文化的交汇点上进行审视,放在古今融合、学科贯通的广阔视野之下进行观察,其目的是希望从中国传统诗学出发,进入一个更为辽阔自由的空间,探求人类共同的文化现象、艺术规律。钱钟书在《诗可以怨》一文中说:“人文学科的各个对象彼此系连,交互映发,不但跨越国界,衔接时代,而且贯穿着不同的学科。由于人类生命和智力的严峻局限,我们为方便起见,只能把研究领域圈得愈来愈窄,把专门学科分得愈来愈细,此外没有办法。所以成为某一门学问的专家,虽在主观上是得意的事,而在客观上是不得已的事。”这段话其实暗含了一层意思:虽然研究领域的狭窄是人类智识的严峻局限造成的客观后果,但真正理想的研究状态却是破除这种人为的壁垒,方有可能见到真相和全豹。钱钟书一生的学术努力,正是为了“打通”种种来自文化差异、地域差异、学科差异的无形壁垒,进入更为辽阔广袤的学术空间。
如果说王国维、钱钟书都力图用现代学术精神对中国传统诗话进行改造,那么,郭沫若则是力图用五四以来新的“时代意识”对中国传统诗话进行改造。比较《札记》与《人间词话》、《谈艺录》,前者与后两者之间内在的学术追求存在明显差异。早在发表于1928年的《桌子的跳舞》一文中,郭沫若就断言:“没有时代精神的作品是没有伟大性的。”而当五四新文化人普遍反对传统士人“文以载道”的主张时,郭沫若在发表于1930年的《文学革命之回顾》一文中深刻指出,五四学人同样是在“文以载道”,只不过,不同的时代,所载之“道”的内容会发生巨大变化:“古人说‘文以载道’,在文学革命的当时虽曾尽力的加以抨击,其实这个公式倒是一点也不错的。道就是时代的社会意识。在封建时代的社会意识是纲常伦教,所以那时的文所载的道便是忠孝节义的讴歌。近世资本制度时代的社会意识是尊重天赋人权,鼓励自由竞争,所以这时候的文便不能不来载这个自由平等的新道。这个道和封建社会的道根本是对立的,所以在这儿便不能不来一个划时期的文艺上的革命。”一直将表现“时代精神”、“时代的社会意识”作为造就文学作品伟大性前提的郭沫若,在《札记》中同样以“时代意识”作为审视古人的尺度和标准,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完成了对中国诗话传统的延续与改造。
虽然在创造社初期,郭沫若曾经倡导过“为艺术而艺术”的非功利性文学观,但从总体上看,郭沫若与王国维、钱钟书是非常不同的,他是一个紧跟时代潮流的文人,在更多时候,他不仅赞同甚至极力倡导文学成为政治工具、政治宣传品,成为时代精神的传声筒,成为现实政治的留声机。因此,我们看到,即便是闲云野鹤般的《札记》,它与现实政治的联系仍然远远超过了《谈艺录》和《人间词话》。在《谈艺录》序言中,作者虽然也提及那个时代的社会动荡与战乱硝烟,但从《谈艺录》本身我们却看不到时代风云、现实政治的投影,而在《人间词话》中,我们同样看不到王国维的政治态度和现实社会的风云激荡。比起郭沫若的其他著述而言,《札记》显示出难得一见的恬淡从容气质,但与当下现实政治、社会意识的全方位贴近,仍然是郭沫若写作《札记》的有意追求。这一方面限制了郭沫若的视野,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另一方面却也因此忠实记录了中国知识人当时的政治处境与心灵历程。从外在形式上看,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是用文言文写作的札记体著作,与传统诗话并无二致,但它内在的艺术理念、美学见解却深受康德、叔本华、尼采的影响,是中国传统士大夫接受西学全面洗礼之后的产物,在精神气质上与传统诗话貌合神离,是旧瓶装新酒的经典之作。郭沫若在写于1929年9月20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中如此评价王国维:“王国维,研究学问的方法是近代式的,思想感情是封建式的。两个时代在他身上激起了一个剧烈的阶级斗争,结果是封建社会把他的身体夺去了。然而他遗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品,那好像一座崔巍的楼阁,在几千年来的旧学的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而郭沫若的《札记》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保持了传统诗话的外在格局甚至是风韵神采,但“时代意识”却又赋予了《札记》强烈的当下感、现实感,使之最终仍然溢出了传统诗话的框架。
三
《札记》并没有对袁枚进行全盘否定。从郭沫若年青时代的文章看,他对中国传统学术,包括乾嘉学派的学者都保持了某种敬意。在五四以来大力提倡“打孔家店”的时代潮流中,郭沫若却再三对孔子给予了高度评价。在《札记》中,郭氏不再附和袁枚对清代考据派的一味批评,反而处处为乾嘉学派正名,甚至自己也身体力行,兴致勃勃地运用现代科学提供的新成果、新观念及最新史学发现对《随园诗话》涉及到的考据问题进行二度考证,不再单纯强调诗歌创作的个性、激情与美感,显示出向传统文学观念回归的倾向。在《札记》中,郭沫若和传统诗话的作者一样,文、史、哲不分家,考证功夫与文学鉴赏融为一体,史学眼光与文学趣味打成一片。这一点和钱钟书的《谈艺录》很类似,都旨在打破僵化的学科疆界,以更广阔的视野来看待文学问题。当然,钱氏主要是力图寻求古今中外共有的文心、诗心,而郭沫若则是回归了中国传统文人的学术视野。从个人所扮演的社会角色看,郭沫若比钱钟书、王国维更接近于传统士大夫:他既是政治家,也是文学家;既热衷于考据,又痴迷于论诗研文。郭氏对学术研究、文学创作及现实政治异乎寻常的热情,与中国传统士大夫“铁肩担道义,妙手绣文章”的人生信条高度吻合。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郭沫若的《札记》最终还是逸出了传统诗话的格局,焕发出独特的光芒呢?答案是明确的,即郭沫若一再强调的“时代意识”。郭沫若一直致力于用新的时代意识来重新解读、改造传统。他的第一部诗集《女神》就运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量典型意象来诠释五四时期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而他的戏剧作品,几乎是清一色的历史剧,同样是以强烈的时代意识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进行全新艺术诠释的结晶,是献给现实的蟠桃。对当代政治、当下社会的深度介入,使郭沫若对时代意识有一份特别的认同。从青少年时期开始,郭沫若就自觉与时代意识保持高度一致,热衷于做时代的弄潮儿,似乎从未想过要与当下的政治斗争、社会变革、时代浪潮保持某种适当的距离。于是,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政治动荡总是在郭沫若的内心激起惊涛骇浪,直接促成了郭沫若思想的变化动荡。写作《札记》的时代,所谓的时代意识,累积了中国社会半个多世纪以来政治格局、现实生活、社会意识的急剧变化,内涵极其复杂,既有五四精神的激荡,又有革命风暴的洗礼,更有建国以来主流意识形态的强烈浸染。
“时代意识”究竟赋予了《札记》怎样的特质,使之迥异于《随园诗话》的价值观,并迥异于任何一部传统诗话的价值观呢?1929年,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中曾说:“谈国故的夫子们哟!你们除饱读戴东原、王念孙、章学诚之外,也应该知道还有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没有辩证唯物论的观念,连国故都不好让你们轻谈。”在郭沫若看来,即使是谈国故,论旧学,也必须挣脱千百年来中国传统思维模式的束缚。以辩证唯物观为向导,以时代意识为指南,方有可能为国故研究带来生气与活力。正是基于这一看法,郭沫若的《札记》有意以“时代意识”为评判尺度,对清代大才子袁枚的《随园诗话》进行了一番颇具当下意味的全新解读,使《札记》呈现出有别于传统诗话的独特色彩。
具体来看,“时代意识”给予郭沫若《札记》的馈赠最为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底层视角与“原罪”意识。
从五四到建国之后,中国知识分子的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知识人从民众的精神导师和国民性的批判者,变成了需要接受民众教育的对象。在《札记》写作的年代,知识分子摘掉资产阶级的帽子,加上劳动者的称号,被视为对知识分子的加冕。这是以往任何年代都难以想象的事情。即便是倡导平民文学的五四时期,知识分子之于工农民众,仍然具有潜在的优越感。可到了郭沫若写作《札记》的20世纪60年代,经过历次思想改造运动之后,知识分子普遍具有了强烈的原罪意识,精神上的优越感早已丧失殆尽,工农大众成为需要仰视而不是需要教化的对象。怀着这种强烈的原罪意识,以下层民众的视角,来重新审视以教化民众为己任的传统士大夫,当然就会得出迥异于昔日的结论,尤其是对郭沫若这种真心实意认可“时代意识”合法性的知识分子更是如此。用当下衡量知识分子的“时代意识”来研究袁枚,这位昔日的精神偶像,自然是千疮百孔,不堪一驳。
底层视角确实带给了《札记》不同于《随园诗话》的全新视野。在《札记》中,我们看到了袁枚所缺乏的对女性命运的深切关注、对下层民众的由衷赞赏、对通俗文艺的热情肯定,一改中国传统知识人自古以来对下层民众的俯视姿态及玩赏女性的轻薄态度。在中国古代,即便是所谓的人民诗人,在对待民众的态度上,也难免有以救世主自居、以民众精神领袖自居的倾向。在郭沫若早年的历史剧中,这种倾向仍然十分突出。如屈原,如聂政,都被作者塑造成了民众的精神领袖,是万人仰慕崇拜的英雄。在《札记》中,我们看到,郭沫若对下层民众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改变,底层视角取代了早年的精英意识。这种变化,使他对袁枚的自我美化、自我吹嘘、自我膨胀有一份特别的敏感,所进行的批判自然也能一针见血、切中肯綮。士大夫这种过于良好的自我感觉,其实正是郭沫若这一代知识分子当年曾经有过的感觉。对袁枚的批判,实际上也是作为知识分子的郭沫若所做的一次自我反思与自我批判。
在《咏棉花诗》《关心农家疾苦》《马夫赴县考》《青衣之诗》《讼堂养猪》等多则札记中,郭沫若以下层民众的视角来看待与评价诗歌创作的优劣,得出了与传统士大夫完全不同的道德判断、价值判断。诗歌应该表现什么呢?是士大夫的趣味,还是劳动大众的情感?在“时代意识”的支配下,郭沫若给出的答案当然是后者。对《随园诗话》收入“青衣”之诗,郭沫若极为赞赏。但让他感到遗憾的是,袁枚的情感与趣味仍然不出士大夫的范畴,并没有与下层民众打成一片。由于极力要与下层民众的情感保持一致,郭沫若对于诗歌的乡土气息特别欣赏,努力在农民的生产活动中发现诗歌的美感,而且,郭沫若的婚恋观也迥异于传统士大夫。在《马粪与秧歌》一则中,郭沫若认为,女性嫁给不识字的马夫做妻子远胜于嫁给达官贵人做妾,并赋诗云:“与为参领妾,何如走卒妻?炕头逾软榻,马粪胜香泥。村汉骑知骏,秧歌唱入迷。可怜不解事,哀怨报情痴。”特别有意思的是郭沫若在《枫叶飘丹》一则中对一首深闺少女所作小诗的评价。诗其实写得不错,是说落叶满花径却无人来扫,倒是微风充当了清扫落叶的责任。写到这里,郭沫若大加感叹,认为作者太缺乏劳动意识,连扫落叶这种小事都不愿亲力亲为,是十足的旧时代的寄生虫,鄙夷之情溢于言表:“‘呼婢扫’三字尤其刺目。自己不能动手吗?何以必须呼婢?实则红叶满苔,正饶诗意,不宜动扫的念头。要扫,也不能袖手依人。”以这种方式来评价诗歌,在以前的士大夫是不可想象的,完全是“时代意识”使然。所谓“劳动者最光荣,剥削者最可耻”,是五四之后特别是新中国建立之后才有的价值观,而中国传统士大夫所信奉的一直都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观念。正因为站在劳苦大众的立场上看问题,所以第七十则《讼堂养猪》附录中出现了以“生猪”饲养为题材的诗作,首次以文学大家的身份为农民眼里的宝贝“生猪”洒墨挥毫,大加讴歌。以“生猪”为诗歌创作的题材,在郭沫若之前之后都是罕见的,而在郭沫若解放以后的诗作中,这类表彰农业生产、农民生活的诗作并不在少数。艺术趣味让位于政治需要和时代风向,使郭沫若的后期创作呈现出别样的色彩,这一点也表现于《札记》之中,使之具有了中国传统诗话阙如的乡土气息,并在某种程度上沦为现实政治理念的图解。
“时代意识”赋予的底层视角,不仅全面刷新了郭沫若对知识分子与民众关系的理解,也全面刷新了他对旧时代妇女命运的看法。比如针对袁枚想当然地将林黛玉视作妓女的错误,郭沫若一方面指出是由于袁枚对小说这种通俗文艺的偏见造成的疏漏,另一方面又深刻指出这种疏漏正源于中国传统士大夫对女性一以贯之的玩弄心态。在《鸿毛与泰山》一则中,郭沫若同样批判了传统士大夫对女性的玩弄心态,对旧时代的妇女深受夫权、纲常伦理的迫害表示了深切同情,尖锐批判了传统士人对女性的轻薄无情。这种眼光无不来自于五四以来追求男女平等、崇尚个性解放、反抗封建专制的时代精神的馈赠。
其二,科学兴趣与阶级意识。
自五四以来,崇尚科学成为主流意识形态。郭沫若早年曾经是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的拥趸者,在日本留学期间学的也是属于自然科学范畴的医科。在郭沫若一系列的学术著作甚至是文学创作之中,我们时常可以看到他浓厚的科学兴趣,常常以当年获得的医学知识来解释文学现象和精神现象,包括文艺家的气质、诗人的灵感等等。郭沫若曾说:“在封建思想之下训练抟垸了二千多年的我们,我们的眼睛每人都成了近视。有的甚至是害了白内障,成了明盲。已经盲了,自然无法挽回。还在近视的程度中,我们应该用近代的科学方法来及早治疗。已经在科学发明了的时代,你难道得了眼病,还是要去找寻穷乡僻境的巫觋?已经是科学发明了的时代,你为甚么还锢蔽在封建社会的思想的囚牢?”在《札记》中同样也不例外。有多则札记正是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对《随园诗话》提到的现象进行解释,这种解读方式在中国传统诗话中极为罕见,得益于中国自近代以来对西方自然科学的大力输入,得益于中国近现代以来科学观念的逐渐建立与普及,尤其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对自然科学的普遍崇尚息息相关。
以阶级观念、阶级意识来解读《随园诗话》也是《札记》的特点之一,比如其中的《草木与鹰犬》《黄巢与李自成》《农民与地主》等三则,从小标题上就可看出特定的“时代意识”赋予郭沫若的阶级意识与阶级观念。而在具体的解读过程中,郭沫若下意识地对古代的诗人划分阶级成分,可以看到当时的政治气氛对郭沫若思维方式的巨大影响。虽然从阶级立场、阶级意识的角度对中国古代诗人及其诗歌进行解读分析,未尝不能提供独特的眼光与洞见,未尝不能展开新的视野与思路,但如果以僵化的阶级斗争图式、阶级立场划分来解读诗人,将诗歌片面理解为阶级意识的载体,一方面放大了诗歌的政治功能,另一方面也忽略了诗歌的美学意义,造成诗歌批评的惟政治化倾向,最终使诗歌创作的评价尺度产生严重偏差。
“时代意识”与古代诗话形式的结合,使郭沫若的《札记》不同于任何一部传统诗话,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反映了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思想界的巨大变化与知识分子进行自我更新、自我救赎的精神成果。不过,“时代意识”既赋予了郭沫若卓识,使他能够发前人之所未发,见前人之所未见,为读者提供了全新的阅读体验与思想成果,并成功摧毁了袁枚这位曾经的精神偶像,但同时也因“时代意识”的深度介入,妨碍了读者对袁枚及其《随园诗话》进行历史还原的可能性,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郭沫若对袁枚诗论的解读落入某种特定的盲区。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时代意识”之于郭沫若的《札记》,亦是如此。
[1]钱伯城.问思集[M].上海:中西书局,2011.
[2]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十六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3]钱钟书.七缀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4]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