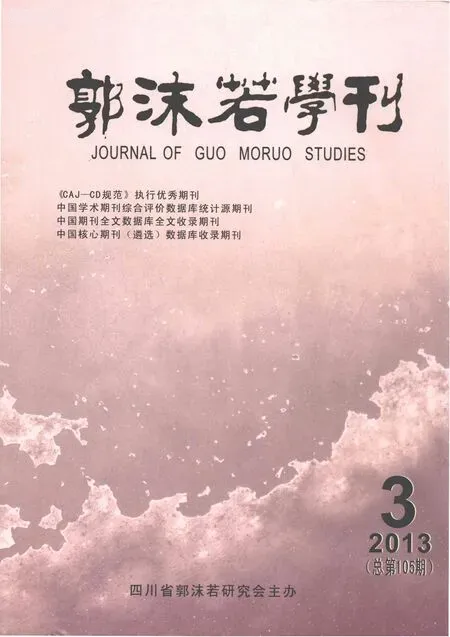郭沫若游学家书中的交通文化*
张建锋
(成都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四川 成都 610106)
郭平英、秦川编注的《敝帚集与游学家书》收录了郭沫若68封寄给父母、兄弟的书信,时间从1912年6月至1923年1月,跨度为十年半。这些书信写于国内的成都、武汉、天津、北京和日本的东京、冈山、福冈等地,是郭沫若离开家乡四川乐山,在外求学期间。除了能够“了解郭沫若青年时期的志向抱负、生活履历、学业成绩,还有生活趣味、家庭亲情”之外,也能反映当时的交通路线、交通工具和邮政状况,成为珍贵的交通文化记录。本文结合郭沫若的回忆《初出夔门》对此进行论述。
一、郭沫若出川留日的交通路线
1913年6月,天津陆军军医学校来四川招生,录取了6名考生,郭开贞(郭沫若本名)是其中之一。郭沫若因此出川到天津。郭沫若从成都出发,到重庆后,于1913年10月17日在给父母的信中写到:“男第八号由成都出发”,“是日即宿茶店子。九号由小东路进行,宿龙泉寺。十号宿乐至县。十一号宿遂宁县。……十二号在遂宁暂息一日,因由此地下重庆时,当由水路进发,换轿觅舟,不免少延时日也。十三号晨下船,是夜抵东安县。十四号抵合川县,即从前合州。嘉定傅说之现在代理该县知事,故次日(即十五号)于合川复住一日焉。……十五号夜仍归宿船中。次晨(即十六号)复发,舟行二百余里,不到重庆三十里处宿焉。今晨八钟已抵重庆矣。在途共计十一日”。这封家书反映了当时由成都至重庆的一条交通路线及其路程、行程时间。信中所谓“小东路”或者“小川北路”,与通常说的“东大路”有别。当时的东大路是出成都东门,再经过简州(即今简阳)、资阳、资州(即今资中)、内江、隆昌、荣昌、永川、江津等地到重庆,路较宽阔,行路不难,但路程较远,费时要十多天。郭沫若在《初出夔门》中对不走东大路的原因作了说明:“因为军事初停,东大路的匪风甚炽,便选了小川北路,由简阳经过乐至、遂宁、合川等地,乘船由涪江南下以入重庆,也同样费了十天。”郭沫若陆行到遂宁后,改为水路由涪江而下,所经东安县(今潼南县)为民国元年新建县,治所梓潼镇。民国二年废省改道,东安县隶川北道潼川府。民国三年,川北道改名嘉陵道(道治阆中),东安县因与广东、湖南两省县名重复,又定名不久,地在潼川府之南故更名潼南县。
郭沫若由重庆走水路沿川江航线东下,乘坐的是当时川江上唯一的轮船“蜀通号”,该船只能开行到宜昌。到宜昌后郭沫若换乘外国船到汉口,于1913年11月3日在给父母的信中写到:“卅一号抵宜昌后,是夜即上大亨轮船。十一月一号夜开发,行两日夜,已于今午抵汉口矣。”郭沫若在《初出夔门》中回忆写到,他们一到宜昌,便“到日本邮船会社去买了当天午后要开赴汉口的XY丸的统舱票。当天下午,十几个小川耗子就跟虾蟹一样,一个二个被那从黄海以外凫来的庞大的水栖物吞进腹里去了。”“由宜昌至汉口的三天,的确是成了虾蟹。”可见当时从宜昌至汉口行程三天,日本轮船已有长江航路。据《中国日本交通史》载,除了汉口至宜昌线,还有上海至汉口线、宜昌至重庆线、汉口至湘潭线、汉口至常德线等。郭沫若的家书反映了当时长江航运的路线、行程及航运公司、船只的情况,很是珍贵。
郭沫若到汉口后,在汉口的客栈里住了一夜,1913年11月4日早晨到大智门车站,沿京汉铁路北上。前往天津的郭沫若是在保定下的火车,在保定的客栈里住了一夜,11月6日转乘的是专往天津的火车。因为超级慢,郭沫若由清晨一早上车,坐到了午后四点钟光景才到了天津。到天津后,于1913年11月6日在给父母的信中写到:“夜过黄河桥,长十九里,上悬电灯,下映河水,光明四灿,黄白相间,水声风声,助人快意。五号午后三钟,到直隶保定府,即由此下车。六号再搭车赴天津,午后六时始到。依此路线进行,比枉道北京较捷”。京汉铁路即芦汉铁路,光绪十五年(1889)张之洞倡议修建,至二十二年(1896)铁路总公司成立后方才正式开工,二十四年(1898)芦保段完成,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将卢沟桥铁路延伸修至北京正阳门,同时保定以南各段相继完成,三十一年(1905)黄河铁桥建成,全线直达通车。郭沫若的家书反映了当时北上天津铁路的路线情况、运行状况和黄河铁路桥的风貌,是比较难得的铁路交通文化记录。
郭沫若在赴日本前的1913年12月25日晚在给父母的信中写到:“兹已定明日搭乘京奉晚车,同张君次瑜,由南满、朝鲜漫游赴日。”郭沫若在《初出夔门》中写到:“次瑜的路线是决定由京奉铁路经过朝鲜的,二十八号的晚上照着约定了的时间到北京东站去聚齐。”这个回忆里的时间有误,对照当日寄出的明信片上的邮戳,应为1913年12月26日。傍晚时分郭沫若从北京正阳门火车站登上京奉列车东行。27日清早出山海关,当晚到达奉天(今沈阳),在南满车站日本租界里的日本客栈住宿一日。28日晨从奉天搭乘日本火车沿安奉铁路东行,当晚抵达安东。过海关后,换车驶往朝鲜境内。29日早晨列车途经朝鲜旧京汉城(今首尔),当晚到达釜山。郭沫若在1914年2月13日写给父母的信中说到:“由南满、朝鲜绕道陆行,路费用去一百元。”郭沫若的家书反映了由京赴朝是经过京奉铁路转安奉铁路,过安东海关后再换车入朝的路线情况,还记录了沿线的主要行经站点和全程的路费,殊为难得。
二、郭沫若游学家书中的现代交通工具
郭沫若从成都出发,乘坐的交通工具是传统的轿子和帆船。他在《初出夔门》中说当时东大路“交通工具是原始的鸡公车、肩舆和溜溜马。”到了重庆后,踏上出川的路途,郭沫若开始接触现代交通工具。1913年10月17日写给父母的信中说到“蜀通号”轮船。“蜀通号”轮船是川江航线上最早定期航运的现代轮船,1910年2月通航,每月往返两次。郭沫若在《初出夔门》中回忆到:“便乘着当时川河里所有的唯一的一只轮船‘蜀通号’东下。”“就这样,我们,至少是我自己,自有生以来才第一次搭上了火轮之船”。1913年11月3日写给父母的信中说到,去宜昌乘坐的是大亨轮船。比照《初出夔门》中的回忆,“大亨轮船”是日本邮船会社的“XY丸”轮船。
郭沫若是在汉口大智门火车站,乘京汉铁路的火车北上的。这是郭沫若第一次乘坐火车,本该有特别的感受,可他在《初出夔门》中写到:“和火车见面是有生以来的第一次,论理应该有些新奇的记忆,但无论怎样的搜索,所能记忆的却只是过磅时的麻烦,车站上的杂沓,车厢中的污秽。而尤其使人失望的是车行中所接触到的窗外的自然。”之后,郭沫若对由保定专往天津的火车有过更多的感慨:“这一趟的车怕是世界第一的超等慢车,每到一站都要停,停的时候比动的时候多,动起来也好像是沙漠中的骆驼走路。由清晨一早上车,坐到了午后四点钟光景才到了天津。”郭沫若对北京东站有好感:“到了车站,停不一会次瑜也到了。东站是很宏敞的,因为买票和种种手续还要费些时间,和我十分惜别的京官兄弟老三,便把我拉着在宏大的站厂里处处巡走。”到了奉天,郭沫若乘着有轨马车到南满车站的日本租界去,他有了新的感受:“那车站前租界街道的宏阔——怕有北京正阳门大街的四倍——才尽量地睁开了我惊异的眼睛。”直至坐上日本火车,郭沫若才算体验到了这种新式交通工具的“优越性”:“第二天清早搭上了安奉铁路的日本火车,一上车尤其使我吃了一惊。”“我们的车票是二等联络票,由北京一直坐到东京。由北京出发时所坐的京奉线的二等车,和京汉线的三等是毫无差别的。车厢既旧,又污秽,而座位是光的木板。一上日本车,就像真的进了乐园。座位是蓝色的天鹅绒绷着的,玻璃窗也明朗,地板也异常洁净,而一车所坐的都是日本人。我疑心是把车坐错了,坐上了头等,上了车后又私自跑下去看了一下车上写的字,依然是在腰间的一条蓝带上写着白色的‘二等’两个字。”可见当时日本火车的“内饰”,从座位、车窗到地板都是“现代化”的。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到,初次接触火车的郭沫若面对现代交通工具、交通设施的复杂心理和对现代文明的向往。
郭沫若到日本后,更多地接受了现代交通文明。他在1914年2月13日写给父母的信中说到:“近在神田研究日语,离寓有中国八九里远。每日步行而往,必乘电车而归,以午后五钟下课,急于赶饭故也。但坐电车,两次需合中国钱九十文,每月乘车必需一円半钱。”电车的快捷是不言而喻的,而花费也比较大。郭沫若由东京抵达冈山后,于1915年9月7日致父母信,说:“男已于本月同湖南李君来此矣,车行一日,觉无甚苦。”可见在日本坐车是比较舒适的,与他坐车从保定到天津时的感受是天壤之别。在1916年9月16日写给父母的信中,郭沫若说到:“方今世界大通,邮便走天下,较之古人家书万金,动需年月之苦,已不啻有万里咫尺之别。写真在望,犹男侍立膝前;家报飞传,犹男喋亵座右;虽远居异国,实则无异家居。”现代交通的发达,运输、邮政的发展,改变着人们的空间意识。郭沫若真有“天涯若比邻”的感觉。通过邮政传输,还增加了信息交流和文化交流。在1916年12月27日写给父母的信中,郭沫若说到:“此间新闻杂志所载写真插画,大有吾国内地所无者。……自明年始,当择一两种按月寄归,以娱二老,并以开通乡间风气,增广见闻也。”郭沫若试图通过书信方式寄回日本新闻杂志刊登的图片,进行信息交流,起到传播异域文化的作用。这无疑是较早的中国内地乡镇与国外交通的例证。
三、郭沫若游学家书中的邮政信息
郭沫若1913年动身出川,他的游学家书一直写到1923年,其投送、传递中的信息正可以反映民国初期中国的邮政情况。郭沫若的家书分两种:一种是平信,一种是明信片。两种信件都有邮戳,邮戳上的信息反映了当时的邮政状况。中国邮政是在西方国家的直接侵略下发展起来的,尽管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就创办了国家邮政(即大清邮政),民国三年(1914)中国已经正式加入万国邮会,但邮政事务实际掌控在外国人手里。这可以从郭沫若游学家书上的邮戳内容反映出来。通观游学家书上的邮戳,大致由上、中、下三部分构成,内容是投递时间、投递地址的汉字及其英语。至今留存清晰可辨的邮戳有:嘉定府邮戳,文字内容为汉字“嘉定府”及其英语“KIATINGFU”;成都邮戳,文字内容为汉字“成都”或“成都府”及其英语“CHENGTU”;重庆邮戳,文字内容为汉字“重庆”及其英语“CHONGKING”;万县邮戳,文字内容为汉字“万县”及其英语“WANHSIEN”;宜昌邮戳,文字内容为汉字“宜昌”或“宜昌府”及其英语“YICHANG”;汉口邮戳,文字内容为汉字“汉口”及其英语“HANKOW”;北京邮戳,文字内容为汉字“北京”及其英语“PEKING”。这些带英语的邮戳反映的是当时“客邮”在中国盛行的状况。
1912年6月郭沫若由成都寄给父母的信,用的是“大清邮政明信片”(CAR TEPOSTALE—CHINE)。贴的邮票上有“大清国邮政”字样,面值一分,图案为龙。这就是中国发行的第一套邮票——大龙邮票。这枚邮票表明,此时虽然已经进入民国时代,但民国的邮政还在大清的轨道上运行着。1913年11月郭沫若由汉口寄给父母的信,用的就是“中华民国邮政明信片”(CAR TEPOSTALE—CHINE)了。贴的邮票上有“中华民国邮政”字样,面值一分,图案背景是海平面上太阳光芒四射,中心是中华民国国旗,环绕国旗的是英语“THEREPUBLICOFCHINA”。1913年12月由北京寄给父母的信也是用的这款明信片。可见这是当时全国通行的普通明信片。
郭沫若寄回的家书,通过邮戳上的时间可以了解当时的邮信时间长短、邮路快慢和邮递路线。1912年6月13日写的明信片,成都邮戳的时间是6月14日,嘉定邮戳的时间为6月16日,可见从成都到嘉定费时3天。1913年12月25日写给父母的信为明信片,由北京邮出,二枚北京邮戳的时间均为“二年十二月廿六”,嘉定邮戳的时间为“三年正月十四”,可见从北京到嘉定费时20天。1914年8月1日写给父母的信,由日本邮出,上有邮戳五枚,其中两枚为日本邮戳,三枚为中国邮戳。一枚日本邮戳地名为“千□□山”(疑为千叶馆山),时间为“3.7.31”即大正 3年(1914)7月 31日,另一枚日本邮戳为东京(TOKIO)邮戳,时间为“1.8.14”(即1914年8月1日)。国内宜昌邮戳的时间为“三年八月十三”;重庆邮戳的时间为“三年八月廿二”;嘉定邮戳的时间为“三年八月三十”。可见这封从日本“千□□山”邮出的信,途经东京、宜昌、重庆,邮到嘉定用了31天。
由日本本乡邮回嘉定的书信中,有四封信的邮戳时间起止完整。1915年3月17日写给父母的信,由日本本乡邮出,本乡邮戳的时间为“4.3.18”,即大正4年(1915)3月 18日,TOKIO(东京)邮戳的时间为“18.3.15”,即1915年3月18日,重庆邮戳的时间为“四年四月七日”,嘉定府邮戳的时间为“四年四月十二日”,可见邮递这封信费时26天。1915年6月25日写给父母的信,由日本本乡邮出,本乡邮戳的时间为“4.6.27”,即大正4年(1915)6月27日,国内嘉定府邮戳时间为“四年七月廿三”,可见邮递这封信费时27天。1915年7月20日写给父母的信,由日本本乡邮出,本乡邮戳的时间为“4.7.20”,即大正 4年(1915)7月 20日,国内重庆邮戳时间为“四年八月十日”,嘉定府邮戳时间为“四年八月十五”,可见邮递这封信费时27天。1915年7月20日写给元弟的信,由日本本乡邮出,本乡邮戳的时间为“4.7.21”,即大正4年(1915)7月21日,国内重庆邮戳的时间为“四年八月十二日”,嘉定府邮戳的时间为“四年八月十六”,可见邮递这封信费时27天,而且这封信是由日本本乡发出,经汉口、万县、重庆到嘉定的。由此可见,当时从日本本乡邮出的书信,其投递的路线是到东京转投,至中国后沿长江航线由汉口到万县,经重庆到嘉定,正常时间大约27天左右。当时日本有定期轮船航线至上海、天津、青岛、大连、牛庄(今营口),而长江航线有上海至汉口线、汉口至宜昌线、宜昌至重庆线,邮路的通畅是可以保证的。照此可以推算,由日本本乡邮出的1915年7月5日写给元弟的信,其本乡邮戳时间“4.7.□”中缺失的时间可能是5。因为嘉定府邮戳时间为“四年七月卅一”,倒推27天,正好是大正4年(1915)7月5日。
由日本冈山邮回嘉定的书信中,有二封信的邮戳时间起止完整。1915年9月7日写给父母的信,由日本冈山邮出,冈山邮戳的时间为“□.9.7”,即大正4年(1915)9月7日,国内重庆府邮戳的时间为“四年十月一日”,嘉定府邮戳的时间为“四年十月十五”,可见邮递这封信费时39天。1915年10月21日写给父母的信,由日本冈山邮出,冈山邮戳的时间为“□.10.21”,即大正 4年(1915)10月21日,国内宜昌邮戳的时间为“四年冬月二四”,重庆府邮戳的时间为“四年十一月”,嘉定府邮戳的时间为“四年十一月十三”,可见邮递这封信费时24天。与前一封信相比,两者相差15天,可见当时邮路也是不那么稳定的,有时快有时慢。
这也可以从另外几封从日本冈山寄回嘉定的书信中得到验证。1916年12月23日写给父母的信,由日本冈山邮出,冈山邮戳的时间为“5.12.23”,即大正 5年(1916)12月 23日,国内汉口邮戳的时间为“□□十二月卅日”,万县邮戳的时间为“六年一月八日”,重庆府邮戳的时间为“六年一月十一日”,到重庆费时20天。1917年4月11日写给父母的信,由日本冈山邮出,冈山邮戳时间为“6.4.12”,即大正 6年(1917)4月 12日,国内一地(按残损的英文推测可能是“宜昌”)邮戳的时间为“六年四月廿三”,重庆府邮戳的时间为“六年四月二八”,到重庆费时17天。1917年5月4日写给父母的信为明信片,由日本冈山邮出,冈山邮戳时间为“6.5.5”,即大正 6年(1917)5月 5日,宜昌府邮戳时间为“六年五月十□”,重庆府邮戳时间为“□□□月二十”,到重庆费时16天。1917年6月23日写给父母的信,由日本冈山邮出,冈山邮戳的时间为“6.6.23”,即大正 6年(1917)6月 23日,国内宜昌府邮戳的时间为“六年七月三日”,重庆府邮戳的时间为“六年七月七日”,到重庆费时15天。与1915年9月7日那封信到重庆费时25天相比,相差最多的是10天,最少也是5天。从日本福冈寄回嘉定的信也是这种情况。1919年11月9日写给父母的信,由日本福冈邮出,福冈□□邮戳的时间为“□.11.10”,即□年11月10日。国内万县邮戳的时间“八年十一月廿三”,嘉定府邮戳的时间为“八年十一月三十”,费时21天。1922年1月11日写给父母的信,由日本福冈邮出,福冈箱崎邮戳的时间为“11.1.11”,即大正11年(1922)1月11日。国内邮戳四枚,可辨认的有“十一年二月一日万县”,说明到万县已费时22天,而前一封信到万县只用了14天,相差7天。
再看几封从日本邮到重庆、成都的信,情况就更清楚了。1914年9月29日写给父母的信,由日本小石川邮出,小石川邮戳的时间为“3.9.30”即大正3年(1914)9月30日,国内重庆府邮戳的时间为“三年十月十八”,到重庆费时19天。1914年10月28日写给父母的信为明信片,由日本东京邮出,上有邮戳四枚,一枚为日本东京邮戳,时间为“3.□.29”,即大正 3 年(1914)□月 29 日。国内邮戳三枚,汉口邮戳的时间为“三年十一月六”;万县邮戳的时间为“三年十一月十四”;重庆邮戳的时间为“三年十一月十七”,可见到重庆费时20天。1914年12月24日写给父母的信,由日本本乡邮出,二枚日本邮戳的时间均为“3.12.24”,即大正3年(1914)12月24日。国内邮戳二枚,宜昌邮戳的时间为“四年一月七日”,重庆府邮戳的时间为“四年一月十五”,可见到重庆费时22天。1914年10月22日写给五哥的信为明信片,由日本本乡邮出,上有邮戳四枚,一枚为本乡邮戳,时间为“3.10.27”即大正 3年(1914)10月 27日;二枚为国内成都府邮戳,其中一枚时间为“三年十一月二十”,可见到成都费时24天。综合上述情况可见,从日本邮回的郭沫若家书,国内的投递、转递路线大致是经汉口、宜昌、万县、重庆、成都到嘉定。
透过郭沫若游学家书邮政信息的梳理,我们能够看到民国初期的邮政状况。清末至民国初期掌控中国邮政的是“客邮”,而日本因为是邻邦,加之当时欧美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之中,日本趁机扩张海外航线,东亚往来航线几乎由日本操控。这既保证了日本的经济贸易往来,又促进了交通运输、邮政事业的发展。客观上也增加了中日两国间的人员交流、往来和信息沟通。郭沫若游学家书涉及的交通路线、交通工具和邮政信息,成为珍贵的交通文化史料,可以补史书之阙。从郭沫若游学家书的个案,可见当时中国交通之一斑。
[1]郭沫若.敝帚集与游学家书(郭平英、秦川编注)[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2]郭沫若.初出夔门[A].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3]王辑五.中国日本交通史[M].上海:上海书店,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