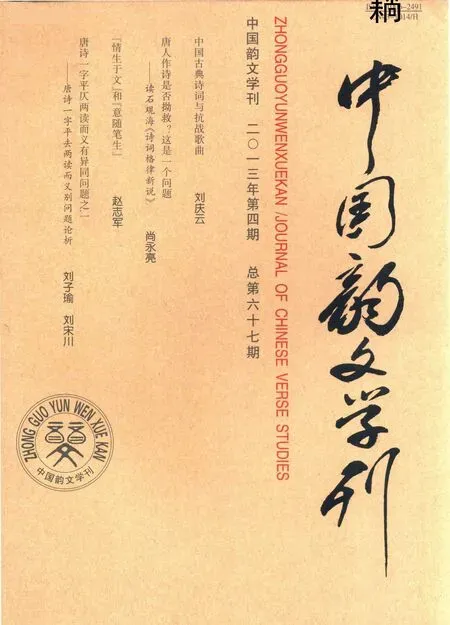荀子《赋篇·佹诗》辩体述论——兼论“赋”之文体学意涵在先秦的萌芽
刘 浏
(北京物资学院 发展规划办公室,北京 通州 101149)
我们在细读中国古代经典文本时经常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即文学史或文学理论批评史上一些陈陈相因的基本概念和传统观念往往会自觉不自觉地影响我们的理解与判断,使我们先入为主地形成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并为印证结论去寻找依据。当我们碰到那些与既有结论不符甚至相悖的史料文献时,则不得不采取或避而不谈,或穿凿附会,或质疑其真实性的态度和做法,以至于某些结论并非(至少不全是)历史语境下的真实。比如,我们通常认为,“诗”与“赋”是各自独立、判然有别的两种文体,二者没有交集,一首作品不能既是诗又是赋。但是在这样一个观念背景下,当我们读到《荀子·赋篇》时,发现其中除“礼、智、云、蚕、箴”所谓“五赋”外还有《佹诗》及其小歌,就不由得产生疑问:《佹诗》是“赋”吗?若是“赋”,何以荀子名之曰“诗”?若不是“赋”,何以又隶属于《赋篇》?是后人在编排《荀子》各篇章时的“误入”?抑或是在荀子时代,“诗”、“赋”本同义?又或者整个《赋篇》纯系伪作,为后人假荀子之名羼入?在荀子时代,“赋”是否已经有了区别于“诗”的文体学意涵的萌芽?当代学者有论及此,歧见颇多,下文拟结合前人之研究就这些问题加以辨析。
一
前人对荀子《赋篇》的考释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七种:
(一)“赋”为“自作诗”
“赋”有自作诗与诵古人之作两义。唐孔颖达分别在《毛诗正义》和《春秋左传正义》中援引东汉郑玄之说,但文字略有出入。《毛诗正义》释《常棣》:
郑答赵商云:凡赋诗者,或造篇或诵古。所云诵古,指此召穆公所作诵古之篇,非造之也。《春秋左传正义》释“所为赋《硕人》也”:
郑玄云:赋者,或造篇或诵古。然则赋有二义,此与闵二年郑人赋《清人》,许穆夫人赋《载驰》,皆初造篇也。
《春秋左传正义》所引郑玄语较《毛诗正义》少一“诗”字,或引起理解上的偏差,但只要一对比我们就会发现,两处文中的“赋”字或是作动词,或是表示一种创作行为,即“赋”可以是自作,也可以是诵古,但所作、所诵者皆为《诗经》作品或与《诗经》相类似的作品。
朱自清援引了这一说法,他认为“荀子《赋篇》称‘赋’,当也是自作诗之义”。但他没有解决的问题有二:一,既然是自作诗,为何要在篇目上冠以“赋”名,而不直接以“诗篇”为篇目?二,既然所作都是诗,为何前五首题目均不标名曰“诗”,独《佹诗》着一“诗”字?前五首与《佹诗》究竟在形制上有哪些本质区别?
(二)“赋”即“铺陈”
《文心雕龙·诠赋》开宗明义:“诗有六义,其二曰赋。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有学者立足于这一解释,将铺陈体物作为“赋”的基本表现手法和基本特征,并以此来对照解释荀子《赋篇》。如袁济喜云:“荀子的《赋篇》首次将自己的创作命名为赋。而他所说的赋,就是用铺陈的手法,描写五种事物的状态。”许结、郭维森则认为:“此五节(礼、智、云、蚕、箴)所以冠以赋名,也因为一是韵语,二用铺陈,论及一物必多方形容,设谜面形容一番,揭谜底又形容一番,称作赋是有其根据的。”此二说认为这五则短文皆用铺陈手法,所以荀子名之曰“赋”。但问题是,《佹诗》及其小歌没有使用铺陈手法,为何也同列于《赋篇》?
(三)“赋”即“隐语”(谜语)
有学者认为,荀子《赋篇》之“赋”乃“隐语”。朱光潜云:
(隐语)它是一种雏形的描写诗。……中国大规模的描写诗是赋,赋就是隐语的化身。战国秦汉间嗜好隐语的风气最盛,赋也最发达,荀卿是赋的始祖,他的《赋篇》本包含《礼》、《智》、《云》、《蚕》、《箴》、《乱》六篇独立的赋。
马世年在其《荀子〈赋篇〉体制新探》一文中认可了朱光潜的说法,他认为:在荀子的时代,“赋”并非严格的文体名称,而只是一种用来讽谏的表述形式。“隐”可用来讽谏,故可将“隐”称作“赋”。又因为刘勰《文心雕龙》的《诠赋》、《谐隐》两篇分别提及荀子的《礼》、《智》和《蚕赋》,所以刘勰是明确将“礼、智、云、蚕、箴”这五篇隐语称之为“赋”。至于《佹诗》之所以能与前五首并列,盖因《战国策·楚策四》“客有说春申君”章和《韩诗外传》卷四节录其小歌且有“因为赋曰”字样,刘向《别录·孙卿新书叙录》又说“因为歌赋”,因此,《佹诗》也可以称作“赋”。
马氏之说似乎告诉我们:在汉代人眼里,“诗”、“隐”、“赋”是同义的,是可以互相置换的。这一结论是否成立颇值得商榷,毕竟刘勰只说“荀卿《蚕赋》,已兆其体”,即《蚕赋》给后来的“隐语”开了个头,但并没有明确表示《蚕赋》就是“隐”,或只要是“隐”就可以称为“赋”。我们看《文心雕龙》,既有《诠赋》,又有《谐隐》,如果二者没有区别,刘勰何必分而论之?此外,《佹诗》的内容完全不是“隐语”,又如何与“隐”同义呢?
(四)《佹诗》为“赋”,“礼、智、云、蚕、箴”五篇为“隐”
赵逵夫认为,《赋篇》前五首为“隐”,但他没有将“隐”与“赋”视作同义语,正是因其不同,赵氏对《赋篇》的划分界属提出新的看法。他认为,前五首不应划入《赋篇》,《佹诗》及其小歌才是名副其实的“赋”。也就是说,前五首应为“隐篇”,《佹诗》及其小歌才是真正的“赋篇”。理由是:
第一,它明白标曰“佹诗”。《汉书·艺文志》说:“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不歌而诵谓之赋”。则所谓“诵其言谓之诗”的“诗”,同“不歌而诵谓之赋”的“赋”,实为同一概念。故《艺文志》又说:“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屈原的作品亦是既谓之诗,亦谓之赋。杨树达说:佹,假为恑。《说文》:恑,变也。变诗,犹变风变雅。所谓佹诗,正显示了从屈原以来歌诗向诵诗的转变。第二,此部分有小歌。所谓小歌,即屈原抽思中的《少歌》,与乱的性质相同。则这一部分在结构形式上与屈原之赋相似。第三,句式同于屈原《橘颂》及《涉江》、《抽思》、《怀沙》三篇的乱辞。第四,有些句子,是从屈赋化出。
赵氏援引杨树达之说,将“佹诗”解释为“变诗”,是不错的,但将“诗”与“赋”均出之以“诵”这一形式而将二者视为同一概念,似乎不当。许结、郭维森《中国辞赋发展史》则认为:
《赋篇》后有佹诗一首,或云应独立成篇。……此篇句式参差,末称“愿闻反辞”,又有小歌,当属楚辞体。所以称“诗”,亦犹《惜诵》之称诗。
上引二说都将《佹诗》与屈原楚辞相对照,认为二者形似,既然楚辞可称屈赋,那么《佹诗》亦可称“赋”;既然《惜诵》可称诗,那么《佹诗》亦可称诗。但细察之仍有很多不解之处:如果“诗”与“赋”本同义,《赋篇》只包括《佹诗》及其小歌,那么荀子为何不直接标名“佹赋”,岂不更符合“赋篇”之篇目?若前五篇是“隐”而不是“赋”,那么刘勰为何将荀子《礼》、《智》与宋玉《风赋》、《钓赋》并举,说它“爰锡名号,与诗画境,六义附庸,蔚成大国”,为“别诗之原始,命赋之厥初”?很明显他是把荀子这五篇(至少两篇)作品视作“赋”的起源。此外,屈原《惜诵》等楚辞作品既可称诗、亦可称赋,能用来证明《佹诗》既可称诗、亦可称赋吗?
(五)前五首为“赋”,《佹诗》为篇末所附
一些学者在论及《赋篇》时,以“末附《佹诗》”、“后附《佹诗》”、“篇末附有《佹诗》两首”等语一笔带过,仿佛《佹诗》及其小歌不属于正文。如郭建勋云:
《荀子·赋篇》虽总题中有“赋”字,但所辖的五个单篇并未命名为“礼赋”、“知赋”等,况且《赋篇》末尾又附有“佹诗”和“小歌”。《赋篇》之“赋”,非确指“赋篇”。
郭氏所言颇令人费解,《赋篇》之“赋”如果不是确指“赋篇”,那它到底指的是什么呢?
(六)《赋篇》系伪作
张小平《荀子赋篇真伪问题及研究》一文认为:一,班固《汉书·艺文志》对荀赋的评论非指今日所见《荀子·赋篇》中的作品,而是指《诗赋略》所列“孙卿赋十篇”,这十篇不包括今日所见《赋篇》和《成相篇》等杂体赋;二,《赋篇》的民间隐语特点以及各篇相对独立的杂凑性质,显示了它可能出自众多民间无名氏之手。至汉初,有人把它杂凑而成,托名荀子以行世;三,《赋篇》全文不见一“赋”字,且拟题格式与“孙卿书录”其它篇章不相符合,故推测其原本为“唐勒赋四篇”、“宋玉赋十六篇”这样的格式,即“荀卿赋若干篇”,在流传中脱字而被误作“荀卿赋篇”沿用至今,后人加标点为“荀卿《赋篇》”;四,《赋篇》中诸篇“隐语”是杂体赋,不能将此诸篇定性为赋之正体,更不能作为赋源之正宗。
《赋篇》真伪及其是否为赋源正宗暂且不论,既然张氏承认前五首单篇作品是班固所说“杂体赋”,那么与之并列的《佹诗》及其小歌也应是“杂体赋”,这就又回到了“诗”为何是“赋”的问题。
(七)“赋”为“直陈”,《赋篇》为一整体
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云:
这七段(按:即前五首加《佹诗》及小歌)合成一整篇,并非如前人所谓五赋末附一诗。“赋”字乃是这七段的总题。“赋”训“直陈”,言直陈作者对政治的意见。
此说没有引起学界的重视和认可,但提出了一种全新的解释,为理解先秦时代“赋”的含义提供了新的角度,可惜陆、冯两位先生没有提出这一说法的依据。
上述诸家之说,均未能解释清楚《佹诗》及其小歌为何是“赋”的问题。如果我们揭去后人强加于这一问题上的种种障目之叶,不用主客问答、铺陈描写等文体要素去比附之,而是直接将其放在荀子的时代去探究,或许可以得出耳目一新的结论。也就是,“赋”这一词在荀子以及之前的时代人们是如何理解与使用的?厘清这一问题,《佹诗》为何是“赋”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二
荀子《赋篇》中的文字除原书外,最早见于西汉前期。《佹诗》之小歌的后半段见于《韩诗外传》及《战国策·楚册四·客说春申君》,此二者皆不称《佹诗》或小歌,而径称之为“赋”。《客说春申君》所录如下:
(荀卿)因为赋曰:宝珍隋珠,不知珮兮,祎布与丝,不知异兮。闾姝子奢,莫知媒兮,嫫母求之,又甚喜之兮。以瞽为明,以聋为聪,以是为非,以吉为凶,呜呼上天,曷惟其同!
《韩诗外传》所录如下:
(荀卿)因为赋曰:琁玉瑶珠不知珮,杂布与锦不知异。闾娵子都莫知媒,嫫母力父是之喜。以盲为明,以聋为聪,以是为非,以吉为凶,呜呼!上天!曷惟其同!
与今传《佹诗》对照,《客说春申君》与《韩诗外传》所录,除略去《佹诗》开头“念彼远方,何其塞矣,仁人绌约,暴人衍矣。忠臣危殆,谗人服矣”六句之外,仅有个别文字或少量句子分合之差异。如《佹诗》句末之“也”字,《客说春申君》皆作“兮”字,而《韩诗外传》则合并两四字句,成一七字句,省略“也”、“兮”等语气词。文字上《佹诗》与《韩诗外传》基本一致,《客说春申君》则与二者差异较大,如“琁玉瑶珠”与“宝珍隋珠”,“杂布与帛”与“袆布与丝”,“闾娵子都”与“闾姝子奢”,“嫫母力父”与“嫫母求之”,“以盲为明”与“以瞽为明”等。总体观之,三者用字虽有小异,但意旨并无差别,三者系同一篇作品在流传过程中的不同版本,当无疑义。
刘向《别录·孙卿新书叙录》也说:
春申君使人聘孙卿,孙卿遗春申君书,刺楚国,因为歌赋以遗春申君。
刘向在这里说“为歌赋”,比《客说春申君》和《韩诗外传》多出来一个“歌”字。我们将《诡诗》及其小歌与“歌赋”相对照,似乎可以推测:刘向所说的“歌”指小歌,而“赋”指《诡诗》,二者合称为“歌赋”。
上引三部典籍,《韩诗外传》为西汉初年韩婴所著,《战国策》、《别录》是西汉末年刘向汇编史料文献而成。以此三者观之,战国时人已将《佹诗》视为“赋”,直到西汉末年,这一认知仍然不变。然此“赋”究为何义,需进一步分析。
至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诗赋略》始言“不歌而诵谓之赋”,很多学者认为这是“赋”在文体学上的首次界定,但我们重新细读班固原文,似乎并非此义。原文如下:
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言感物造耑,材知深美。可与图事,故可以列为大夫也。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春秋之后,周道浸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班固所引“不歌而诵谓之赋”不见于韩、毛诗传,可能引自《鲁诗传》,出处已不可考。但“不歌而诵谓之赋”与“登高能赋”并用,就说明“不歌而诵谓之赋”的“赋”和“登高能赋”的“赋”意思是相同的。“登高能赋”见于《毛诗传·鄘风·定之方中》,曰:
建国必卜之,故建邦能命龟,田能施命,作器能铭,使能造命,升高能赋,师旅能誓,山川能说,丧纪能诔,祭祀能语,君子能此九者,可谓有德音,可以为大夫。可见“升高能赋”是君子“九能”之一。孔颖达《毛诗正义》对“升高能赋”的解释是:“升高能赋者,谓升高有所见,能为诗赋其形状,铺陈其事势也。”按孔氏所言,“升高能赋”是指用“作诗”的方式来铺陈描述登高所见。但我们看《韩诗外传》所载孔子令诸弟子登高作赋,所“赋”却并不是诗。试看原文:
孔子游于景山之上,子路、子贡、颜渊从。孔子曰:“君子登高必赋,小子愿者,何言其愿,丘将启汝。”子路曰:“由愿奋长戟,荡三军,乳虎在后,仇敌在前,蠡跃蛟奋,进救两国之患。”孔子曰:“勇士哉!”子贡曰:“两国构难,壮士列阵,尘埃张天,赐不持一尺之兵,一斗之粮,解两国之难,用赐者存,不用赐者亡。”孔子曰:“辩士哉!”颜回不愿,孔子曰:“回何不愿?”颜渊曰:“二子已愿,故不敢愿。”孔子曰:“不同,意各有事焉 ,回其愿,丘将启汝。”颜渊曰:“愿得小国而相之,主以道制,臣以德化,君臣同心,外内相应,列国诸侯莫不从义向风,壮者趋而进,老者扶而至,教行乎百姓,德施乎四蛮,莫不释兵,辐辏乎四门,天下咸获永宁,蝖飞蠕动,各乐其性,进贤使能,各任其事。于是君绥于上,臣和于下,垂拱无为,动作中道,从容得礼,言仁义者赏,言战斗者死,则由何进而救?赐何难之解?”孔子曰:“圣士哉!大人出,小子匿,圣者起,贤者伏。回与执政,则由赐焉施其能哉!”诗曰:“雨雪瀌瀌,见晛曰消。”
子路、子贡、颜回三人所“赋”都不是诗,可见孔子所云“登高必赋”的“赋”不是(至少不一定是)“作诗”,而是一种兴之所至的口头陈说,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即兴演讲”。陈说的内容可以是登高极目所见之景,也可以是游目骋怀之志;陈说的形式不是拉长声调的吟唱(歌永言),而是不被曲调、情感充沛的演说;陈说的手段和普通对话不同,它在特定的场合下(登高)产生,且运用了丰富的修辞手法和高超的语言技巧,使人听之悦耳、闻之动心。所以班固才称其为“不歌而诵”,这里的“诵”绝非背诵或朗诵,而是一种感情充沛、言辞动人的演说,是先秦时期的一种口述文学样式。前文引述的陆侃如、冯沅君将“赋”训为“直陈”的说法或源出于此。
这种口述文学样式的生成与《诗经》渊源颇深。西周时期,礼乐兴旺,周天子与诸侯国之间以及诸侯国相互之间会面,使节们以吟唱《诗经》作品来委婉地表达态度和意愿,这是一种讲“礼”的表现,体现了一种高层次、高品位的规格,同时也带动了这一套含蓄有礼的外交辞令在社会上的流行。所以孔子批评其子孔鲤说:“不学《诗》,无以言。”进入春秋时代,列国纷争,礼崩乐坏,“学《诗》之人”如今“贤人失志”,于是“作赋以风”。这里的“风”不是指像荀子、屈原这样的失志贤人以作“赋”的途径来向君王或大夫表达劝谏讽喻,而是指他们虽“离谗”仍不忘“忧国”,在命途多舛、民生多艰的环境下,抛弃了“诗”那种优雅有礼的表达方式,而使用即景生情、借物言志的方式来作一番自我情绪或意见的诉说。因此,鲁迅说,“离骚者,因得忧患而发牢骚也”,陆侃如、冯沅君说,荀卿《赋篇》是“直陈作者对政治的意见”,不为无据。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合理地假设:“赋”在先秦时代,尤其是荀子的时代,已然有了一点后世文体学意涵上的萌芽,即它是一种早期口述文学的样式。虽然存世文献未见详载其作为这样一种文学样式的具体要求与规范,但我们差可判断:“赋”作为一种口述文学样式,不是一般人可以掌握和使用的,其作者必须具备一流的语言修辞能力,即所谓“能赋”。
三
能够证明这一判断的是较之“升高能赋”、“登高必赋”更早的一条关于“赋”的记载,即《国语·周语》记载周天子“听政”制度所提到的“瞍赋”:
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
三国东吴韦昭释“瞍赋”曰:“无眸子曰瞍。赋,公卿列士所献诗也。”韦氏对“瞍赋”的解释源自东汉经学家郑众的说法:“郑司农曰:讽诵诗,主诵诗以刺君过,故《国语》曰:瞍赋矇诵,谓诗也。”按郑氏解,“赋”和“诵”均指向“公卿列士所献诗”,但《国语》原文及其它地方均没有这样的暗示。且揆之常理,公卿列士既已献诗于前,又何劳瞍、矇“赋、诵”于后?叠床架屋,千篇一律,周天子岂非不堪其烦?因此,这里“瞍赋”的“赋”、“矇诵”的“诵”,包括前面“师箴”的“箴”,都应当是某种特定的口头陈说形式,而且指向不同的内容以期达到特定的目的。
在礼制完备的周代,周天子身边的每一种人都有其特定的地位和职能。三公九卿列士参议国事,遂献讽谏之诗;瞽为乐师,遂献曲;史为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为天子执政提供历史借鉴,遂献书。此三者均用“献”这一动词,这不仅是“进献”动作的完成,还包括公卿列士的吟唱、瞽师的演奏、史官的叙述讲解这些实质内容。同样,师、瞍、矇等人因其职责不同,或进箴言,或直陈,或隐语(此处用王力释“诵”之义项三:“用婉言隐语讽谏。《左传·襄公四年》:国人诵之曰:臧之狐裘,败我于狐骀。《国语·周语上》:瞍赋,矇诵。”,从不同角度、以各种方式向君王表达劝谏之义。所以,我们看到在此三者之下,又有“百工谏,庶人传语”等等,其目的都是为劝谏君王斟酌行事。
因此,“瞍赋”的“赋”当是一种独立于“诗”、“曲”、“箴”、“诵”之外的一种口头陈说形式,而且它对使用者的身份、语言能力以及使用时的内容和程式有着特定的要求和规定。当这种口头陈说形式从特定人物(瞍)的专门职能逐渐演变成为“大夫”、“君子”必须具备的基本能力之后,就有了前文引述的“升高能赋”、“登高必赋”等等说法,这也正是班固所谓“失志贤人作赋以风”之所本。
“瞍赋”的内容也绝不是“诗”,因为在先秦语汇中,凡提到“诗”,均特指《诗经》及与之相类似的作品,而且“诗人”一词在先秦典籍中从未出现过,在《史记》、《汉书》中出现凡二十三例,无一例外指向《诗经》之作者,这说明,从先秦直到汉代,人们对“诗”的认知和使用是十分固定的。
我们从“赋”字的本义上来看,为赋税之义,《说文解字》释作:“赋,敛也。”《尚书·禹贡》云:“厥土惟白壤,厥赋惟上上错。”《尚书》传曰:“赋为土地所生,以供天子。”可见,“赋”可作动词,亦可作名词。作动词即征敛,作名词即征敛之物。这是从天子的角度自上而下,如果换成被征敛者的角度自下而上,“赋”又有“进献、贡纳”的动词义和“进献贡纳之物”的名词义。征敛之物铺陈满庭供天子观看,则又引申出“赋”的“铺陈”之义。而当职掌者向君王陈述所献之物的名称、数量、形色、功能等等时,又引申出“赋”的“陈说”之义。这种陈说在特定的场合(王庭),面对特定的听众(天子或国君),当然就必须有程式的轨范与修辞的讲究。形式上,它可以是韵文、也可以是散文,可以是齐言、也可以是杂言,关键在于它是“不歌而诵”或曰“不歌而说”的口述文章。
当我们把先秦文献中凡涉及言语行为的“赋”之用例集中到一起来对照这一结论,我们发现,“口述文章”这种解释是完全说得通的。从“瞍赋”到“升高能赋”、“登高必赋”,再到“公入而赋”、“姜出而赋”、“卫人赋《硕人》”、“许穆夫人赋《载驰》”、“郑人赋《清人》”、“秦人赋《黄鸟》”等等用例,我们可以看出“赋”在先秦时代作为一种口述文学样式的演变脉络,即作者从周天子身边的特定官人,到春秋时期的诸侯国君、大夫阶层,再到战国时期的普通百姓皆可“赋”;形式从“瞍”之遵循特定规范的口述,到诸侯国君、大夫、士人及普通百姓的即兴口述;目的从最初的劝谏君王斟酌行事、谨慎为政,到充分表达作者的情绪、态度和意见。这种种变化围绕着唯一的、核心的不变,即运用丰富的修辞手法来口述的这一表达方式,这应当就是“赋”的文体学意涵在先秦时代的萌芽。到汉代,“润色鸿业、劝百讽一、铺张扬厉”的汉大赋只不过继承了先秦“赋”的名称,且逐渐淡化了“口述”和“即兴”的色彩,同时强化了主客问答式的书写方式和繁缛的修辞技巧,逐渐形成后世文体学意义上的“赋”的特色,而这已经与先秦“赋”渐行渐远、分道扬镳了。
行文至此,《佹诗》及小歌为什么是“赋”的答案已十分明显。那就是,荀子所称“赋”乃“口述文章”之义,而礼、智、云、蚕、箴等五首与《佹诗》及小歌等均为“口述文章”,荀子将其“口述文章”归为一类,遂名之曰《赋篇》。
[1](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疏.毛诗正义[M].十三经注疏[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周)左丘明传.(晋)杜预注.(唐)孔颖达正义.春秋左传正义[M].十三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3]朱自清.诗言志辨[M].朱自清说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4]袁济喜.中国古代文体丛书:赋[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5]许结,郭维森.中国辞赋发展史[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
[6]朱光潜.诗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7]马世年.荀子《赋篇》体制新探[J].文学遗产,2009(4).
[8]赵逵夫.屈原和他的时代[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9]李涤生.荀子集解[M].台北,学生书局,1988.
[10]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新著[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11]李希运.论荀况与宋玉的造赋成就[J].临沂师范学报,2000(4).
[12]郭建勋.汉人观念中的“辞”与“赋”[A].马积高、万光治编.赋学研究论文集[C].成都:巴蜀书社,1991.
[13]张小平.荀子《赋篇》的真伪问题及研究[J].江淮论坛,1996(6).
[14]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
[15](汉)刘向.战国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16](汉)韩婴撰.许维遹校释.韩诗外传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0.
[17](汉)刘向.别录[M].(清)姚振宗辑录.七略别录佚文[C].师石山房丛书(第一部)[Z].
[18](汉)班固撰.陈国庆编.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9]鲁迅著.傅国涌编.鲁迅的声音:鲁迅讲演全集[M].珠海:珠海出版社,2007.
[20](清)汪远孙.国语发正[M].皇清经解续编本.
[21]王力主编.王力古汉语字典[M].北京:中华书局,2000.
[22]刘浏.扬雄“诗人之赋”辨义[J].文艺评论,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