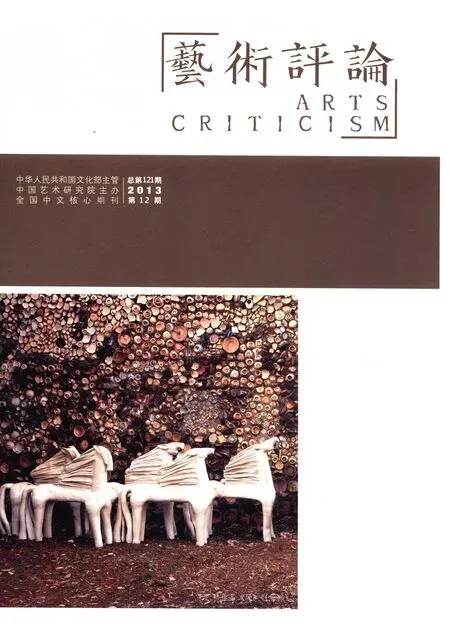幽默大家黄永玉
刘骁纯
刘骁纯: 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员

90高龄的黄永玉,是近百年来中国的文学大家、雕塑大家、重彩写意画的开拓者、新兴版画的奠基人。其艺有庄有谐,庄谐一身,本文主要从美术方面谈他尚未充分论述的幽默、诙谐、寓庄于谐。
知天命,从心欲
黄永玉说:“‘文革’中我也曾哭过一次,忍不住地热泪滂沱,那是读到巴尔蒙特诗句‘为了太阳,我才来到这世界’时,头埋在被子里,哭得像小孩子。”黄永玉本是个有泪不轻弹的刚强汉子,少年时代浪迹江湖,青年时代为朋友打抱不平犯过事,后来为民主和抗日投入了新兴木刻运动,再后来当了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并主持黄永玉版画工作室教学,官至中国美协副主席和全国政协委员。如此强人怎会如此大哭?从心理上分析,这应是半辈子追求光明却被“光明”踏在脚下的巨大委屈的彻底宣泄。
“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屈原《九章·哀郢》)他爱画《楚辞》,反复地画醉酒,也都是一种怨忿心结的精神释放。
这次宣泄极为重要。由此,他在知天命前后彻悟了天命,故有印章:“五十以后”;儿时的顽皮天性再次被唤醒,故又有印章:“老夫聊发少年狂”。从而,黄永玉杜绝了老舍悲剧在自己身上发生,并一步步开始了他的幽默人生。
所谓“老夫聊发少年狂”,主要是指在“少年”和“老夫”之间,他的人生和艺术一直以严肃或寓谐于庄的面目为世人所知。他14岁加入“东南木刻协会”,15岁在《大众木刻》首次发表木刻作品《下场》,19岁首次自印木刻集《春山春水》,从此一步步踏上左翼木刻运动。23岁加入中华全国木刻协会,参加反饥饿反内战学生游行。由于为沈从文等许多知名青年文人的作品作木刻插图,黄永玉名声鹊起。解放前创作了《马雅可夫斯基像》(1944)《拜伦像》(1944)等代表作,解放后创作了《阿诗玛》(1955)《饮》(1957)《小鹿你好》(1957)《春潮》(1961)等代表作。“文革”后转攻水墨彩墨,开创了排笔扫墨,彩绘花鸟人物的重彩写意画,创作了《白描水仙长卷》(1976)《省墩》(小鸟天堂,1978)《松下童子论》(2003)《白玉兰》(1974)《红荷图》(1976)《荷花》(2000)《今宵月色》(2010)等代表作……
但如果从这一段激情燃烧的历史岁月,追溯到他的童年少年时代,他却是个喜欢幽默的调皮顽童。他6岁开始着迷《时代漫画》、《上海漫画》,曾在家中木板墙上用毛笔涂鸦脸谱,胡乱写上:“我们在家中,大家有事做”,旧迹至今犹存。11岁找了个小画友办“美术学院”并自任“院长”。他有过逃学、记过、留级、留校察看的记录,但始终痴迷于漫画。他说:“我的‘美术事业’是从漫画开始的。”
因此,黄永玉知天命前后迈向幽默人生可以说是返老还童,天性回归。
幽默即错位
幽默即错位,即打乱惯性思维的错位引发的笑。黄永玉说:“颠倒常规,好笑;掩盖颠倒,更好笑。”他又说:“什么是幽默,我告诉一个说不清楚的专家,‘正常的情况失去平衡,就叫幽默感’。”
1980年代初,当他的重彩写意画受到“不是中国画”极大压力时,他与所有革新派的慷慨陈词都不一样,只是超然的一句话:“谁再说我画的是中国画,我告他。”对于中国画的百年大论争,他好像置于度外什么都没说,又好像千肠百回什么都说了。这就是幽默的力量。
他主张艺术好玩,开心,自谓湘西刁民。据广军回忆,黄永玉看了一位求教者曾说:“你的画很好,就是少了一点淘气。”
首先是树立“儿童本位”理念,以少年儿童为活动主体,在理解、尊重儿童心理情智发展的前提下,围绕儿童开展阅读推广活动。其次是建立“阅读分级”的理念,为年龄阶段不同的孩子提供差异性的读物,使得阅读更加有效和均衡。最后是建立“亲子阅读”的理念,发挥家长在引导儿童阅读中的重要性,让孩子和家长共同分享阅读的感受和乐趣。
黄永玉在《水浒人物》后记中说道:“水浒中男女多捣蛋纵酒任性乡民……尽为余当年浪迹江湖时之朋友熟人,街头巷宅,野火荒村,信手拈来,写日常见闻经验,边写边笑,席地坐卧,旁设茶酒,或互通新闻,或指天骂娘,混沌乐陶,不觉困惑矣。”这种超旷与逍遥,令黄永玉的艺术越来越不循常规,越来越不按规矩出牌,搅出了一片“世事洞明皆学问,落花流水亦文章”的新天地。
在万荷堂客厅挂着一幅方力钧赠的油画绣品,典型的方力钧风格,灰色、光头、无聊,挂在这里与挂在欧美大展上给人的感觉大不一样,不是意识形态的对抗而是师生对话。方力钧的玩世很严肃,黄永玉的严肃很玩世;方力钧自我无赖,黄永玉无赖世态。
黄式文图体
黄永玉式的文图体,是他的幽默的主要艺术呈现方式。他的文图体,与其说是文辅绘画,不如说是绘画辅文。所画蒋门神,是被武松打倒在地的大汉,题曰:“即是门神,不揍也扁。”文已幽默,但却不能不看画。一个大胡子赤膊者躺地,上身画成扁平。图中也有两处错位,一是蒋门神与年画门神的错位,一是“揍扁他”之类的口头语与扁平造型的错位。
《李逵苦吟图》有两处绝妙的错位,一是粗笨人的粗笨手中拈了一朵花,一是文字:“诗词面前人人平等”。图因文而进,文因图而妙,文图照应方得全趣。
黄永玉爱说反话,这一点不限于《大画水浒》。所画郑板桥,题曰:“板桥夫子提倡难得糊涂,其实是种很费力的打扮。他自己就做不到……如今处事,大多因为糊涂上当居首。”画题为《难得小心》(1991)。郑板桥本来说的就是反话,反话一旦流行就被扶正了,于是黄永玉又搞出一个反反话。郑板桥警世,黄永玉醒世。
动物幽默,是黄永玉动物画中十分迷人的部分。
鹦鹉,“鸟是好鸟,就是话多。”此调侃也。
狗,“狗和人,你讲句公道话,谁真诚?”此叹世也。
蛾,“人们!记住我的教训,别把一盏小小的油灯当作太阳。”此警世也。
蛇,“据说道路是曲折的,所以我有一副柔软的身体。”此“无厘头”也。
1965年,41岁的黄永玉在邢台参加“四清”期间开始写“动物短句”,“文革”中“动物短句”受到批判,1973年黄永玉随邓小平复出而复出,1974年黄永玉又随邓小平受批判而再受批判,他画的猫头鹰成为“黑画”代表作。
黄永玉画猫头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虽取自然形态,但作画并非无心,它正是黄永玉幽默人生的写照:看穿一切而又超然处之。“文革”批黑画时说他暗刺“文革”,并非无据,只是批判者心胸太窄,把宽泛的幽默锁定在一个小点上了。猫头鹰遭批,反倒使黄永玉画猫头鹰兴致大增,画了许多猫头鹰。1999年,黄永玉借青花瓷绘《鸱枭真经》将他命悬猫头鹰的所感所思淋漓尽致地宣泄出来。其所绘者,有立有卧,有正有背,有双眼睁有双眼闭也有一睁一闭者。题曰:“对人对事,对欢乐对难过,对美好对丑恶,对舒服对辛苦,对头头对手下”,凡有不顺眼想不通时,“以鸱枭为师即畅然通顺。曰眼开眼闭法,曰双眼皆开法,曰双眼皆闭法,曰背身法,曰卧倒休憩法。”“与人无干,奈我不得也。”
形的幽默
形的幽默指形象自身的幽默,它或因相貌组成因素的错位,或因相貌与相貌关系的错位而成为引人发笑的幽默。形的幽默对美术来说至关重要。
《大家张伯驹先生印象》(1992)有长长八百余言的悼念文字,字里行间满含对张先生的极高崇敬,所配图像,却是一幅漫画像。此画着意于龙钟老态——佝肩驼背,含胸抄手,扁嘴豁牙,花眼迷目,缓步踽行。这一切都不是好看的,但却是自然的。粉饰产生不了幽默。
这张画最突出者是土里土气的颇为夸张的灰色大袄,大袄里探出的小头细颈因不匀称而显得有趣,手里提着鲜艳的粉红小包因反差而显得有趣,老人探着下颌眯着眼睛看路的样子有趣,头上扣着的小毡帽也有趣……
这张画中一切有趣处恰恰又是可敬处,连那个粉红小包文中也有记述:一次吃饭偶遇张伯驹夫妇,在一角简单吃些东西后,张先生将剩余面包包起来,“提小包自人丛中缓缓隐去”。黄永玉说他当时“目送此庄严背影,不忍它移”。由此看来,幽默不是搞怪,形怪未必有趣,幽默来自神形意趣综合感受的襟怀和才能。
有一幅《满城风雨近重阳》,句出北宋诗人潘大临,黄永玉题曰:诗人诗兴刚起“适催租人至,从此世上原应有四句好诗,只得此头一句矣。”此处所引,乃潘大临的一句诗典故,故事的幽默是古人的,而由此引发的幽默形象却是黄永玉的。盘坐的古装人物如玩偶。看身体,合是书写之状;看头,180度扭向后方,惊异之状可同情可爱又可笑。此画的幽默方式是童叟错位,即将孩童天真稚拙顽皮可爱可笑的形神元素和成人形神元素奇妙地融合在了一起。
童叟错位是人物幽默十分常用(不是惟一)的方式,在金冬心、齐白石、华君武、关良的画中能见到,在汉代说书俑、民间雕塑和玩具那里能见到,在黄永玉的雕塑与绘画中也能见到。
伊甸园,是他惟一的性幽默题材,有水墨画也有雕塑。在这些作品中,对《圣经》中人类创生的故事做了痛快淋漓的调侃,这里不仅将古典油画中最后的遮羞树叶去掉,而且直接表现了性。在水墨画《伊甸园演义》(1995年)中,亚当被塑造为长须浓髯五短身材的老夫,夏娃被塑造为肥胖老妇,亚当吃了禁果阴茎勃起而惊愕,同样惊愕的夏娃紧盯着亚当的棒棒,题款为方言:“乜咬咗一啖就整成咁!”意为咬一口苹果怎么整成这个样子,印章“意外”恰为这对孩童般的天真男女点了题,另外两方印章:“聊发少年狂”、“有胆匪类”说出了黄永玉无法无天的放肆。这种放肆提出了一个不算小的问题:孩童般的无赖天真和成人式的负疚羞涩,对于吃了禁果的亚当和夏娃,哪个更贴切?
我特别喜欢黄永玉顽皮有趣的大写意雕塑,虽然他1992年以后才正式投入雕塑艺术创作,但一出手就不凡,很快就显出大家气象。
从黄永玉作品看,幽默与搞笑、滑稽不完全一样,它是笑的艺术而又不止于笑。幽默是智慧,是哲思,是臧否,是悲悯,是泛爱,是旷达,是开心,是调侃,是警世,是天性,是才华,是博学广识,是玩世不恭,是看破红尘,是形骸放浪,是笑天下一切之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