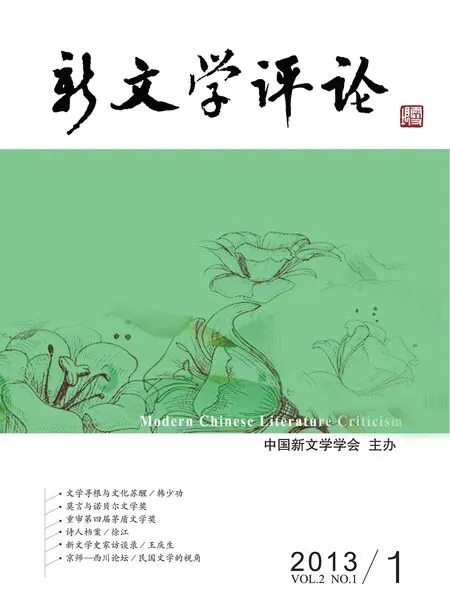一意且孤行
——论徐江
◆ 王士强
一意且孤行——论徐江
◆ 王士强
我这个战区
就一个人 一支枪
——徐江:《花火集·792》
作为诗人的徐江是有争议的,有的人喜欢他有的人不喜欢他,而且不喜欢他的人恐怕还要多于喜欢他的人。“江湖中人”(所谓“诗江湖”果真贴切)谈到徐江,首先想到的往往还不是他的作品,而是他的人,比如他的“好斗”、“刻薄”、“狂妄”,等等,徐江经常被标签化为一个“恶人”、“坏人”。这一现象其实是有问题的,至少,对一位诗人来说,关注其文本比关注其人更为重要,此其一;其二,即使是他的诗歌文本中有反道德、反伦理等所谓“恶”的因素,也不宜简单地将之与作者本人的价值取向划等号,因为他可能正是以之为手段而作出某种揭露、展览、批判,其间的情形非常复杂。以徐江作为观照对象,可能首先需要去除附着在他身上的厚厚的(而且是负面的)道德油彩,如此才可能较为客观地对其进行观察。诗人徐江的价值其实不在其“话题性”,而主要的在其诗歌文本的创造性。作为1990年代以来“民间写作”的重要诗人,他诗歌创作所独具的特色,他诗歌文本的价值与意义,可能都并未得到足够的关注和重视。本文拟主要以徐江的诗歌作品为对象,对徐江的诗歌创作进行总体式观照,在历史与诗学的双重视野中进行一定的价值界说。
一 有感而发、言之有物、抒情性
徐江在北京师范大学上大学期间开始诗歌写作,其时他与几位同学伊沙、侯马、桑克等形成了一个诗歌写作的小圈子,共同走上了诗歌之路。80年代的后期,他们可以说赶上了一个诗歌“青春期”和理想主义精神的尾巴,其写作受到了“朦胧诗”、“第三代诗”的影响,但他们摆脱“影响的焦虑”的时间很快,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个性,并在90年代站到了诗歌的“前沿阵地”,几位诗人也渐次成为后来被称为“90年代诗歌”的代表性人物。这其中,有感而发、言之有物、直接、简洁、有力等大约是他们的共同追求,而与80年代诗歌中多重的意象、繁复的隐喻、乌托邦情结、史诗追求、语言诗学等的取向判然有别。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他们是以对于80年代诗歌的“反动”而树立其诗人身份的。当然,即使是对同一个写作圈子来说,每个人也是不一样的,徐江、伊沙、侯马、桑克其实也不尽相同、各具特色,具体问题仍需具体分析。
徐江的诗大抵有感而发、率性而为、言之有物,其中可见真性情、真自我。这其实本应是诗歌写作的一种常识和常态,但如果结合其开始写作时1980年代后期的文化环境,却又不能不说是难能可贵的。因为彼时诗歌界“炫技”之风盛行,文化转向、语言转向、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史诗、解构……颇有些让人应接不暇。而在这些“新技术”的背后,折射的则是面对新世界的新奇及奋起直追、时不我待的焦虑、价值多元意义消解之后的虚无与混沌等诸种情绪的勾兑。在这样的情况下,守本心、发乎情、不做作、不故弄玄虚便显出它的意义来了。我们看到,徐江的诗虽然也有一些学徒期的模仿之作,但在有感而发、言之有物的方面却从未偏离,尤其是对于彼时非常流行的生硬晦涩、不知所终的文化寻根,以及进行词语的暴力拆解与肆意组合的语言游戏这两种写作维度,他都保持着高度的疏离与警惕,从这个角度来看,徐江起步期的创作即可谓持中守正。他回忆早期写作时写道:“我写我童年时的那种孤独,因家中没有住房而体会到的那种既具体又空无的零余感,我对城市四时变化的观察,对光阴逝去的困惑……这使我比别的初学者有了更开阔的捕捉诗的领地。”他早期的诗《窃贼》写道:“我选定一个黄昏/潜入家门/以便不被他们瞧见/我从异地归来//靠着厨房角落/我坐下来享受/瞬间的美妙/边盘算该偷些什么//后来我睡去/岑寂中被哭声唤醒/我看见童年的我泪流满面/用小手擦抹窗上的雾气/窗子越干净/外面的雾越深//我记起了此行的目的/对 我偷/他的哭声。”对于时间的敏感对一位诗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诗歌写作一定意义上正是对一去不返的时间的对抗,是对之的挽留。我们看到,徐江在这里甚至显出了某种“多愁善感”,这有些出人意料却又在情理之中。在《雁雀》中,他主要写的是童年的“孤寂”和“忧郁”:“童年时,我每每沉于/孤寂。有时/那种无言的抑郁/(你们知道的)/会袭来,抽打着/ 阳光下/我的嬉戏,玩偶,以及/水洼中飘浮的/一两枚枯黄的,树的幼叶。”他写小的时候:“我坐在教室里/面向黑板,有一点儿神不守舍。/没人注意我/我悄悄侧头,望着窗外:辉煌的/下午阳光中,麻雀在窗台跳/有一两次/白云浮动的蓝天上/一排雁群飞过去。”写这首诗时的“现在”虽然已经时过境迁,但是“我是多么地留恋,少年抑郁中/那一次次被迫记下的/残忍的下午/它尚含希望的夕光呵”。才二十岁出头却已开始“怀旧”,确可称得上少年老成,也显示了其之所以成为诗人的天赋异禀。
《辞书》、《为人类喝彩》在徐江早期的作品中较具代表性,它们都表征了作者面对历史、面对人类的一种普遍性认知与感受。如他在《辞书》中指出的“一排排辞书站在我面前/嘈杂的响声闹成一片/‘妈X、混蛋、妈拉个巴子、丫挺的/丢老姆、他奶奶、锤子敲你先人板板’//我现在不用翻书/就查清了人类的历史”,这种书写,显然与鲁迅对于“吃人”的历史的发现非常类似,只是徐江在这里面对的是“人类的历史”,指出的是在人类文明背面的一些文化基因和存在。《为人类喝彩》则取字面意义的反义,写了“原子弹的爹”、“爱滋病的妈”、“屈死鬼”、“当官儿的”、“姑娘”一次次向鱼贩子“盛开”、“狼变成狗”勤奋吃屎、“焚尸炉”加紧建设、“鞋刷擦着”月亮等等现象,这里的“喝彩”分明不是“喝彩”,或者说,是“喝倒彩”,其所指向的是一种负面而颇具普遍性的文化和社会状况。虽然是写较大的文化议题,但是作者从具象入手、从自我出发,因而并不给人虚浮空泛的感觉,相反是真切且能感人的。在1980年代末的诗歌作品《悼念一个北京的孩子》中,作者显然将“诗”与“史”合而为一了,诗的开头说:“北京的孩子死在故乡的街上/勒韦尔迪的书说/‘有时一个词足以把一首最美的诗葬送。’//没有火灾发生/没有水/吞没世界/但在那世上最漫长的黑夜/毁灭,披着滴血的大衣/在硝烟的城区潜行……”对于这样一个悲伤事件,“我看见/我们的童话顺流远去。/我想起有一个时期/一个叫狄兰·托马斯的青年俯身英格兰的草坪/为他的伦敦哭泣”。而此事在“我”心中引起的震动则不可谓不巨大:“而我的声音被紧紧锁住/再无笛声,/再无幸福的鸟儿翩然飞翔。/此刻 我置身欢歌人流却再难唱出一支歌/哪怕是首忧伤的怀乡曲/它当年宛如一面旗帜/在我与我同龄的少年心中飘扬。/北京的孩子死在他故乡的街上/那最后的钟声将为谁敲响?”这种现实书写既是对良知的考验,也是对诗歌技艺的考验,因为热烈的情绪很容易将诗歌本身灼伤、使艺术性下降。我们看到,徐江较好地实现了两者之间的平衡。
徐江早期的诗歌情感性很强,有较强的抒情特征,但其抒情方式与此前“朦胧诗”的隐喻、象征、公共抒情不同,其个体性更为明显,多书写与自我有关、眼前身边、亲身经历、深有感触的人与事。书写方式也大多直陈其事,并不“朦胧”,更不会让人不知所云一头雾水。他早期的作品如《好妈妈,老妈妈》用的甚至是一种比较“老套”的手法来书写对母爱、亲情的发现与珍视,在技法上或许没有太多可讨论之处,但是其表达的感情却是普泛性、永不过时的。这甚至可以作为徐江作品中的一个基调来看待:他对世界并非是没有爱的,他此后虽然不时以愤怒、忿恨对人,但那未始不是源于另一种更为强烈的爱,他只是较为吝啬地表达他的爱与赞美而已。徐江诗歌的“抒情”是作为一种基调、底色存在的,与知识化、理念化的写作相对,它内在地保证了诗歌的有效性与感染力。现代诗的抒情虽然不是唯一的,甚至也不是重要的,但实际上抒情之于诗歌又是不可少的,只是其抒情方式发生了较大的转变,正如徐江自己所坦言的:“‘反抒情’其实也是一种抒情,只不过它采取了异乎寻常的方式。艾略特、金斯堡都有抒情的因素。伊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算是我们这一代诗人中最会抒情的一个,他抒情得很巧妙。至于我本人,当然责无旁贷是位抒情诗人。诗歌就是抒情的嘛。如果有朝一日,诗真的不能抒情了,那你们想想,它成了什么?”
二 反乌托邦、口语、“民间写作”
1980年代中后期以来,于坚、韩东、伊沙、徐江等诗人代表了诗歌中祛魅的向度,他们使诗歌回到了日常的、生活的层面,在此基础上寻找和生发诗意,而不是一味地高蹈、飞升。这种反乌托邦的特质并非没有哲学上的追求和深度,而只是以一种较为平易的面目出现,相比不接地气、假大空的乌托邦写作,其内涵反而是更为丰厚的。在徐江的诗歌中,日常化、生活化、反乌托邦、反自我装饰是其一贯的特征,这一点与他所谈论的“俗人的诗歌权利”有关。在徐江看来,诗人写作应该是作为一个“俗人”(而非所谓的精英)来写作,应该真诚、有一说一,而不是故弄玄虚、自欺欺人。“我们能不能在保有自己诗歌趣味的同时,多写一些自己感兴趣、身边的普通人也感兴趣的作品?我们能不能把远离诗歌已有多日的读者,稍稍地再汲纳回一些到诗歌中来?我们能不能在写诗和谈诗时不那么满脸神圣、不食人间烟火?你在家中跟父母或妻儿说话肯定不是这个样子,那你干嘛不能用一副和生活中同样的表情嘴脸来轻轻松松地写诗呢?除非诗在你这儿不单是为和读者袒露心扉、还要用来‘做秀’!”他进而指出:“尊重俗人的诗歌权利。为俗人们写作。这个信念在我不算漫长的十几年写作历程中不时地跳出来,提醒我,让我看看我自己写的东西是不是过于狭隘、过于不知所云了。”这个问题的提出是有针对性和特殊意义的,其背景便是90年代以来的“知识分子写作”。注重知识体系、精神高度、技艺锤炼的“知识分子写作”在这一时期事实上占据了强势的地位,形成了一定的霸权,而对其他的诗歌存在造成了一定程度的遮蔽。我们看到,“90年代诗歌”一定程度的体制化、固化成为后来所谓“民间写作”的靶子。这里面的问题显然由来已久,有的学者便认为:“在这里,真正被动应战的,是一再被遮蔽、被忽略、被排斥在‘阐释话语权力’之外的‘民间’一方诗人,亦即非‘知识分子写作’圈内的诗人以及大量代表着更新的诗歌生长点的年轻诗人。”世纪末的“盘峰论争”是如上所述诸多矛盾的一次“总爆发”(徐江是这次会议的“主将”之一)。这一“爆发”打破了诗歌界的某种格局,并改变了新世纪诗歌的某种走向。这种论争当然涉及话语权的争夺和利益分配的问题,涉及具体的人与事的纠葛,但还是应该看到,其背后是两种诗歌观念、诗歌美学的交锋与对峙,这后一点是更为重要也更具意义的。这种论争为此后的诗歌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有着积极的效应。这正如诗歌评论家罗振亚所论述的:“这场诗学论争是先锋诗歌内部一次开诚布公的大面积的平等对话,众声喧哗激活了诗坛人人敢于站出来亮明观点的热烈民主氛围,打破了诗界十几年来秩序井然、温文尔雅却又过分沉寂的局面,增添了诗坛的生机和‘人气’,两种写作方式、审美观念间的冲撞为诗歌发展带来了契机。”这种变化也可以看作徐江、伊沙、于坚、韩东等的“民间写作”为新世纪诗歌所带来的一种积极的“诗歌遗产”。
在诗歌《住校诗人》中,徐江以自嘲的口吻写了自己也曾当过“住校诗人”(毕业以后没有合适的工作,仍然住在学校),他们“在宿舍烟雾和噪声里/把杯中白酒和劣质咖啡/送入腹中 我和朋友们/迈出成长的第一步//打工 被训斥/接受生活/对我等的流放/寂静中听一支曲子/落泪到天明”,“我在饥饿中寻求/这个国度最好的诗句/别人也一样/我们趟开杂草/把种子播下去”,结尾则“总结”了其普遍性意义:“所有对于虚妄生活的反抗/以及对美的坚定/也都是从那时开始的。”这种“对于虚妄生活的反抗”和“对美的坚定”道出了他价值取向和美学选择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在《给……》中,其诗句“我哭了/扑倒在消逝的美面前//真是这样的呵/这就是我已走过的半生”同样表达了与之类似的立场。这样的写作距离内心、心灵、感受更近,而距离知识、理念、修辞、技术更远,与之构成了一种紧张关系。如他自己所指出的:“许多当代诗的写作,仍是变了形的风花雪月、学识炫耀、理趣游戏和身心发泄,仍是一种‘伪现代’。”这和于坚在20世纪末发表的影响较大的文章《穿越汉语的诗歌之光》中所表达的观点非常接近:“这个充满伪知识的世界把诗歌变成了知识、神学、修辞学、读后感。真正的诗歌只是诗歌。诗歌是第一性的,是最直接的智慧,它不需要知识、主义的阐释,它不是知识、主义的复述……诗人写作是神性的写作,而不是知识的写作。在这里,我所说的神性,并不是‘比你较为神性’的乌托邦主义,而是对人生的日常经验世界中被知识遮蔽着的诗性的澄明。”实际上,他们也的确属于“同一阵营”,有着近似的立场与追求,都包含了对某种庞然大物的怀疑,都在颠覆一种权力构型、解构一种话语模式。
徐江诗歌在语言方面主要使用口语,这一特点在其“同道”伊沙那里更引人注目、为人所谈论更多。实际上徐江在口语的方面同样走得很远,他不但有创作实践方面自觉的探索,也有着理论方面的深入思考。如他指出:“现代诗里的‘口语’与日常的口语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它在书写的同时,能够进行自我提纯。那种把方言、时尚用词、网络用语随意搁置在诗行中的做法,充其量只能看作是某些水平不高、天赋有限者的一次冒险或试验。在很大程度上,它们更靠近人们所说的‘口水诗’,本质上与‘诗的口语’无关。两者犹如《水浒传》中‘李鬼’和‘李逵’之间的关系。”“诗歌中的‘口语’不是生活口语的原样,它们永远要经过作者天赋和其诗歌美学的剪辑与润色。纯天然的口语,多数时候在诗歌中呈现的是散漫,只有挤掉它身上的水分,现代诗对天然与自由的追求,才能得到充分亮丽的显现。”应该说,他对口语诗的这种认知是很深入、很到位的。口语具有活泼、生动、自由的特质,但同时也可能带来随意、复制、泡沫化、无意义化等问题,只有扬长避短,才可能真正为诗歌开辟出一条广阔的道路。我们看到,徐江等的口语诗写作,的确为1990年代以来中国新诗增添了一种新的气象和可能性,改变了此前诗歌的某种格局。诗歌中的口语写作(或者说口语诗歌)日益发展壮大、逐渐成为了当今诗歌中的主流,它或许包含了某些负面因素、产生了不好的影响,但其正面意义是应该首先被认识到的。无视这一点是不客观、不公允的。
三 一个人与世界的关系:“杂事诗”
自2002年起,徐江的诗歌写作发生了一次重要的转型,他开始了以《杂事诗》和《花火集》为主的长诗写作,而短诗作品则大幅减少。从徐江此前写作重感兴、非体系、随意、自然的特点出发,他本不会属意于传统意义上那种体大思精、结构严密、体系严整的长诗写作。那么,徐江之与“长诗”产生如此机缘,要么是徐江的写作发生了一次写作立场与观念上的变革,要么则是他所写作的长诗与一般意义上的长诗并不相同。我们看到,更多的应该是属于后者,他的写作主要的还是沿着此前的逻辑展开,他的长诗其实仍多为短制,其之为“长”诗更多的在于诗歌内在的精神线索、精神主题层面,而不在传统意义上的情节、结构、故事等层面。实际上,新世纪以来,类似的长诗写作的探索并不少,伊沙的《唐》、侯马的《他手记》、沈浩波的《蝴蝶》等,这些作品都在外在形式上比较松散,而主要是靠内在的精神一致性和向心力形成一个整体,甚至有诗人认为他们在“试图以集体的力量改变人们对长诗的观念”。徐江的《杂事诗》的确在文体方面走得较远,与通常意义上人们对长诗的理解迥然有异。仅此就值得人们进行认真的观照。
关于《杂事诗》的主题,徐江接受笔者访谈时说是“一个诗人与世界的关系”,他在与侯马的对话中则详细阐释道:“《河》是《杂事诗》一个突然性的开篇。某一天福至心灵,突然想为我从小就喜欢的海河(我很小的时候就常让母亲带着在它的浮桥、铁桥等各式各样的桥上走来走去)写一首颂诗,但人到中年,又不太想写成国外那种高蹈式的颂诗,我想从纯私人的角度,写写一个注定生命有限的人,与一条源远流长的大河的关系。写完之后,我渐渐发现它为我打开了一条通道:我可以顺着这条通道一直写下去,去勉力呈现一个诗人与他生存的世界的关系——亲密与冲突,并在语言的自由与控制、题材与呈现之间,探索抵达和谐的不同形式。”徐江是天津人,海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天津的“母亲河”,《杂事诗》自海河写起,其实颇具象征意味,它既是现实、地理意义上的一条河流,更是文化、生命、个人意义上的一条河流。如其诗中所写“那种清冷与陌生/令我深深为之沉迷/穿上好奇和渺小/重回空阔童年的某个场景/而每当/盛夏的熏风拂面/我仿佛看见了我渺茫的向往/正逆流而上”(《河》)。这条“河”与个人记忆、个人生活有关,构成了“我”的世界,构成了生活的某种边界,尤其是,它还是精神的家园和归宿,是与个人的追求和向往息息相关的。在这样的背景下来理解《杂事诗》,我们就会发现这首诗其实并不像表面看来的那么“杂”,正所谓形散而神不散,这首诗面对的是“我”与“世界”的二元结构(两者不一定对立,但确为两种不同的存在),处理的则是两者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有张有弛、直奔主题、旁逸斜出,但始终没有离题太远,而是构成了这种“关系”的不同侧面。这种“关系”因而是弹性、生动的,有张力,脱离了一元宰制,富于诗性与想象空间。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说,这首长诗表达的其实是一个人的精神世界或曰精神成长史,如此,全诗便具有了特殊的意义。
徐江的《开场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其与“世界”、与“人群”的态度。诗如下:“我今天/站在这里/只是代表/那些/被你们/过去/现在/将来/误读的声音//体会一下/孤独。”这里所说的“误读”与“孤独”显然并非个案或例外,而是一种根本性、宿命性的处境,如此表述既有着对于个体命运的体察,同时也显示了主体的强大。在《自我介绍》中,他如此表达自己的立场:“下面将要出场的这位诗人/在过去的二十年/创作生涯里//始终努力着/不像你们知道的/任何一位中国诗人那样//甚至/不像你们熟悉的/任何一个中国人那样//去写作/和思考/他怀疑任何宏亮的声音//也怀疑所有卑贱的声音/警惕地监控/每个阶段的自己。”诗人,的确既需要怀疑“宏亮的声音”,又需要怀疑“卑贱的声音”,更需要自我反思、反省,“警惕地监控/每个阶段的自己”。只有这种不停的怀疑、不断的反思,诗人才可能获得真正的个人立场,并对自我与世界的关系进行调整,从而避免偏执、停滞、僵化,这是保持创造性的重要前提。徐江在《杂事诗》中的自我形象其实也是其一直以来形象的延续:爱憎分明、直言不讳,有时甚至显得不无刻薄。这样的形象难免惹起争议,但其实也是见诗人真性情的,正如在其诗集《杂事诗》封面所写:“我写万物——这是一种狂妄,万物写我——则是一种谦卑”,实际上他的诗中既有“狂妄”又有“谦卑”,两者是交织混合在一起的。狂妄时则指点江山、睥睨众生,有类造物主;谦卑时则瞻前顾后、小心翼翼,“低到尘埃里”,这也和鲁迅之谓“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颇为近似。比如《种族歧视》里的徐江,便显得有些“狂妄”:“我对不知感恩的人/怀有种族歧视//我对全心全意/忧国忧民的人/怀有种族歧视//我对到处讲黄段子的人/怀有种族歧视/我对一点黄段子都不听的人/怀有更大歧视//歧视/不爱国的人/歧视人/随时爱国。”这种“歧视”,当然并非真正的歧视,而是借此表明自己的立场和态度。他在一些诗中甚至自称“寡人”、“朕”、“孤”等,其实这并不能表明徐江目中无人,很多时候是刻意为之,甚至是故意的反讽。实际上在其内心是充满爱、充满关怀的,正如他的《无人设问》中所体现的:
——有一天,你会厌倦吗
——厌倦?当然。现在也会厌倦啊。而且,一切。
——你真的会厌倦吗
——每个人都会。每天,每时,每分
——那么,厌倦这一切
——是呵,一切。或许,除了爱……


四 一个人的世界:“花火集”

“花火”本指礼花、焰火,它在瞬间开放,但璀璨、美丽,能够长久地留存在人们的记忆之中。徐江应该正是基于这个原因,而将他的作品命名为《花火集》的。在这里,他捕捉奔腾跃动、稍纵即逝的思想火花,使它们成为了一些文字的“焰火”。这些焰火多为碎片式的顿悟,个人化特征明显,可以看作一种精神独语,是个人私密空间的深度敞开。比如这首可以看作是夫子自道:“唯一的不同是中年的我/依然反抗着”(527),虽然人到中年许多人已经不再反抗了,但自己并未放弃和动摇,仍在战斗着,这是一种强调和宣示。又如,“在天上俯瞰/房间中烦恼的自己”(696)则化身出不同的“我”,在互相的观照中获得精神的提升和抚慰。《花火集》以“我”为中心,但这并不代表其中就没有“生活”,其中也有不少对世情、对人生百态的呈现,略举几例:
业主们用沥青在小区墙上痛骂开发商
“新世界骗人”
——114
扮演“主席”的演员
常到电视上卖药
——464
导演让鲁迅躺在病床上
对观众讲他健硕的人生
——721
它们都只是生活中的一个场景、片段,但却是具有高度浓缩性和代表性的,能够反映和折射出丰富的社会内容,有着丰富的“潜台词”。如上所引114中的“新世界”既是一个具体的小区的名称,显然也可以视为一个代称而具有广泛的指涉,对于生活中某种美好承诺的审视让人深思。464中所描写也是一种普遍现象,而在“主席”与“卖药”之间,无需多言,许多的世相百态足以自动呈现。721中同样指出了一种普遍现象,在“导演”、“鲁迅”、“观众”之间形成了强烈的张力,“病床”与“健硕的人生”也形成对照,或许有人会认为这种书写不无尖刻,但对于揭穿某些关于鲁迅的神话又的确堪称鞭辟入里。
徐江在《花火集》中充分发掘了现代汉语的诗性,让日常的语言重新熠熠生辉,焕发出诗性的光彩。他如此写“蚊子”:“草里的蚊子见我过来/都偷偷乐了”(540);如此写“雾”:“大雾狂啸着/在高速路上追尾”(563);如此写“雨”:“车的大灯刚一打开/雨就倾盆而下”;如此写“老磁带”:“老磁带里/住着年轻的歌”(661);如此写“花香”:“花香/有声音”(712),如此等等,堪称令人叫绝。他写“生病”颇具古典诗歌的意境:“我自生病/蟋蟀自在窗外锯它的秋天”(541);写“可怜的孩子”则让人忧心、沉重:“可怜的孩子呵/可怜的——长大了的孩子”(785)。他诗中的“火车”日常而荒诞:“那列火车在正午跑着/亮着灯”(524);他所写的“英雄”颠覆了传统的概念:“‘你知道英雄是啥做的?/是水!’”(640)他所写到的“光”则让人忍俊不禁:“上帝说要有光/爱迪生赶忙摸出一只灯泡”(227)。徐江的这种诗歌探索大概与新诗史上的“小诗”、禅诗写作不无相似和共通之处,一方面为现代汉语诗歌的体式作出了有益的探索,另一方面汉语在这里重新恢复了弹性、生动性,变得更为丰富、多姿多彩起来。此中情形正如他自己的诗中所写:
汉语围着我跳舞
你知道
——700
五 “我信有天使在我的屋顶上飞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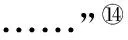
徐江其人其诗所受到的误读都很多:表面上的攻击性掩盖了他的“仁”与“爱”,表面上的冷酷与强硬掩盖了其内在的温暖与平和,表面上的泥沙俱下掩盖了其内在对尽善尽美的追求……一切似乎都可以从相反的角度进行解读。只有当走进他的作品,细细考量,才会发现,噢,原来如此,原来他是这样的,此前的印象是先入为主的、不可靠的!徐江作品的实际水准与其经典化程度之间或许是并不匹配的,这也是到目前人们谈论他的人多于研究他的诗的原因之一。当然,文章千古事,所有的一切都需要经过时间的检验,一时的热闹或者淡漠都不能说明问题,一切都才刚刚开始!徐江的写作当然也有问题,比如在我看来,他诗中有时会出现一些强烈的道德评价的词汇(这应该也是引起人们对他进行道德化评价的一个原因),比如某些诗句过于调侃而有失当之嫌,比如有些作品价值立场显得暧昧、游移、矛盾,有些诗作显得过于随意、散漫,等等。但是,最重要的是,他有着自己对现代汉语诗歌的独特追求,他进行着自己的诗意创造,并写出了具有独特风格的作品。
一意孤行,独自为战,这是诗人徐江一直以来所坚持的立场与姿态,如其诗句所言,他一个人、一支笔,便构成了一个“战区”,他一个人在战斗。应该相信,他会一直“战斗”下去、“反抗”下去,同时,也会将“对汉语的救灾”进行下去,将永不厌倦的“爱”进行下去,如他一直所做的那样。
注释
:①徐江:《叼着烟与经典握手》,《杂事与花火》,(澳大利亚)原乡出版社2004年版,第237页。
②徐江:《答〈葵〉所提出的十七个问题》,《我斜视》,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9页。
③徐江:《俗人的诗歌权利》,《诗探索》1999年第2辑。
④沈奇:《中国诗歌:世纪末论争与反思》,《诗探索》2000年第1~2辑。
⑤罗振亚:《朦胧诗后先锋诗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6页。
⑥徐江:《给诗歌的献词(2003)》,《诗探索》2003年第1~2辑。
⑦于坚:《穿越汉语的诗歌之光》(代序),见杨克主编:《1998中国新诗年鉴》,花城出版社1999年版,第13~14页。
⑧徐江:《论“现代诗”与“口语”》,《诗探索》(理论卷)2011年第4辑。
⑨天津“80后”诗人王彦明语。此处关于长诗的叙述受其启发,特此说明并致谢。
⑩侯马、徐江:《关于〈杂事诗〉:落叶纷飞中的问与答》,见徐江:《杂事诗》,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7页。





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