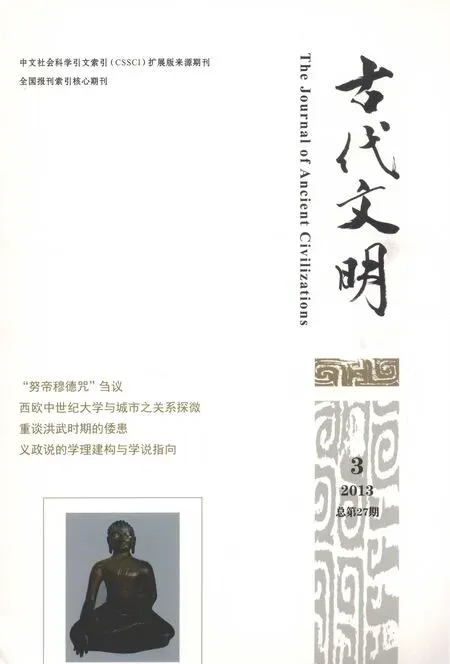义政说的学理建构与学说指向
曹胜高
一、义政说的学理渊源及其指向
《易传》的作者虽然晚出于战国,然其对“义”的理解却符合商周政治理念,在于其把握住了“义”是维护社会秩序的一个原则。《尚书•仲虺之诰》中有句经典的话:“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义制事,以礼制心,垂裕后昆。”以义制事,便是强调“义”在处理军事、政事中的基础性地位,是对行政行为的原则性约束。其与“以礼制心”并举,其中的“事”是指外在事功之事,也就是说,用“道义”的原则,用“合宜”的标准来审视行政措施和行政制度。这里“合宜”,诚然是做到“允执厥中”,照顾到方方面面的利益,选取最为恰当的方式。
我们可以将“义”视为周政的经验总结,在于《尚书》中多次提到“义”在处理社会秩序时的原则性特点。如《尚书·泰誓上》载周武王誓师所言:“同力度德,同德度义。”意谓君臣惟有同心同德,则能谋义。此所言之“义”,乃灭商之大义:“受有臣亿万,惟亿万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商罪贯盈,天命诛之。予弗顺天,厥罪惟钧。”谓万众一心,代天罚罪,残除殷纣。在周人看来,殷纣王及其部属的所作所为,已经背弃了“立人之道”的仁和义。《尚书•毕命》说得很直白:“兹殷庶士,席宠惟旧,怙侈灭义,服美于人,骄淫矜侉,将由恶终。”周人眼中商族成员,骄奢淫逸,恃强自大,不仅不合宜,而且违背道义。这样,武王灭商便是守义。《逸周书•太子晋》讨论文王、武王之别,便以仁、义相分:
如文王者,其大道仁,其小道惠,三分天下而有其二,敬人无方,服事于商,既有其众而返失其身,此之谓仁。如武王者,义杀一人而以利天下,异姓同姓,各得其所,是之谓义。
思想的演进,是无数细微的观念被聚合、被强化而形成一个条理相对清晰、概念相对明确的语义场。条理清晰的路径,便是思想史;而概念明确的抽象,便是哲学。在这过程中,有些相似的概念被吸纳、被融通,而相异的概念则被分离、被区别。仁、义等学说的条理清晰,要经过概念辨析;而概念明确,则必须条理化。思想史是哲学学理得以形成的历时过程,而哲学学理则是思想史得以演进的理论推力。限于《论语》的体裁,孔子仅对“义”的价值做了判断,但并没有进行更为清晰的学理阐释,而孔门弟子在对“义”和“信”等同等重要的概念进行的辨析,进一步强调“义”在公共秩序方面的必要性。
在孟子看来,君主行仁政,是出于性善;而必须行仁政,则出于道义。他如此论述“仁”与“义”的关系:
由此可见,“义”的提出,是以群体的要求为指向,是对公共利益的强化和公共价值观的认同。这种强化,意在形成“人何以能群”的外在规范;这种认同,意在达成“人何以能群”的道德共识。有了外在的规范,处理人际关系、物我关系时才能有可资参照的依据;有了道德共识,用于调整不同群体利益诉求的依据才能得到认同。当公共利益编成共同利益,道德共识变成社会约定,“义”便由早期的学说资源成为学理建构的依据,“义政”也由两周的部分实践,逐渐成为秦汉间日趋强化的行政学说。
二、义政说的理论基点及学说史价值
亲亲秩序既然在兄弟反目、叔侄相攻的历史现实中崩盘,没有制度维系的尊尊,便是以方伯争霸形式进行的武力相功,以胜者控制败者、强者抗衡强者而获得一度平衡。这种混乱中的平衡和武力掩护的秩序,从历史长河来看,只是暂时的稳定,一旦脆弱的支撑要素此消彼长,历史会作为洗牌者,重新调整秩序。
方今之时,复古之民始生,未有正长之时,盖其语曰“天下之人异义”。是以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百人百义,其人数兹众,其所谓义者亦兹众……是故选择天下贤良圣知辩慧之人,立以为天子,使从事乎一同天下之义。
如果“一人一义”之“义”是个人利益要求、个人价值体现,那么作为天子,要有足够的圣知辩慧,来抽取众人之“义”,建立一个普遍适用于天下的利益观和价值观,成为社会认知的最大公约数。《墨子•尚同上》:“乡长唯能壹同乡之义,是以乡治也……国君唯能壹同国之义,是以国治也……天子唯能壹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这个公约数,对个体而言,是人之为人的根本;对社会而言,是人类之所以为人类的共同价值。若君臣上下皆能以天下之利为利,以天下之害为害,以天下之义为义,则自然能够得到天下的拥护。
古者圣王之为政也,言曰:“不义不富,不义不贵,不义不亲,不义不近。”是以国之富贵人闻之,皆退而谋曰:“始我所恃者,富贵也,今上举义不辟贫贱,然则我不可不为义。”亲者闻之,亦退而谋曰:“始我所恃者亲也,今上举义不辟疏,然则我不可不为义。”近者闻之,亦退而谋曰:“始我所恃者近也,今上举义不避远,然则我不可不为义。”远者闻之,亦退而谋曰:“我始以远为无恃,今上举义不辟远,然则我不可不为。”逮至远鄙郊外之臣、门庭庶子、国中之众、四鄙之萌人闻之,皆竞为义。
其中的富贵,指代财富与权力;所谓亲近,指代尊崇和近臣。如果能够按照“义”的要求来处理富贵、亲近问题,则志同道合,上下齐一,君臣放弃一家之私、一族之利,便可建立起一个具有历史担当和社会责任的政府,最大限度地维护公共利益。
墨子“义政”的提出,是对周秦间“力政”的反拨,其理论来源是是天志说,其《天志上》言:
顺天意者,义政也。反天意者,力政也。然义政将奈何哉?子墨子言曰:“处大国不攻小国,处大家不篡小家,强者不劫弱,贵者不傲贱,多诈者不欺愚。此必上利于天,中利于鬼,下利于人,三利无所不利,故举天下美名加之,谓之圣王。力政者则与此异,言非此,行反此,犹幸驰也。处大国攻小国,处大家篡小家,强者劫弱,贵者傲贱,多诈欺愚。此上不利于天,中不利于鬼,下不利于人。三不利无所利,故举天下恶名加之,谓之暴王。”
义政说消解了“亲亲”、“尊尊”的界限,打破以血缘定亲疏,以家族为尊卑的社会关系,使社会成员以同一尺度来审视人际关系,并将等级秩序进一步弱化,使上下均服从于超越性的道义,以之作为行政的理据。从社会运行的角度,墨子清晰地看到了天下不安的原因,在于各依其优势而掠夺他人,小而在人,中而在家,大而在国。从国家管理的角度来说,墨子认为要通过提倡“兼爱”之心、“非攻”之理、“尚同”之法、“尚贤”之制来改变“交相害”的社会现状。
义有七体,七体者何?曰:孝悌慈惠,以养亲戚。恭敬忠信,以事君上。中正比宜,以行礼节。整齐撙诎,以辟刑僇。纤啬省用,以备饥馑。敦懞纯固,以备祸乱。和协辑睦,以备寇戎。凡此七者,义之体也。
这简直可视为“义政”的具体蓝图,可以与《礼记·礼运》中的小康、大同之论相提并论。由于坚守了“义”的准则,在处理亲戚、君臣、礼仪、刑罚、器用、祸乱、军争关系上,皆能做到以道义为守,以尚同为用。
这种上下尚同的要求,是对君主、臣下的双向约束,即二者必须同时担负着公共义务和历史责任。君臣之间,就不再是依附和被依附的关系,而是共同肩负天下大义,彼此成为合作和制约关系。所谓合作者,便是君臣各有职责,相辅相成;所谓制约者,便是君臣各有分工,相辅相成。由此来审视孟子的仁政论,就发现其理论上的窘境,正是在于缺少义政说所强调“上下尚同”,而学说上的突围,也是以此为方向。
问题是,孟子几乎没有见到理想中的仁君,即便是梁惠王那样有恻隐之心的国君,亦未能如孟子所愿而行“仁政”,其根源孟子隐约意识到了,但却没有彻底想清楚。之所以说他隐约意识到,是他开始“仁义”并称,即一个国家能否推行仁政,与其说取决于国君的性善,毋宁说取决于国君的责任担当。由于孟子学说是基于由内到外的性善论,带有自我完善的心性修养,而基于交往、交易、交际而产生的社会关系,不可能如亲亲关系那样具有先天的保护、亲切和照顾的本能,因而以单纯的性善、仁爱等理念熏陶出来的思路去面对复杂的社会关系时,便显得局促不足。
理论的出发点常常决定了学说的走向。孔孟基于仁爱、性善的自我修养论,延展到政治学说时,只能寄希望于仁君的出现,其对国家秩序的改造,也是通过培养仁人志士来充实官僚体系,通过由上至下的道德示范、礼乐教化,推行王道。这注定只能用于治世,且需数百年持之以恒的努力。面对诸侯有恻隐之心而不愿行仁政时,孟子意识到要以“义”来劝诫,其《告子下》言:
为人臣者怀仁义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仁义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仁义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怀仁义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君臣要以仁义相召,这其中的“仁”是基于爱人、爱家、爱国的情志;这其中的“义”,便是彼此的责任。但附在“仁”之后的“义”,显然没有墨子“义政”论那样的理直气壮。由于他认为“义”亦起于心,故而对于“义”的论述,更多强化为君臣相互的责任,而非天下之责任。《离娄上》:“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在他看来,仁之心性,使其彼此尊重;义之责任,使其相互制约。君臣恪守本分,不超越自身的职责,就能保证行政秩序的畅达。
孟子对“义”的强调,是由基于亲亲关系的“仁”推导出来的,其“义”更多是心性修养的产物,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君臣之义”,不是基于共同责任的强调,是基于等级秩序的认同。相对于墨家以天下为义、以上下尚同为用的“君臣之义”,存在一个天然的区隔。那就是墨子所谓的“天下之义”,是超越君臣关系的天下大义,带有先天法理依据的意味,是无限责任,墨子之后的学者强化“义”在社会关系中的相互负责、彼此信任的理念,使之成为社会责任观、政治担当感的理论框架。而孟子所谓的“君臣之义”,是君对臣的责任和臣对君的责任,虽有道德约束,但更多是二者之间的有限责任。此后思孟学派着力强化“仁”的基础性作用,而将“义”蜷缩在君臣关系的狭小境地之中,寄希望于明君贤相合作的模式,成为后世儒生不能解脱的一个心结。从这个意义上说,墨子“义政”学说,弥补了孟子以仁政论天下秩序中的理论困顿,即寄希望于君主德行来推行仁政,方向上是与虎谋皮,方法上是缘木求鱼。秦汉学者对国家建构的想象中,便汲取了义政理念,对天下秩序做了全新的解读。
三、周秦间义政论的学理走向
义政的提出,从较为宽阔的角度发展了王道学说,使得自上而下的明德论,有了一个自下而上的约束,得以成为周秦思想发展史不可或缺的一环。但孔子、孟子对君臣关系、社会关系的设想,更多是基于学理探讨;而墨家学派的义政实践,因立足于下层民众,没有能够在国家层面推行。因而孔、孟、墨对王道学说,更多是理论上的滋养,而不是制度上的设计,其不能用于诸侯,非诸侯不为,乃其学说与时势不合拍。秦汉学者对社会秩序的思考,便以义政作为基本的行政理念。
荀子将“义”视为人得以为群的基本要素之一。《荀子·王制》言:“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以义。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故宫室可得而居也。故序四时,裁万物,兼利天下,无它故焉,得之分义也。”分之以礼,和之以义,如此人类社会方可形成既有差异又有共识的合理结构。由于荀子将“天”视为自然之天,直接放弃了孔孟的先天道德感、墨子的天志论,而直面社会问题,这样,其所谓的“义”,不再如《易传》、《墨子》那样被赋予超验的色彩,而被视为社会的公平正义,是人类基础的道德共识、基本的社会责任。
荀子由此审视王道,便削弱了孔孟德政、仁政的想象,转而务实地提出了“义立而王”的主张。《荀子·王霸》说:
故用国者,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三者明主之所谨择也,仁人之所务白也。絜国以呼礼义,而无以害之,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仁者不为也。擽然扶持心国,且若是其固也。之所与为之者,之人则举义士也;之所以为布陈于国家刑法者,则举义法也;主之所极然帅群臣而首乡之者,则举义志也。如是,则下仰上以义矣,是綦定也;綦定而国定,国定而天下定……故曰:以国齐义,一日而白,汤武是也。汤以亳,武王以鄗,皆百里之地也,天下为一,诸侯为臣,通达之属,莫不从服,无它故焉,以义济矣。是所谓义立而王也。
义既然是社会责任、道德共识,那么要想称王,必须以天下大义为衡量选才、用人、立法、行政的依据,完全超越了思孟学派强调的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五种基本关系。《荀子·子道》明确提出:“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又说:“父有争子,不行无礼;士有争友,不为不义。”在这样的视域中,“义”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最高原则,明显跳出了孟子所谓的“君臣之义”,使之成为更为博大高远的、具有普遍价值的大义,是全体社会成员必须服从的社会原则。
至少在荀子时期,“义”已经被提升到了理念的高度,成为社会义务、历史责任、文化担当的代名词。从儒家学说生成史来看,这是对孟子学说的否定之否定,完成了对西周以来对“义”的学理辨析,即确定其来源不再被视为人心生发,而是为社会约定的内化。这样“仁”与“义”的关系便被明确下来,“仁”是源自人心,是我者的情感体验及其走向;而“义”则来自公论,是他者的理念共识,其对我的作用方式,是由外铄而内化为我者的羞恶认知。
这类讨论有两个明确的指向,成为秦汉之际学者的共识。一是“义”的强制意味越来越被强调,其中所蕴涵的“正义”的意谓,带有立足于社会共识而与之俱来的法理色彩。《礼记·乐记》提出了德刑源自仁义:“刑禁暴,爵举贤,则政均矣。仁以爱之,义以正之。如此则民治行矣。”如果说“爵举贤”出自仁爱,那么“刑禁暴”便属于义正。《大戴礼记·主言》也说:“圣人等之以礼,立之以义,行之以顺,而民弃恶也如灌。”约束日益严重的道德滑坡和人性沦丧,单靠德政的庆赏和教化已经无法约束,以礼规范之、以义约束之、以顺引导之,成为乱世治民的必要策略。而所谓的“立之以义”,便是明显的惩戒。《礼记·郊特牲》便明确说:“大夫而飨君,非礼也。大夫强而君杀之,义也。由三桓始也。”大夫非礼之举,国君严惩不贷,这是基于天下秩序的考量,与性善性恶无关,是维护天下大义,而与《逸周书·太子晋》中所谓的“义杀一人而以利天下”同理。
儒家出于司徒之官,更多秉承司徒德政之论;而法家出于理官,则秉承了周政中刑政之说。故法家所谓的“义”,便是维护社会秩序中惩戒奸宄的依据。《申子·君臣》言:“君必有明法正义,若悬权衡以称轻重,所以一群臣也。”明法是法制,而正义则是法理。法理是基于社会共识而形成,其一旦形成,便具有严正的威力。《慎子·威德》便说:“蓍龟,所以立公识也。权衡,所以立公正也。书契,所以立公信也。度量,所以立公审也。法制礼籍,所以立公义也。凡立公,所以弃私也。”法律、礼仪维持的社会最为基本的秩序,代表着社会最大的共识、最基本的原则。
法家强调严刑峻法的学理依据,便是法乃公义的体现。正因为法家认为法制是社会公义的象征,是对私义的约束,所以其不仅至高无上,而且要令行禁止。《韩非子·饰邪》言:
夫令必行,禁必止,人主之公义也;必行其私,信于朋友,不可为赏劝,不可为罚沮,人臣之私义也。私义行则乱,公义行则治,故公私有分。人臣有私心,有公义。修身洁白而行公行正,居官无私,人臣之公义也。污行从欲,安身利家,人臣之私心也。明主在上则人臣去私心行公义,乱主在上则人臣去公义行私心,故君臣异心。
秦汉之间学者的理想人格,便是推崇对天下责任的担当。《大戴礼记·曾子立事》言:“君子爱日以学,及时以行,难者弗辟,易者弗从,唯义所在。”认为君子学习修养,不畏艰辛,不仅是自己的社会义务,更是社会责任。《大戴礼记·曾子制言下》说得更为具体:“凡行不义,则吾不事;不仁,则吾不长。奉相仁义,则吾与之聚群向尔;寇盗,则吾与虑。国有道,则突若入焉;国无道,则突若出焉,如此之谓义。”衡量君子的标准,不在于其穷通,而在于能够坚守正义。这种正义性是基于天下的考量,而不是一国一君的标榜,入有道之国,出无道之国,事仁义之人,远不仁不义之长,显然赋予了君子独立的人格。这种独立的人格,是以道义、正义、公义作为判断的依据,而不是世俗的标准。
这样,在秦汉时期便形成了基于两种不同学说的独立人格,一是以道家所强调“遗世独立”以全天性,其侧重鼓舞士人鄙弃现实政治的猥琐,通过远遁来保持在精神上和行为上的自由自在。二是以儒家、法家等为代表的“入世独立”以坚守道义,其侧重鼓励士人在现实中坚持个人操守,百折不挠去维护正义、公理,从而保证政治行为不背弃公共利益、社会秩序不原理公共价值。秦汉士大夫对道义的维持和对秩序的建构,是对独立人格的学理认同,其从政过程中入世、出世际遇,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独立人格的保持。从这个意义上说,义政不仅成为秦汉国家建构的理据,成为政策考量的参照;而且义之理念,浸润成为个体修为,也成为秦汉士人衡量个人品格的依据。